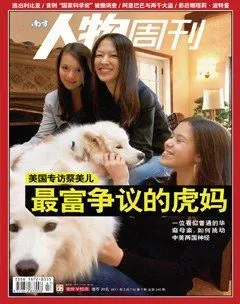《大地惊雷》不是自我颠
2011-12-29 00:00:00穆冉
南方人物周刊 2011年7期

一老一少,结伴而行,一起上路——如果这部电影来自巴西,那么它是《中央车站》;如果它来自法国,那么它是《蝴蝶》;如果主人公是一位大叔和一个萝莉,踏上的又是一条复仇之路,那它应该是《这个杀手不太冷》或者《大叔》——好了,不用再猜了,这次的答案,应该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它是科恩兄弟的新片《大地惊雷》。
对于一些资历更老的影迷,《大地惊雷》(True Grit )这个名字实在不新鲜。早在1969年,好莱坞传奇影星约翰·韦恩就曾拍摄过一部同名西部片。难怪2月初在柏林电影节开幕之日,《大地惊雷》作为开幕影片率先登场时,哥哥乔尔·科恩会一再重申:“我们只是改编了查尔斯·波蒂斯的小说,而不是翻拍。”
尽管科恩兄弟反复提醒,但是影迷依然会乐此不疲地比较新旧两版的异同。那些期待在科恩兄弟的开放叙事中展开一番脑力较量的影迷彻底失望了,他们不明白好莱坞这样的两个好脑子为什么如此照本宣科;喜欢新版的人,则一如既往地扮演铁杆粉丝,他们依然能从新版不同于旧版的十几处改编里,饶有兴趣地品味出科恩兄弟的深意。
怨不得部分影迷对《大地惊雷》失望,在科恩兄弟的作品系列里,这部新片的确一反常态,一以贯之的黑色悲情标签退居后景位置,他们从前最痴迷和擅长的对黑暗人性的鞭挞不复存在,高端影迷一直追求的影像哲思杳无踪迹。取而代之的是以钢琴作为主奏乐器的深情配乐、极其封闭的经典叙事结构,以及从头至尾传递出来的希望之光。说《大地惊雷》是科恩兄弟迄今最温暖的电影,毫不为过。
“如果非要把身段放到这个位置,那就别做科恩兄弟了。”好莱坞影评人的愤怒,可能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这两位独立电影旗手的这次主流转身心存不满。从前的科恩真的不在了吗?当然不是!在主人公马蒂与马场商人的谈判中,在面包射击的枪法比赛里,那对让你忍俊不禁的兄弟分明还在;在悬挂着尸体的枯树林里,在剁下两指的小屋中,在驮着熊头袄的马背上,那对刺激你肾上腺的兄弟分明还在;在黑夜与凶犯四人的狭路相逢里,在林边旷野的生死对决里,那对让你提心吊胆的兄弟,一直都在。
接受《娱乐周刊》专访时,科恩兄弟提到了5部拍摄于上世纪70年代的西部片:赛尔乔·莱昂内导演的《西部往事》、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不法之徒》、罗伯特·唐尼导演的《墨西哥人的宫殿》、费·唐纳薇主演的《道克》和约翰·休斯顿的《罗伊·比恩法官的生平》。《大地惊雷》的拍摄就是受到它们的启发。”
在不断撇清跟老版的关系后,科恩兄弟一再否认新片是针对美国当下萧条的国内现实有感而发。不过,没人规定导演在宣传期必须说实话。不管一个艺术家怎样否认他的创作与现实无关,你都必须相信一点:时代的阵痛,在每一个创作者的血液里。
在好莱坞,一个成人和一个孩子的故事,通常会属于两个导演:一个是蒂姆·波顿,一个是斯皮尔伯格。但无论谁来拍,都是对成人世界的批判。如果派拉蒙公司把它交给科恩兄弟,拿掉他俩心仪的西部背景,他们也绝不会放弃职业导演孜孜以求的话语权。
少有一部西部片以一个14岁的女孩为视点展开故事。这位不爱红妆爱武装的主人公,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机智和勇敢。从头到尾,马蒂面对“敌人”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只有最后被苏醒的毒蛇攻击喊救命的那一刻,你才意识到她的确只是个孩子。在大小警官先后放弃的时候,只有她进退维谷却目标如一,百折不回一路向前,兑现了亲自扣动扳机的诺言。影片对年轻一代的强烈认同和厚望让人想到《刺杀肯尼迪》,在那部影片结尾,导演奥利弗·斯通写道:献给那些为追求真理不断向前的美国新一代年轻人。
尽管有人不买账,但还是有一拨又一拨的观众走进影院力挺科恩。投资3800万美元的《大地惊雷》上映3周北美票房便达1.1亿,史上最高票房的科恩作品应运而生。
如果还有人认为科恩兄弟在刚刚落幕的奥斯卡 “失意而归”,那么他们一定懒得回应——在《巴顿·芬克》斩获戛纳金棕榈、《老无所依》力夺奥斯卡小金人之后,票房,这最后一块失地也被他们一举收获。下一部电影还会是个惊喜吗?问他们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