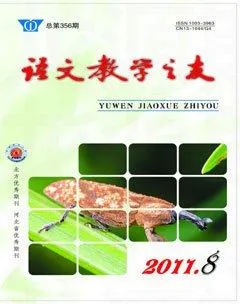贬谪心境的诗意化手法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都把入仕实现政治抱负作为最高理想。然而宦海沉浮,稍不留神即有贬谪之危,于是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这些文人本想建功立业、彪炳史册,却在参与朝政中遭遇挫折而受到贬谪。遭贬之后,既无法改变自身处境,又无力改变社会现实,他们难免陷入痛苦泥淖,只能吟诗作赋以述心志。人穷诗工,阴差阳错,这些诗作在文坛永垂风流。通过解读贬谪诗中的艺术手法,现代人就能近距离地窥见被贬谪诗人的心灵光辉。
寓情于景,哀婉言伤痛。贬谪的经历,使诗人们的生活处江湖之远,仕途的失意加重了他们的感伤。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句中“疏桐”的孤单,恰符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暂居定慧院的凄凉心境;“缺月”的不完满,恰符合苏轼对于人生的认知。他因贬谪产生的孤寂的身世之感就这样被寄予到客观景物之中。韩愈的仕途也是不顺的,他一心为国为君“除弊事”,犯了人主之怒,被贬为潮州刺史。《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即写他贬谪途中之景。云横“秦岭”不见家,也不见长安,云遮雾绕的重重山岭阻隔了故里、君王。韩愈罪贬潮州,乘驿赴任,家亦遣逐,小女道死,殡之山下,大雪阻路,马难前行,诗人留恋不忍离去,尽生英雄失路之悲。同样,柳宗元在《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中写道:“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诗人登上城楼,是为了遥望远方的同样因参与新政遭贬的战友。他站在城楼远眺,山上树木蓊郁,遮断视线,使他望不到远隔千里的战友,他不禁黯然神伤;他把视线收回,俯视着城外的江流,江流逶迤东去,使他不禁又产生了“江流曲似九回肠”的悲哀。江流这一眼前实景,正应了司马迁《报任安书》“肠一日而九回”句意。苏轼用“缺月”、“疏桐”言寂寞,韩愈借“云横秦岭”、“雪拥蓝关”诉彷徨,柳宗元以“岭树”、“江流”传愁思。可见,景中寓情,的确是贬谪诗人抒发内心情感的常用手法。
对比衬托,反差显伤感。文人被贬谪,身份、境遇、心态,不免由昔日的云端坠落地面。身份的反差、处境的优劣、思想的变化,表现在诗中就是对比反差。孟浩然40岁游京师,应进士不第后漫游吴越,穷极山水,以排遣仕途的失意。在《与诸子登岘山》中,他这样写道:“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想当年羊祜镇守襄阳,立下功劳,为百姓做了一些好事,是以名垂千古、与山俱传;想到自己如今被排挤出京,仍为“布衣”,无所作为,死后难免湮灭无闻,这和“尚在”的羊公碑两相对比,就不免生发悲意,徒增伤感了。韩愈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则用“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直写获罪被贬的原因。一封奏书,招致被贬千里之祸。“朝”、“夕”之间命运发生急剧变化和巨大反差。“九重天”言宫禁之深、皇权之威。“路八千”言贬谪之远、受挫之惨。作者巧妙使用“一封”与“八千”、“朝”与“夕”,让数量与时间之间形成强烈的对比,把变故具体化、形象化,增强了感染力。就因那“一封书”之罪,所得的命运是“朝奏”与“夕贬”,而且一贬就是“八千里”,诗人虽遭罪获遣亦无怨悔。可见,对比手法能恰当地表现出诗人前后处境的反差或者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也为历来的贬谪诗人所钟爱。
比附兴起,曲折现情志。绝大多数的贬谪诗,都以“怨愤”为基调,凄怨的倾诉和激愤的抗争通过一系列的艺术技巧呈现,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刘勰《文心雕龙》言:“比者,附也;兴者,起也。”朱熹亦言:“比则取物为比,兴则托物兴词。”总结二者共同处,大抵说在文章中不能直言。如屈原《离骚》中“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就运用了“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称物芳”表现自己“死而不容”的高洁情志;辛弃疾的《摸鱼儿》中“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用陈皇后的遭嫉妒,暗写自己被排斥及政治上的失意;柳宗元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中“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也运用比兴的手法写了登楼所见的风急雨骤的景象,“芙蓉”与“薜荔”,正如诗人美好与高洁的人格,而“惊风”与“密雨”足见诗人所处的客观环境的恶劣。诗人之所以不明说,和他们自身的贬谪处境是分不开的。屈原放逐异地,辛弃疾弃置不用,柳宗元遭遇迫害,他们在政治上处境孤危,在作品中就只能或以花草自喻,或以外物作比,或托儿女之情写君臣之事,来间接隐晦地表达自己内心的忧虑。所以,贬谪诗人出于自身特殊的处境考虑,作品中多采取比兴手法,曲折地表现自己的情志。
贬谪之于诗人,无异灭顶之灾,但他们在巨大的生活落差中经受住生命的磨难,思想也如凤凰涅槃般蜕变,贬谪心境便诗意化为真正的不朽艺术。
(作者单位:南通市通州区姜灶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