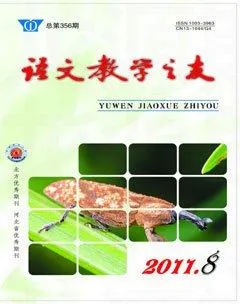“略读”课文不可“忽略”
贵刊2011年第2期刊登了李军亮老师的一篇文章《“略读”课文教学的思考》。展读之余,引发了我的思考,很想借此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一些做法。
首先,对“略读”课文的定位,容易诱发不少误解,最典型的是当下在“略读”课文处理上少数教师的态度不积极,引发学生不重视。文中有些提法不足以引导人们走出这些误区。
误区之一,“略读”课文应该“读的简略”。精读和略读不是一对相对的概念,精读的另一面应该是“泛读”,传统精读课文的任务在于“示范”之读,为此它需要借助师生的互动,最大程度地向学生展示学习其他课文的思路、方法,而泛读则是更广层次的阅读,它不需要字字计较,而求读的广泛,取其精髓而如五柳先生的“不求甚解”,强调每有会意时的阅读的愉悦。至于课文之略读,我看视为“扶读”或“助读”更为妥当,略读课文不是“不花气力的大略的读”,更不是教师不加指导学生浅浅的读,而是在相对较少的时间内(一般一课时),通过教师的扶助,对课文在某一方面力求有所突破的阅读。据此,“略读”课文便可定义为“有限精读”。
误区之二,精读课文是重要的考点,而略读课文相对次要。于是略读课文成了功利性阅读的重灾区。按照考什么就教什么的逻辑,不少教师语文课往往止步于几篇“重点课文”反复讲,反复练,诚如文中所说的“敲骨吸髓”式的精读,务必使学生烂熟于心。而对于略读课文则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勾画几个生词,提出一两个问题,甚至还向学生坦言“不是考点”,只作了解即可……略读课文完全成了可有可无的小玩意,在功利性阅读面前,它成了精读课文的陪衬,成了语文课文中的“鸡肋”,种种情况,在毕业班则更是愈演愈烈。
笔者认为在提升学生阅读能力的重要性上,课文无论“精读”还是“略读”同等重要。在多年的教学中,我常常把它们作为提高学生阅读水平的两块重要阵地,略读课文决不能讲得肤浅,读得简略,更不能忽略不计。对略读课文的教学,我注重以下方面:
一、“略读”课文,是学生自主学习的主阵地。略读课文教师讲得少,但学生却必须全神贯注,使出浑身解数,更加自由地贴近文本从而解读文本。前些时候我教学略读课文《石榴》(苏教版八年级《语文》下册第一单元),郭沫若这篇散文文质兼美,是散文中的精品——你能读得简略吗?教学这篇课文,我从前面的精读课文《白杨礼赞》复习入手,归纳抒情散文的赏析技巧,然后放手让学生根据本单元的已有积累,自选角度从一方面突破课文,这个放手的比照教学,学生有的赏析美句,有的从《白杨礼赞》结构和象征意义上类推揣摩本文寓意,学生自主学习热烈,课堂讨论的氛围不亚于精读课文。略读课文有时可以上成汇报课、展示课、讨论课,从而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热情。综观这节课,教的并不简略,在散文的立意方面不少学生还有自己全新的见解。我常常赋予略读课文一个使命,让它“牵一发而动全身”,作为本单元的复习或是拓展的抓手,在复习中,本单元的重点被全方位地烛照出来,而阅读拓展课则借助于略读课文作本单元有效地拓展和延伸,因为这样的课堂教学综合性强,很好地培养了学生梳理和整合知识的能力。在这样的课堂里,教师又怎会处理的简略呢?
二、追求略读课文的定向突破。处理略读课文不必像精读课文那样“瞻前顾后”,这个重点,那个难点,略读课文不追求“招招致命”,而追求“一招破敌”,即要求一堂课有限的教学目标被“强势”突破。如教学略读课文川端康成的《父母的心》(苏教版八年级《语文》上册第三单元)。因为前面已经精讲了朱自清的《背影》,教学这篇文章,我重点讲授“一波三折”式的文章结构——至于小说其他艺术成就则“留白”于课后——课堂全力主打“结构牌”并当堂训练拟写作提纲,让一波三折式的结构在学生内心烙上深深的印记。
三、架设课外阅读的桥梁。前面说过精读课文在于“范读”,而成功的略读课文在于“引读”。课内略读课要善于“留白”。阅读教学有时是有缺憾的,课堂呈现的空间和时间总是有限,略读课文则不必追求面面俱到。一篇《父母的心》,川端康成的“紫色的哀怨”哪是一节课几分钟能说的了的呢。说不能面面俱到,那就要使出千般手段,调动学生课后阅读的热情,如果学生能在课后找寻这种哀怨,这节课就是最大的成功了。教学《呼兰河传》节选(苏教版九年级《语文》下册第五单元),我就上成了汇报课。要求学生假期自读原著,课堂展示:作者的童年美吗?作者的童年快乐吗?让学生结合课文去想、去写,并将他们的答案装订成册下发,而我的略读课只是给他们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这样的略读课教师所费的心思并不少,在呵护学生阅读热情上因为无所“羁绊”,略读课文反而更加大有作为。
总之,略读课文之于精读课文,更不能读得肤浅,从而放弃了一块有效提升学生阅读能力和阅读兴趣的的重要阵地。略读课文,教师和学生都不可忽略。
(作者单位:高邮赞化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