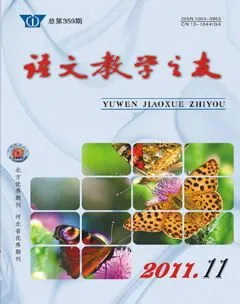如何引领学生体味古典词作中的“无言之伤”
古典诗词的“含蓄美”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表现——“有言”与“无言”。“有言”侧重于“言外之意”的发掘。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言不尽意”;钟嵘《诗品序》中的“文已尽而意有余”;皎然《诗式•重意之事例》中的“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无言”在哲学美学范畴里表现为“大音稀声”、“无言之美”,也可通过“此时无声胜有声”之类文学创作来彰显古典诗词的“含蓄美”。但笔者在唐宋词作中发现诸多“无言之伤”,也就是说作品中的种种“不语”带给抒情主人公和鉴赏者的往往不是愉悦和优美,而是伤痛和唏嘘。笔者试搜集这些个案,总结创作规律,探索引导学生体会这种“无言之伤”的方法,从而进一步加深学生对“含蓄美”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认知。
一、个案赏析
1.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
词作中“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一句的“无言之伤”很具代表性,颇值得品味。要达到抒情主人公面对“不语”的落英内心最全面而深刻的情感层面,就必须结合意象层层設问,引导学生充分挖掘“无言之伤”。
(1)女子因何而流泪?
(2)为何而问花?
(3)花儿什么反应?
(4)如果你是该女子,对花儿的反应会作何感想?
剥笋式的提问引起了学生极大的兴趣,一步步地挖掘也就渐渐走入了抒情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女子因花而有泪,见花残而感伤,其实是以花自比,残损的不仅是花,还有被岁月凋蚀了的容颜、被在章台路上乐不思蜀的丈夫伤了心的她。进一步,她将花儿对象化,问出心中的纠结。花儿的缄默无语再次伤害了她。无言之伤,情何以堪。一个有情的她,怎敌得过一个无情的他,再一个无情的它?问花的结果就是自伤。
2.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八声甘州》上阕写景,用了不少典型的意象,诸如:暮雨、江天、关河、残照。聪明的柳永为使上阕的景自然过渡到下阕的情,而将上阕的最后一个意象“江水”人格化——“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问题設置如下:
(1)江水这一意象的普遍象征意义是什么?词句中象征什么? (2)“东流”这一动词有何深意?
(3)江水的“无语”反应有何意义与效果? 学生对“江水”意象较熟悉,无论是“大江东去浪淘尽”的时光流逝,还是“毕竟东流去”的一去不复返,亦或是“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浓浓愁绪,都提示学生来理解本句。“东流”即东流入海不回头,那江水的特质就是消逝。再结合上句“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中对年华逝去的慨叹,可知此处的江水象征时光等美好事物的流逝。进一步,江水本不能语,抒情主人公却执拗地认为“无语”即“无情”。无论谁,若对羁旅多年、境况窘迫、有家难归、思乡心切,于茫茫天地间无所适从的人儿不理不睬,都是一种残忍,犹如伤口上的一把盐。
3。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当“尘满面,鬓如霜”的词人好不容易在梦中穿越到妻子fI9ZjfYJuBEF3h/AL7njAA==活着的时候,却“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一种揪心的痛就在这无言中漾开。
(1)让他俩说话好不好?
(2)“无言”表象背后的心理是怎样的?
(3)“无言”对表达词人的思念有何高妙的效果?
設想的千万次见面却只能默默无语,初想真遗憾。可让他们说,在有限的时间内,虚幻的境界中能说什么?想说的太多无从说起,只恨言辞太苍白无力;一切尽在不言中吧,无言胜有声。設计的心理台词是:“说些什么呢?”“不用说,你懂的。”就让止不住的泪代表内心的激动,洗“轻”内心的痛,留下“执手相看泪眼”的画面念想。
二、创作规律
1.客体“无言”,伤主体
当“无言”的角色是客体或者意象时,其实是抒情主人公主观情感的投注,大都是内心孤寂的外放表象。客体本不会说话,它们的任何举动都是自然规律、正常现象。要求它们开口说话本身就是“无理”。而这种“蛮不讲理”折射出的是深情与剧痛。这是一种拐了几弯的含蓄。
2.主体“无言”,伤在心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一个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会说不出话来?大致是极度愤怒时、十分激动时和无比痛苦时。而最符合我国传统审美情趣的是第三种。人们常说:说出来吧,说出来就舒服些。可作者往往会自虐式地让话烂在肚子里,让苦发酵在心中,成就“无言之伤”。
三、鉴赏方法
在一个崇尚直白、直观、直接的当代社会中,如何引导学生去体会词作中无法言说的伤痛,这是个难题。方法就显得十分重要。笔者根据教学实践,总结出一些操作性较强的方法,以供参考。
1.结合意象,广泛了解造成主体伤痛的原因。
古典诗词中的意象是了解抒情主人公情感的重要媒介,在诗歌理论中我们还单列了一种意象语言。一般每个意象都会有相对的一重或多重象征意义,学生如在这方面有所积累,就可以结合意象,了解抒隋主人公伤痛的原因。如上面第二例中的“江水”。
2.剥笋式提问,深入挖掘主体伤痛的根源。
这种方法的使用涉及到伤痛的深度问题。教师在备课时可倒推式設计问题。如姜夔在《扬州慢》中写道“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我们心中自然明了月亮这一意象的出现具有今昔对比的意蕴。昔盛今衰是结论,往前推论曾经的二十四桥边是什么境况?现在是什么境况?为什么特写月亮?写月亮“无声”合理吗?而课堂上就可以由浅渐深地引导,从月亮本无声开始达到“昔盛今衰”的结论,从而体会词人在这巨大落差中的伤痛。
3.种用同情心理,“超视”地体会主体的伤痛。
这里的同情心是指同样的感情,是要求学生設身处地地为抒情主人公着想。跳出小我,超越自己狭隘的视角(超视)来关照抒情主人公的内心感受。如当李煜“无言独上西楼”时,可要求学生設想自己就是一位面对风雨飘摇的帝国的君王,并只能拥有李煜的个性特点,会怎么想、怎么做?“无言”中包含的丰富内容也就在这“超视”的审美中挖掘出来了。
4.設计情境,让学生在“当境”中感同身受。
有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伤痛是学生生活中有过的体验。教师可以通过语言、投影或音乐等手段的渲染,让学生穿越到彼时彼刻。如第三例苏轼悼念亡妻。只要学生曾有至亲去世,定会深刻理解“无语”的内涵。再如柳永写道“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只要学生曾与亲人、朋友分别过,就能体会只流泪不言语的痛楚。这样,我们就能让彼时彼刻地痛成为此时此刻的伤。
需要声明的是语文课并不是要把学生上哭。体会古典词作中的“无言之伤”的度要把握好。能认识到“伤”的原因和“伤”的深度,达到对“含蓄美”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认知即可,不宜过度煽情,上成一堂矫情的课。
(作者单位:南通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