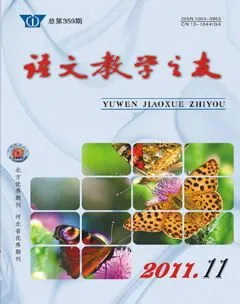构建语文课堂知识生成观
近几年来,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语文基础知识大讨论的历史制高点后,语文学界又一次掀起了争论热潮,引起本次争论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于人们对新课标中“不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的不同理解;二是现实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着忽视和排斥教授语文知识的现象。众所周知,语文知识是语文课程中最基础的内容,也是提高学生语文素养和语文能力的源头活水。更为核心的是,其他学科在教材中已经将教师要教授的知识点确定好,而语文教材仅提供教学的文本,学科知识内容大部分是由执教者自身生成和把握,因此衍生了教材、教学的多元解读理念,不同的教育者因观念、学识、经验等不同而造成了差异,这种语文课程的不确定性也给语文教学带来了很多争论。
目前。不少语文学界的工作者一再呼吁应重视语文基础知识的教学。虽然如此,上世纪学术研究中遗留的两大问题——“语文知识的内涵和外延”、“语文知识的有效性”依旧是争论的焦点,这两个问题正是导致了语文知识命似浮萍、长久未定论的根源。
我以为,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语文知识的明确分类。在以前的研究讨论中,语文知识类型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一刀切地谈如何落实语文知识,忽略了不同类型的语文知识所承担的课程功能和课程目标的差异、不同性质的语文知识所需要的教学设计不同的客观事实。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做法致使课堂陷入了讲与不讲、讲多与讲少近乎一样的泥淖中。
过去。关于语文知识有个约定俗成的“八字宪法”表述,即“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由于这种说法并没有具体论述分类的原因。也没揭示相互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语文知识的类型不如说对语文系统的简单概述,因而显得势单力薄,不成一家之说。
目前,关于“知识类型”较被认可和接受的研究成果是从现代认知心理学角度将其分为: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此种语文知识类型的根本视域和立场是学生,符合了以生为本的教学活动宗旨,能有效结合课程与教材目标并践行。“陈述性知识是关于事物‘是什么’的知识,它是人们对事情的状态、内容、性质等的反映。”“程序性知识是关于‘做什么’、‘怎么做’的知识,它是人们关于活动的过程和步骤的认识。”“策略性知识是关于学习的策略的知识,即如何确定‘做什么’、‘怎么做’的知识。他的标志是明确认识自己面临的学习任务,知道自已目前学习所达到的程度,能调用恰当的学习方法,能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反省和调节。”③这是知识教学最理想的境界,更多的是依靠学生自我的领悟和监控。
从三个课例来看,夏志明老师的《陈太丘与友期》是以陈述性知识为主,黄德初老师的《我愿意是急流》侧重的是程序性知识,张璇老师的《说数》是以分析为主要教学方法贯穿策略性知识的教导。三位老师在知识的选择上都进行了组织和建构,并没有出现无效知识的现象,这是其知识、经验和能力的体现。但是,纵观三个课例,在关于语文知识教授上有两方面需要商议:
一、陈述性知识的有效教学方式。如《陈太丘与友期》中成语积累这一教学环节上,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工具书积累成语,却只是流于单纯地积累成语,对成语的意思没作点拔和解释,这对初一的学生来说是很难掌握的,所以这一环节由于教学方法不妥当使得知识形成性低。而黄德初老师在《我愿意是急流》中的比喻手法、倒装的条件句这样的陈述性知识教授中就处理得很好。对华师附中的学生来说,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不会存在问题,但是要让学生确切地体会这两种手法在此诗歌的妙处就要另花一番心思。黄老师是通过反复地比较让学生深刻地体会其中高妙,这两点知识就不仅在学生知识建构中得到确认而且使之建立有效的知识图式。
从这两个课例的比较中得出启示:(一)陈述性知识是语文知识的基础,也是较为简单易懂的知识,要求的心理过程主要是记忆。这往往使教育者产生不正确观念一易懂就易教,这是有待纠正的,因为这种观念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陈述性知识是要求掌握的,看似懂的不一定透彻掌握,最终目的是可以灵活运用。新课标要求:学生能运用语言是对语文课程的所有类型知识的目标和指示。
(二)一种知识得以掌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学方式的使用。以体验为主要途径的教学方法是提高陈述性知识效度的重要策略。体验,以学生为主体视域,旨在调动学生生理器官、思维感知以达到如身临其境之感,拉近学生、作者、文本等之间的距离,通过直觉的方式把这些知识事实积淀在主题内部。如“引吭高歌”如果夏老师植入让学生拉长脖子、大声愉快地唱,学生不仅明晓“引”的意思,而且懂得在各种情况下灵活运用该成语。总之。在语文知识的教授上,执教者必须对所要教授的语文知识的目标、内涵性质有准确的认知,并结合所教的学情具体解决。
二、陈述性知识要转化为程序性知识。中学语文教学不应以陈述性知识而是以程序性知识为主体,陈述性知识对语文教学的意义是有限的,语文课程目标在于“学生能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陈述性知识是不能满足学生对语言运用之要求,必须转化为程序性知识,程序性知识的教学意义是巨大的,是最需要的也是目前教学最缺乏的。而这两者的转化的契合点在于“用”,将陈述性知识融入某一情境中,即把知识实践化、生活化以达到两种知识的有效转化或结合,这种“用”也正是程序性知识“做什么”或“该怎么做”的要求所在。如黄德初老师在《我愿意是急流》教学的最后一环节——让学生仿照诗歌另赋新诗,此为“用”,让学生用已学知识尝试做某件事,即是迁移,这种教学方法对程序性知识的掌握是高效的。“用”较之感悟、体验多了明确的指向,又较之分析、理解多了具体的操作训练。黄老师的“用”是非常大胆的,教学设计也是本课堂的亮点,程序性知识趁热打铁地得到即刻落实。而且通过“用”让学生顺着外显知识指示的方向挖掘了诗歌教学中很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缄默知识,并最终实现缄默知识向外显知识的转化。用外显知识引导学生缄默知识的获得是语文教学的难点,所以训练的教学方法为黄老师突破了教学难点和实现了教学目标。训练法是教学活动中常用的教学方法,不少教师用得不慎造成了题海战术,所以训练法必须有所针对性,做到有的放矢。它对程序性知识类型是很有效的。
张璇老师执教的《说数》是一篇科学小品文。张老师教授的知识中主要是策略性知识,对此张老师采取的主要是分析的教学方法,这点非常合理。因为只有通过理性认识和逻辑推理的分析过程才能让学生体会科学小品文的准确性和文化之美。如:张老师在落实教学目标之一“掌握科学小品的准确性、生动性”时,设置了“是非大考场”的教学环节,她不仅要求学生对所给出的语段作出判断,并要求学生对自己的判断找到根据。另外,张老师课堂知识的衔接性非常紧凑且渐进有序,在学生细致体会文章的科学和准确性后,引导学生体会科学小品另一特点——文学性,这两个环节让学生对掌握文章中形象生动的说明方式的策略性知识有了清晰的认识。更值得肯定的是。张老师不是通过传统满堂灌的方式来教学,而是组织学生以探究的方式一层一层地剖开其中的“策略”,即本篇科学小品文所使用的说明方法。这种分析引导学生不断地思考以达到深入策略性知识的“元认知”和实现学生对认知过程的自我调控。全面地理解知识生成的过程并对自身某部分的认知进行新一轮的修正和建构。策略性知识的掌握虽然更多的是依靠学生自身对认知活动的调控过程,对中学生有较高的要求。所以对策略性知识的掌握,教师的引导显得尤为重要。而教师在教授策略性知识时所采用的教学方式又是能否有效地引导的关键所在。一般而言,张老师所采用的分析教学法就是针对策略性知识的,这是由策略性知识的性质、功能所决定。
这三个课例充分地展示了语文知识的类型,同时也为不同类型的语文知识所应采取的教学方式提供了启示甚至是示范作用。语文知识再一次成为语文学科研究讨论的焦点,可见这是语文学科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在考试指挥棒下,语文知识形态已被扭曲、语文知识的教学也已被异化。因此我们要正视这一问题,只有对语文知识类型的熟知并与恰当的教学方法相融,才能达到认知的高度,否则教育目的、课程目标都将会成飘渺虚无的浮空之言。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