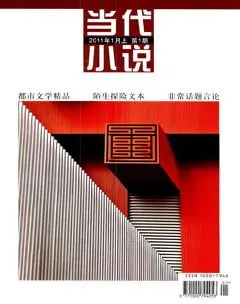张大力之死
一
六月八号,那个狗吐舌头一样炎热的午后,大力咽下了他人生中最难咽的一口气。大力当时是死在医院的病床上,阳光从对面的窗户玻璃上直射进来,洒在了他干瘦但洁白的身体上,晶莹透亮。大力的生命终点就是在这个时候急剧降临的。他微睁着眼睛,用那双忧郁而深邃的眼睛,平静地扫视了一下屋里所有的一切,而后安详地闭好。大力就这样死去了,全然没有那种声嘶力竭的尖叫和难以忍受的痛苦状。
大力死的时候,没有同他的父母和两个姐姐说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力是不是早已忘掉了他们的存在,还是在故意躲着他们?大力一生中有七成的时间都在躲着别人的眼光,死的时候,他一样不愿同别人的眼睛对视,即便这些是他的亲人。我当然还知道,这是一个他不曾改掉的习惯。
大力死的时候二十六了。这样的年纪应该是一个男人正值家庭和事业旺盛的季节,大力却在这个时候停止了呼吸,贪婪而自私地享受着另一个世界里的幸福和自由。大力不知道,那个狗吐舌头一样苍茫炎热的夏季,他的死,却给了那个他生活了二十六年的村子多大的意外与震惊。
大力死了,是死在工地上。这是人们在埋葬大力时议论最多的话题。
二
大力姓张,与我同岁。我至今惟一记着的是,大力还与我同月。大力的上面有两个姐姐。在七十年代的乡下,有两个女娃是件挺晦气的事情。大力的爹也觉着挺晦气,因为每每在牌桌上,大力的爹只要输了牌都觉着丢脸,面子的事,最大。狗日的,再不弄出个男娃来,老子还在村里混个球!大力的爹嫌大力娘的肚子不中用,说你的肚子再不中用,就休了你。大力的娘就害怕了,常常躲在被窝里一个人偷偷地抹眼泪。大力的爹那时候是村里的队长,手里有权,休一个老婆不是什么大事。对大力的娘,他说他忍了好几年了,没男娃,日子绝对过不下去。
当然,生男娃也不光是女人的事,大力的爹那时候就常常在晚上“下功夫”。他爹,你再大点力,要不能生出个男娃?大力娘在这个男人带给她快感的时候,也常常这样过分地要求他。狗日的……大力爹骂道。
一九七八年六月的时候,大力终于出生了。据说得知是男娃后,大力爹高兴得不得了,在村里的六个十字路口磕了头,放了炮。
大力的名字据说就是因为大力娘的那句话而得来的。当然,这些也只是传闻,或许还有更深层次的涵义,我们不得而知。
让大力爹意外的是,大力生下来后非但没如他期望的那样强壮有力,反而多了一分女孩子少有的如花似玉。少年大力在学校里最讨人喜欢,他不打架、不骂人,所有的老师都喜欢这个爱脸红、爱忸怩的假丫头。大力为此苦闷过,他甚至常常瞎想,自己不应该生来就是一个男孩的。大力只希望做一个干净的女孩子,安安静静地长成姑娘。他拒绝了父亲为他制成的弹弓和有爆发力的链子枪。但大力知道,自己长着女孩子万万长不得的东西,而正是这个东西,也将决定着他人生的下一个站点究竟会在哪里?
似乎所有人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大力的学习进度比别人晚了好几拍。十三岁的时候,我已经上了镇里的初中,而大力,还在村里的小学四年级里艰难地爬行着。学校的老师反馈回来的结果是,你们家大力太女孩子了,除了不说话、不打架外,他还每次考试不及格,这怎么能在学校呆下去?我看你们还是叫他别念了,趁早学点什么手艺吧?老师的苦口婆心对大力爹是个沉重的打击。那天晚上回家后,他把大力吊在了自家的门框上一夜,第二天早上放下来时大力腿都僵了,走不了路。这是大力第一次被他爹拾掇。大力从那天起就害怕他爹了。他说就是那次后他再也不敢看他爹的眼睛,凶残得像个土匪。说这话的时候,大力是在我的家里。我娘说,大力,你爹咋能这样对你,你可是他亲生的呀。我娘刚说完这话,大力的眼泪就扑簌簌流了下来,流过他白嫩的脸颊,而后静静地挂在嘴唇边上,灵动饱满,自然而感人。大力就这样变得自卑了,自卑得更像一个姑娘。
那年月,年轻叛逆的性格是玩伴们青春期最张扬个性的方式之—。当然,大力也曾竭力地叛逆过,要不然,大力这辈子死的时候一定会抱憾终生的。我只记得那年是三娃偷着摸了他爹的五毛钱,然后从商店里买来了五包发霉的延安牌香烟,鼓鼓囊囊的,揣满了上衣和裤子的四个兜。三娃中午的时候曾约我和张琪一起去麦场后面的草垛会合,我问他啥事?三娃嘿嘿笑着诡秘地不说话。我说好吧。我过会儿来。当我偷偷从家里溜出来的时候,正好碰见了大力提着桶去喂猪。我说大力,走。大力红了一下脸,问我啥事?好事呗!我说。我不去了,我还要喂猪了。那你快喂,我等你。我不去了,你去吧。大力,你什么时候才能像男娃儿一点呀?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力已经最怕别人说他不像男娃了。因为他知道,自己长得再像女娃,也终究是男儿身。大力的脸红得更厉害了!你到底去不去?我急了,逼着他问。好吧,你等会儿我!
当我领着大力赶到会合地点的时候,三娃和张琪已经到了。他咋来了?三娃有些不痛快地背靠着草垛问我。大力也是我们的兄弟呀,我们不能不仗义,是不是?听我这么一说,三娃没再吱声,只背过脸去,从上衣和裤子的四个兜里先后拽出了五包烟。看!我和张琪都大吃一惊。这么多!张琪贪婪地流着口水。别犯愣呀,快打开。三娃对我和张琪说。张琪打开了其中的一包,然后给了三娃和我各一根。我没火呀,张琪说。嘿嘿,我早预备着呢!三娃说着就嗞的一声划响了一根火柴,火苗不大,但馨香入鼻。他给自己先点上后,又分别给我和张琪点上了。三娃用白嫩的牙齿歪叼着烟,故意扮着一副二流子的模样说,看,拽不拽?我和张琪连连点头说拽。那年月,在镇上的中学上学,镇上的学生最喜欢欺负我们乡下的。他们往往一放学就一伙人站在公路的边上,个个嘴上叼着一根烟,俨然一副社会混混的样子。当然,我们是不敢惹的,我们也惹不起。我们惟一的顺从就是挨他们的打,或者被他们敲诈。大力没上过中学,他还不懂,所以他对我们的举动还不是很明白。在大力看来,抽烟是成人的事,就像他爹那样,即使村里每次开会,他爹的嘴里也离不了烟,就那样歪叼着,十足的霸气。大力内心还是渴望自己成为男孩的,他甚至梦想着能成为他爹一样有霸气的男人。三娃,也给我一根吧。大力那天看着看着突然对着我们仨个说。啥?你也要抽烟,算了吧?三娃白了一眼大力,一副瞧不起的样子。听三娃这么一说,大力的脸又红了,他低下头,偷偷用余光瞥着我,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三娃,给他根吧,让他也神气神气!我说着就从张琪的手里取过那包烟,看着三娃,静静地等着他的答复。大力也把眼光转向了三娃。他希望三娃能给他一个机会,一个表白自己性别的机会。三娃最终默许了,三娃的默许带着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只是让我们谁都没有想到的是,从没抽过烟的大力,抽烟的姿势竟是那样的洒脱与自然,他修长的于指夹着的烟卷,就像毕加索手中夹着画笔的姿势一样惊人。这是大力吗?看着大力嘴里吐出的带有烟圈的烟雾徐徐上升,我们三个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大力一生中从未给过我们任何的意外与惊喜,但那天他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
那以后,我们四个便常常相约在天快黑的时候偷着跑到草垛后边去抽烟。我们都愿意模仿大力抽烟的姿势,大力的姿势不光洒脱自然,而且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魅力,完全与镇上那种小混混的样子判若两样。大力的心里得到了莫大的满足,他为自己所取得同伴的赞赏而不停抽着烟,直到三娃的那五包烟全部抽完。没有了烟,大力似乎又开始孤独和自卑了起来,似乎只有在抽烟的过程,大力才是很男人的、很自我的样子。
大力在积极寻求烟的渠道,直到最后,他把手伸进了他爹的烟袋里。他趁他爹不在家的时候,用手在那个用松紧带扎起来的黑色烟袋里抓了一把烟叶,然后悄悄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尔后再抽个时间偷着跑到草垛后面用废纸卷起来抽。大力卷烟的动作我见过几次,娴熟而老道,一看就明白是个抽烟的老手。大力有没有上瘾我不知道,我只觉着大力是在寻求一种寄托,精神的寄托吧?因为似乎只有这样,大力才会看得起自己。当然,大力偷他爹的烟卷我们几个是不知道的。那时候我、三娃和张琪已经到了开学的季节,我们再也很难凑在一起秘密商量一些地下活动了。大力就是在那时候开始把手伸向他爹的烟袋的。
大力最终被他爹抓住了。大力是在有次抽完烟后,随手把烟头扔在了草垛边上,他用脚碾了一下,就走开了。没承想,那晚后半夜起了风,把人家的草垛给点着了,红透了半边天。受到损失的草垛主人到处在打听是谁点的火,最后打听来打听去,有人说是队长的儿子,说是经常看到队长的儿子一个人去草垛后面抽烟来着。大力他爹气得要死,赔了钱不说,还丢了脸。最让他气愤的是,从不惹事的大力竟然也学起了坏,抽起了烟。那个年代,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抽烟,就如同现在的孩子会在这个年龄段上打麻将一样让大人愤怒。
大力又一次被他爹给拾掇了。
这一次,大力他爹让大力跪在院里的祠堂前接受心灵的忏悔,大力跪着跪着就打起盹来,被他爹看到了,气得不得了,随手抄起一根棍子,照着大力的后背就是一下,这一下,让大力当场栽倒在地。大力在家里足足躺了四个月,医院的医生说幸好伤得不是地方,要再往下偏一点,就把肋骨打断了,依当时的医学水平,小县城接都接不上。
大力无疑是幸运的,好在没残。但大力他爹无疑是害怕了,他说他今后再也不打大力了,只要大力能好好活着就行。好好活着,这是大力他爹对大力寄予的最低要求,在我看来,也许正是这句话,却成了大力一辈子都在攀登的高峰。
三
大力的童年应该是富足的,印象中城里孩子刚刚时兴过的东西,大力家不久之后就都会有。当然,这些东西中有一部分是大力他爹买的,但大部分是别人送的。我时常会在记忆中努力搜索一些过往的东西,与大力的,或者与他发生过的一丝半点的记忆。
大力与我的关系除过同龄外,最重要的是我们两家离得近,只有二、三十米的距离。大力他娘常对大力说,你看人家高成,多聪明,你咋不多学着点呢?现在看来,学习这东西除过用力外,最重要的还得用脑。大力用过力,但脑子就是听不进去,谁也帮不了。
现在,大力是不用再那么努力了,他可以静静地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倾听我给他一点点讲述我们过去的那些故事。
大力生来身体瘦弱,弱不禁风的样子,让谁见了都觉着他本应该是个女娃的坯子。大力长着一张很好看的瓜子脸,皮肤白皙、手指纤细而修长,就像秦腔戏里的苏三一样。只是所有这些,都阻止不了大力是个男娃的事实。大力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开始拒绝别人说他是女孩子。他多次把自己幻想成为一个与他外形不一样的人,一个让他爹看得起的人。这是大力的渴望。有许多次,他都偷偷对我说起过。
当然,十三四岁的年纪仍然是属于童年的,一个能勾起人欢快记忆的美好季节。那时候,也就是大力学会抽烟之前,他一直安安静静在学校和家里做着听话的自己。有一次,我刚从镇上的中学放学回来,大力就来了。大力进来的时候没有声音,把我娘吓了一跳。大力,你啥时候进来的?我娘冲着大力问。大力脸就红了,低下了头,不吱声。快进来吧,大力,高成在呢。我娘知道大力的性格,没有再盘问下去。大力抬起头笑了下,就冲着我写作业的屋子来了。我问大力有啥事,大力站在门口,边冲我笑边从兜里掏东西。最后大力掏出了两块泡泡糖,塞到我的手里,说了句,给你,便跑开了。大力无疑是给了我一个惊喜。有许多次,我都央求过爹给我买块泡泡糖,爹总说太贵,一个要两毛钱呢。那天写完作业后,我和大力一起坐到村子后面的水渠上,摇晃着双腿,把那个白色的泡泡糖在嘴里反复咀嚼着。大力比我聪明,没几分钟,大力就能用舌头吹出一个又一个漂亮的白色泡泡了。我在学校里见过别人吹,自己却如何也学不会,有好几次,或许是我用力不对,我甚至都把嘴里嚼得发软的糖块不小心吐到了干涸的渠沟里。大力从不笑话我的笨拙,我也在他面前从不表现得不好意思,我会赶紧跳下去把掉在地上的东西捡起来擦擦,然后扔进嘴里,再反复练习吹泡泡的技巧。黄昏的一缕阳光照在我们灿烂的脸庞上,金黄金黄的,就如那时我们的年龄一样年轻。
随着年纪的增长,大力似乎对男孩子的东西表现出了某些兴趣,但真正使他感兴趣的东西其实只有游戏机。游戏机是开发智力的好东西,大力他爹对此并不反对,于是,那个时候,只要我从几十里外的高中回家时,都会在街头碰到他手中握着一个巴掌大小的游戏机在玩着。游戏的音乐欢快而动听,让人觉着陶醉。
那是一九九四年的冬天了,在这个冬天,大力与我一样十六岁了。十六岁的大力在街头整日玩着俄罗斯方块的电子游戏,对此,过往的行人都嘲笑他,说这么大的人了还天天在街头玩游戏。这句嘲笑的话语颇值得分析。意思不是说十六岁了就不能玩游戏了,而是说如果要玩,可以在家里或者其它什么看不到的地方躲起来玩,因为十六岁的年龄,在农村,是应该承担一部分父辈责任的年纪了。而恰恰正是大力这种外露出的贪玩本性,授人以柄,给了路人说话的自由和批评的权利。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大力爹的耳朵里,他没收了大力的游戏机,对大力说,再不好好念书,就回家来。大力真的就回家了。其实那时候大力面临的压力也很大,在班里他岁数最大,个子最高,成绩也最差。我甚至到今天都想不明白,大力一点也不傻,一点也不笨,为什么他的学习却一塌糊涂呢?当然,这其实也是大力父母一直揭不开的一个谜。在今天,面对着病床上那具冰冷的尸体,面对着再也不能朝我微笑的大力,我想我定是得到了答案:大力生来就该是一个女孩子的,他不该长着男孩子的东西苟活于世。
四
一九九八年的冬天,我在连部接到了娘从老家打来的电话。娘对我说,阿成,大力跟你一样,也当兵啦!什么,大力当兵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的心里突然间像压了一块石头一样难受起来。大力的性格怎么会适应部队的生活呢?是谁让他当的兵?我问娘。他爹呗!大力他爹说让大力跟你一样,在部队锻炼锻炼,兴许还能当出个名堂来哩!
以我现在十二年的军龄来看,我当初的预言一点也没错。大力是不适合在部队里呆的,部队紧张的生活节奏大力永远也跟不上趟。
大力戴着大红花,穿着不合身的新军装,从那个他生活了二十年的村子里第一次迈向了军营。在咸阳的那个晚上,大力至死都忘不了。一个扛着三颗星星的军官对自己和其他几个新兵说,你们都过来,跟我去理发!理发本应是件很平常的事儿,但大力接受不了把头发理得像和尚一样短的窝囊样。他忸怩的动作让肩扛星星的军官很反感,硬是把他推进了理发店。大力是不敢反抗的,大力的反抗只有无声的哭泣。从咸阳到酒泉,大力摸着自己光秃秃的脑袋,流了一路泪。
新兵连的生活很快就开始了,大力的进度明显跟不上别人的节奏。新兵训练课目多得要死,一个接一个,大力总是拖排里的后腿。新兵排长是个刚分下来的大学生,颇有耐心,他为此专门给大力开小灶,积极开导他,还挑了有训练经验的班长训他。只是,大力仍然不见长进。两个月后,一向温文尔雅的排长也火了,骂了句,瞧你那熊样,什么时候才能像个兵!
大力是在排长的斥责声中躲起来的。排长知道,新兵的考核成绩是衡量一个干部水准的惟一指标,于是他把大力藏了起来,并对他说,你装病吧!装病,就不用参加新兵考核了!这样,也不影响整个新兵排的成绩。大力说了声是,然后静静地看着排长,这是他参军以来头一次看到排长兴奋的样子。
那阵子,全连的新兵都在摩拳擦掌积极应战,只有大力,一个人在卫生队的病床上安静地躺着。排长是托了一个老乡的私人关系把大力弄进来的,排长为此费了很大力气。大力躺在洁白的病床上,看着屋顶,常常会想起许多自己的心事。大力或许不曾料到,六年后,他自己会一样躺在洁白的病床上,正一点点等待着死亡。
大力训练成绩的一塌糊涂,预示了他要被分到炊事班的厄运即将变成现实。那几天,大力总能梦见他娘对他说,大力,回来吧。梦醒后,大力就一个人坐在床头,像个姑娘一样嘤嘤地哭。
部队还是给了大力机会的,但大力却没能力抓得住。
新兵下连前,管理股长下来给副团长挑公务员,大力一眼就被相中了。看着眼前这个长相清秀的兵,管理股长说你多大了?大力红了脸,低下头说自己二十了。管理股长回过头对陪同的新兵连长说,成熟点好,成熟点好!大力就这样成了团首长的公务员。
当公务员第一天,公务班班长盯着大力看了好半天,才说,你叫张eRgxFE5EwvTE5iPtxw+KWg==大力?大力点了点头,说是。大力看得出,老兵有些不高兴。老兵没再说什么,只把大力带到了副团长的办公室,说你干吧。说完后就把副团长家里和办公室的钥匙扔给了大力,扬长而去。在部队有一个传统,叫以老带新,以弱帮强,但那个老兵没教大力任何东西,而是甩给了他一个包袱,让大力感觉沉甸甸的。
大力在给副团长当公务员的第一天,毛手毛脚的他先后在办公室、会场上和家里打碎了副团长的三个仿瓷水杯。事后副团长瞪了大力一眼,转身就走了。晚上管理股长匆匆忙忙带着人到公务班搬大力的铺。管理股长指着大力说,你小子,咋那么不小心呢?
大力的命运在一天之内急剧变化,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像数学上的抛物线,变化的速度让人回不过神来。大力只记得,离开公务班的那天,公务班长对着自己嘿嘿笑着,一脸的得意……
大力回到了老连队,被分到炊事班烧火。烧火在炊事班是最没技术含量的一个工种,大力却在这个岗位上一呆就是两年。大力在烧火上无疑是有灵性的,就像他当初玩游戏一样,不愠不火。
两年后,大力带着遗憾退伍了。走的那天,大力同样戴着大红花,鲜红鲜红的。
我只记得选改上士官的第四年,我在探亲回家的时候见到了大力。大力听说我回来了,主动到家里来看我。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大力身上没有一丁点军人的影子,他甚至连军人最起码昂首挺胸的动作也没有。大力是已经退伍的军人,一个曾经拥有两年丰富军旅生活的军人,怎么会没有军人的味道呢?大力走后,我问娘,他回来时就这样子吗?娘说可不是咋的,跟当兵前没什么变化!这是娘的感受,却再次印证了我当初的预言。
大力参军的大部分原因都是由于他爹。娘说,自从我走后,大力的生活中已经没人与他成为朋友了。他的孤单显而易见。这就是大力最终也同意当兵的牵强理由。
大力最终的死究竟与他在部队里的遭遇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不得而知,但我清楚,大力的确已经死了,而且死得那么朴实和自然。
五
大力死的那天,大力爹一直站在病房的角落里,不敢朝大力躺的地方瞅。大力爹一直很自责。他说都怪他,要不是他让大力去打工,也不会出这么大的事儿。而现在,大力是听不到他爹对他说的任何话语了,也看不到他爹对他凶狠的眼神了,大力现在只需要安稳地睡一觉,来缓解这些年来在世上经历过的各种苦痛与辛酸的折磨。
大力结婚了,娘又一次在电话里给我报告着大力在家的情况。咋这么早?我问娘。都二十三了还小,你看人家大力,多听他爹的话?娘的意思我听得出来,她是嫌我二十三了连个对象都没有,因而拿大力结婚的事来“敲打”我。
在我看来,大力结婚的确早了些,对于一个能承受住压力的男人来说,二十三岁似乎足够了,但对大力,还完全过早。
大力的婚事全仗着他爹的张罗,四邻八舍,去的人不少,大力就这样在众人的“挟持”下上了架,像一个鸭子,却完全像是被赶着上去的。
当然,在从部队退伍之后的四年里,大力也曾在他爹严厉的斥责声中努力地外出打过工。他先去了一家水泥厂,但人家一看他瘦弱的身材,就将他拒之门外了。后来他又主动去过镇里的一家纸箱厂,在那里给人家糊箱子。大力纤细修长的手指似乎只与那些与生俱来的箱子有缘分,只是没干多久,厂子由于效益不好倒闭了,大力只得重新回到家里。
大力在家里等待的过程,就像一只受伤的猫在等待着抚慰一样。只是大力爹不会抚慰,只会肆意大发雷霆,把个不大的屋子弄得鸡犬不宁。
大力娘有天偷偷流着泪对大力说,大力,你出去吧,出去干点活,要不然,这个家早晚会被你爹喊塌的。大力娘说的明白,她看出了大力爹与儿子之间的矛盾根源在哪里。但她也知道,这是为了大力好。这个家迟早是要大力挑起担子的,不趁早出去寻点挣钱的路子养活家,咋成?
大力就是在这样的逼迫下,一次又一次走向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知道,在打工的过程中,大力受到过的屈辱与委屈肯定不少。而这些,只能由他一人独自承受。
不知为何,从那一年开始,大力家的家庭内战爆发得极为频繁。大力的媳妇,那个从不张扬的女人,也开始指着大力的鼻子叫骂开了。大力选择了忍让,这些年,他已经习惯了忍让带给他的另一份安宁。
二十六岁,一个男人最为宝贵的季节,大力就这样从自己事先预谋好的施工楼顶上掉了下来。大力掉下去的时候背对着大地,他希望把自己摔得粉身碎骨,最好化为一片白云,随风而去。
大力没死,从五层楼高的楼顶背对着摔下来居然没死,甚至连他清秀的脸庞也完好无损,这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
大力被送到医院里进行了五个小时的抢救,据说光抢救费就花了好几万。当然,这些钱是施工单位支付的。因为没有人知道大力是故意的,大力将自己的死设计成了一种意外,他成功了!
被救醒后的那段日子,大力就那么安静地躺着,不说一句话。
娘打电话告诉我大力出事后,我急忙从新疆的部队请假赶了回来。我希望在大力人生最后一个逗留的地方,多陪伴他一些日子。
六月八号,那个狗吐舌头一样炎热难耐的午后,大力终于咽下了他最后一口气,安静地走了。
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一句话:宁可高尚地死去,也不卑微地活着。兴许大力就是这样想的。
责任编辑:李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