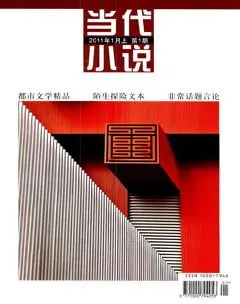弄堂风流
李家爸爸
两条弄堂面街,窄窄长长。其实不长,只为窄,显得长。弄堂里的大人,大多旧知识分子,都有一定背景。据说,上海四九年解放时,新政府不知该如何处理这批人,于是,统统收编进了同一大学。这两条弄堂,其实也是这大学的宿舍。
除了夏天太热,屋里实在呆不住,不得不出来乘片刻凉,平时,即使星期天,这些大人也是足不出门的。惟有例外的,是上下班时。那时的他们,开门出来,或由外面走进,总先探头瞥上那么一瞥。这一瞥,只是道光,急促一闪,然后,快捷收回目光,俯首,缩起肩膀,脚步格外匆匆,弄堂里这段不得不经过的路,越快走完越好。
李家爸爸不同,进出弄堂,脚步也匆匆,却跨得大,身板挺直,头不下俯,黑得发亮的目光笔直视向前去。这目光,其实根本不看任何人,只是视前而已。
弄堂里谁都知道,李家爸爸进这家大学,是由当时的上海市长亲自介绍,并用轿车亲自陪送去的。大家都知道,李家爸爸当年,曾经当过孙中山秘书。
李家爸爸有个年轻的太太,小他一二十几岁。其实也不年轻了,只是看上去年轻。她,白白的皮肤,清清瘦瘦,干干净净。细细的眉毛,细细的眼睛,细细的皱,偶然有的笑,也是细细的,细细的目光从细细的眼缝里甩出,眉头稍稍皱一皱,被她看过的人,也就成了细细的了。这目光,那年代不少,只是,李家妈妈的相对显明些。
李家有五个子女,三女二儿。三个女儿毕业于清华、北大、同济,大儿在复旦,是数学系高材生。都是响当当的名牌大学,都是人材。惟小儿子,出生晚了,过了“好”年头,只上了中专。按说,小儿子总是最受宠的,可李家爸爸最不宠的就是这个小儿子。
李家爸爸最喜欢的是大儿子。他的喜欢,因少有表情配合,看是看不出的,主要体现在对大儿的培养上。弄堂里的人,每到夜晚,习惯听到小提琴的弦音,从他家传出,在窄窄的弄堂里回来荡去,撞到墙上,撞到玻璃窗上,然后,从各家各户的门缝里渗入。琴声时而悠扬委婉,时而急促亢奋,时而沉沉的,带着人的心思一起旋转、起伏、飘游,说不尽的缠绵。该说,精致委婉的倾诉,最能拨动人心中的那份温情,那份美妙的柔意,却那年头,那样的夜晚,听来总让人压抑,虽说是享受,但却是份重的享受。大儿子的提琴是李家爸爸亲自教的。做父亲的自己已不拉,只是教儿子。天热,打开的窗口望进去,暗暗的底楼屋里,常见李家爸爸一旁站着,纹丝不动,看儿子拉琴,看得很专注。偶然,也见他动动嘴,动动指,指点一下,很偶然。他的动,不过动一动,不过吐两个字。久久地,他就那样手捏下巴,专注地听,黑乎乎的目光一闪不闪地黑着,于虚无中远了去。也只这样的时刻,才让人感到,这目光的尽头,还无声地活动着遥远的记忆。大儿的琴拉得很出色,是复旦交响乐队首席小提琴手。据说,上海交响乐团也曾邀请过他,但他没去,想来还是名牌大学高材生更具魅力之故。
文革时,李家自然抄了家。抄家后的李家,原有的那份荣耀威严,不再那么荣耀威严了。其实,那份荣耀与威严,从四九年前远远拖来,已拖得很久很长,本也是衰弱了的。
李家大儿六五年大学毕业,七0年结婚。结婚时,老两口让出了光线最好的二楼,睡去了底层,小儿则搬去三层角。大儿媳是个护士。应该起码是个医生的。但那时,标准彻底变了,组合也都错了位。儿媳出生较好。这“好”,已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好。这样的“好”,在过去,那是连进也进不到李家妈妈细细的目光中的。
婚后的大儿子,不再拉琴了。开始回家上楼,还常弯进底楼屋里,看看他的父母,却最终,还是违不过媳妇的意愿。媳妇纤细的手指,在他袖管上轻轻一拉,轻轻一推,他的身体便失去了分量,即刻转了向。天长日久,大儿子的脚步,走过底楼,也就没了那份迟疑;天长日久,脚步一停不停地走上楼去,也成了大家习惯了的自然的事。
李家爸爸老了,那几年,突然老了,老得非常快。天热时,偶然,他也出来乘上片刻凉。弄堂里的人吃惊地发现,他的身体,已像只被晒过的虾米,干干燥燥,萎缩不少,脊梁也弯了,像只弓,直直向前的目光,不再那么坚定、那么自信、自负,似也越发记不得曾经有过的气派,开始游移,开始有了接触其他目光的意愿。然而,没人愿意接受这目光,没人。大家根本不知,接受了,能和他说些什么。
李家爸爸卧床了,冬天、秋天、春天、甚至夏天,都卧躺在床。床边茶几上,大大小小、七歪八倒铺满了各种各样药瓶。底楼房里,没有光线,黑洞洞的。上海的天气又潮湿,总有那么多的水气,地底、墙缝中渗出,带一股阴、一股霉。一年四季,每到夜晚,人们总能听到李家爸爸的咳嗽声。这咳嗽声十分苍老、十分悲惨,碎了一般,翻动许多痰泡,每次都是响亮地开始,然后一点点微弱,直至没声,以为完了,可停一停,又更加急促、更加剧烈地开始。每次听上去,都像是气绝,那口气断了般,再也回不过来了……李家妈妈也突然老了,风湿性关节炎,腿不能走,心脏也不好,眼睛还得了不知什么病,老出水。那时候,照顾这对老夫妇俩的,就只有住在三层角里的不太喜欢的小儿子了。
小儿子在一家厂当科长,人缘很好,认识许多人。父亲需什么药,想吃什么,都由小儿子去买。父亲进出医院,也是小儿子去联系,小儿子把他背上背下。李家爸爸退休工资算高,用什么钱,都他自己出。但他与小儿子很计较,找回的钱,一分一厘算清楚,时常还怀疑,怀疑小儿子贪污、报虚账。人都躺在床上了,却还捏紧钱,一张张数,数毕,深凹的眼抬起,恶狠狠地,皱瘪的嘴,叽里咕噜不清不楚吐几句。小儿子气得几次准备不再管他,可想怎么也是老子。已够可怜,也就软了心。李家爸爸有些积蓄,不多,但有些,全都塞在枕头下。偶然,他的孙子——大儿子的儿子,去他房里转一圈,他便直起身,用蚊蝇般的声音,有气无力唤过孙儿,被窝里抽出甘蔗渣似的手臂,指头戳进枕头,摸索一阵,扯出几张钱,抖抖嗦嗦递给孙儿,骷髅般的脸,跟着漾开老树皮似的笑,很皱很皱,笑出仅剩的几颗牙……
据说,李家爸爸曾给孙夫人写过信,说他想写一本孙中山先生的回忆录。孙夫人办公室倒是给了回信,谢谢他的好意,说已有人写了。李家爸爸年青时喜欢写诗,老了也写一点,他让他小儿子,找人帮他出了本诗集,他自己出的钱。都是些五言格律诗,还是用蜡纸、钢笔刻的,油印机印的。没几个人看,看了,也没几个人懂。
李家爸爸的追悼会,出席的大多是小儿子的朋友,他自己早已与人没了往来。几个女儿在外地,赶不回家,就算赶得回,也觉意义不大。李家妈妈病身在床,腿不能走,眼老出水,自然去不了。大儿子是去了的,还有些伤感,掉了几滴泪。大媳妇也去了,只不知是否因为悲伤,总绷着脸。小儿子胸前戴了朵白花,很忙,里里外外招待人……追悼会上,自然要念一念李家爸爸的生平。也就那一刻,大家才又重新想起他的不一般,想起曾经有过的辉煌,想起他让人敬畏的不看人的目光。不过,这想起,也因遥远,因时代颜色的关系,已是模模糊糊,远不似当年那般影响人。
九十年代末回上海,我再进这条弄堂,去了李家。李家小儿子是我朋友,关系很好,以前老一起玩。弄堂似比记忆中窄很多,且旧不少,砖的墙壁也都剥落,像是又过了一个年代。黑洞洞的底楼屋里,李家小儿子与我聊了些往事,聊得我心思重重。他还放了音乐,仍是莫扎特、李斯特、贝多芬的。想起了他大哥,我问,他回说,一早已去美国。想起那儿时听惯的静悄悄的夜晚的优美凄婉的琴声,问他大哥如今还拉不拉,他说他也不知道。似乎他们也没多少往来。音乐声中,打量一下四周墙壁,想触摸些许记忆,却不料,意外发觉,屋子尽处隔开一道墙,墙上有个小窗口,窗口中,一张皱得不能再皱的脸,眼已混浊不清了,正木愣愣看着我……李家小儿子对我说:“她在床上已躺了好多年了……”
胡老教授
五十年代胡老教授就已病休。那时他不老,不过五十八、九。
胡教授是在课堂讲课时当场跌倒的,讲着,一阵头晕,眼一黑;失去了知觉。胡教授患高血压已是多年的事,可那次医生说,已到不能继续讲课的程度。
胡先生早年留学美国,读的是会计学。想必曾是胸有抱负,埋头小阁楼勤奋过一阵的。那年代,中国人的地位不怎么样,在外难免受点歧视。有人说,自尊与自卑相辅相成,但胡先生身上却只有自尊与自傲。在美时,一次路上,一洋人拦住他问:“你们中国人是否都吃老鼠。”胡先生当即拉大嗓门,手指人鼻:“我们从来不吃老鼠,只有你们才吃!”说完,轻蔑一瞥,放开嗓门,哈哈大笑,一声一个音节,一声响过一声,而后,昂首阔步,灿灿烂烂扬长而去。这话虽谈不上多少巧妙,可怎么说,也算以牙还牙了。胡先生有几张美国时的留影,荡秋千时照的,他身体魁梧,坐在秋千架上该说不怎么合,但照片上看,却实在协调得很。他笑得开怀自如,旁若无人,身体、手脚放得开,潇洒非常,完全不把身后过来往去的美国佬放在眼里。胡先生回国后成了胡教授,很吃香,名牌大学都来请他,门庭兴旺,车水马龙,其辉煌,想来没多少人生能赶及。
胡教授开始退休几年,常有学生、同事、领导来看他,过后稀少了,除每月一次,支部书记前来送上工资,顺便坐他家沙发上,抽几支配给教授的高级香烟,其他就没什么人记得他了。开始,弄堂里的人走过他家门口,都会徒生几分敬崇,久了,“胡老教授”也就仅仅成了个称呼。
他有七个子女,都在外地,上海就他和太太俩。六零年一天,太太突然去世,他抱住太太,悲伤得哭出声来。后来,他在家供了张太太的照片,放得很大,还叫照相馆染了色,上面挂了黑带,两旁写有一副他的亲笔对联:“老伴已去,我将何为?”很多年过去了,照片、黑带与对联还那样供着。
据说老教授年轻时很骄横,脾气大极,满满一桌的菜,稍有不满,他能暴怒大吼,掀翻整张桌子,吓得他太太赶紧再烧一桌……为此,他后悔不已,常以此自责,怪太太在世时没好好待她……
胡老教授家朝弄堂的门原先是用钉子钉死的,不开,不知哪年起,开了,且常开。每次经过他家,敞开的大门右侧,总能见他坐写字桌前的大半侧面。每天,一张“解放日报”来,他匆匆翻阅一遍后,铺在桌上,拿过一边的纸牌,拆开,“噼噼啪啪”洗几边,便用那牌在报纸上接起龙来。“接龙”是种一人玩的游戏,接通接不通,都能无止境地一次次再接过。于是,老教授接得很少有停。接通该是很开心,却他脸上从不见开心。“接龙”那刻,他是最无表情的一刻。
我小时候“康乐球”打得好,是附近一带有名的“球王”。胡老教授知道后,哈哈大笑,说:“你是球王?哼,我才是球王!”我那个年纪怎么也不会“买他的账”,说:比。他说:比。我家有康乐球盘,他家也有。我说:用我家的球盘。他说:看看,怕了吧,只敢用你家的。我说:好,就用你家的。于是,一老一小“怒目相视”地比起来。他毕竟老了,打不过我。于是便发急,急,就“赖”。他赖的方法是说我赖。我当然不懂该给他个“台阶”下,俩人便暴着青筋“吵”。吵久了,我说:“重比,算我让你。”重比后我还是赢。老教授的趾高气扬受到沉重打击,脸憋彤红,球棒一扔:“不打了。”跟着再补一句:“赖皮”。我便也球棒一扔,道:“打不过人家就赖,这么大年纪了!”说完忿忿离去。
老教授有这点好,下次再见,与我又是朋友,人前也坦言:“他打得好,我打不过他”。但即便如此,只要偶然他赢一盘,马上不得了,“我赢了,我赢了,我是球王,我是球王”地大声叫,跟着,又是“哈哈哈哈”洪亮得震得坏玻璃窗的笑,像是存心要气死我。
老教授英文很好,尤其那时代,好的程度就显更高。弄堂里有个张家爸爸,原国民党中将的儿子,因打成右派,从原大学调去一家中专打杂。打了几年杂后,忽又被任命当起英语教师。张家爸爸原先学的是经济,英语不怎么样,于是常去胡老教授处求教。也就这时,老教授的风度看得见一些了。对求学的,他一概慷慨无偿帮助。然而,老教授留美的时代是不讲语法的时代,他知道该这么用,却不知为什么这么用。“右派”张爸爸偏偏执迷不悟,老钉住“为什么”问。被问急了,老教授大声责问道:“中国人讲话需要语法吗?!”……老教授口语极好,轮到对话,次次打断张家爸爸,纠正他发音,纠正他用词,纠正多了,又不耐烦了,叹口大气,出口伤人道:“你这种英文怎么好去教学生?”——出口伤人,在他老年,算是做人做得最痛快的时候了。
老教授七个孩子中最喜欢的是“小七子”。小七子最小,也最聪明,口才也最好。其他孩子都怕爸爸,就小七子不怕。小七子的不怕,也就爸爸一发火,二声“爹爹”叫,几句好话一说,爹爹也就火气全消。六十年代初,小七子到了娶媳妇时。小七子是不怕找不到媳妇的,只是他在东北一家大学教书,不想在那成家。
那年回沪探亲,小七子认识了二医大的毕业生,叫金莲娜,名字就很洋派,长得白里透红,如花似玉。金莲娜是大资本家千金,上海的金家是有点名气的。名门闺秀终是名门闺秀,那种高贵、矜持、与人保持的距离,换个人是学都学不像的。金莲娜二次见过小七子后便喜欢得不得了,声言即使跟他去东北也不动摇。这爱情,怎么也是感人的,却那热情,又有点不像名门闺秀。难说她喜欢小七子,与他有个教授爸爸有无关系——这种心理微妙得很,层次越高的人表现越微妙。
莲娜的父母是在一家高级饭店与胡老教授见面的。那天,胡老教授乘了辆三轮车去,一向随便的他,碍于儿子面子,穿了件呢制二用装,魁梧的他,再提一根斯的克,气派大得很。金老先生带着十二分敬意,提前候在店门口。见到那刻,敬意又添三分,老教授的腿刚跨下三轮车,金先生便迎上前,笑容可掬,头,格外文雅地点着,双手齐伸过去,握住老教授,“您好,您好”连声,“胡教授”更被当作名字叫起来。金先生年纪不大,五十多,保养很好,皮肤滋润,手软乎乎,又肉又暖。该说也是受惯仰慕的,但面对胡教授,却一味谦卑,想要显出些教养来。饭桌上,金家夫妇一次次提到美国,可老教授偏偏不接口。其实,退休后的这些年,只要有机会,他还是愿意提提美国,提提当年被名牌大学请来请去的事的,可对未来亲家,他一点说的愿望都没。
莲娜来到胡家,使得我们这条安安静静的弄堂兴奋了好一阵。一扇扇关起的门中,大人们都在议论:看看到底是有钱人家小姐,这种打扮,看就高档;多好的皮肤,又白又亮;看看人家,说起话来轻声轻气,嘴巴抿住……知识分子的太太们,看资本家千金,又能看出许多味道。
莲娜知道自己在众人眼中的形象,也因此更想保持这形象。进出家门,脚步轻点,胸部微挺,目光垂地,不看人,偶然见了,淡淡一笑,若即若离,很有分寸。
有次去胡家,她刚买回一包熏青豆,说味道好极了,叫我张开嘴,让我尝尝。她用食指与拇指捏上一粒,兰花指翘很高,抿嘴笑递过来,递到唇边,手指一松,一放抿嘴又一笑……熏青豆,让人尝一粒,感觉实在有点受辱,但当时,我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了她讲究翘起的兰花指上。
六六年的一天早晨,胡老教授的家门上出现一张白纸黑字的大字报。
老教授楼上原先有个乡下女佣,后认了女主人为“妈”,又经妈作媒,嫁了位军官,住在小阁楼里。因楼上楼下合用一厨房,想来受过点胡老教授的气。文革开始后,军属的神气可想象了,她穿起双草绿色解放牌球鞋,也像军人了,居委会里走进走出。大字报是请人写的,她签的名,骂胡老教授为“寄生虫”、“吸血鬼”,说他“十多年无所事事,整日在家接龙,白拿社会主义工资”。
胡老先生血压又升高了,面孔通红,额敷冷毛巾,脚插盛有热水的脚盆……
军属还不罢休,与他学校联系,不能让他逃过运动。于是来了抄家的。意外的是,抄不出什么。老教授家一张床,一张写字台,两只沙发,几把椅子,都是旧的,质地也很一般。书柜里,书也寥寥无几,且都已发黄,落了厚厚的灰。想是该有些金银财宝,结果也没有,连存款都远不及想象中多。没人相信,便撬地板,撬了地板还是什么都没,于是便把“寄生虫”送去了“五七干校”。
胡老教授残存的一点辉煌,那几天,糊里糊涂就过去了。
老先生本就想得穿,这场运动后,想得就更穿了。他将补发工资看做“外快”,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请几个运动中帮过他的邻居去饭店美餐一顿。“吃吧,吃吧,想吃什么自己点。”他挥着大手道。人家不好意思,他就自己动手点一大堆;人家还没吃,他就自己带头先吃起来。胡家的门,从此也敞得更开了;凡有人去,男人,递过罐头香烟;女人,则拿出奶油话梅。吃过一根或一粒,他说再来。再来过了,又说自己再拿吧。有时,他与人聊一阵,开怀大笑几声;没什么可聊了,也不客气,继续顾自“接龙”。他对自己,也越发不约束了,鸡蛋、牛奶、特别是红烧肉,该是不能多吃了,但他不管,照旧。
胡老教授与邻居的往来越来越多,谁家有些什么事,他必解囊。隔壁刘家老先生去世,他送了个花圈,还叫了三轮车,前去参加追悼会。我插队那阵,回沪探亲,常去他家坐一阵。老先生对外面世界知道甚少,也不想知道。谈起农村生活,几句听过,便摆手:“不要听,不要听,年纪大了,不想听这些。”一次返乡前,他敲开我家门,塞给我十元钱,说:“自己去买点东西吧。”说过转身便走。我追上去,发现他的眼竟红着,湿润着。见我看他,他侧过脸,宽大有劲的手,抓住我胳膊,使劲捏两下,用力往后一甩。
老先生一点归还的钱,没过多久全用光了。每月工资,没到月底,就已分文不剩。他不愁,活得很开心。实在没钱时,会向他的钟点女佣借。他家照样传出他中气十足的笑声。弄堂里的人,喜欢他,也越来越多地帮他,有上街的,都会问他一声,要不要带点东西,烧了好吃的,也总会端给他尝尝。那时候,胡老教授的称呼已被大小邻居一致改成了“胡家公公”。
那年寒天回上海,我带了好些农产品,说要去看他,家人听了,异口同声劝我别去。我奇怪,问为何。家里人说,他儿媳不准他与任何人往来。他儿媳能管得住他?他会听她?我感奇怪。
家里人说:“不同了,现在不同了……”
胡老教授从来看不惯他儿媳妇。“小气”、“贼腔”、“虚心假意”,人前人后都这样称,并一概谓之“虚伪的资产阶级作风”。文革开始,他与媳妇各管各,互不加照应。胃出血那次,也是邻居送他上医院,照顾他,帮他烧、买、洗。补发工资了,他没太多想到儿媳。她生了孩子,吃住在家,老先生规定她,每月交十元生活费,其实只是意思意思,可媳妇的忍受已到极点。
“有这种人吗?钱都用在别人身上,分不清自己人和人家人。”一场运动,莲娜已忘了自己的身份,忘了该给人的距离感,大概也知舆论的重要,遇上人,她就这样说。
一个月初,莲娜去交那十元钱时,笑呼“爹爹”,钞票拿在手,伸过去又缩回:“这钱,以后就算你给孙子买些东西吧?”老先生一听,大声道:“孙子归孙子,该买什么我会买。这点钱,你都想不给?”说罢,仰靠椅背,放大声,笑得十分鄙夷。笑得莲娜恼羞成怒,面孔憋通红:“恨死了,恨死了,真是恨死了……”声音依旧轻细,却咬牙切齿,提起那十元,一撕两半,细尖的手指,点到公公的后脑勺:“老糊涂,老糊涂,你真是老糊涂了!”
“你你你,你竟敢打我。”胡老教授大叫起来。
里弄小组长来了,居民委员会也来人了。但是,清官难断家务事。
小七子从东北赶回,阿三、阿五、阿六也分别从北京、南京、无锡赶来。
“小七子总不能容忍他媳妇这样对待他爹爹吧?”我说。
“别傻了,小七子还能帮他爸爸么?”
“那其他子女呢?”
“不还一样。”
想不通,实在想不通。“他不是一直在子女中很有威信吗?”
“八十岁的人了,还有什么威信;他的子女早已不是小孩。”
胡家的门还开,只是不常开;开也只开半扇,为的是透气。
不知胡老先生后来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底楼房子,黑洞洞的,又潮湿。一个人不与任何人来往,没人说话,没人照顾,还有高血压,双腿又不灵便……
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傍晚,他正站开着的半扇门前,面朝外。他穿一套深色衣服,背后是没光线的黑漆漆的屋。一片黑色中,脸成了白白一团。霎时间,许多记忆浮起,我叫了声“胡家公公”,朝他走去。可他无动于衷,像在看我,又像没在看。然后,呆板的目光,似有似无,随着白白的脸一起,缓缓地呆板地移动,不知落在了哪;再后来,两声“踢橐”的脚掌拖地响,白白的脸退了回去,像一团渐去的光,消隐在一片漆黑中……
家里人说,胡家公公得了老年痴呆症,已认不得人。
胡家公公去世那几天,弄堂里特别静。没人被邀参加追悼会。我回沪知晓后,去龙华殡仪馆祭拜了他。那时我很穷,只买了个简单小花圈,放在他的骨灰盒上。欣慰的是,骨灰盒边,我看见了刘家、李家,好几家邻居送的花篮,做得都很精致,还看到了右派张家爸爸的一只上好丝绸做的,两条白带上面写着:哀悼胡老教授;学生张××。
司法部长
十八号这幢楼,先前住着教授一家,可没过多久,搬去了十四号。许多年后,一个静悄悄的夜晚,教授的儿子,大我十一岁的六四届大学生,依然面带惧色地说:“十八号有鬼。”有鬼?!我骤感一紧。教授的大儿子停了停,倒吸冷气,压低的声音阴森不少:“这鬼是个清朝的官,总在黄昏将去未去时出现。我姐姐常这时楼下屋中练琴,多次听到窸窸窣窣声,以为是幻觉,偶然一次,一回头,黑漆漆的楼梯上见走下个人来,戴一顶清朝官帽,夕光中,还看得到他官服上那个方形图案……后来,我妈妈也见了这个鬼,一模一样穿着,也出现这时辰。一次,这鬼还走到我妈身后,站着,听她弹了好一阵琴……”
这故事完全符合十八号给我的印象,听得我毛骨悚然。
十八号先后换过几家人家,都没住长,直至搬进杨守中一家,这幢楼才算安定下来。
杨守中,前某地司法部长,也有说是监察院院长。无法考证了。但大家一致清楚知道,他是杀害王孝和的凶手。
杨守中不高,矮矮,却壮实;头,大大圆圆;黑脸、黑胡、黑发、黑眼珠,尤其两条眉毛,又黑又粗,眉角处还翘出两簇半寸长的黑眉梢。他总绷一张脸,目不斜视,凶光毕露,拄一根斯的克,挺胸昂头,步子跨很大。弄堂里的孩子,隔老远,常冲他的背影叫:“反革命、杀人犯”,连本是反革命子女的也跟着叫。但只要他一回头,两条剑眉一紧,黑洞洞的眼珠里射出两点刺亮的光,大大小小胆壮胆弱的孩子都会吓得赶紧转过身,有的甚至惨白着脸逃进弄堂。
杨守中家有两扇门,一扇朝弄堂,一扇面街,他从来进出面街那扇。出门,这边是住宅,多人;对面是火车线,少人,他从来走的是对马路。出去,径直过马路,九十度转弯;回来,行至对门,直角穿马路去家。他家里,从不出一点声,笑声,说话声都不出;也从不见朋友、亲戚来往。他们也不想理任何人。也没任何人敢理他们,一家老少六个人,像六个灵魂,生活在十八号这幢阴森森的楼里。
最老的灵魂是杨守中母亲。她像只猫,老得在等死的猫。白色的皱皮,白色的眉毛,两只眼睛是两条拖得长长的线,往外荡下;萎缩的身体,弯成一团;脸上没表情,丝毫都没有,完完全全像只已死去的老猫。
夏夜无风时,弄堂房子热得难熬,人家都出来沿街路边乘凉。杨守中有时会将母亲放在藤椅上,连着椅子一起搬出。左右无人时,也会陪着坐一会儿;有人,搬出母亲后,便折身进屋,唤太太出来陪。他太太坐一边,便掌一把扇,替婆婆扇扇。婆媳俩也不说话,除了那把扇,一动不动,路灯下,像两只影。可只要影子在,左右乘凉的,就算离得远,都会感到她们的存在。
一天清晨,有人见一辆殡仪馆的车从杨家面街门前开走。猜是杨守中母亲死了,但无法证实。之后,杨家日日传出一股香火味。有好奇的孩子,爬上屋顶,穿过厚厚的窗帘缝隙,望进他家去,见暗洞洞的屋里有香烟缭绕,见杨守中跪在地上,磕头不止。
杨守中有两儿一女。两个儿子已工作,长得神气,介书生样。好一阵,弄堂里人奇怪地发现,俩人总是湿漉着头发回家。后来有人说,游泳池老见他们,天天都见,他俩总是闷头游泳,一游就是几十圈。有人说,是身体不好,需要锻炼。可这说法怎么都有点不通,于是更显神秘。又一阵,两个儿子忽然又都不见了。
—个冬日深夜,寒气袭人,路上不见行人。弄堂小组长去敲杨家面街的门,身后跟两便服男。门刚开,便服男抢先箭步窜入。不久,杨守中下来了,戴着手铐,被押进一辆飞驶而来的吉普车。据说,古普车黄昏时就在马路对面不远处停着。
杨守中被逮捕了。没人知道为什么,又像无需知道,似乎是件早晚要发生的事。但弄堂里的孩子,还是神神秘秘地议论着,作各种猜想。消息终于传来,不知有多少准确性,是小组长通过街道派出所那条线打听来的:杨守中派他两个儿子分别从广东、海南偷渡去香港、台湾,带了两封他的亲笔信,装在胶丸里。信是写给蒋介石的,还有一份反攻大陆的具体计划。但他失败了,两个儿子分别在边境线上被捕。人人听了嘘吁不住,寒毛竖起。那个寒冬更寒了,寒得人不由缩颈扛肩,夹紧袄衣。等到大家缓过劲来,方才想起,杨家隔壁住一对神秘夫妇,不与人接近,没人知道他们在哪工作。这对夫妇一定是公安局派来监视杨守中的,隔着墙壁一定装有窃听器……
杨家更静了,只剩太太和女儿了。母女俩守住一幢阴森森的房,俯首垂目,无声无息进出,脸上各添分刚毅,皱纹的更皱纹,光洁的更光洁。
六六年,狂风暴雨。一日,隔壁弄堂来几个孩子,聚在我们弄堂,说他们附近一家花园洋房里,抄家抄出个地道,通很远,里面藏有一沓沓的变天帐,还有刀剑等武器。有人问,有没有枪支。回答不仅说有,更说还有发报机、手榴弹。人家听呆了,惊慌中更觉黑洞洞的复辟阴谋。有人想到了杨家。那时弄堂里已有几家被抄,杨家还未轮到,是因杨太太已退休,没了专政单位。一位小将当即掏出袖章,臂上一套,挥手道:“走!抄家去!”一群孩子便跟着向杨家冲去,差不多踢开了门,蜂拥而入。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十八号这幢阴森森的楼。
家里不像想象中那么阴森,也没什么贵重物品,原本质地不错的床单、窗帘、被子,也已旧的旧,破的破。小孩们一个个忙着撕书,忙着将—张张唱片踩碎。一屋的乱糟糟。有人在扇杨守中太太耳光。她站着,一动不动,似乎耳光不是扇在她脸上。
抄家孩子走后,杨守中太太关门时,说了一句,她说:
“当年周总理还是我们救过的!”
一星期后,杨太太开煤气自杀,但被女儿发现得早,没死成。女儿跪在地,眼泪无声地淌,求母亲再别干这件事。母亲合着眼“嗯”了声,眼角处一滴湿。又过几星期,一日清晨,女儿外出买菜回来,母亲已吊死在门廊上,双眼翻白,荡下的舌头,长长一条,已泛一层灰。女儿都没哭,白着脸,找来把剪刀,扶起踢倒的凳,站上去,剪断绳子,抱着母亲一起摔下。等到好心肠的邻居赶到,流着泪说:“你怎么这么大意,怎么不看住她。”女儿漠无表情,久了,答一句:“她想死,谁也看不住。”
杨守中的女儿不艳,但有冷峻的美,像母亲。她原先是二医大的高才生,五七年打成学生右派,去农村劳动教养,六四年才放回。母亲死后,她一人守住一幢楼,独进独出,不与任何人往来。她也没工作,不知靠什么生活。
不知又过多久,大概一年,大概二年,一日,杨家被封了,所有门窗都被贴上了公安局封条。杨家女儿不见了。面对那些纵横交叉的白封条,人们不禁生出许多悲凉、许多恐慌。但渐渐地,却又习惯了,似乎这幢楼天生就该贴上封条。
又是小组长那传来消息,杨家女儿上交了房子,自愿去农村,嫁给一个乡下人。嫁给乡下人?大家都想不通了,连弄堂里的小孩都想不通,好像灰蒙蒙的天,气压很低,压抑得很。后来,又有消息传来,说她嫁的是一个劳改犯,是她早年劳动教养时在农场结识的。嫁给劳改犯,应该更惨,但人家却都觉得可以理解了。
七十年代的一天,杨守中的女儿回来过,带了个黑乎乎的男人,一副乡下人样,想必是她丈夫。她也黑了,头添苍发,也像乡下人了。她原先很白,很像医生。两个黑乎乎的人,走到弄堂口,停了停,再走几步,在她家面街的门前站住,朝窗里望了望,仅几秒,显然是怕人发现,即刻就又走了。她没看见我。也许看见了,以为我认不出她;也许我长大了,她认不出了。望着俩人渐去渐远的背影,直到望不见,想:她大概再不会回来了吧?
后来,十八号底层空了出来,东西堆去了楼上。二楼三楼依然上着封条。空出的底楼,搬进一户新家,一位年轻的讲师,和他年轻的太太。但不久,这位讲师就疯了,他说天天晚上听到楼上有脚步声和呼吸声,像是有人在叹息、在踱步……
责任编辑: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