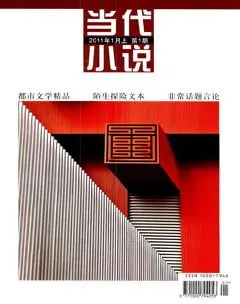偿债
柳佳慧听到一声异常尖锐的刹车在村道上响起。
她不由得心跳加速,有点喘不过气来。
她听得出来,车是男人德贵的。
她在围裙上揩揩手,慌慌张张跑出门。
刺耳的刹车声,像用开水烫过的刀子,把村子像切皮蛋那样切开了。马上过年了,她特意买了德贵喜欢的皮蛋。那松花他总也看不够,要她别切坏了它们。而她总把它们弄得一片模糊。后来她想了个办法,用开水把刀口烫一下,就把皮蛋切得整齐漂亮了。但现在,发烫的刀子切错了地方。村子顿时凝固下来。紧接着,有人大声呼叫。
她预感到男人出事了。
自从男人开了车,她就常有这种不好的预感。她很害怕自己的预感。它一旦粘上来,就赶也赶不走。她顿脚。掐自己。捶自己的脑袋。都没用。她越想越真切,最后她仿佛看到了事故现场一样浑身发抖。她对自己说,你怎么这样坏呢,你不是个好女人,总是想这些不好的事情。要等男人把车开进院子里,她才放下心来,给男人端上热饭热菜。她脸上笑着,心却在不停地自责。
她说,你还是学门别的手艺吧,工业园那里,又开始招工了。
他说,你晓得他们为什么老是招工?就因为很多人不愿干了,工资太低。
她说,低就低一点。
他说,那帮外水佬,老欺负我们本地人,我才不去。
这一点,她当然也知道。那些厂,都是招商引资进来的,对本地人自然就歧视了,好工种、高工资本地人都没份。即使本地人和外地人打架,公安局也帮着外地人。因为人家是老板嘛。他心高气傲,肯定受不得这气。这一带村庄里的青壮年男人要么到外面打工去了,要么就是开车。只有那些没闯劲的家伙才到厂里做事。
他早出晚归,赚的钱都是自己的。他们很快盖了一栋三层楼,修了院落,成了村里显眼的人家。她又说,现在别开车了,要不,我们到村口开一家批发部吧?她看到镇上有几家批发部,生意好得不得了。他们村子在国道边,开批发部肯定赚钱。他笑了,说,批发部?你以为那么容易啊,过几年再说吧。
真的?
真的。
既然有了这么一个理想,她也就妥协下来了。
但他每次出车,她还是提心吊胆的。开车收入高,风险也高。辛苦更不用说。有时候车开到半路,坏了,哪怕是半夜哪怕是天上下刀子也走不了,还得钻到车底下去鼓捣。她说让我跟你去吧,半路上,你也有个伴。他说你现在的任务是要怀上孩子,别的不用管。不知怎么回事,他们结婚都三四年了,可她一直没怀上孩子。有几次,像是怀上了,但没多久,身体又调整到了往常的轨道。她怀疑是自己太紧张的缘故。自从他开了车,她就常没来由地紧张。男人半夜回来,要跟她亲热,她不让,说你太累了。第二天一早,男人要跟她亲热,她又说,你要出车。
她后悔今天早上,就依了他。今天他不用跑远路。毕竟马上就过年了。今天他到几个已经说好的客户那里去拿钱。所以当她说你要出车的时候,他忽然变得执拗起来,他说我现在就出车。她一松劲,就没挡住。但某种禁忌依然在事后钳住了她。
所以那种不安全的感觉,今天特别强烈。每逢年节,她就更加紧张。好像它是一只快到手的鸽子,她怕一不小心,它就会扑啦啦飞走了。她一边准备着过年的东西,一边神不守舍地东张西望。从清早开始,天空就阴沉沉的,后来就下起了雪。
看到雪,她反而沉静下来了。
男人曾跟她说过,天气越恶劣,路面越难走,开车的人便越会小心的,你看,那些交通事故大多是在人没有准备的时候发生的,对不对?她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几时她担心的事情变成了事实?说不定,她的担心,可以暗中阻止那些坏事情的发生呢。这样一想,她又有些高兴起来了。
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
她有点等不及了。她盼着把这一天快点过完,好开始新的一年。她的心理负担总是和季节的变化有着某种关系。真的,每开始新的一年,她都精神焕发的,不像大了(或者说是老了)一岁,反而像是年轻了一岁。因为她离自己的理想又近了一步。
可就在这时,她听到了灾难的声音。她远远看到他们家的车撞到了墙上。男人被村里人揪了出来,像个可怜虫似的抱着脑袋。她心里安稳了些,但马上意识到,可能更严重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事后想来,当时的情景就像一场恶梦。
男人喝了酒。他本来是不会喝酒的,但他在客户那里拿到了钱,一时高兴,就拉着对方到镇上的酒馆里喝了几杯。后来她一直怀疑男人是早上累了,肚子里空。这个原因,男人当然不会讲出来。啊,她真该死!男人把车开回村子里,车子忽然失去了控制,朝几个正在踢毽子的小女孩冲了过去,国权的女儿小青当场就给轧死了。
就这样,腊月廿九成了他们的末日。
男人被警察带走了。什么都不用说。该坐牢就坐牢,该赔钱就赔钱。事情既然已经发生,她反而镇静下来。她暗暗吃惊了,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她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好像一个人担心天塌下来,等真的天塌下来了,他反而呼呼大睡?她狠狠给了男人一巴掌。那一刻,她恨他。把一切都毁了。但过后又后悔。她怎么能把责任都推到他身上去呢?所以她也狠狠抽了自己一巴掌。当然这是在家里,没有别人看到。男人是在拘留所里过的年。她把该送的东西都送进去了,说,世上没有后悔药吃,所以你也不用后悔,外面的事我会尽量处理好。
就这样,眼看着旧年就要过去,眼看着他们的船快要靠岸,可忽然一股猛力蹿出来把她一推,重新把她推到了靠不着岸的地方。她一个人用力撑着竹篙。这时别人都是她羡慕的对象,除了国权家里人。国权只有小青这么一个独生女儿。她到他们家去的时候,国权和他老婆莲芝已经哭得没有声音,只有肩膀在抖。交警都已经处理过了,他们也不能把小青留在家里。他们刚从小青坟上回来。现在,小青在条台上的相框里望着她。她不禁也哭了起来。其实两家以前关系一直很好。有什么好吃的,互相通个有无。小青也经常到她家里来玩,婶婶婶婶叫得很亲热。她把条台上的小青贴在自己胸口上,说,小青啊,婶婶我对不住你!下辈子我变牛变马还你。小青好像在说,婶婶,你不知道,德贵叔叔在那一刻好可怕,像一头发疯的牛一样瞪着又大又红的眼睛。小青跟她说话时,总是仰着脸,像一朵向日葵。现在,成了冰冷的黑白。
她说,国权哥,莲芝姐,马上过年了,你们还是想开一点,有什么办法呢,唉,我也不晓得说什么好了。
他们呆呆地望着她,好像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她说,我晓得,你们恨我,恨德贵,如果我是你们,我也是一样的,真的,如果我是你们,我心里还好受些。
他们嘴唇动了动。
她说,我对不住你们,现在,你们要对我说什么,尽管说,哪怕是骂我打我。虽然不管我怎么说怎么做,也救不回小青的命,但我要尽自己的力量弥补你们,这样,小青在天上也会好受一些。
他们把头转过去,不理她。不过这也很正常,难道还要他们把她当亲人当救星一样看待么?她都死有余辜了。
她结结巴巴的,也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好。安慰别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让别人也让自己很尴尬,何况现在还跟自己有关,何止有关,她简直就是罪魁祸首,她就更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了。她和德贵是初中同学,在村子里也算是读了一点书的人了,按道理,遇到这样的事会表现得更好,可有一次,她在路上碰到了以前的一个老师,听说他女儿在爆竹厂被炸死了,看到老师,她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她觉得自己的话一点力量都没有,怕人家说她说假话。再说,事情刚过去不久,如果老师在尽力忘记这件事,那她不又把它提起来了吗?可装作不知道肯定也说不过去。结果,她只是对老师笑笑。等老师走过去了,她才大吃一惊,她怎么对老师笑呢?老师大概在想,他女儿被炸死了,她居然还对他笑!这件事让她内心折磨了好久。她刚嫁给德贵那年,她爷爷死了。爷爷活了九十多岁,后来简直是在活受罪,所以爷爷死了并不是什么坏事,但她做孙女的,总不能对爷爷的死兴高采烈吧?在奔丧的路上,她一直很着急自己哭不出来。结果,当着那么多亲戚和村里人的面,她真的没哭出来。这件事又折磨了她好久。
记起晚上就是除夕夜,她脑子转了一下,忽然知道该干什么了。她开始自作主张地忙活起来。她先把堂前打扫了一下。出了这么大的事,脏乱是不用说的。毕竟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不打扫怎么行呢?在弯腰做事时,她忽然意识到自己慢慢平静下来,不那么尴尬了。她真的愿意当牛做马,只要国权和莲芝能重新高兴起来。和国权他们相比,德贵不在家里过年算什么呢。哪怕是坐牢,也终究会被放出来。不管怎么说,她是不会再让他开车了。她已经决定好,等把赔偿的事情处理好,她就干脆和德贵出去打工。可他们欠国权家的心债,恐怕永远也还不上。她开始给国权家做年夜饭。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年还是要过的,而且要过好。没过好对第二年都有影响。她打了两桶井水,把锅碗都洗干净了。她没系围裙,身上很快弄脏了。不过这样也很好。她又烧了一壶热水,用来发干菜。要用点烧酒,她到条台上找,发现在小青的相框旁边。她迟疑了一下,还是伸出了手,谁知身后忽然响起一身怒喝:你给我放下!她有些吃惊地回过头来,见国权的脸比刚才更黑了。
莲芝也说话了。她抬起头,说,求求你,你走吧。
她已经差不多两天没听到莲芝说话了。还好,她听得出来还是莲芝的声音。她有些惊喜地上前两步,抓住莲芝的手,说,莲芝姐,我跟你们一块儿过年吧,我当不了你们的女儿,就给你们当妹子吧,你以前不就把我当妹子吗?
莲芝说,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意思呢?
她说,有,怎么没有呢,我愿意给你们当牛做马,来还欠下你们的债。
国权吼道:你滚吧,我们不稀罕!
她看到,莲芝也用力剜了她一眼。于是她抹了把脸,从他们家跑出去了。
这个年,她是一个人过的。她还从未一个人过过年。别人家越是放爆竹,自己家越是冷清。
下午,从莲芝家出来,她又去了县里。本来不想去,但毕竟明天就过年了,今天是一个分水岭。她还有希望,希望坏运气快快过去,好迎接好运。一些商店已经在准备关门了。她挤了进去,给德贵买了条烟。德贵怎么离得了烟呢,现在更离不了。果然,他见了烟就扑了过来。才一天没见,他像老了十岁,头发是乱的,眼睛是红的,脸又黑又青。他三两口抽完一支烟(看样子,恨不得把整根烟直接往肚子里吞),又抹起了眼睛。倒是她显得镇定。她说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你想得再多也无用,等你出来,我们一切从头开始吧。待了一会儿,她就出来了。这时街上的行人少了,车辆也少了,到了车站,最后一辆客车已经开动了,她追了一阵,没追上。那基本上是一辆空车。是啊,要回家的,都早已回家了。想想,她自己什么时候在大年三十这个时候还在外面?还好,她招停了一辆摩的。价格比平时贵十倍。她毫不犹豫地坐了上去。她对自己的奢侈暗暗吃惊。其实再等等,说不定还是有便宜车坐的。
回到村子里,许多人家已经在贴门神了。一片新鲜湿润、喜气洋洋的红色。她也开始煮年夜饭,贴门神了。她把灯都打开了,顿时,新年的气氛就扑拥过来了。德贵不在家,她也要跟德贵在家一样过年。她不想不愉快的事。一切等新年过后再说。爆竹响起来了,先是稀稀落落的,渐渐成浓密的一片。她也把爆竹点燃了。她不害怕。她勇敢地用打火机去点燃了它。它疾速地炸响,有一颗弹到了她手上,很疼。但疼得很舒服。她故意离近了些。爆竹不停地弹到了她的手上,身上,还有脸上。真的,她打算今晚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也不想。她狼吞虎咽地吃年夜饭。像小孩一样放爆竹。自己给自己压岁钱。放压岁钱的时候,还说了几句吉祥话。然后坐下来看电视。看赵本山。宋祖英。尽量让自己看得津津有味。本来她很少看这类节目。往年这时候,她正在给爹娘还有两个妹妹打电话,互相问好聊天。现在,她看了看电话机,没理它。他们都已经知道她这里的事情了。她不想带给他们不愉快的想法。她也不想接他们的电话,便把线拔了。爹娘叫她回娘家过年,她没肯。她说你们老糊涂了吗,出了嫁的女儿怎么能回娘家过年呢?看看,她多么深明大义。
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了。看到外面的新鲜太阳,她长吁了一口气。昨晚,她居然没做梦。这很好。村里人认为除夕夜做梦不好。而去年除夕,她就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梦,结果也就很不好。她骨碌爬起来。真的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了。她看了看新鲜的对联,它们就像新年一样充满了希望。她刚把电话线插上,话筒就几乎跳了起来。爹问,佳慧,还好吧,我和娘一直在打你的电话,你两个妹妹也是一样。她忽然说,昨晚,我在莲芝家。
话一出口,她愣了。她怎么会这样说话呢?大年初一,她怎么就跟爹爹撒谎呢?她在莲芝家干什么?难道她能变一个小青给他们?爹又说了一些关心的话,才放下电话,她还在那里发愣。她终于意识到,不管她怎么努力,她还是没法不想那件事的。它已经成了压在她心上的一块大石头。
不行,她还是要去莲芝家看看。她也不管是不是正月初一了。一想起这些,她耳朵里就是莲芝的哭声。昨晚,她把电视开得大大的,不然,莲芝的哭声就会从门缝和窗子里呜呜地钻进来。她拿了两包东西,还有一瓶烧酒,就往他们家去了。村里人开始互相拜年了。小孩子都穿起了花花绿绿的新衣服。然而男人们看到她,并没跟她打招呼。几个平时爱跟她开玩笑的,也故意装作没看到她。好像她是他们需要回避的。不过她也不在乎。因为本来,她也是这么想的。她和德贵,都已经成了村里的罪人和不吉祥的象征。她也就犯不着冒犯别人的忌讳。她走小路到了莲芝家。
莲芝显然对她这么早登门感到意外。她看到莲芝朝她点了点头。她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她恨不得上前抱住莲芝痛哭。他们家一点过年的样子都没有。依然穿着昨天穿的旧衣服。墙上没贴一张新画。甚至门神都没贴。她把东西放在桌上,问,国权哥呢?按道理,要说几句过年的话,可现在怎么说得出口呢?莲芝说,还没起来,从昨天一直躺到现在。她想到房里去探视一下,说几句话,又觉得不方便,就犹豫着站在那里。谁知房间里忽然咚咚响起脚步声,国权衣服也没披,跨出房门对她破口大骂起来,说,你这个丧门星,这么早跑我家来干什么,你还嫌害我们家不够啊!你别假惺惺的黄鼠狼给鸡拜年,我知道你安的什么心思。说完,又气呼呼地回床上去了。
国权的怒骂并没有让她多么难堪。好像她正需要谁的一顿怒骂似的。莲芝怕她尴尬,安慰她说,国权这两天都这样,你别怪,他也骂我,没带好小青。他把我什么都骂遍了。她对莲芝笑了笑,说,我不怪他。
她还是坚持让自己坐下来。不管忍受什么羞辱。她理解国权。她是个读过书的人。她很羡慕电视里那些知书达理、深明大义的女人。她看她们总是看得热泪盈眶。当然也有的女人文化并不高。比如有一个女人,男人遇到了不幸,欠下了一堆债,而这些债她根本不晓得也没有任何凭证,但她还是答应还这些债。嫁给德贵的时候,他们就说好了,要做村里最好的夫妻,最好的人。他们是自己谈的恋爱。当初她爹还不肯,嫌他穷。她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爹。果然,他们没让爹失望。他们成了村子里白手起家最先富起来的年轻夫妻。他们说,我们要做有理想的人,不跟村里素质差的人一般见识。不占小便宜。不搬弄是非。谁有困难就去帮忙。他们发现,做一个好人,是多么愉快的事情。
想到这里,她有些开朗起来。她拉着莲芝的手。莲芝的手割了她一下。她低头一看,见上面有好几个裂开的口子。她说莲芝姐,国权哥的意思我懂。我没有别的意思。到时候,交管部门怎么判,我都认。但我们不要因此成为仇家啊。
莲芝叹了口气,说,你的心意我懂,但我满眼满脑子全是小青。我也晓得,你以前待小青比自己的孩子还亲。你也不用为我们担心,受这样的打击,也不是第一次了,小青那个姐姐,跌到池塘里才五岁。唉,这是老天跟我们家过不去。
她说,那天我看电视,说有个人被车撞了,司机跑了,(你不知道,一看到这样的节目我就心惊肉跳)他断了几根肋骨,肾也被割掉了一个,两年后,查出了尿毒症,要换肾。可他们哪有钱买肾呢,就在亲人里找合适的肾源。他两个哥哥一个妹妹血型不配对,他爹倒是配得上,可年龄大了医院里不敢做。他还有个弟弟也配得上,但脑子有问题,医院里说这样的人也不能。到县里、省里开证明,可医院还是坚持说法律有规定,不肯做。你说这不是命苦的人么?可惜我的血型不对,不然我就给他捐肾去。
莲芝说,我知道,你是好心人,你家德贵也是好心人,不论上街下县,每次在路上碰到我,他都要停下车子,捎我一程。好几次帮我家拉东西都不肯收钱,说是顺路,怪只怪我们命苦,也许我家小青就是这个寿数。
她说,也不能这么说,我家德贵什么都好,就是面子薄,有时候明明不能做的事情,或自己没那个量做的,他也要充好汉。别人叫他喝酒,他就喝。有时候说不定人家是一句客气话,可他都当了真。这次,他要是没喝酒……我早就提醒过他。去年也是这样,人家叫他去喝酒,他真去了,可他到那里,人家都已经动手了,菜都吃得差不多了,光叫他喝酒。这哪是叫他去喝酒,无非是看他开车,想让他送那些客人回家,帮忙送送客我不反对,可不该劝他喝酒对不对?他回来还不敢跟我说,后来我晓得了,狠狠说了他一顿。
莲芝说,唉,男人都这样,爱这个东西,说起来,德贵比我家国权好,他喝醉了酒不是打人就是摔东西,不但打我还打小青,有一次,把小青打得好几天走不了路。刚才,他还跟我念叨这些,可现在,他后悔也迟了。
这时,房间里传来国权的哼哼声。两人沉默下来。过了一会儿,莲芝说,佳慧,不谈这些了。
过年后,交管部门的裁决书下来了。德贵犯交通肇事罪,后果严重,但主动打电话投案认罪态度较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同时附带民事赔偿十万元给受害者家属。这个结果在柳佳慧的预料之中。她把车卖了,加上存款,又向娘家人借了一些,都付给了国权和莲芝。国权对那些钱看都不看一眼。莲芝倒是推托了一下,说,既然小青已经没了,要这些钱又有什么用呢?她说莲芝姐,你要不收下我心里更难受。其实她已经听说国权去县里找了人。其实按道理,德贵判个缓刑也不是不可能的,但国权一心想要德贵坐牢。不过这也是她和德贵应得的下场,相对于小青一条命,十万块钱不多。所以她对国权也没有一丝的不满。她鼓励德贵安心服刑。听说监狱里很乱,她也花钱花东西去找了人,希望他在里面少受些皮肉之苦。
德贵始终眼泪汪汪的。
她还是那句话,对德贵说,钱是人赚的,等你出来,我们再重新开始。
开春了,她开始往田里播种。这些事以前都是德贵做,她顶多在田塍上帮帮忙。现在都只能靠自己了。种田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本来她打算到外面去打工。两个妹妹叫她跟她们一起去,她想了想,还是没答应。她不想离德贵太远,要经常去探望他。她知道,德贵其实是个很脆弱的人,至少,没有她坚强。她要不断地鼓励他。她要把田地弄得跟以前一样生机勃勃,把家里弄得跟以前一样热气腾腾。要是没有热气,就不像个家了。德贵不在家也不要紧,就当他到外头打工去了吧,村子里,这样的人家也不少,男人在外面打工,女人在家里种田地照顾老人带小孩。
一有空,她照样去莲芝家里。帮她做些事。她说到做到,要让两家关系更好,这样才对得起小青。哎,那是个多么水灵灵的女孩子啊。莲芝已经怀了孕。她差不多四十岁了,怀起孕来有些吃力。脸上又重新泛起了雀斑,像细小的蝴蝶一样密密麻麻停歇在那里。莲芝都有些不像莲芝了。她陪莲芝说话。做针线活。互相做好吃的。莲芝想吃酸的,她就到野地里给她摘“酸眯眼”。她们似乎又重新恢复了以前的那种亲密无间。国权从地里回来,有时候也在那里坐坐。依然严肃而沉默。只在喝了几口烧酒之后,脸色才有些松动。
这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不知是在自己家里还是在莲芝家里,国权坐在硬木沙发上不停地摁电视机的遥控。看那沙发,更像在自己家里。奇怪,她怎么会梦见国权在她家里看电视?然后,她又跳到了另一个梦里。这个梦跟她白天看的一个电视节目有关。一个三岁的小孩子浑身都是被指尖掐出的伤痕,孩子的妈妈斥责孩子不听话,后来,她拎起女儿朝墙上摔去,只听一声闷响,孩子跌到地上。这个节目她看哭了。想不到世上还有这样狠心的娘。然而晚上她在梦里重复了那做娘的虐待她女儿的过程。那小女孩像是她的大妹。小时候,大妹长了一头的黄疮,散发出阵阵难闻的气味,娘要她抱大妹她总不愿意,作为报复,她把大妹头上的黄疮一片片剥下来。大妹疼得哇哇大哭。她呲牙咧嘴的,把妹妹剥得不成人样,丢在什么地方,然而大妹又跟了过来,缠住她不放,而且还威胁她要告诉娘,她气得上前拎起她的脚,大妹则伸出手来掐她的脖子。大妹的手忽然长成大人的手,骨节粗突,硌得她脖子很痛。想不到她居然有这么大的力气……
实际上,还真有人掐住她脖子。她很快辨认出来,是国权。他怎么进来的?不知道。然而不知怎么回事,她没有叫喊。叫喊的反而是国权,他说,你男人轧死了我女儿,现在,你赔我!
她不怪国权。要怪就怪德贵。怪她自己。当国权看到她和莲芝依然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坐在一起,不禁大惊失色。他不再敢看她的眼睛。她想,或许,她已经把欠国权和莲芝的债都还上了,她现在不欠别人,只欠小青的。是啊,小青的债,她怕是永远也还不上了。她变得小心了。晚上,要仔细检查门扣。她准备了一把剪刀。只是她还没想好,如果真的再发生那样的事,她是把剪刀对准对方还是自己。
后来的一天,再给莲芝摘“酸眯眼”的时候,她自己也忍不住大嚼起来。酸酸的、红红的汁液沿着嘴角不顾一切地漫出。她有些惊喜又有些麻木地想,说不定小青没有死,她钻到她肚子里来了。她说,小青小青,你的债我是能还清的。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