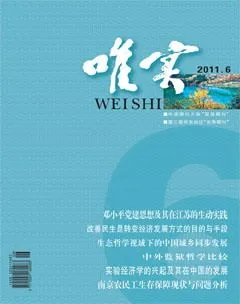农民社会资本的嬗变及其公民身份的塑构
作者简介:岳立涛(1988- ),男,山东临沂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和政治社会学。
摘 要:在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背景下,随着农民流动性的增强,农民的社交关系网络、信任关系和行为规范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社会资本正由内生型逐步嬗变为建构型。这一嬗变过程,培养和激发了农民的自主性、权利意识和公共利益关怀,有助于其公民身份的塑构。
关键词:社会资本;公民身份;嬗变;留守村庄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6-0087-0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亿万农民离土离乡,进城务工经商。以往“视土地为生命”,世世代代在土地上“勤扒苦做”的农民,开始摆脱对土地的依恋情结,相继步入城市,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城市化浪潮之中。由于进城务工经商的收入远高于农民从务农中可以获得的收入,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热情一直很高涨。即便在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背景下,部分地区出现了农民工失业返乡的现象,外出务工的农民数量仍然十分庞大。国家统计局最新监测结果显示,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2.42亿人。其中外出就业1.53亿人,本地非农就业0.89亿人。[1]农民外出务工,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农民步入一个更为开放的环境,接触的人和事更为广泛,这就极大地开阔了其视野,提高了农民的认知和交往能力。从社会资本角度讲,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更是对农民社交关系网络的破解与重构。社会学家已经发现,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农民的流动,传统的家庭和家庭派生出的邻里、社区等最终会趋向衰落,旧有的社会网络、共识性规范和信任关系会因此告于消解。[2]伴随农民生产、生活和交往环境的改变,农民与生俱来的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社会资本正发生着某种嬗变,这种嬗变反过来又将对农民自身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农民社会资本的嬗变
“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关系网络等。本文选择以留守村庄X为例,通过该村呈现出的一些具体特征来展现当前我国农民社会资本嬗变的具体过程。X村位于山东省南部山区的L市,是一个典型的内陆山村,村庄占地面积1.2平方公里,村民513人,143户(截至2010年)。长期以来,村民以种植花生、地瓜和小麦为主,金银花是该村主要的收入来源。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准来看,X村属于相对落后的村庄。截至2000年,该村常年在外打工的有53人,占村民总人口的10.6%,其他村民大都以种地和饲养牲畜为生。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城乡企业的快速发展,村里的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据初步统计,2010年该村外出务工人员将近300人,占村民总人数的58.5%,其中,夫妻双方均常年在外打工的有近80户。显然,X村是受社会转型特别是外出务工经商浪潮影响颇为显著的村庄。笔者根据在X村的调查研究发现,该村村民的社会资本正由内生型逐步向建构型嬗变。
随着农民“人情”理性的萎靡,农民的“亲邻圈”呈全面收缩态势,代之而起的是建立在合作共事基础上的社会化关系网络。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这个熟人社会的特性,一是地理位置,通常表现为邻里关系;二是建立在血缘和姻缘基础上的亲属,通常表现为亲戚关系。亲邻关系特别是邻里关系是农民独具特色的社会资本。古话“远亲不如近邻”,可以看出邻里关系在传统农民心目中的地位。但是,随着农民流动性的增强,农民传统的人情理性正日趋淡薄。如今,农民的“亲邻圈”逐渐收缩,而以合作共事为基础的新型社交关系网络正不断凸显。
案例一:孙某,男,43岁,自2005年以来常年与妻子在外地打工。据孙某介绍,因为常年难见一面,他与邻居的关系疏远了很多,逢年过节碰到一起,大家不再像以前那样无所不谈,更多的是一些礼节性的寒暄。孙某特别提到,邻里之间“串门”的现象如今越来越少。务工农民回乡后,大都倾向于待在家中看看电视或者收拾一下家务,整理一下庭院,极少外出。“以前过年的时候,村里的大街上非常热闹,到处簇拥着人群,如今这条街整日冷冷清清,只有来往的行人匆匆而过。”另外,由于长期在外打工,家里只有年迈的老人和不经事的孩子,一旦亲戚家有红白喜事,对于远一点的亲戚,孙某则选择故作不知搪塞过去,稍近一点的亲戚,则托人送点钱过去,表表心意,只有非常近的亲戚,孙某才会请假亲自参加。查看孙某的家庭支出账簿,自从外出打工以来,孙某的人情支出项目减少了将近一半,虽然每一份的份额有所增长,但是走动的亲戚越来越少。如今,与孙某保持走动的只是非常近或者关系非常好的亲戚。与亲邻之间日趋淡薄的关系相反,孙某与外界的交往却越来越多,现在孙某逢年过节花在老板、厂长、同事及“拜把兄弟”身上的钱已远远超出在亲戚邻居方面的花销。据孙某讲,“大家都在一起共事,难免会有相互需要的时候,现在多花点钱也是为了以后的路更好走一些。”
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的传统民间信任关系逐步消溶,契约型信任脱颖而出。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大家世世代代累居于同一地域,形成了亲密无间的“熟人关系”,在这种“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常常建立在习俗和民间信仰的基础之上。随着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数量持续上涨,农民越来越多地与外界形成生产合作和人际关系网络,这就失去了传统民间信任的关系根基。为更好地减少市场经济交往活动中的欺诈、排斥等行为,增强行动的可预测性,降低信任的风险性,以契约为基础的信任关系逐渐得到农民的亲赖。
案例二:杨某,男,48岁,是村里外出打工较早的村民之一。谈及信任时,杨某告诉笔者,“现在,亲兄弟也不如‘白纸黑字’可信,这几年在外打工,目睹了很多亲兄弟反目成仇的例子。在金钱面前,什么亲情、友情,都经不起折腾。有了‘白纸黑字’的凭据,私下解决不了,可以请法院帮助。法院办案什么都得讲证据。‘白纸黑字’就是最好的证据。”杨某拿出一张与堂弟签订的借款合同,上面有双方的签字和手印。据杨某反映,现在这种现象在X村十分普遍,村民都感觉口说无凭,有了书面的凭据心里才会踏实。除了这张书面的借款合同之外,笔者在杨某家的墙壁上看到“XX借果皮93公斤”字样,杨某随后告诉笔者,这是姐夫家借果皮的凭据,是姐夫亲自写下的。“以前借粮的时候因为不作记录,时间久了却忘记了具体的重量,或是双方记忆的重量存在偏差,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在比较显眼的地方做一下记录是非常必要的,这种记录一般都是由借粮方亲自书写或找第三方代写。”这些所谓的“合同”或“凭据”虽不十分规范,却反映了农民信任关系的巨大变迁。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信任关系在农村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传统的民间信任正日渐消溶。
情感趋向型行为规范日益消沉,以功利性为主导的行为规范逐步占据核心位置。伴随着传统亲邻关系和信任关系的销蚀,农民再也无法直接从以往社会资本那里得到有效保护与荫庇,他们开始感到一种社会资本缺失后的孤立无援,面对现实生活无时无刻不隐藏着对于互助的需要,孤立的农户不得不重新去编织新的“关系网”。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以情感为纽带的乡村人际关系逐渐向利益化趋势发展,农民的行为规范中,“个人利益本位凸显,使经济理性取代生存理性和传统亲情而成为人们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准则,纯朴的乡风也逐渐被功利的算计取代”[5]。
案例三:张某,男,57岁,两个儿子常年在外打工,女儿和女婿也在外地经商。张某见村里承包土地比较便宜,每年都与妻子承包六亩左右的田地。笔者问张某两位老人如何能耕种这么多土地。张某告诉笔者,年龄较高的农民外出打工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无奈只能在家多种点田地。每年农忙季节,夫妻两人肯定忙不过来,儿子和女儿又都在外打工很少请假回家,请邻居帮忙更是不好意思开口。现在,每家每户都在忙着赚钱,以往亲邻之间的义务性帮助几乎销声匿迹了。这种情况下,家里承包土地比较多的农户只能花钱雇佣帮工,帮工不一定是自己村上的村民,也可能是邻近村庄的村民。谈及雇佣帮工问题,张某感慨道:“以前农忙季节,亲戚邻居都会出手相助,而且这种帮助都是无偿的,根本不用发工资,顶多请到家里吃顿饭。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人们却把钱看得越来越重要,如今做什么都得花钱,没钱谁会理你!”雇佣帮工在X村已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当前农村生产关系的变动,更是农民行为规范由情感趋向型转变为以功利性为主导的生动说明。
个案调查虽具有特殊性,但从中也可见一斑。村庄作为农村社会的缩影,个案的解剖无疑将有助于对整体的解说。受交往环境和社交人群变动的影响,农民的社会资本存量中,基于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内生型社会资本所占的比重日益减少,通过合作共事,以契约信任为纽带的建构型社会资本正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趋势在大部分留守村庄乃至整个农村社会正初现端倪。
二、社会资本嬗变对农民公民身份的塑构
当前,农民社会资本的嬗变培养和激发了农民的自主性、权利意识和公共利益关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塑构农民公民身份的作用。
内生型社会资本对农民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情感慰藉和生活救济两个方面。农民一旦在生活中身陷囹圄,自然地会从内生型社会资本网络中得到帮助。所谓“守望相助、邻里相携”,在中国乡村熟人社会中,人情因素只是正常生活的需要,对于财富的增长和个人的发展并没有多少作用。内生型社会资本成为农民在遭受国家和社会剥夺后弥补心理落差的良药,这恰恰滋生了农民的“惰性”心理,泯灭了农民的自主性和权利意识。同时,内生型社会资本往往体现出特殊主义的封闭倾向。正如马克思在论述法国小农时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8]这种封闭性成为现代农民形成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阻碍因素。可见,在中国乡村社会中,内生kpXe+jQ8AD/LjkXCOxKDcQGCKS/h+n4/bTwTIoD1pys=型社会资本主要是作为一种村民互助的民间资源,它并未发展出能够明显地影响村庄公共生活的能力。[9]
建构型社会资本建立在农民合作共事的基础上,本身就以相互利用、合作或竞争为动因。关系网络中的个体都期望通过这种社会资本获取更多的资源回报,每个个体都是十分活跃的。同时,由于建构型社会资本的特殊成因,它时刻强化着人们的利益关怀,这种利益关怀不仅局限于私人利益领域,而且激发着农民对公共利益的关注。长期生活在这种社会资本网络中,更能培养个体的自主性、自觉性和公共理性,而这些正是农民获取公民身份必备的特质。随着流动性的增强,农民接触到的人和事更为广泛,农民不断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也是丰富个人知识、增强个人能力的过程。农民的交往范围不断扩展,看到很多从来没见过的新鲜事物,通过对比发现很多现实问题,而且,在建构型关系网络中交谈的内容也不再以“家常”为主,很多农民开始关心村务甚至国家大事。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好学”理性促使其权利意识不断提升。
案例四:村民刘某,男,48岁。为缓解孩子上大学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从2005年起刘某常年在外地打工,只是逢年过节时候才会请假回家。家中只有妻子照看两位年迈的老人,同时经营着全家的三亩三分田地。由于村里农户家的水表大都被冻坏,而且更换成本较高,村里水费转而实行人头制,每人每月5元。尽管刘某及其儿子常年在外地,极少回家,但村里还是照收水费。刘某多次找村主任协商未果。2007年,刘某来到镇政府请镇领导为他做主。在镇领导出面干预下,村里最后决定每年只收取刘某及其儿子两个月的水费。事后,刘某感慨道:“其实村里有很多这种现象。以前,因为大家都不出面,自己也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不一样了,从这几年在外打工的经历中我开始认识到,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随大溜只会让自己吃哑巴亏,自己的利益还得自己争取。”
案例五:X村村内主干街道一直是土路,每逢下雨天便泥泞不堪,村民怨声连连。由于村里集体收入微薄,村委会一直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修整。2009年,村委会决定号召村内比较殷实的家庭捐款修路,捐款者姓名将雕刻在村头的功德碑上。在村委会的动员下,全村共筹集资金3万元,修建村内街道已是绰绰有余。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在筹集资金后第二天,村内捐款者纷纷向村委会提出要求:村委会应当将3万元资金的使用明细对村民公布。一位村民告诉笔者,“钱是大家出的,我们有权利知道这些钱是怎么花的”。在村民的多次要求下,村委会对村民做出了满意的答复,捐款的每一笔花销都在村务公开栏上公示,从而保障了村民的知情权。接受笔者调查的李某坦言,村务公开本是上级政府的要求,监督村委会的活动也是村民的权利,村民有权了解公共资产的使用情况,外地很多农村都是这样做的。
案例六:X村一面靠山,两面环水,只有村西头的公路与外界相连,成为村民外出的必经之路。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邻村新开了一家沙场,村西头的公路上来往的大型车辆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大型车辆不仅增加了交通事故的数量,而且使整条公路面目全非,原来平坦宽阔的公路变得颠簸不平。村民纷纷向村委会反映,要求限制来往车辆的载重量,但是村委会迫于种种考虑一直没有采取措施。2009年4月,一批村民自发在公路上设置路障阻截来往大型车辆,甚至与沙场发生群体冲突。这一事件惊动了县政府,在县领导的协商下,沙场承诺为村民修复路面。村民张某告诉笔者,村头公路关系到每位村民的切身利益,大家在公路上阻截车辆纯粹是自发性行为。跟村民的公共利益过不去,自然也就是跟每一个村民过不去。
以上三个个案也许不具备统计学上的覆盖性,但若作类型学的关照,却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农民社会资本嬗变在塑造现代农民公民身份过程中的具体影响。
由内生型社会资本向建构型社会资本的嬗变是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社会资本变迁的必然趋势,但这种嬗变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不彻底的。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社会资本可能会因为农村邻里关系的淡化而消逝,但是,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只会是筛选式的缩减。甚至有研究者发现,“随着农村经济改革和现代化的发展,作为传统的重要因子的家族势力却重新复兴起来”[10]。就目前整个中国农村社会来看,内生型社会资本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只是在部分留守村庄中,因为农民流动性的瞬间加剧和社交面的突然拓宽,内生型社会资本的根基开始动摇。
内生型社会资本对于塑造现代农民的公民身份并没有太大意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负面的影响。农民社会资本的嬗变不仅塑造了农民的公民身份,而且是对乡村社会传统的“扬弃”,标志着传统乡村社会开始走出封闭的场域,逐步融入整个社会的风云变幻之中。农民社会资本的嬗变是农民现代化以及农村现代化的必然环节。“现代化的本质是社会变化,是打破传统的各种程序,即破坏原有的社会稳定,但是社会的稳定又是现代化的保障,可以说,没有社会的稳定就没有现代化。”[11]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即如何才能实现农民社会资本嬗变和农村现代化的有效对接?为此,要尽量实现;要避免农户社会资本嬗变不均衡引起的资源占有上的不公平,以免在乡村引起新的两极分化;要时刻提防建构型社会资本中功利性因素的过分张扬,避免农民群体的道德沦丧。同时,国家要“加强制度上的强化、约束和指导,运用制度的力量逐步引导农民把理性思维和现代意识转化为他们的‘新认同’”[10]。□
参考文献:
[1]徐博.统计局:2010年内地农民工总数达2.42亿人[EB/OL].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02/12/4641191_0.shtml.2011-02-12/2011-03-27.
[2]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721.
[3]希特.何谓公民身份[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7.
[4]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C]//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吴毅.亲缘网络[J].开放时代,2002(1).
[6]李明照.现代化视野下村落家族势力的复兴:寄生性的再生长[J].社会科学辑刊,1999(2).
[7]布莱克.比较现代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黄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