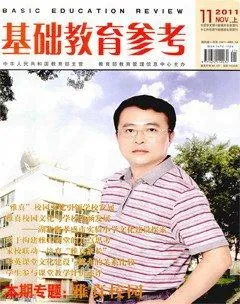教
不要总是自以为是地面对学生,不要总是一厢情愿地想改变一个人,最好的办法是改变自己,然后再去一点一点地影响他们。既然改变不了现实,那么,对于让自己头疼的学生,从改变自己出发,让讨厌变为喜欢,这也是一种快乐之道。
学生丁宝,是一个天性比较聪明的孩子。初一的上学期曾经考过班级的第一名,但是,由于行为习惯的问题,他再也没能重现昔日的辉煌。他在课堂上的“非常规”表现,在我多次宽容地提醒、课堂上的表扬激励和友善地帮助式谈话之下,始终没有多大的改观。
有一次,丁宝上课东张西望、做小动作等“非常规”行为频发,我不得不找他好好谈谈。他上课一直不听老师讲,书也不拿出来,督促之下才极不情愿地把书放在课桌上。依然是一人偷偷地玩,一副课堂旁观者的样子。对于他,只是用眼神提醒他多次,也不点名地旁敲侧击地警告;但是,他还是我行我素,我不想浪费宝贵的教学时间,也不需要为他一人而暂停讲课,也就不管他。后来,我请他到办公室,让他坐着与我自由的对话和交流,他似乎很懂事。对话和交流式教育,在他心中也许视为一种软弱。只是隔靴搔痒,只治标不治本。
我的宽容式教育可能是放纵了他。但是,这一次上课,一直无所事事的他,竟然得寸进尺,开始发出声响,先是用凳子发出几声,我继续不管。我不能够因为他一人而让绝大多数学生的学习受到影响。他又接着用矿泉水瓶发出声音,吸引了少部分人的注意。这时,我不得不请他到教室外面去。因为我与学生有约定:“如果觉得坐在教室不舒服,可以以做小动作、影响其他同学学习,或者是扰乱课堂纪律为由,提出到教室外去的申请。”这是我对不想学且影响其他人学习的学生的一个约定,也是让这些不想学好而表现自己的学生一个台阶。我不想粗暴地对待学生,在多次教育无效的情况下,我尊重学生的选择,满足他到教室外呼吸新鲜空气的愿望。
他很得意地走出教室。到了教室外的他得意洋洋地在教室的前门和后门来回走,像是在表演,一个小丑的表演,其他人见了之后,一个个不停地看我。我不被他的淘气所“激怒”,而是以生活生产中的知识运用来继续我的讲课,多数人还是被我的复习吸引住。来回走了几趟自觉无聊的他,没有舞台和观众的他,无趣地去了一趟厕所。他的表演他的捣蛋,并没有干扰我的讲课。因为教学任务没有完成的我全当他不存在,根本没有把他当回事,给他来个冷处理。
下课后,我让他到我办公室来,他没有来。老师的话,在他心中没有多大的分量了。我找他也只是想帮助他,希望他能够正确看待自己,能够改掉一些坏习惯。但是,这仅仅是我的一厢情愿,他不接受。我在办公室等他,见他迟迟不来,我就到教室请他。他一见到我,赶紧从后门溜出教室往厕所方向跑,我苦笑不得,拿他没办法。我跟在他后面上了趟厕所,然后准备下班回家。他也从二楼又转回了教室。在他看来,好像是逞能了,好像是胜利了,也许是在同学面前逞了威风。而我心痛地感到他的愚蠢和无知,甚至渐渐对“狗咬吕洞宾”的他感到十分地厌恶。
我心里很想说他愚蠢:是他不知道做人的道理,不知道“求师拜学”之道,更不知道“求学”的学子之“求”字。不知道“求”字的含义,反而以为老师“求”他学习;他的愚蠢还在于他不接受我的帮助,不知好歹地逃避。说他无知,他以为自己小丑般的行为而骄傲,在其他同学和老师眼中,他以自己的行为给自己标注好坏的类型。也许,他还会在其他同学面前炫耀他与我玩“捉迷藏”的游戏;也许,他以为他玩弄了老师。这是将自己的愚昧当聪明的无知啊!这是他的“本末倒置”的学习观。这是我的真实的心理。但是,我转念一想,我比他父亲的岁数还大得多,就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看待吧,不再计较他的“淘气”和“顽皮”。
但是,回到办公室,我很想知道他的家教如何?他的行为习惯是否与家教有关。其实,前几次的交谈,我已经知道一些,他说他父母不太管他,后来,又听班主任说他父亲根本不接老师的电话。
找到他的班主任,我跟班主任要了他家长的电话,班主任拨通了他母亲的电话,他母亲听完后的意思只是说:“他不听话,可以打,送进来就是接受教育的,进了学校就是你们老师的事。为什么总是要麻烦我们家长啊!”当时,我说:“我们不是不教育他,而是正在帮助他。但是,教师的教育并不是万能的啊!”接着,我把他的一些行为向她说明。他母亲就是一个劲地说:“不能够把教育的事推给家长。”教育孩子,不仅仅是教师的事,也要家长配合,共同发力。在这个平时不关心孩子心理的家长面前,我只能切准她的软肋,对她母亲说:“这样的学生,不是我们学校施教学区的学生,是你们通过关系找人转学来的。我一定积极要求学校对这样屡教不改的学生按校纪处理,要求他转回自己的所在的施教区就读。”这时,她母亲无话可说了。有时候,求助家长对教师来说,也是一种无奈,或一种无能。对于一些屡教不改的学生,一定要给点威慑,要让他们有畏惧感,这样,对自己的言行才有责任感。
回家之后。我渐渐地坦然了。原先心里有点“火苗”的我,不想对他发怒。事后,我冷静地思考:为什么我要管他?为什么我要积极地帮助他呢?小学科任老师也想开展思想教育?作为业余作家的我,主要是想要看看学生的心理,只是不想他不学好,只是不想他自暴自弃,把自己转变成“问题学生”。而他和他父母却不领情。这也是我从教以来第一次遇到如此不接受教师帮助的家长。当然,我也有错,错在我不该帮助他,错在我违反了将学生的“求学”责任淡化,而是将教师的职责视为“求——教”,求学生“学”,求学生“被教”。错在提醒他多次之后,他仍不知错就改之后。我就不该把他当做积极上进的学生看待,不该把他当一回事,而是应该多一些等待,多一些宽容,多一些鼓励。尽管他是一个不需要靠表扬来教育的孩子,这是一个能够洞穿老师心理的学生。但是,他终归会渐渐地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不过,这次,他错了,错在太聪明了,太自以为是了,错在反客为主,把学习当做是老师和家长“求”他学。
几天后,又到了上他班的课了,他还在教室。我没有继续找他谈话,或训斥他。对于他,我不想过多地指责和敌对,只是提醒全班同学注意:上课时不要影响其他人学习,不要做损害班级名誉的事,不要做老师和多数学生不欢迎的“害群之马”式的人物。我继续我的教学,对他,我不再追究他的无知,我不需要在他身上花费太多的精力,不想一厢情愿地强按牛头喝水,怕他“给点阳光就灿烂”,怕给他一点“颜色”,他就“动漫”。冷处理有时也是一种帮助。这一节课上,他的表现有所好转。对于他这样比较聪明的学生,一些高高在上的说教,一些旁敲侧击的教育,一些有意无意的鼓励和帮助,是不起作用的。我只有采取“冷处理”的慢艺术等待他的自醒。以欣赏的心态来等待他的自觉。
在接下来与他相处时,我还是回到我教育的原点,从他的写作特长人手,让他写“学生小老师”的点评,在小老师上完课后的下课前几分钟点评。他对这项任务很重视,写得非常出彩。他的“出彩”是课堂的“亮点”,也是学生最开心的时刻。对于他的“噱头”式表达语言,我又建议他将本节课的重点和难点的知识穿插其间。这难不倒他。他依然写得很带劲。这会不会影响他的正常学习呢?不。这反而促进了他的学习,他要认真听小老师讲解啊。不让他写的时候,他总是要制造点“动作”来吸引我或者是其他同学的注意。与其这样,还不如让他写。
如果你想要快乐,换个角度思维,也许宽恕和等待,也是一种快乐之道。你只有在放弃了批判和怨恨之后,才有可能体会快乐和欢愉。如果你无法宽恕,惟一一个痛苦的人会是你自己。改变一厢情愿,放弃自以为是,也许,世界就为我们打开另一扇门。对他,对学生,我还应该是多一些宽容,多一些等待,不能够急躁地想“立竿见影”,多找一些学生的优点并在其中找到教育的契机。
教育,本身就是一门生产快乐的艺术,就是发现快乐、体验快乐的过程。发怒,是一种教育的失败,是自我贬低。别拿学生的错误贬低自己,宽容和等待,也许是最好的帮助,也是一种成功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