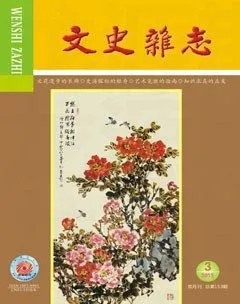才名与骂名
甲申(1644)变起,爱新觉罗·福临称帝于北京,强悍的清兵随即向南推进,汉臣死节的死节,迎降的迎降。其欲死未死而终至变节降清的一个,便是钱谦益。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江苏常熟人。他文才出众,是“江左三大家”之一;又曾参与东林党人反对阉党,而被视为士林领袖。如此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却在国亡家破之际贪生怕死,贻笑后世。其先,他的爱妾柳如是郑重地劝他以身殉国,他也表示同意,且大张旗鼓地声言欲效法屈原,投水自尽。可当其载酒湖上时,又临时变了主意,从日上三竿磨蹭到夕阳西下,终究没完成最后一跳。他为自己找的一条无法赴死的理由,竟是“水太凉了”!
接下来的一件事是剃头。史惇《恸馀杂记》载:
豫王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忽曰:“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则髡辫而入矣!
据说钱谦益降清后,穿的是经改造的清朝官服,这种官服是没有领子而有阔大袖子的样式。无领以示顺清,阔袖以示怀明,顺清怀明却不清不明,人乃讥其为“两朝领袖”。
由于这个“两朝领袖”大节有亏,故人人得而欺之。据说有一天他穿着满洲官服出门,路上遇到一位老人,看他顶戴花翎,便拿拐杖敲他的脑袋说:“我是个多愁多病身,打你这倾国倾城帽。”又,孙静庵《栖霞阁野乘》谓:
清初黄叶道入潘班,尝与一林下巨公连坐,屡呼巨公为兄。巨公怒且笑曰:“老夫今七十余矣。”时潘已被酒,昂首曰:“兄前朝年岁,当与前朝人序齿,不应阑入本朝。若本朝年岁,则仆以顺治二年生,兄以顺治元年降清(笔者按:钱氏降清实在顺治二年,时为南京弘光政权礼部尚书),仅差十余月耳。唐诗云:‘与君行年较一岁’;称兄自是古礼,君何过责也?”
不仅老者打,少者讥,连文人们也丝毫不给他面子。王应奎《柳南随笔续笔》载:
金是瀛,字天石,居华亭之皋桥,自少以诗文名。国初与同里吴骐、王光承并以隐逸徵,不起,时论高之。是时松郡人文最盛,奉吾邑某宗伯为盟主,而宗伯亦屡至其地。一日,舟次白龙潭,诸名士方群趋迓之,天石忽投一诗云:
画舫沧江载酒行,山川满目不胜情。
朝元一闭千官散,无复尚书旧履声。
宗伯得诗默然,即日解维去。
文中的“巨公”和“某宗伯”,徐珂《清稗类钞》直接说是钱牧斋。钱牧斋屈膝不久,江南一带即流传着这样一首诗:
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
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
诗载于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该书还说钱谦益见到这首诗后,数日内很不高兴。他不高兴别人戳脊梁骨,别人却恨他没有脊梁骨。钱泳《履园丛话》评论说:“虞山钱受翁,才名满天下,而所欠惟一死,遂至骂名千载。”其实,钱谦益入仕清朝时间很短——仅做了半年的礼部侍郎,便告假回原籍。以后,钱氏还秘密为反清复明做了许多工作,以66岁高龄被清兵逮捕,坐了40天大牢,幸得柳如是营救,方才死里逃生。对此,乾隆帝当然有所闻而愤恨其假投降,遂诏令史馆把钱氏列入《贰臣传》乙编,称他根本不能与同属“贰臣”的洪承畴相提并论。乾隆帝还写诗挖苦这位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所谓文坛领袖:
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
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
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
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