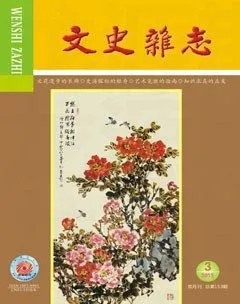廖平对医学古籍整理的贡献
廖平(1851—1932),字季平,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人,是清末民初著名的经学大师、思想家。廖平先生的经学思想主要在于“今古文经学之辨”。廖平先生主张今文经学《王制》为孔子之学;古文经学《周礼》为刘歆之学,即古文经《周礼》出于王莽之时,有许多人认为是刘歆迎合王莽之意而伪作。廖平先生的经学思想曾经对清末光绪年间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康有为曾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批评、否定汉儒以来的旧经学为名,实为提倡变法维新而张本,在清季振聋发聩,轰动一时。当时有识者皆谓:尽管康有为之书与廖平之著作有本质不同,但康有为之书是受廖平之书启发而成。廖平先生后来又培养了经学大师蒙文通先生,为弘扬几千年来传承的中华文化不遗余力,是中国文化史上彪炳千秋的著名人物,被尊称为国学大师。
但不为人所周知的是,廖平先生不仅是经学大师,又是一个在祖国医学古籍整理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医学大家。廖平先生一生著述近一百四十部,凭借他对中国古代典籍深厚钻研的功力,除经学著作外,晚年兼及医学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曾辑评中医古籍二十余种,以《六译馆医学丛书》刊行于世,约数百万字,裨益于当世及后代学人。六译馆,是廖平先生晚年的书斋之名。廖平先生早年号“四译”,晚年更号为六译;之所以称“六译”,即有译书辑述之意。《六译馆医学丛书》中所辑多是唐代以前的珍稀医学古籍。廖平先生不仅校勘精详,而且对唐宋以来的医学大家的研究工作进行了详加评述,考订源流,辩章学术,尤其是对脉学、《伤寒论》的研究,发前人所未尽阐,见解独到,影响深远。他从古典文献学的角度所做出的贡献略胜于明清以来诸医家对《伤寒论》的研究。廖平先生整理医学典籍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伤寒杂病论古本》[1]一书中。现以该书为主,略谈廖平先生的贡献。
廖平先生对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中所叹“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这一桩公案的考证,厘清了自宋以后数百年来的“《伤寒论》唐初已亡佚”的误解及以讹传讹。唐初孙思邈编撰《千金要方》时,流传下来的《伤寒论》已经不是全貌。据说孙思邈能见到的只是其零星的条文与方剂,所以他才在书中感慨“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而引以为憾。宋代以来的医家还据这十余字断章取义地认为:孙思邈当时撰《千金方》时,《伤寒论》已经亡佚了,所以孙思邈看不到《伤寒论》。廖平先生却以他钻研古籍文献的功力,认为从《千金要方》中这句话的前后文来看,并不能确定这里的“仲景要方”究竟指代的是什么,“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这句话有歧义:“要方”既可能指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中的方剂,也可能是指张仲景所创制的治伤寒的“秘方”。廖平先生判断“要方”是秘方的可能性更大,并从古代医籍中考证出“要方”是治疗伤寒初期的摩膏、散、丸等药方。[2]由于江南的医师珍视这些药方而不传于后人,这些药方就从流传到唐代的《伤寒论》中脱失了;但在一些同时代的医方著作中仍可见,如在流传于日本的《医门方》、《医心方》中,流传于宋代的《小品方》中可见到。
廖平先生对《伤寒论》古本原貌的考证,主要是据传世的《诸病源候论》、《外台秘要》、《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医门方》等存世文献而进行的,没有看到出土文献,如敦煌文献中所保存的唐宋医学典籍。虽然如此,廖平先生对《伤寒论》唐前古本原貌的考证结论,仍然有信服力。如他认为汉代的《伤寒论》流传到唐代,就已经被分成《伤寒》与《金匮》两部分了,前者论治伤寒,后者论治杂病。汉代张仲景《伤寒论》的原貌体例是:先论述治疗伤寒病的总法则,即先养生预防(“不治已病治未病”思想),伤寒初期用摩膏、散、丸等轻剂发汗驱寒,至伤寒重期不得已,才用汤剂,用汗、吐、泄下的方法驱除病邪。其次,论治具体病证在前,最后将药方(剂)单独列于书后。这与宋本《伤寒论》将论治与方剂的内容编排在一起的体例明显不同,显然是《伤寒论》在流传过程中被重新编排的结果。廖平提出了汉代《伤寒论》原貌“方证不同条”的见识,要比后来的学者提出同类的观点要早很多。颇为有趣的是,廖平先生以《春秋》三传(指《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本出一源,传本各异”的例子,指出《伤寒论》自东汉以后流传,由于其“论治”与“药方”各成体系的编排特点,必然导致《伤寒论》分《伤寒》与《杂病》(即方剂)流传的命运。因此,无论是晋代王叔和在《脉经》中的整理,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的引用,还是唐代王焘《外台秘要》中的搜集、孙思邈的前后二次搜集、编撰,有关《伤寒论》的内容却都是总源于汉代《伤寒论》;只不过在具体次序上或有不同,这恰恰反映了《伤寒论》在流传、传抄过程中的版本歧化。这种举一反三、庖丁解牛般地游走于经学与医学之间的认识,显示了廖平先生雄厚的国学功底。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廖平先生有生之年未曾见到过敦煌文献中的材料,但在廖平先生去世后五六十年中,随着中外敦煌学家对敦煌文献中的医学材料的研究发现,却验证了廖平先生对《伤寒论》古本以上考证结论的说服力与可信性。如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医学卷子P.3287,内容正是唐代前期抄写的流传于唐代的《伤寒论》的治疗总则《伤寒例》。卷子原文中有“神丹安可误发,甘遂何可妄攻也”[3],指伤寒病多由表中风寒始,后渐入里,故治法是先解其表,后乃下之。“神丹”是发汗的轻剂,“甘遂”是攻下的猛剂,如伤寒已入里,造成阴虚阳盛的真热假寒之证时,用发汗的丸剂“神丹丸”就是药不对证。因为神丹丸只是治疗在伤寒初期中表后恶寒、发热、体痛时所用,以温阳散寒,发计解表。此卷子中的“神丹”在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正写作“神丹丸”,证明抄写于唐初的敦煌卷子与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的《伤寒论》内容是同源的,证明《伤寒论》在唐代并未亡佚,而是仍旧被大量传抄、流传,且能从中原内地传播至边疆一隅的敦煌,表明《伤寒论》的传本不少。又如敦煌残写本《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也是唐前期的写本,内容是从南北朝时期名医陶弘景的著作中摘录的方剂,其中的数十首方剂与《伤寒论》中的医方相同或十分相似,但也有方名、主病等不同之处。这二者的相似性反映了二者同源于西汉的《汤液经法》,表明东汉张仲景著《伤寒论》时是创造性地运用过《汤液经法》中的药方;差异性则反映了《伤寒论》在魏晋南北朝流传期间,随着环境、气候的变化,疾病病证的新变化,后世医学家对《伤寒论》方剂有所改造,以适应医疗实际的需要。这也就证实了廖平先生认为《伤寒论》在流传、传抄过程中版本出现歧化的“本出一源,传本各异”推论的正确性。
注释:
[1]廖平:《伤寒杂病论古本》,成都存古书局,1919年。
[2]王使臻:《廖平对〈伤寒论〉唐古本的文献研究》,《中华医学实践杂志》,2003年。
[3]李应存:《实用敦煌医学》,甘肃科技出版社,2007年。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