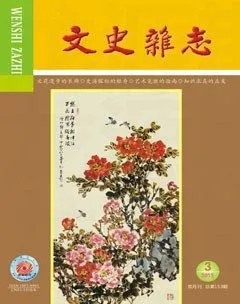“春风送暖入屠苏”的“屠苏”作何解
作家李国文先生极为推崇北宋文学大家王安石的一首小诗《元日》,认为是春节应景诗中的“魁首之作”。李国文先生写道:“假如你也置身其中,那爆竹的噼啪响声,那屠苏的沁人芳香,那日光的炫目亮度,那春风的无比温馨,给你以听觉、嗅觉、视觉、触觉的全面冲击。”(《联谊报》,2009年11月28日)。显然,李国文先生把这里的“屠苏”译作香喷喷的“美酒”了。然而,天气暖和了要喝酒吗?尤其是在江南,这不通啊!那么,“屠苏”究竟所指为何?“春风送暖入屠苏”的“屠苏”应该如何翻译方才符合作者原意?
王安石的《元日》,虽为小诗一首,却像一幅北宋江南民间的生活风俗画,如实描绘了当时的新年风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是江西临川籍。临川为古越地,风俗质朴。王入仕后,在苏浙一带做过地方官,而他在江宁和苏南等地生活游历的时间最长,将近三十年之久。所以,《元日》小诗就是江南民间生活习俗的现场记录。但王安石作诗喜欢用古。他在这首小诗中,不仅描述了除夕之夜当地民间纷纷以新换旧“悬挂桃符”的古老习俗,还用了“屠苏”这一古意深奥的词汇。对于诗中的“屠苏”,今天很多注家(包括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著者)都将之解释为“美酒”、“一种酒类”,想象着它是“美酒飘香”。但我们无论如何读这首《元日》,都难以读出其中有“喝酒”、“饮醪”的意味。那么,这首《元日》里的“屠苏”是指什么呢?
其实,“屠苏”是远古时代的语言遗留,“屠”为古越音记音字,发音类舒。“屠苏”当为荼(原始茶)的一种古老的称呼,故其有花草之意。北周王褒《日出东南隅行》:“飞甍雕翡翠,绣桷画屠苏。”此为花草。梁刘孝威《给客少年场行》:“插腰铜匕首,障日锦涂苏。”此为遮阳草帽。“屠苏”还有“草舍”之意,汉服虔《通俗文》曰:“屋平曰屠苏。”三国魏张揖《广雅·释宫》:“屠苏,庵也。”北宋《广韵》:“屠苏,草庵也。”
“屠苏”确实又有“酒”的意思,它是先从“原始茶”和“原始汤药”演变发展而来的。明代焦竑《焦氏笔乘续集》:“山东一家,五百口共爨二百余年,不染疫疠。其家每年收苦草,日一束,阴干,至冬至日为末,正旦五更密调之,每人服一匙,即古屠苏之义。”这里,由“苦草”做成的“屠苏”,表面上是药汤,其实正是“原始茶”。唐代陆羽撰《茶经》,其中记载:“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案:即硬干酪),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荼苏而已。”此处“荼苏”为记音词,可写作“屠苏”。“荼”写为“屠”,古已有例,南宋罗泌《路史》载:“子姓有荼氏,即屠。”这里的“荼”、“屠”均为古越音,发音与舒相类似。
所以,“屠苏”先是“原始茶”(即可食可用的花苞、芽叶、草根等,后又引申为可居可住的草舍),再为“原始汤药”,最后又变成了可饮用的药酒。北宋《太平御览》记:“元日服桃汤。桃者,五木之精,厌伏邪气,制百鬼。今人进屠苏酒、胶牙饧,盖其遗事也。”可知,这里的“屠苏酒”是“桃汤”类药酒。
由于“屠苏”既有草舍之意,又有汤药及饮料之意,但时过境迁,后来的人渐渐搞不明白了,于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释便硬凑出来了。唐代韩谔《岁华纪丽·元日》“进屠苏”注:“俗说屠苏乃草庵之名。昔有人居草庵之中,每岁除夜,遗闾里一药贴,含囊进井中,至元日取水,置于酒樽,合家饮之,不病瘟疫。今人得其方而不知其人姓名,但曰‘屠苏’而已。”唐人“已不知其人姓名”,可后来竟有谋利的药商“考证”出“其人”是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是他发明了“屠苏”这剂独特的配方;说除夕之时,他给邻居一包用大黄、白术、乌头等配成的草药,放到井里浸,翌日取水置酒饮,可除病疫,云云。
由唐及宋,由北宋而至南宋,“屠苏”由主要指“草庵”的意思变成主要指“药酒”的意思。北宋文学家苏轼《除夜野宿常州城外》诗云:“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苏轼弟苏辙《除日》:“年年最后饮屠酥,不觉年来七十余。”南宋陆游《除夜雪》:“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这里的“屠苏”、“屠酥”指的才是“屠苏酒”。
虽然,两宋及以后的诗人骚客的笔下,“屠苏”多以“酒”义入诗,但它原来的“草庵”、“草舍”本义,并且又作为“房屋”乃至“家园”的引申义却未曾消失。北宋山东籍文士张因写有咏浙南名胜仙都峰的长诗排律《鼎湖》,其中诗云:“姓刘天师半山居,修真自给草屠苏。”仙都峰在缙云县境,这里是古代黄老文化的一个中心,居山里草庵中修参者自古不绝。诗中的“草屠苏”显然是“草庵”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王安石的《元日》,其中的“春风送暖入屠苏”,应该把这里的“屠苏”译作“美酒”还是译为代表“家园”、“房屋”的“草舍”才符合诗人的原意,想必读者诸君此刻也有判断了。笔者认为,如将此句译为“春天的暖风开始吹进家门”,诗意就畅通了。
作者:一赵子石头记文化工作室(青岛)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