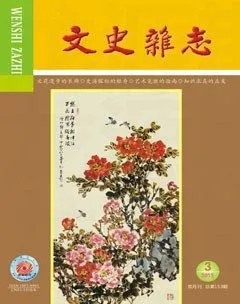相如与文君两情相悦的传奇爱情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流传了两千多年;之所以被传诵,是因为他们之间是两情相悦的浪漫爱情,非常美好,人人都向往和追求。可是,学界则有人提出司马相如劫色劫财,设骗局之说。这很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味道。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两情相悦的爱情故事,见载于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与班固《汉书·司马相如传》。从两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卓王孙慕相如声名,将他与县令王吉请到家做客,相如弹琴并以琴心挑逗文君,而文君偷听偷看,“心悦而好之”,之后便与相如私奔至成都。此记载应是两情相悦走到一起的情爱原型。至于南朝宋的佚事小说之集大成者《世说新语》等书记载相如与文君后来如何如何,则只能作为相如与文君爱情故事的参考,不足以当作史实。
相如与文君既然是两情相悦,按道理就应该谈婚论嫁,通过正式媒聘而成婚。但是,卓文君其时“新寡”,按汉代礼仪、风俗,就不能谈婚论嫁。西汉是中国封建礼教形成的重要时期。按照礼教的规定,死去丈夫的妇人不能再嫁。虽然她暂时住在娘家,但她应是夫家的人,要为丈夫服丧三年。《史记》、《汉书》都没有说文君已经“来归”(被夫家遗弃的妇女返回娘家),所以她实际还是夫家的人,只是在娘家住着罢了。卓王孙是临邛首富,夫家也不敢把新寡的文君“遗弃”。夫家没有遗弃,文君想“来归”也不行。
守丧期间的文君若要改嫁,夫家会竭力反对,也不会有人家敢娶,更不会有人敢作媒。因此,新寡的文君要通过正式媒聘再嫁,此路不通。卓文君出嫁后不久,丈夫就死去,她会背上“克夫”的骂名。史籍未载她生子与否,但从《西京杂记》载“文君十七而寡”看来,没有生育。卓文君出嫁不久,丈夫死去,还有不会生育的嫌疑。卓文君当时的情况并不妙。
所以,当文君得知父亲所请贵客,乃是才华横溢的司马相如时,便不由自主地躲在屏后探头外望,见相如衣冠齐整,容雅风流,顿生爱慕之心。相如正沉醉琴中,忽听屏后传来一阵环佩叮咚之声,抬头一看,正与文君打了一个照面。文君的美貌使他心醉神迷,于是心机一动,指法立变,弹唱出一曲《凤求皇》(即《琴歌二首》)。歌曰: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
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夕升斯堂!
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
皇兮皇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
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
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司马相如的琴弦着实拨动了卓文君的心弦。她随即作出蔑视传统伦理的大胆私奔之举,与司马相如结成终身伴侣。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只是将司马相如作为一个俊雅倜傥的风流才子来看。事实上,司马相如除了一表人才,满腹诗书之外,还有胆有识,敢作敢为。他与寡居的卓文君自由结合,固然是惊世骇俗;婚后生活拮据,夫妻二人开店卖酒,他让卓文君当垆,自己穿上酒保的衣服,涤器市中,旁若无人,也是一般儒生做不到的。更为难得的是,身为汉赋大家,他在汉武帝身边十几年,却不把献赋当作向最高统治者献媚取宠的手段,不与那些阿谀逢迎、鲜廉寡耻之徒为伍,不愿作没有灵魂的御用文人;而是有条件时争取有所作为,难有作为时便努力保持自己的节操,所以,他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终其一生,除了出使西南临时挂过“中郎将”衔以外,长期担任的不过是“郎”、“孝文园令”等低级闲职。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寂寥,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确乎如此。
关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婚姻生活的最后结局,严格地说,史书是缺乏记载的。但是,从《史记》交代相如出使西南返回时,“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这些内容来看,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因两情相悦而走到了一起,也因始终的两情相悦,其爱情生活始终充满浪漫和甜蜜。
不可否认,在古代上流社会,不带功利色彩的纯感情婚姻应属少数,大多数婚姻会受到政治、军事或经济的影响。秦始皇把自己的十五六岁的女儿华阳公主许配给70岁的将军王翦,目的是要王翦好好带兵打仗。汉武帝时,将细君公主嫁给乌孙国昆莫猎骄靡为妻,是为了“和亲”。只要条件许可,谁都想找经济条件更好,才干更强,外表更美的配偶,而不是相反。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两情相悦有没有功利色彩?应该说是没有政治、军事或经济方面的功利的,有的只是才子和佳人不顾封建礼教、传统伦理而追求自由生活和美好爱情的个性一致。郭沫若先生于1957年10月1日在卓文君家乡邛崃县为“文君井”的题词说得好:
文君当垆时,相如涤器处。反抗封建是前驱,佳话传千古。会当一凭吊,酌取井中水,用以烹茶涤尘思,清逸凉无比。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实系千秋佳话,故井犹存,今人向往。
本来是一段反抗封建传统礼教的美好爱情传奇故事,可是,王立群先生却偏要说:“琴挑文君:千年一骗局,劫色劫财”,“这个流传千古的爱情传说原来是一个先劫色后劫财的骗局”。这是经不起推敲的谬论。“劫”是抢劫、强夺。事实是“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文君)驰归成都”,是文君自愿,自己先跑到相如住处,再一起跑到成都的。相如没有“劫色”,更没有“劫财”。他与文君是两情两悦,私奔联姻,而且相爱相守一辈子,也证明不是“劫”。
从文献记载看,相如不是好色好财之徒。在35岁前,他没有好色行为,更无“劫色”前科。他钟爱辞赋重于财色。《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又载:“(相如)时时著书……未死时,为一卷书。”临死前写成一卷《封禅书》。相如的价值取向,与劫色劫财似无关联。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与《汉书·司马相如传》基本相同。在卓王孙请相如赴宴时,《史记》载:“相如不得已,强往。”《汉书》载:“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王立群发现《汉书》比《史记》多一个“为”字,并说:“‘为’者‘伪’也,即司马相如故作清高,假装不愿赴宴。班固写得比司马迁更透彻,他揭示了司马相如和密友王县令的确策划了一个大阴谋。”
其实,司马迁写得很明白:县令将相如请到临邛,“缪为恭敬”;相如在卓家弹琴时“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汉书》上这两句也一样。L3A76o8DRYmFGsFa/Dpfvg==其中的“缪”即假装,就是假意做得更加恭敬而已。司马相如和县令王吉本是亲密故友,做得恭敬一点,其目的是引起临邛卓王孙和众客人对相如才艺的重视。而“为”不是“伪”,不是假装的意思。如“为”是假装,班固会写成“相如缪不得已而强往”。即使王吉是有意想牵这根红线而“缪为恭敬”,也非常正常。司马相如35岁未恋未婚,卓文君年纪轻轻就成新寡,难道他们没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即使作为县令的王吉欲做“红娘”,也是难能可贵,他们有什么错!宴会上弹奏音乐,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哪知道卓文君“窃从户窥”,司马相如于是弹出了他向卓文君求爱的心曲;文君熟谙音乐,自然是知音。这样,两心相碰,产生了爱情的火花。琴心相通生恋情,这是多么美妙,多么浪漫的爱情!
王立群又把文君提出要回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的意见栽到司马相如身上,说什么“早就想好,只是没说,等文君说出来,因为要考虑他的面子”。这个逻辑推理非常荒唐。《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原话是:“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这几句话,无论如何也推不出“是司马相如用计让文君先说出来”这个意思的!卓文君提出回临邛是想借长兄的钱为生,并非是逼父卓王孙拿钱。再说,卓王孙虽爱小女,但后者违背自己的意愿,找了一个落魄的穷文人,还私奔了去,杀了她都有可能,怎会容忍文君回来“逼其父出血”?这纯粹是杜撰出来的欲加之罪。
历史上确有颜之推、司马贞、苏轼等人骂过司马相如是“窃赀”、“窃妻”等语。不过,以司马相如卓文君之举,不遭人“骂”反倒令人奇怪。再进一步看,北朝颜之推写了20篇“家训”,他当然要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礼教思想去灌输其子孙,而不可能教他们去学卓文君私奔,不可能教他们去学司马相如用琴声与心仪的姑娘谈恋爱。唐朝的司马贞是朝廷的弘文馆学士,《辞源》上说他“注文繁征博引,常断以己意,颇有发明”。他在《史记索隐》中推断司马相如“窃妻”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苏轼生活的时代是宋明理学开始繁荣的时代,最讲究“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婚姻上尤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等礼教。当过宋朝礼部尚书的苏轼自然会维护礼教,不会容忍司马相如、卓文君的“琴挑私奔”,遂有“窃妻以逃,大可笑”之语。王立群教授将这些“贬派”之语(且多为断章取义)拿来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并无多少说服力。
可以肯定,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在封建时代,为追求张扬个性的爱情所具有的不惧世俗的大胆叛逆精神和为之奋斗过的爱情传奇故事,将永远留驻历史。更重要的是,司马相如的创新精神与宏富辞章,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人们对司马相如的人品并不怀疑。在司马相如的家乡成都,至今还保留着取自相如之语的“驷马桥”地名,还有纪念相如夫妇的“琴台故径”、“文君酒家”;经过整治的锦江之畔,又新塑起相如的花岗石造像。当人们在此徜徉之时,油然而生出自豪之感,缅怀之情……
作者单位:四川农业大学成都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