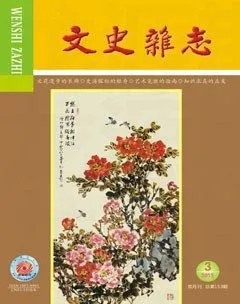隔海遥忆孙家勤
2011-12-29 00:00:00汪毅
文史杂志 2011年3期

午后的小憩是我的“天天读”,包括念大学时下午欲面对的考试。自然,2010年10月30日(星期六)的午后小憩亦是我的“必修课”。刚入寐,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听罢孙家勤老师的弟子游三辉先生传递的噩耗,我的睡意顿飞,喃喃自语的就那么一句:“怎么会呢?”因为,在我的眼里和心里,孙家勤老师那么富有童稚心,而且身体那么的棒,他的年纪应是与神仙比高低的呀!况且,4月份我们还在台北有3次谋面,6月初他在重庆涪陵办画展时还给我有过电话……
屈指算来,我与孙老师的交谊忽忽近20年。我们的交谊,缘自张大千先生。那时,我在四川内江张大千纪念馆馆长任上,联系大风堂门人是我的工作之一。在我所联系的数十位大风堂门人中,孙老师无疑是重点——这并非因为他是教授和博士,而在于他以弘扬大风堂艺术为己任,被大千先生誉为“吾门当大”。他于1994年10月21日给我的信中,谦虚而自豪地写道:“家勤列入大风堂甚晚,但朝夕追随长久。”他还应我所约,寄来文采飞扬的“侍师日志”稿件,发表在我主持编辑的《大风堂报》上。
至于我与孙老师的第一次谋面,是1996年的5月30日,在台北。首次见面,我便领教了孙老师的童稚心、细心、幽默、超强的记忆力。其细节是,我被李再钤教授(孙老师台湾师大的学兄)安排在席桌的41A座位时,孙老师竟一脸童稚状:“汪先生,简直奇了,41A不正与你的年岁相同么?看来你与大家好有缘,一到台湾就坐在了与你年岁吻合的座椅上。”这一段内容,我写进了所著的《台湾文化之旅》一书(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出版)。
继后,我与孙老师交谊的长河可谓浩浩汤汤,一路奔流:有关于我编或著的《张大千名迹》、《大风堂的世界》、《张大千张善子黄山记游》;有关于孙老师寄给我的他所出版的各种画册,甚至在台湾巡展的请柬;有关于我俩的电话、节日贺卡、书信;有关于我俩的一次又一次谋面(如2004年10月在杭州参加游三辉先生的画展、2008年11月在黄山参加张大千大风堂会馆的开馆)……一朵朵快乐飞溅的友谊的浪花,是那样的谐和与美好。
然而,在这些难忘的记忆中,最让我挥之不去的是2009年10月与2010年4月我俩的谋面。
2009年10月30日上午,《大风再起——孙家勤画展》在杭州浙江美术馆隆重开幕,我应孙老师邀请前往参加。颇巧的是,这之前一天(29日上午),我应内江市政协所邀作专题讲座的内容之一亦是“大风再起”。这与孙老师身体力行倡导的“大风再起”不乏呼应。故29日晚上飞抵杭州见面时,我用四川话说:“这一回我当了君子,动口,今天在内江鼓吹‘大风再起’;而孙老师你这一次当了‘小人’,动手,明天在浙江美术馆举办画展,让‘大风再起’。”是的,我俩就是这样快乐与谐趣着!(其实,这样的快乐与谐趣是需要童稚之心、爱心、包容心、智慧的,甚至大智慧。)
30日下午,安排的是《大风再起——孙家勤画展》学术研讨会。会上,除了作较为长篇和系统的学术发言(遗憾,一直未见到美术馆的整理记录),我还即兴口占观《大风再起——孙家勤画展》诗:“立雪大风君当大,承古创今扬‘三家’。耋年新猷并蒂美,两岸竞艳丹青花。”然而,怎么也料不到一年后的10月30日,竟是冰火两重天,竟让我收到关于孙老师的噩耗,一个只能让我在电话里喃喃自语“这怎么会呢”的噩耗!
2010年4月,中央电视台拍摄《百年巨匠——张大千》(3集)文献纪录片赴台湾,我作为文史顾问应邀前往。抵台北当天(3日)晚上,孙老师便来宾馆与我们商量4日清明节在摩耶精舍(台湾张大千先生纪念馆)的开机仪式,并特意送给我一张《荷花图》,其题款是:“尝求问于大千师画荷要旨。师言:当以能描绘其生于野塘趣为上,即可全其性,更能表其清。勤仰遵行之,今绘此奉汪毅先生教正。山东泰安孙家勤于丽水精舍。”从画款传递的信息中,让我感到孙老师对张大千先生的敬重,以及对我研究张大千不断走向深邃的希冀。唉,我实在没有料到此画竟成为孙老师馈赠我的遗物!大千先生有诗句:“荷花世界梦俱香”。而孙老师馈赠我荷花图不也正是要传递这种信息么?噢,我当珍视这一片绚丽的荷花世界,我当用心收藏这摇曳梦香的每一朵荷花!噢,我当深深祈愿:天国中的孙老师,你的梦啊也如同这清新美丽的荷花绽放!
至于4日在摩耶精舍开机时定格在孙老师脸上的肃穆凝重情景(平时的孙老师却是一个喜乐神呀),让我实在无法忘怀。他与我轮番将四川青城山泥土一层又一层轻飏梅丘(张大千先生的灵厝)的过程,让我感到他的心的颤栗和轻飏。这一情景和感觉,我写进了《台湾文化之旅》——赴台日志(三)中,并连载于《巴蜀史志》。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我寄此期《巴蜀史志》杂志和四川博物院资料给孙老师时,正好是2010年10月27日——孙老师的寿终正寝日。难道这就是感应?噢,孙老师,你给我了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孙老师与我的最后一次通话是2010年6月上旬,时他在重庆涪陵举办画展。电话中,他再一次谈到来年在四川博物院举办画展的事宜(我知道他的心思,是要以此告慰大千先生),并言及已看到所寄《文史杂志》第3期(双月刊)中我写的文章《破译孙家勤教授艺术的密码》;还说再出画册时用此文章作序言。当我说去重庆涪陵看他时,他却以即将返台北为由相婉拒(其实,他是怕我鞍马劳顿)而约定来年我们在成都四川博物院的画展见。然而,实在没有想到相见成都的期许竟成为幻影!
噢,隔海相忆,隔海遥祭!
作者单位: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都)
链接:孙家勤小传
孙家勤(1930-2010),本系国画大师、教授,于2010年10月27日因病辞世。
孙家勤教授,号野耘,山东泰安人,为孙传芳将军幼子,1930年生于大连,自幼习艺,1947年入北平辅仁大学美术系国画组,辗转来台后,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又从黄君璧等诸家学习,因成绩优异留校担任教职,期间与艺坛好友喻仲林、胡念祖同创“丽水精舍画室”,开台湾联合画室之先河。1963年孙教授拜张大千先生为师,远赴巴西入八德园三年,得张大千先生真传,其后为巴西圣保罗大学文史哲社会学院创立中文系,任该系主任,修得历史博士学位,并通过终身职教授资格,1992年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聘为交换教授,1995年起担任本系国画专业教授。
孙家勤教授专攻国画人物,用笔细腻,画风清秀,韵味雅致,旅巴三十年,受张大千居士影响甚深,在传统风格上力求突破,以追求唐宋精髓为依归,临摹“大风堂”所藏名画,尤以敦煌壁画为本,体会古人用心之处,各得其意,于山水、花鸟、走兽等画科及技法演变上无一不知不晓,可写可工,信笔拈来趣味恒生;并不以自身所学为满,思想活络,以大自然为师开创绘画新思维。大千先生曾谓:“大成元明以来,人物一派坠而不传,孙生可谓能起八代之衰矣,晚得此才,吾门当大。”传承古今,享誉中外,可谓当今国宝级画家,对于中国绘画影响甚深。
(摘自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美术学系系务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