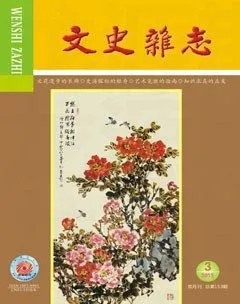建构巴蜀文化自信的可贵努力
2010年,由四川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邓经武的新著《六百年迷雾何时清——“湖广填四川”揭秘》。该书把一个从民间至学界、从四川及至全国都感兴趣的话题,而且几乎是众口一词、早成定论的历史问题,再次呈现在人们眼前。
该书最大的价值,首先在于立意高远地建构起巴蜀文化的自信心
该书针对“四川人都是湖北麻城孝感乡移民的后代”的流行说法,对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的历史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实事求是的剖析论述,认为所谓“湖广填四川”,不过是一个被民间无限放大,又在文人学者们的虚构和想象中形成的传言而已;明初从“湖广”大规模移民填充四川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清初从“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填川当属子虚乌有,从而对“湖广填四川”的陈说进行了较为彻底的“解构”,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这是该书的一大亮点,其目的在于建构川人的巴蜀文化自信心。
此前,人们论述巴蜀文化尤其是近现代巴蜀文化时,往往在“湖广填四川”与近现代巴蜀文化之间建立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有论者认为:“‘湖广填四川’也给四川地区带来了诸多的文化影响,随着‘湖广填四川’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巴蜀文化那种有地方特色与地域风格的文化体系受到了冲击,以前四川人的思维沉寂与定势被打破了,而融入了许多新鲜和灵气。”[1]还有论者认为:“元末明初的战乱,湖广省就有不少人移民到四川,到了清代前期的大移民,一百万余人中,有一半人是来自两楚——湖北、湖南。人口的大移动,带来了文化的大交流,风俗的大融合,最为突出的是楚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大交融。以四川官话——四川第一大方言的形成为例,受湖北话影响最大,可以说是以湖北话为基础,经过长期的衍变形成了现今的四川话。”[2]显然,这里将湖北话认作四川话的“母亲”了,这是本末倒置、源流混淆之论。作者认为,川、鄂两地语音有雷同现象,不能仅仅用“湖广填四川”来解释。四川话自有其本和源,流变及今,从来没有中断过。从汉代扬雄说“蜀左言”,到明代李实记录的“蜀语”,都证明四川话源远流长。比如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笔下的“将息”、“蹉跎”、“啾啾”等词语还活在四川人的嘴上。
历史话题“湖广填四川”更是一个文化问题。此前的言说无疑都是巴蜀文化“断裂论”,好像一夜之间巴蜀文化“人间蒸发”了,“移民文化”汹涌而入并取而代之,成为巴蜀之地文化的“中心”、“主流”、“正统”,“移民文化”成为“文化之母”,滋生出“新”的巴蜀文化来。巴蜀文化“断裂论”绝对是不实之论。邓经武对“湖广填四川”的解构,就是在否定这种“断裂论”,重树川人的巴蜀文化自信心,可谓用心良苦。
其次,该书从“历史的偏旁”寻绎真知,见微知著,得出崭新而独到的结论
“湖广填四川”是一个牵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口等多个领域的话题,又是一个穿越了历史、勾连着现实的话题。早已有许多所谓“全方位”的“宏论”,要在这里有新的突破,殊为不易。该书作者从微观入手,深入剖析典型事例,终成一部极有学术价值的研究专著。其创新的勇气,扎实的分析,严谨的治学,在日益浮躁的世风下确实难得。
在言说“湖广填四川”的话题时,人们总是广征博引地方史志、家族谱谍,以示自己言说的“合法性”和说服力,这已经形成固定的“学术套路”。邓经武却不依陈说,揭示地方史志、家族谱谍的相互矛盾和不实的“历史的缝隙”,推翻那些所谓的“公理”或众口一词的“定论”。如“麻乡约”、“解手”常常成为“湖广填四川”的重要证据。邓经武从这个“历史的偏旁”进入其间,通过正反相较、寻绎史实、文史交错的一番剖析之后,自然得出清清楚楚的“学术结论”:“麻乡约”、“解手”与“湖广填四川”没有关系,此前的言说都是牵强附会,纯粹是道听途说。
该书在“众说‘湖广填四川’”、“传说与典籍的对立”、“史料与史实的辨析”、“传说与史实的尴尬”等部分里,其从“历史的偏旁”寻绎真知、见微知著的特点尤为明显。家族谱谍是研究移民现象的重要“史料”,历来为学界重视。但一般人如我往往不作真伪的辨证,直接使用家族谱谍材料,犯了“偷懒”的毛病。邓经武从修谱的起源、发展说起,指出最早者距离明初洪武元年已经是560年,距离清初顺治元年也有220年,其内容大多数必然是后人的追溯,外加官方政治、经济等因素的“扭曲”,真实性可想而知。现在能看到的四川人的大多数家族谱谍,在移民原因、时间、来源地籍贯等诸多方面都是混乱的,不足为据。
再次,该书是学术化与大众化融合的有益探索
学术研究向来都是“圈内人士”的“象牙塔”,以所谓“高深”而“自炫”者有之,甚至以“莫测”而“自闭”者亦有之。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行文的可读性。邓经武在可读性上是下了一番功夫的。翻开目录一看,章节标题没有标“新”立“异”,没有“奇”谈“怪”论,却言简意切,“眉”清“目”秀,浑然天成。像“谈巴说蜀:四川人‘根’在哪里”、“正本清源:莫走错庙门上错坟”都是雅俗共赏的好标题。各章目之下列出的节目标题,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兹不赘录。
轶闻趣事的叙写,语言方式的选择,都体现出可读性。“麻城孝感乡今何在”这一章,介绍麻城县、孝感乡这个聚焦点,虽然有一些典籍史料引用,但行文如流水般活泼、自然,时有小小浪花跃出水面,让人惊喜。如“唐代蜀人李白曾经步履所至,宋代苏东坡也到过这里访友,其笔下的‘河东狮吼’典故就产生于麻城,这就是今天人们广泛运用的‘野蛮老婆’的同义词。”[3]“河东狮吼”是典故,文雅含蓄,“野蛮老婆”是时言,通俗直白。又如“四川民间传言最多的,是两个历史人物:诸葛亮、张献忠”、“湖北省麻城县,注定要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地方’”,这是书中一节的开头,平实中藏着悬疑,简洁而有韵味,有引领阅读之效。
总之,该书从微观入手切入“湖广填四川”的话题,通过典型事例的深入剖析寻绎真知,在几成定论的问题面前举起“异帜”,以一家之言揭开“六百年迷雾”,旨在建构人们的巴蜀文化自信心,立意高远,极具现实意义。探索学术化与大众化的融合之路,让学术争鸣走进寻常百姓家,让一个四川乃至全国都关注的“大众话题”,真正为“大众”知晓并分享——这种努力,是一个知识分子神圣而又值得骄傲的行为。
注释:
[1]李华:《浅谈“湖广填四川”对巴蜀地区的文化影响》,《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2]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3]邓经武:《六百年迷雾何时清——“湖广填四川”揭秘》,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页。
作者: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