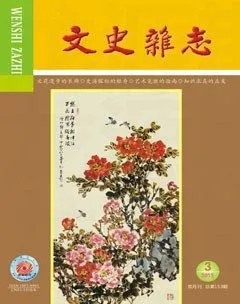“鹳山双烈”中的郁华
2011-12-29 00:00:00吴斌
文史杂志 2011年3期


浙江富阳县富春江畔的鹳山上耸立着一座纪念亭——鹳山双烈亭。长眠此处的是民国时期中国著名的高级司法人员郁华(字曼陀)和著名左翼文学家郁达夫兄弟俩。鹳山有“华东文化名山”的美誉。在鹳山东侧有“松筠别墅旧址”——是由著名书法家黄苗子(黄苗子是郁华的大女儿郁风的丈夫)题写。郁达夫3岁时父亲即去世,与二兄一姐全靠太夫人陆氏抚养长大。民国初年,大总统黎元洪因郁门婆媳戴氏和陆氏两代守寡扶掖子孙,亲笔题词赐匾额:“节比松筠”。郁华(图一)因此命名其居为“松筠别墅”,作为奉母养老的小筑。后郁华被日伪特务暗杀于上海。1937年12月,日军入侵富阳。郁母陆太夫人大义刚烈,绝食殉难以抗争。而今楼上陆母卧室还悬挂着她绝食殉难前一年的留影。现松筠别墅已被辟为“郁曼陀、郁达夫烈士事迹陈列室”。
郁达夫,中国现代诗人、作家、爱国主义者。胡愈之曾评价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夏衍先生也曾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社。”
郁达夫作为诗人、作家因其文名远播而为人熟知,其长兄郁华却被人们渐渐淡忘。但在近代中国政法史上,郁华却是一位名垂青史的爱国法官。他是抗战以来在上海租界内第一个遭汪伪汉奸特务机构“76号”杀害的中国高级司法人员。1952年10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郁华和郁达夫均被人民政府追认为“为民族解放事业殉难的烈士”。
一、义举助革命
郁华早年负笈日本,先后就读早稻田大学、法政大学,回国后,供职于清政府外务部。1911年,郁华任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北京政府大理院推事;1913年奉派赴日本考察司法制度,回国后,继任大理院推事,兼司法储才馆、朝阳大学、东吴大学等院校刑法教授;历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刑事司科长、最高法院东北分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兼代分院院长。由此,郁华的名声久已为日本人所熟悉。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军国主义者就威逼郁华为侵华日军服务,他坚辞不从。当时日寇对我东北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郁华坚持民族大义。为摆脱日寇纠缠,郁华星夜潜藏皇姑屯农家,随后又化装兼程回到北平,由此可见郁华的民族气节及其风骨。
民国21年(1932年),郁华出任国民政府设在上海租界内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并兼任东吴法学院、法政大学等大学教授。在这段时间内,郁华基于其正义良知和法律素养,多次营救进步人士,积极帮助田汉、阳翰笙等革命者。
1933年3月28日,由于叛徒告密,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的廖承志,被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勾结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监禁在租界拘留所。他们突击审讯,逼迫廖承志说出上海地下党名单,又暗示他母亲可能危险;但廖承志毫不退缩,怒斥国民党勾结外国人迫害革命志士的罪行。3月30日,江苏省高等法院上海分院刑事一厅开庭审理,主持审讯的庭长正是和柳亚子相熟的郁华。柳亚子前往旁听,郁华将南京军法处要求将廖承志引渡到南京的消息告诉了柳亚子。这为爱国进步人士营救廖承志赢得了机会。柳亚子立即将情况告诉了何香凝。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宋庆龄的主持下,召开了临时执委会议,随即发表宣言,要求立即释放廖承志。在各方面努力下,廖承志最终获释。廖承志出狱后,何香凝为表谢意,亲自绘制《春兰秋菊图》一幅赠送郁华。1954年,何香凝又在画上补写题词:“1933年承志入狱,其时得曼陀先生帮忙,特将此画纪念。”同年5月,郭沫若见到画和题词,又在画端题诗一首:“难弟难兄同殉国,春兰秋菊见精神;能埋无地天不死,终古馨香一片真。”
郁华的正义言行深深影响了其弟郁达夫。郁达夫的很多壮举也都和郁华有关。学者李剑华在回忆郁达夫的文章中说:“达夫先生……同情革命,富有正义感,在三十年代的腥风血雨的岁月里,曾通过他在法院工作的哥哥郁曼陀,着实营救了不少共产党同志。”
郭沫若先生后来在为郁华撰写的碑铭中也说道:“先生持法平而守己刚正,有投书以死相威胁者,先生不为所动,爱国青年之得庇护以存活者甚众。”
二、文章抒气节
郁华一生为人正直、清廉,喜爱诗画。早在辛亥革命前夕,郁华就参加了柳亚子等人组成的进步文学团体——南社,积极倡导文章气节,常以诗画抒发爱国热忱,有《静远堂诗画集》、《郁曼陀陈碧岑诗抄》等著作。柳亚子评郁曼陀的诗是“鹏举冲冠之作,文山正气之歌”。
郁华对诗词书画均有较高的造诣和研究。在日本留学时,郁华曾在报刊发表67首《东京竹枝词》,被传诵一时,并得到日本汉诗泰斗森槐南的高度评价。
郁华回国后继续进行诗歌创作,在诗歌里热忱抒发他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及其报国效民的心志。在一首题为《乙亥中伏暑牯岭》的诗中,郁华写道:“人世炎威苦未休,此间萧爽已如秋;时贤几辈同忧乐,小住随缘任去留。白日寒生阴壑雨,青林云断隔山楼;勒移那计嘲尘俗,且作偷闲十日游。”
在郁达夫的《秋霖日记》中,郁达夫和此诗。前小序交待:“海上候曼兄不至,回杭得牯岭暑夹诗,步原韵奉答,并约于重九日,同去富阳。”郁达夫和诗曰:“语不惊人死不休,杜陵诗祗解悲秋;蝎来夔府三年住,未及彭城百日留。为恋湖山伤小别,正愁风雨暗高楼;重阳好作茱萸会,花萼江边一夜游。”
而在一首题为《晓发天台国清寺至螺溪钓艇》的诗中,郁华再次抒发了这种追求:“每逢胜境便勾留,稳藉篮舆作卧游;画幛千林悬晚翠,风帘一桁破晴幽。峰遮月角云低堕,石束山腰水倒流;不信螺溪深百折,壑中藏得钓鱼舟。”
郁华在殉难之前,曾给夫人陈碧岑写过一首诗:“劫余画稿未全删,历历亭台忆故关;烟影点成浓淡树,夕阳皴出深浅山。投荒竟向他乡老,多难安容吾辈闲;江上秋风阻归棹,与君何日得开颜。”这首诗语句清丽,情意深沉。特别是“多难安容吾辈闲”一语,表达了郁华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报国济世的心志。
三、乾坤扶正气
1937年10月,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抗战前国民政府在租界内设立的特区法院继续运行。但日寇的觊觎之心未死,从1938年开始多次跟租界交涉,要求接管租界内的中国法院,并将法院归汪伪政权管辖。美、英、法诸国政府因只承认蒋介石国民政府,拒绝了日本要求。于是日本人将争取租界警察权和中国法院管辖权的重任交给汪伪上海76号特工总部承担。
76号全称是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因位于极司非而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而得名,于1939年5月成立,由周佛海任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丁默邨任副主任委员,李士群任秘书长;以丁默邨为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为副主任。
“76号”接受重任之后,暗杀、绑架替代了外交谈判。租界当局不得不加强各法院的武装戒备,同时由警务处派出武装人员接送司法人员上下班;对于院长、刑事庭庭长等高级人员,甚至由装甲车接送。对此项保护举动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更多的中国司法人员认为这只是向特务示弱而宁愿步行或者通过其他交通工具上下班。郁华便是其中一位。他拒绝了租界当局的好意,坚持自备包车上下班。
1938年4月,日伪特务在上海马路上枪杀了著名的文教界和宗教界进步人士、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博士。郁华在审理这一案件时,不顾自身安危,当庭斥责刺客并判以极刑。刘湛恩之子刘光华说:“我曾亲睹郁华庭长不顾自身安危,当庭痛斥被现场群众捕获的刺客曾某,并判以极刑,其高风亮节、秉公执法确实令人佩服。”由此敌伪汉奸对郁华恨之入骨。
1939年春,郁华接到署名“反共除奸团”的恐吓信说:“如果不参加我们组织,你的生命难保。”郁华泰然处之。敌伪又许以高官厚禄,郁华又严词拒绝。友人多次劝他外出避祸,他却说:“国家民族正在危急之际,怎能抛弃职守?我当做我应该做的事,生死就不去计较了。”他坚守自己的司法岗位,并积极支持夫人陈碧岑和大女儿郁风从事抗日活动。
1939年7月,“76号”特务又在租界寻衅,袭击《中美日报》社,并打砸抢《大晚报》馆,捣毁了排字房,打死打伤排字工各一名。租界巡捕闻讯赶来,特务们开枪拒捕,后有几名“76号”特务受伤被捕。此案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几名被捕特务经公共租界上海第一地方法院一审判处死刑。“76号”的头子李士群、丁默邨策动被捕特务上诉,同时写信给即将承接此案二审的郁华,要求他撤销原判,宣布被告无罪;并威胁郁华说如果不这样的话后果将极其严重。郁华对此嗤之以鼻。在后来的审判中,郁华坚持正义,驳回上诉,维持原判。“76号”闻讯后恼羞成怒,随即命令特务夏仲明、吴振明、潘公亚等人布置暗杀。1939年11月23日,日伪特务对郁华实施暗杀。郁华身中三弹而牺牲。
郁华被害后,上海、香港等地均举行了悼念活动。1940年3月24日,上海各界人士在湖社举行盛大追悼会。当天的香港《星岛日报》发表《学者与名节》的社论,称颂郁华:“重名节、爱国家”,“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精神,是中国在今日持久抗战中所最宝贵的。”
日伪特工暗杀了郁曼陀之后,另一名浙籍法律人士钱鸿业遂代理院务。日寇继续要求接收租界法院,并对钱鸿业照施威胁恐吓,从未间断。为了保证钱鸿业的人身安全,其左右多次劝说他进出乘避弹汽车。然而钱鸿业心中毫无畏惧,视日寇的威胁为无物,依旧每天乘人力车上下班。1940年7月29日,钱鸿业终遭日谍暗杀。郁华与钱鸿业相继殉国,成为当时捍卫民族利益和尊严的法界勇士。重庆国民政府下令予以褒扬。
四、埙箎同殉国
郁华牺牲的噩耗传来,胞弟郁达夫愤笔挥就挽联一副:“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闻海内;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辽东。”这副对联高度评价了郁华执法不阿、为国捐躯的清名亮节,同时义正词严地倾吐了诗人对强寇入侵、山河破碎的无比愤慨。挽联振奋人心,传诵一时。
抗日战争中,武汉沦陷时,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之邀,前往海外从事抗日宣传,后避难于印尼,在苏门答腊被日本宪兵杀害。家乡人称兄弟两人为“双烈”。
郁华被杀害后,夫人陈碧岑将一件血衣暗暗保存下来,请净寺的若瓢和尚代为收藏。1947年4月,富阳地方人士举行公祭,在鹳山修建了“郁曼陀先生血衣冢”。墓额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郭沫若撰写《郁曼陀先生血衣冢志铭》,由马叙伦书成刻石。碑文为:“石可磷而不可夺坚,丹可磨而不可夺赤,谁云遽然而物化耶?凝血与山川共碧!”
1980年,富阳县政府为纪念郁达夫、郁曼陀两位爱国志士,在风景秀丽的鹳山修建双烈亭。亭子正檐,悬挂着茅盾题写的匾额“双松挺秀”四个大字。(图二)亭内四根亭柱上对称地挂着赵朴初和俞平伯题写的楹联:“莫忘祖逖中流楫,同领山亭一钵茶”;“劫后湖山谁作主,后豪子弟满江东”。前者苍劲,后者雄浑。亭北两侧嵌有富阳县人民政府所立的两块镌有烈士肖像和小传的石碑,碑文由著名书法家黄苗子书写,字体质朴舒展,拙中有味;两帧白描肖像出自著名画家叶浅予手笔,形神兼备;肖像上方有双松对峙,象征英灵与青松常在。亭子中间竖有石碑,刻有郭沫若于1963年为郁曼陀遗画而作的题诗。(图三)诗云:
双松挺秀意何如,仿佛眉山有二苏。
况复埙箎同殉国,天涯海角听相呼。
亭子四周绿树掩映。隔着稀疏的枝条俯瞰,水波粼粼的江面,幽静雅致的鹳山,最是安抚英烈魂灵的栖息之地。故乡人们的深厚情意,英灵在天也会有知吧!
作者:中国计量学院法学院(杭州)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