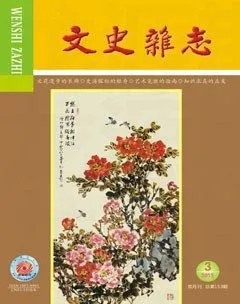解读苏轼的两次制科考试
2011-12-29 00:00:00周云容
文史杂志 2011年3期

制科,又称制举,在宋代又称之为“大科”,是选拔务实人才的重要方式,而且在宋代士子心目中制科进身高于进士科。“然宋之得才,多由进士,而以是科应诏者少”。据统计,两宋三百多年间制科共举行御试二十二次,入等者不过四十余人,而制科入三等者仅有四人:吴育、苏轼、范百禄和孔文仲。《宋史·苏轼传》载,苏轼是两次参加制科考试,而且均入三等,这在宋代是极为特殊的。透过苏轼两次参加制科考试的特殊经历,我们将对宋代的制科考试有更多的了解。
制科,是科举考试中的一种,只不过制科是由皇帝下诏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制举无常科”,目的在于选拔各类特殊人才。制科源于汉文帝时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参加对策,并根据等第授予官职的察举制度。其在唐宋时期得到极大的发展,一直延续到清朝。宋代制科时废时置,却在宋仁宗、宋英宗时达到极盛。宋仁宗时设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茂材异等科等十科。苏轼参加的两次制科考试,分别是在宋仁宗、宋英宗时,也是宋代制科最为兴盛之时。
一、苏轼的第一次制科考试
苏轼第一次参加制科考试是在宋仁宗的嘉祐六年(1061)。
仁宗朝规定参加制科者,须有二位大臣荐举,还须经历三个规定的程序:首先向两制(即掌内制、外制的翰林学士、知制诰、中书舍人)呈送平时所作策、论五十首,两制选取词理俱优者参加阁试;接着是秘阁试六论;最后才能参加皇帝的御试。
嘉祐五年(1060)苏轼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今河南伊阳西)主簿(属正九品)。苏轼未赴任,经欧阳修、杨畋等推荐,寓居怀远驿,精心准备制科考试。试前,苏轼上杨畋、富弼等人二十五篇《进策》、二十五篇《进论》。苏轼所上策、论词理俱佳,被推荐参加秘阁考试。
嘉祐六年(1061)八月十七日,翰林学士吴奎、龙图阁直学士杨畋、权御史中丞王畴、知制诰王安石为秘阁考官。苏轼赴秘阁试六论。
秘阁试六论是制科考试中最关键的环节,关系到能否参加最后的御试,同时也是制科考试中最难的一个环节。在此有必要对阁试多介绍几句。首先,阁试六论的出题范围极其广泛。其出题范围,以九经、兼经、正史为主,旁及武经七书(北宋朝廷作为官书颁行的兵法丛书,包括《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七部著名兵书)、《国语》及诸子;正文之外,群经亦兼取注疏。就苏轼参加的这次阁试六论而言,一为《王者不治夷狄》,出自《春秋公羊传》何休注;二为《刘愷丁鸿孰贤》,出自《后汉书·丁鸿传》及《后汉书·刘愷传》;三为《礼义信足以成德》,出自《论语·子路篇》包咸注;四为《形势不如德》,出自《史记·吴起列传》;五为《礼以养人为本》,出自《汉书·礼乐志》;六为《既醉备万福》(有些资料上为《既醉备五福》),出自《诗经·大雅·生民》郑玄笺。六题中,三经三史,三正文三注流。阁试六题还有明数、暗数之分。《宋会要·选举》中讲:“直引书之一二句,或稍变换句之一二字为题者为明数;颠倒书之句读,窜伏首尾而为题者为暗数。”按惯例明暗相参,暗数一般不过半。其次,对应试者所作六论要求极其严格。应试者试六论,文中必须指出论题的出处,并须全部引用论题的上下文,这样才能称为“通”。不知论题出处者不得为“通”;知道出处而不全引上下文者,也不得为“通”,只能为“粗”。应试者所作六论,须在三千字以上,而且须一天一夜内写成。再次,对是否推荐参加御试的尺度苛刻。按一般规定,六论以四“通”为合格。但是阁试成绩亦分为五等,一、二等不设,第三等为上,第四等以上才有资格参加御试。第四等又分上、下,在宋仁宗景祐年后,第四等上才能参加御试。以此观之,这不仅要求应试者知识面极其广泛,而且对这些知识还要十分熟悉,可谓是烂熟于胸;还要求应试者文理俱佳,才有可能入第四等以上。时人都以秘阁六论为难,把阁试称为“过阁”。为了应付这漫无范围、又无所不问的阁试,苏轼兄弟当初才授官未赴,寓居怀远驿而专心准备。阁试之烦、难,可能也是两宋三百多年间,仅仅举行二十二次御试,几乎十五年才举行一次,而且只有四十余人入等的原因之一吧!
最后,苏轼在这次制科阁试中合格,得以参加御试。以前的阁试文章,不起草,“以故文章多不工”。从苏轼开始,才先起草,所以文章写得“文义灿然”。
嘉祐六年(1061)八月二十五日,宋仁宗在崇政殿亲试制科应试者,称为“御试”。因御试多试于崇政殿或集英殿,又称为“殿试”。
制科御试试策规定字数在三千字以上,而且要在当日内完成才能入等。御试的策题,多由两制拟呈皇帝择选,也常命宰相代拟。此次御试的策题,由翰林学士、知制诰胡宿代拟,其策题就长达五百余字。苏轼首先上《中庸论》、《秦始皇帝论》、《汉高帝论》等二十五篇文章,接着答《策问》,即《御试制科策一道》,举条而对,洋洋洒洒作了五千余字。制科取士,特别郑重,在阁试、御试中都要弥封卷号,进行誉录。在御试中苏轼的代号为“臣”字,苏辙为“毡”字,而且在考官定等次之后,还有覆考官按例复核。司马光是此次御试的覆考官。他在《论制策等第状》中这样讲到:“内‘臣’、‘毡’两号所对策,辞理俱高,绝出伦辈……以‘臣’为第三等,‘毡’为第四等”。从司马光的奏文中可以看出,在这次御试中,苏轼、苏辙的对策文章确实写得相当不错。最后,苏轼“入三等”。但是苏辙在对策文章中极言得失,本当黜落,最后经司马光向宋仁宗争取,入四等。这次制科应试有四人,现在所知的只苏轼、苏辙和著作佐郎王介三人。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制科三等——它委实属于了不起的高等范畴。叶梦得在《石林燕话》中提到:“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虚,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选者,亦皆第四等”;《宋史·苏轼传》中也说:“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而且两宋三百多年间,制科能入三等的只有四人:吴育、苏试、范百禄、孔文仲。由此可见,苏轼制科入三等,实属凤毛麟角。当时的知制诰王安石也在《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大理评事制》中对苏轼这样评价:“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苏轼、苏辙两兄弟一人入制科三等,一人入制科四等,实在是十分难得。欧阳修在《与焦殿丞千之》中这样称赞道:“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宋仁宗在读了苏轼、苏辙两兄弟的制科进策后,“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宋仁宗朝规定:“自今制科入第三等,与进士第一,除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苏轼此次制科入三等后不久,就按进士第一的级别授予官职,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大理评事是掌管刑狱的京官,属正八品;签书判官是州府幕职,掌管文书,佐助州官。这是以京官身份充州签判,比前次所授的河南福昌县主簿来,职位显著提升了。正如苏轼自己所说:“忽从县佐,擢与评刑”了。
那么苏轼在这次制科考试中,究竟应哪一科呢?宋仁宗时制科设置了十科,但实际应举登第者只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茂才异等科三科。苏轼在《答李端叔书》中谈到其所应“科号为直言极谏”;苏辙所作苏轼《墓志铭》也说是应直言极谏科。而王安石所作制文《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大理评事制》以及《宋史·苏轼传》皆说苏轼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关于此问题,是有一定争议的,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二、苏轼的第二次制科考试
宋英亲治平二年(1065),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判登文鼓院,为试馆职,参加了第二次制科考试。
宋英宗还未继位时,就听说苏轼的文名,“欲以唐故事招入翰林,知制诰”,想破格招苏轼入翰林,知制诰(掌起草诏令)。宰相韩琦反对,他说:“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韩琦认为苏轼是了不起的人才,今后自然会被朝廷重用;关键在于朝廷要善于培养他,使天下的人都信服他,都希望朝廷能重用他。那时再重用,则人们就不会有异议。若现在一下子把他提拔到高位,人们未必信服。这样反而会害了苏轼。宋英宗又想用苏轼修起居注,韩琦也不赞成,他认为记注与制诰的地位差不多,不可马上授予苏轼。韩琦主张“不若于馆阁中近上帖职与之,且请召试”,主张给苏轼一个能接近皇帝的馆阁的职务,但要先考试。宋英宗说:“试之未知能否,如轼有不能邪”?不知道苏轼能否胜任馆阁的职务才须进行考试,而他的才能是有目共睹的,他还能不行吗?宋英宗是想不经考试,直接授予苏轼馆阁之职。从中可以看出,宋英宗对苏轼也是相当器重的。但是韩琦仍然坚持苏轼年少资浅,未经考试,不可授予馆职。最后还是依照一般惯例,召试学士院。苏轼认为韩琦“乃古之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欤!”苏轼对韩琦因他资历不够不让他担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修起居注等重要职务是感激的。这可以看出苏轼心胸的坦荡与宽广。
治平二年(1065)二月,苏轼召试学士院,试二论:《学士院试孔子从先进论》、《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此次制科考试是为苏轼试馆职而以制科特旨命试的。最后,苏轼的二论皆“复入三等”。治平三年(1066)二月,苏轼得直史馆。这是史馆中较高的官职了,属从六品。馆职中职位最高的是修撰,其次为直馆,再次为校理;职位最低的为校勘、检讨等。宋初,设三馆: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皆寓居崇文院。宋太宗端拱元年(988),下诏在崇文院中建秘阁。三馆与秘阁合称为“馆阁”。洪迈《容斋随笔》记载:“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崇文院专储三馆真本、帝王手迹及历代名贤的图画墨迹。苏轼在史馆有机会饱读大量珍本书籍、名人手稿和名人绘画,对其在文学道路上的发展提供了不小的帮助。苏轼在《谢制科启》中也说:“育才之地非一,而册府处其最高”,培养人才的地方很多,而皇帝珍藏典籍的册府是最重要的地方。
三、对苏轼的两次制科考试的三点看法
从苏轼的两次制科考试,笔者初步认为:
第一,在宋仁宗朝时,制科制度已日趋成熟,对制科的考试程序、制科进卷、试论六首及其字数都有了明确的规定。
第二,苏轼参加的这两次制科考试,尤其是仁宗朝的这次制科考试,对苏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曾枣庄先生认为,苏轼在这次应制科考试所作的文章中,以二十五篇《进策》、《礼以养人为本》和《御试制科策一道》为最重要,它们代表了苏轼在仁宗朝的政治主张。这是他在神宗朝和哲宗朝都屡遭贬斥的根源,也对他的文学发展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苏轼的一系列应试文章对当时的文坛也带来巨大的影响。嘉祐二年,在进士科考试中“以西汉文词为宗师”的苏轼文章,受到朝廷的赏识,被擢之高等,名震京师;嘉祐六年,苏轼又在欧阳修的荐举下应制科,最后入三等。这进一步显示了苏轼在应试写作上的才华。这一系列文章也充分体现出苏轼的才能和远见卓识。苏轼因应试写作而闻名,从此,“苏轼文章遂擅天下,学者多从讲问,以其文为师法”。苏轼的出现,为宋朝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和活力,可以说是改变了一个时代的文风。
第三,苏轼参加的两次制科考试,有其相关性,也有其明显的不同之处。仁宗朝的那次制科考试是朝廷为选拔务实人才而特旨进行的考试,在选拔的程序上有着严格的规定;英宗朝的这次制科考试,是苏轼先在仁宗朝制科入三等,按照惯例一任任满还朝后,为试馆职而为苏轼一人以制科特旨命试的。这两次制科考试在程序上、考试内容上、在严密程度上是完全不同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苏轼的第一次制科考试的规格高于第二次制科考试。也正是这两次制科考试的不同,展现出制科“特旨诏试”,其形式灵活这一特色。
作者单位:三苏祠博物馆(四川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