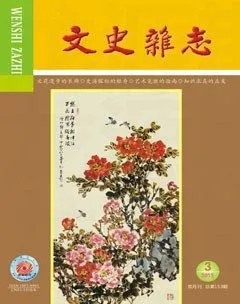周总理与《达吉和她的父亲》
2011-12-29 00:00:00杨泽平
文史杂志 2011年3期

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以下简称《达吉》),于1961年7月1日在全国正式上映。广大观众怀着极大的兴趣踊跃观看。此前周恩来总理于1961年6月19日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批评了一段时期文艺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错误作法。总理讲话联系《达吉》电影和原作引起的争论作了深刻的分析,认为电影和原作各有所长,都是好的作品;明确批评认为作品表现了“资产阶级人性论”、“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等“左”的论点。[1]总理的讲话引起与会者高度的关注,引发了广泛联系《达吉》电影和原作实际的讨论热潮。
一、《达吉和她的父亲》走上大银幕
作家高缨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坚持深入 生活,不断有佳作问世。他深入凉山彝族地区,积累了大量资料,创作出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讲述一个汉族石匠任秉清之女妞妞,5岁时被彝族奴隶主抢进大凉山。当妞妞濒临死亡时,被彝族老奴隶马赫舍命救出而抚养成人。新中国成立后,重回凉山的任秉清认出马赫身边的达吉就是自己的女儿妞妞。两个父亲都希望达吉能留在自己身边。达吉对两个父亲也怀着诚挚的感情,从而围绕达吉的去留展示了三人的感情纠葛并最终获得圆满解决的动人故事。小说最初发表在1958年《红岩》杂志第3期上。峨眉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峨影”)导演张波从《红岩》看到这篇小说,为之拍案叫绝,推荐给艺术副厂长栗茂章、厂长朱丹南,建议作为1960年峨影准备拍摄自1958年建厂后的第二部故事片的剧本用(第一部故事片是老作家沙汀的《嘉陵江边》,与八一厂合拍)。厂领导研究认为这是一个题材新颖、故事感人、民族色彩和地方特色都很浓郁、适宜拍彩色故事片的剧本蓝本,急派张波诚邀作家高缨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同时筹划拍摄的准备工作。为此高缨约请张波重到凉山州普雄县深入生活,回蓉后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初稿。当时厂领导看了长春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长影”)出品的彩色故事片《五朵金花》,认为《达吉》也应拍成彩色片,又担心本厂艺术、技术力量不够,就准备联系长影合拍,得到中共四川省委同意。与此同时,长影第六创作组从《新观察》上看到《达吉》小说后,也准备拍成电影,一经联系,才知峨影早就准备拍摄了。1960年初,第三次全国文艺工作代表会议在京召开,厂长朱丹南在会上见到长影厂厂长亚马,就合拍一事达成协议。朱丹南点名《五朵金花》导演王家乙来执导这部影片。朱丹南于会议间隙回成都就合拍事宜向省委作了汇报,得到批准。高缨后来说,《达吉》电影文学剧本初稿是“大胆依样画葫芦”写成的。中共凉山州委领导看了初稿后不够满意。在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李亚群副部长的鼓励和指点下,第二稿将重点放在表现彝汉民族大团结上。高缨、张波携带第二稿来到长影,导演王家乙看了以后,建议应在充分表现新的历史条件下塑造人物,基调应是欢乐的。于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再修改。
高缨后来感叹自己对改编电影顾虑太多。原来在发表小说和改编中,高缨以及王家乙等受到不少外界压力。有人指责小说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这使得高缨等在改编时尽力回避一些矛盾冲突,尽量削弱所谓“人性”、“人情”的成分。王家乙也有思想负担,因为有上级同志递话“不要在刀刃上跑马”……但在四川、吉林两省主管领导支持下,电影文学剧本还是得以修改出来并得到拍摄批准。
在进一步商谈筹拍事宜时,涉及演员的选定及摄制组其他主要创作人员的聘请问题。高缨当着朱丹南说,你的相貌就像彝族老汉,可以演马赫;王家乙则建议参加会议的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刘莲池担任汉族老人任秉清一角。王家乙还调侃说“一条绳子拴三个蚂蚱”以表共同奋斗的决心。(当影片完成后,朱丹南即赋诗一首:“为在银幕映凉山,诗人两次著新篇。请个名家当导演,三个蚂蚱一起拴。”)长影、峨影两厂领导还确定《五朵金花》摄影王春泉为本片摄影,作曲为雷振邦(《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作曲者),张其(后在峨影拍了名扬海内外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参加导演,配齐了一个强大的摄制组班子。陈学洁担任达吉一角,妞妞(童年达吉)由雷振邦女儿雷蕾担任。(后来雷蕾继承父业成为作曲家,写出《好人一生平安》、《少年壮志不言愁》等著名歌曲。)峨影这边还派出张波参加导演工作,潘秋(老红军,电影《抓壮丁》中饰李老栓)为制片主任,又在各主要工种上派出人员参加摄制。1960年9月初即分内景、外景两条线同时拍摄。主要外景在长白山下完成,但也到凉山选了几组空镜头。
影片于1960年年底拍完,于1961年1月7日送文化部电影局审查并完成样片,电影局提了修改意见;之后影片作了修改,又于1961年6月初送文化部审查通过。这时正好文化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电影创作会议,全国文艺座谈会也在这里召开。影片便拿到两个会议上试映,还发了高缨的小说原作。
二、周恩来讲话破除条条框框
《达吉和她的父亲》在两个会议上放映后,冯牧、赵丹、黄宗英、李希凡、谢晋等人认为还是小说好;有的代表则认为电影反映了时代精神,并为影片中主要人物丰富细腻的思想感情所打动。议论的焦点一是由小说改编为电影,是忠实于8ff0d6c71f7c4d8b2b7042693d343b1d239cce329fc5869a1b08dbce0a9ced3a原作主题、故事情节、叙事风格,还是应在原小说基础上加以升华;二是小说与电影是否都有“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痕迹,一时争论纷纭。这些争论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注意和重视。他在百忙中看了小说,也看了电影,并在1961年6月19日发表了《论艺术民主》的长篇重要讲话(后正式文件则改为《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总理讲话在全面论述“艺术民主”中还联系与会者对《达吉》电影和原作的议论谈了看法。周总理说:
……三年来,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结果反而束缚思想。其实人家也还在想,只是不敢说不敢做。人又不是石头,哪有不思想的道理。现在我们要使人把所想的都说出来做出来。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首先是有一个框子,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有了一个主观的框子就据以去抓辫子,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上学出发,也不经过调查,他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是“右倾”。对《达吉和她的父亲》,认为是“温情主义”,先立下这个框子,问题就来了,就要反对作者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感谢上海的同志,你们建议我看《达吉和她的父亲》,我看了,小说和电影我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可是有一个框子定在那里,小说上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回女儿,有人便说这是“人性论”。赵丹同志和黄宗英同志看电影时流了泪,我昨天看电影也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为什么没有流下来呢?因为导演的手法使你想哭而哭不出来,把你的感情限制住了。例如女儿要离开彝族老汉时,我们激动得要哭,而银幕上的人却别转身子,用手蒙住脸,不让观众看到他在流泪,思想上的束缚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要哭了,他却不让我们哭出来,无产阶级感情也不是这样嘛!听说导演提心吊胆,直到有的同志说了好,他才放下心来。导演在那个地方不敢放开手。这不是批评王家乙同志,而是说这里有框子,“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2]
周总理还说:
《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和电影我都看了,各有所长。小说比较粗犷,表现了彝族人民的性格,但粗糙些。电影加工较小说好,但到后来该哭时不敢哭,受了束缚,大概是怕“温情主义”。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为什么有顾虑?是有一种压力。把“人性论”、“人类之爱”、“人道主义”、“功利主义”,都弄乱了。这些问题,毛主席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时就回答了。我们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人性、友爱和人道主义。现在的搞法,不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阶级分析来看问题,而是从唯心主义看问题。以政治代替文艺,就没有文艺了,还有什么看头呢?……[3]
峨影厂厂长朱丹南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聆听了周总理的重要讲话。会后,周总理邀请了到会的艺术家三十余人到他家作客。在亲切的会见中,无拘束的谈笑中,夏衍向总理介绍了朱丹南。总理风趣地说:“我认识,他是马赫社长嘛!”夏衍接过话茬说,“他还是峨影的厂长哩”!”总理爽朗地笑起来,并握着朱的手说:“好哇!领导生产,又参加生产。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领导干部。”
周总理的这篇重要讲话,不仅端正了人们讨论《达吉》电影和小说时应有的态度,还为发扬艺术民主和繁荣文艺创作与纠正思想作风和文艺批评的关系,作了深刻而详尽的阐述。这以后发表的有关讨论的众多文章虽然看法不一,但都能平心静气而气氛热烈、思想活跃,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周总理的重要讲话也鼓舞了峨影的创作人员,使他们眼明心亮,放下包袱,振奋精神,轻装上阵,激起了更大的创作热情,为以后继续出佳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文艺界迎来新气象
在周总理讲话不久,《达吉》电影便在各地陆续公开上映。总理的讲话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全国有关报刊、文学杂志在浓郁的民主氛围内就作品的思想性、人物典型性、作品中人性表现、小说与电影的特点、文艺批评应有的正确观念和方法等展开热烈大讨论。[4]李厚基、冯牧、谢晋、黄宗英、李希凡、苏恒、陈朝红、履冰等众多文艺界知名人士都踊跃加入,畅所欲言。大讨论前后历时一年,各大型报刊刊发相关文章百余篇。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选编了1962年以前参加讨论的34篇文章,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62年10月出版发行《〈达吉和她的父亲〉讨论文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在1958年文艺评论界有人从“左”的角度批判巴人的“人性论”和徐怀中的影片《无情的情人》背景下,文艺界在经历了好一阵沉寂之后重新出现的一派令人振奋的新气象。
高缨在1962年第7期《文艺报》上发表了《关于〈达吉和她的父亲〉的创作过程》一文,公开阐述了《达吉》电影及小说的整个创作改编过程。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62年3月出版了高缨的《电影文学剧本——达吉和她的父亲》(附原著小说)。作家在后记中也对此作了详尽记述。高缨表明了《达吉》小说的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同时认为改编、摄制的同名电影也是好的——毕竟银幕上第一次表现了彝族人民的生活,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大凉山的新面貌,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彝汉两族的深厚情谊以及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孰料在十年动乱中,江青却颠倒黑白,污蔑《达吉》电影和小说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情味”的毒草,矛头实际指向周总理;由此从厂领导、编剧、摄制组主要成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斗、迫害。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颠倒的历史才还原到它的本来面貌。应该说,《达吉》电影和小说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现在回过头来看,正常健康的、民主争鸣式的大讨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并不多见;其中有益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周总理有关讲话中体现出的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在《达吉和她的父亲》电影上映50周年之际,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之际,仍值得回味与记取。
注释:
[1][2][3]《周恩来选集》下集,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23—348页。
[4]参见张学正主编《文学争鸣挡案》(1949—1999),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单位:峨眉电影制片厂(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