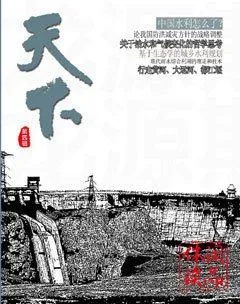漫谈生态水利规划
2011-12-29 00:00:00
休闲读品·天下 2011年4期

记者(以下简称记):今年的旱涝灾害比较多,先是武汉旱情严重,媒体就开始说这个地方缺水如何如何,于是三峡水库就开始加大下泄流量,但没起根本作用,接着,下雨了,一天就下了将近六个东湖的水量,旱涝急转,马上就出现了“到武汉去看海”的情况。请问,您怎么看这种现象?一次降雨到底能产生多少雨水?这些雨水能产生多少地面径流?报道说武汉一天就下了约六个东湖的水量,有这个可能吗?(编者注:当时的报道是在武汉市8494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不到一天就降下7亿立方米的雨水,而东湖最大水容量为1.2亿立方米,相当于5.85个东湖从天而降。)
何冰(以下简称何):我个人觉得这些现象是气候变化引起的,而造成的结果则应该归结到涉水设施不完善和城市化脆弱性上面。北京前一段时间也出现了“陶然逐波,机场观澜”的现象。
从第一个角度来看,简单地说一次降雨在地面上能产生多少雨水量是不准确的,因为不同的降雨形成的地表径流是不一样的。能否形成地表径流,形成多少,一要看它降在什么地面上,二要看降雨强度及其量的多少。一般降雨强度及其量比较小的话就会直接下渗,并不形成地表径流,在流域自然坡面上,有50%左右的降水会渗掉,只有一部分会形成地面径流;城市化后由于地面硬化及城市管网化,减少了下渗量,入渗的比较慢,形成的径流相对就比较大,且汇集速度快。另外,城市化后,河道功能发生了改变,减少了调蓄作用,径流在某些特定的低洼地区大量汇积,从而造成局部区域水量剧烈增加。一般来说,城市一年降雨量约60%左右都能够形成地表径流,一天的降雨量达到约六个东湖的水量是有可能的。因为,在“热岛效应”、季风气候与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下,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发生,东湖作为城中湖的水量本身也不是特别大,而且武汉地区亚粘土较广,渗透系数小,暴雨强度比以前大了很多,水也就容易在地表积蓄,从而,出现武汉一天就下了约六个东湖水量的情况。
目前,由于城市化进程中涉水设施不完善,对于水文特征变化的应对能力不足,造成了类似城市水害的频繁发生。
记:水利史专家周魁一教授给我们讲过这么一个段子,说是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有人建议把梁山泊的水排干变成良田,王安石觉得有道理,但是又顾虑失去蓄水之地,旁边就有个官员说在梁山泊旁边再挖一个湖。这是一个笑话,但是我们现在就在做着类似的事情。现在建的各种水库大坝,无非就是挖一个更深的湖,把一些浅湖的水汇集,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今年长江中下游大旱的时候上游的三峡水库加大了下泄流量,达到121.2亿立方米,但对武汉及周围地区来讲,两周还不如一天的降雨有效果。从水利的角度我们应该如何思考这个问题?
何:从大流域上不好说,毕竟我自己的关注点是在一个城域的范围内。现在一个地方的水资源大概有降雨、过境水、地下水、外调水等,但最主要还是靠当地降雨所产生的地表水。从降雨来说,过去有一个说法叫“一片天对一片地”,一个地区的水资源量大概就那么多。现在的城市化或者说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把太多本该属于水的土地给占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水有那么大的量就需要有那么大的地来盛着。过去有个提法叫“退耕还林”,现在叫“退耕还湖”,还湖干什么?就是调配水资源。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匀,不可能每天都下雨,它就是有时候不下,有时候下暴雨,这就必须有相应的“调节”措施,而自然的调节措施就是河湖。现在我们把太多的河道、湖泊给开发了,自然就没有这个调节功能了。
现在习惯说“九龙治水”,实际上是把水利的某个单一功能给放大了,做成了主要目标。我认为水利是一个“道”(编者注:是指哲学意义上的“道”的概念),是一个综合的,不是说某一个最好,而是综合最好。我们现在总结的水利有六个主要功能,即:水安全,主要是指防洪排涝,解决水多的问题;水资源,解决水少的问题;水环境,解决水质的问题;在前三者的基础上构建水生态;然后是水景观以及水经济。在过去防洪排涝,城市内的多归市政部门,城市外的归水利部门;水生态的水质部分归环保部门,动植物归林业部门;城市内的水系规划也多属于城建和园林。城建是下不到水里的,他不了解水下的环境,自然做不了水生态;而水利又只管城市外防洪排涝,不管岸上的事,不进城,所以造成了“九龙治水”这样的一个弊端。俗话说“有一利就有一弊”,从哲学角度来说,换个角度未必还是最好的,一个东西越亮,它的背面可能越暗,当我们强调某一方面功能时,是否也去考虑考虑可能受影响的另一方面。所以,我觉得,第一,我们缺少的是在一个区域内涉水事务的综合考虑;第二,缺少的是流域内以城乡行政区划为界定范围的中观层次规划;第三,缺少一套对公共资源的“哈定悲剧” 的应对平衡。(编者注:“哈定悲剧”即公共资源悲剧,最初由哈定提出。说的是当草地向牧民完全开放时,每一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增加的收入大于其供养成本,明显这是有利可图的。虽然对于单个牧民来说,他增加一头牛是有利的。但是如果所有的牧民都看到这一点,都增加一头牛,那么草地将被过度放牧,从而不能满足牛的需要,导致所有牧民的牛都饿死,也叫作公共资源悲剧。)城市化意味着现在的自然资源已经不能承载传统的水土资源利用模式,考虑到类似的生存和发展,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这种思维模式是不是能够持续?我们看到的河湖水体污染,其实都是表象,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以一种什么思维方式来协调水土资源”。比如,北京花了数百亿建设北京奥运水系,按理来说应该已经治理的差不多了,为什么一下雨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里当然有气候变化等不可控制因素,但是不是存在涉水体系和规划理念不尽合理等更深层的问题?
记:撇开其他体系原因不谈,对于奥运水系治水理念中的“雨污分流”,您是怎么看的?
何:我认为雨污分流是必须的。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地方,奥运水系在采用“雨污分流”的同时,借助奥运湖充分利用雨洪实现了水资源的良性循环,解决了自身的水资源需求。雨洪利用是一个集收集、储存、过滤、再利用的循环过程,而雨洪利用的前提就是雨污分流。由于生活污水相对比较均衡,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污水,所以污水处理厂可以做生活污水处理;雨水不是均衡的,要么没有,要么很多,是不可控的,它需要有一个调蓄工程,先调蓄起来再净化处理,循环利用。我们现在城市里面的排水系统只有传统市政的排污系统,缺少雨洪调蓄和雨洪利用的体系,奥运水系中的治水理念值得我们学习。
记:但是现实中我们并没有用奥运水系中的治水理念来治水,我们该如何看待现实中的做法,如何去改变它?
何:人类对自然界的期许到底是什么?把自然界变得完全风调雨顺那是不可能的,自然界有它自身的规律。可我觉得我们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遵循自然的规律去做事了,我们实际上是在改造后的自然,问题是改造后的自然它是不是可持续?所以,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关键是我们的这套体系在制定的时候它是不是相互适宜的、综合的。我们现在的很多做法不是综合治理,就像我们大家都喜欢水,于是挖了个湖,挖了个湖以后没水,就上别的有水的地方调过来,这是一个很简洁的方案,但却不是最优的、可持续的方案。如果我们没有可调的水怎么办?或者说我这样做对别人是不是有害?漓江就是特别明显的例子,“桂林山水甲天下”,为了深度开发旅游资源,桂林建了一个“两江四湖”,但是没好水,于是从漓江的上游建了一个渠道把水引过来,大概十几到二十几天换一次水。旅游是有污染的,中国传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我们现在是有了污染就把它排到别人家,“己所不欲”却给了别人。我们现在是“我”想好,“我”这儿没水就把别家的水引过来,引过来后别人那可能会有一些变化,然而有多大变化不知道。水调过来后“我”就把自己这儿该处理的污水通过水循环排到下面,这样实际上是把“我”应该承担的责任转嫁给了下游。真正解决问题,我觉得需要调整的是治水模式。
做城市规划的习惯于“把吃水布置在城市河流的上游,把排水布置在城市的下游”,如果把城市放在流域上一起来看,就会发现这就好像猴爬树一样,向下看都是笑脸,向上看都是猴屁股。怎么讲?你向上看都是人家的排污口,因为你的上游是别人的下游,但同时你又把你的污水排给了别人。我觉得要破解这种问题,流域共建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城市要把自己“家”里的事搞清楚,这就是水权的问题。
记:为什么不能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大流域规划?
何:据我了解有这样的大流域规划。但问题是宏观规划需要中观、微观规划支撑和实现,在城市层面这样的综合涉水规划还比较少,做水资源规划的只考虑把水资源规划做好,做防洪排涝的人只考虑把防洪排涝做好,但是好加好未必就是更好,因为水功能本身可能就有矛盾。现在缺的是在城市层面把涉水功能放在一个平台上,让其各项功能形成综合最好、综合最优。
记:那单从防洪来看,您觉得现在的城市防洪应考虑到哪些问题?
何:城市防洪,我觉得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职责,每一个部门都承担一部分。有人就说北方前两年降雨少,缺水,这两年雨又下的特别多,河湖蓄水量还远远不够,这是为什么?这是我们排的太厉害,排的时候没有综合考虑。我觉得,一方面是“资源利用问题”,当洪水来的时候考虑的多是它是“灾”,没想到它也是“钱”,也是“资源”,所以我们的河道修的很宽,行洪能力很强,当洪水来的时候,我们把可以作为资源的洪水排到了下游,当我们想去利用的时候发现水没了。另一方面是“流域共建问题”,洪水排到下游实际上是一种灾害转移,因为整个流域体系防洪标准是一致的,这个地方由于城市化建设防洪标准提高后,自身防洪安全没问题了,但下游地区可能就有问题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既有流域的问题,也有城市的问题。从流域系统而言,像“三峡”这类工程我觉得多了好,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调蓄库,才可能对水资源进行调配。问题是我们现在调水的工程只讲调水,防洪的工程只讲防洪,水环境的工程只讲水环境,缺少一个大区域范围内进行系统的调配。
我们试图在做一个有思想的城市河湖水系规划。河湖是载体,通过城市的河湖水系来解决几件事:水安全,防洪排涝的问题;水资源,解决区域水资源的调配和高效利用问题;水质的问题,怎么样实现水质好;水生态,怎么构建健康的河湖生态系统、水景观,怎么打造滨水宜居环境;在整个体系的最上层还有一个水经济问题,要建得起养得活,谁来出资,谁来维护,这就涉及到水土资源整合的问题。实际上滨水资源的稀缺性所带来的高价值,水利部门没有享受到,现在滨水土地给你去建设,建设之后土地升值,可以将一部分收益返回给水利部门。所以我们做的就是用土地升值来建设,水资源的循环来养护。现在城市治水既有技术问题,更多的是思维方式的问题。水是近于“道”的,治不好水是我们治水的观念可能存在问题。哲学是解决90%的问题,技术是解决10%的问题,治水是个哲学问题,我们缺的是治水的智慧,不是技术。
记:对于水资源的利用我们现在还面临这样的状况,几乎所有城市的地下水都存在超采现象,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认为既有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有认识方面的问题。
管理的问题是管理不严,抽取地下水最经济、又没人管,所以大家都抽。
认识的问题是大家没有意识到地下水超采的危害,认为地下水取之不尽,又没有危害。地下水并非取之不尽,抽完了就没有了,所以现在井打的越来越深;同时,地表水与地下水有紧密的联系,随着地表水污染,同时也加剧了地下水的污染。还有,随着地下水的下降,地下漏斗越来越大,地质构造中水的张力没有了,土壤中的空隙越来越小,一方面地表沉降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回灌、补充地下水越来越难。地下水超采造成的环境问题许多是不可修复的。
bc533cd472a08e6862d5549227aee44e记:地下水它的压力是地底下形成的,这个压力一破坏我们就恢复不了了,那么,地表水是靠什么力渗到地下去的?在下渗的过程中会不会受到地下水压力的抵抗?
何:简单讲地表水是靠重力下渗的,在下渗过程中会受到地下水的影响。
记:深层地下水与浅层地下水有什么关系?
何:在一个大的区域内,深层水与浅层水肯定是有紧密的关系。就比如一些古老的河床,它其实可能就有地下河,在某些地方被挡住了,它就会涌上来,涌出地面形成地表河流,而另一些地方出现断层,它就会向更深处流动。比如过去用的DDT农药,几十年已经不用了,但是从抽取的深层地下水中还是能检测到,说明它就是渗下去的。
记:有资料说郑州也缺水,一个紧挨在黄河边上的城市还会缺水吗?
何:郑州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它是这样算的,看的是人均水资源量。郑州市多年平均降水量635.6mm,人均水资源量不足200m3,只有全国的十分之一。而黄河水是一个公共资源,黄河流域的水权问题基本上已经明确了,已经分配到沿黄各个城市,每个城市有多少水是有指标的,郑州是不能随便抽取的。
记:您提到您未来的研究方向是基于城乡水务一体化思想的生态水系规划与实践。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何:我们试图在城乡或者区域这样一个中观尺度范围内,不仅从水利,更多的是从城市建设、环境、生态的角度来系统考虑涉水问题,把涉水问题作为一个体系来考虑,我们叫“城乡水务一体化”,城乡涉水问题协调好了,相关涉水功能问题也就解决好了。
实际上这里我们说的水务叫“城乡涉水事务”,不同于习惯上的市政给排水。为什么要说城市与乡村呢?实际上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把许多事情转嫁到了乡村,把农村的水资源调到了城市,把城市的污水排到了农村。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市是强者,农村是弱者,因此在规划中就应该兼顾两者的权益,我们叫做“城乡统筹和流域共建”。
记:从生态的角度看水及涉水事务,以这个理念来建设一个系统,从科学上看这个体系的可行性有多大?
何:从生态的角度看水及涉水事务,是在涉水问题规划中充分考虑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因素,是更加注重生态和可持续发展,它既符合哲学的辩证思想,又符合系统论的科学原理,我们认为在城乡这样的中观区域,建设“城乡水务一体化”这样一种符合生态理念的系统是完全有可能的。
记:如果将城市周边的水系建成自然化的小流域内的蒸发和降雨的循环,将城市下水设施建设成类似于法国那样的水平,包括一个整套的雨水收集利用体系,一个郑州市大概需要多少投资?
何:我不好把法国的涉水设施水平与国内比较,因为标准、措施和系统等无法比较,但可以举个例子,比如郑州,郑州生态水系规划建设投资大概一百多个亿。我说的是基于规划的投资,既不是一次性投资,也不是近几年的投资,而是一个远景规划估算总投资。实施过程中,既可以采取水土经济方式市场解决,也可以采用政策补贴方式杠杆撬动,当然也可以利用自然的修复能力——比如树木绿化种植小苗——慢慢形成。
记:那如果将整个黄河流域恢复到理想的生态环境下,您估计一下需要多少的投资?
何:这个一下子估计不出来,需要认真研究。但我觉得以“城乡水务一体化”、“城乡统筹和流域共建”的思想来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地建设,整个流域的生态恢复到理想状态是非常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