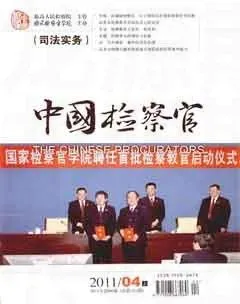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刑事推定问题
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我国刑法规定的毒品犯罪的一种,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相比,罪行较轻。从该罪名的立法沿革来看,非法持有毒品罪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堵截式规定,隐含了对毒品持有行为这一客观事实在法律规范上的推定,这种推定同刑法规定的其他持有型犯罪,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或其他物品罪等罪的推定情形相比,有其特殊性。同时,由于推定概念界定上的混乱,在对非法持有毒品罪以及其他毒品犯罪进行认定时,哪些证明行为属于推定,哪些证明行为属于一般的推论,仍有讨论的必要。
一、对刑事推定的刑事政策解读
在刑事诉讼中,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涉及到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也即休谟提出的对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以及从事实命题能否推导出价值命题。学者们对刑事领域认定事实的标准存在争论,集中在“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论辩上,作为案件事实的客观事实是唯一的,具有时空特性,但作为法庭认定的事实,即所谓法律事实,由于无法完全复制案件现场,只能靠相应的证据加以认定,这种认定是以人的主观判断为基础的,只可能无限接近于事实,而无法同客观事实完全一致,也就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针对这种偏差,不同法律制度的国家针对不同的法律关系确定了严格程度存在差异的证明标准和规则。其中,刑事法律由于隐含的对个人利益侵犯的风险较大,因此,各国对刑事诉讼中事实的认定标准都较高。然而,基于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的需要。国家也会对某些类型的犯罪相应地降低证明标准,并采用不同的证明规则以认定犯罪,刑事推定就是其中一种。
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国家,都有推定的相关立法。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第1—201条第31款规定:“推定”或者“假设”,是指事实的审理者必须发现该推定事实的存在,除非并且直至提出对该推定的不存在予以认定的证据。《法国民法典》第1349条规定:“推定为法律和审判员依已知的事实推论未知的事实所得的结果。”《意大利民法典》第2727条规定“推定是指法律或法官由已知的事实推测出一个未知事实所获得的结果。”
各国对推定从法律上予以规定,隐含了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刑事政策上的价值判断和刑法功能的调整,对此,赵俊甫从风险社会和社会风险的视角对刑事推定的解读很有启发意义,即工业社会带来的诸多犯罪因其对健康、环境和公共安全的威胁而使其成为政治话题,这类犯罪有毒品犯罪、黑社会犯罪、恐怖主义犯罪、腐败犯罪等。无论是对统治者还是对普通社会公众,这些犯罪都是极大的威胁,同时,这些犯罪类型由于隐蔽性强,其犯罪控制难度较大。贝克、吉登斯等人对风险社会的讨论是从社会学角度展开的哲学思辨,在这种语境下,“风险”的含义包括了社会学意义或刑法规范意义上的犯罪侵害的风险,亦即在“风险社会”这一后现代主义的话语体系中,不确定性和碎片化容易增加犯罪发生的风险,使社会个体既可能成为潜在的受害人,也可能成为潜在的犯罪人。风险的不确定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国家在应对这些不安感时会通过制度设计在社会中分配风险,具体到刑法制度,就是通过刑事政策隐含的政治导向的变化影响具体的刑法规范的制定,刑法修正案(八)通过对危险驾驶行为人罪化将其认定为危险驾驶罪就是一个例证。这个例证也是刑法刑事政策化的一个体现,“刑法如今处在一个叫做‘刑事政策’的更为广泛、更为开放的整体的核心”。刑事政策作为一种政治考量,必然会根据社会需要在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在社会转型的当前中国,表现为行政刑法、经济刑法和环境刑法等领域的发达。
从世界各国的立法来看,推定规则主要存在于与社会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这此领域的犯罪具有不同于自然犯的显著特点,即潜在的社会风险大,但是要证明这些犯罪,却存在较大的难度。通过刑事推定的适用来证明这些犯罪体现了对刑法保障机能和安全机能的价值偏好。但是这种价值偏好无疑会对潜在的个人产生人权保障上的风险,因此。推定规则在发挥着有效控制犯罪的功效的同时,常常作为辅助规则被使用。
二、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设置看推定的概念界定
罗森贝克的观点能够反映“推定”这一论域在国外的研究状况:“推定的概念十分混乱。可以肯定的说,迄今为止人们还不能成功地阐明推定的概念。”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均倾向于将推定理解为推论,如“推定是关于某事实存在与否的推断,而这推断又是根据其他基础或基本事实来完成的。”我国学者对推定概念的界定也不统一,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有:
第一,将推定与推论等同。“事实上的推定,本质上属于推论。它是根据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进行推理而得出的结论。就是说,当事实X在诉讼中已经确立时,则事实Y的存在,可以用一般的逻辑法则推出。”
第二,将推定与间接证据证明等同起来。“在诉讼领域,所谓推定,实际上就是在运用间接证据进行证明,即当不存在直接证据或仅凭直接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的真实性时,通过间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进行推理,假定待证事实为真。
第三,推定是基础事实与未知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推定是指通过对基础事实与未知事实之间常态联系的肯定来认定事实的特殊方法。”
这三种观点都较为常见。由于我国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均未对推定进行明确规定,因此,理论上的争议在所难免,何种推断属于证明,何种推断属于推论,难以分辨。我们在此以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设置为例,尝试厘清推定的概念,
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立法沿革来看,该罪的设置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常见难题,即在毒品被查获,但无法证明嫌疑人的走私、贩卖、运输或制造行为时,为了打击犯罪,以本罪处之。这一罪名隐含了对持有毒品行为这一事实在法律规范上的推定。有学者认为,从我国刑法规定看,目前至少存在44种推定,包括了“精神正常的推定”、“携带凶器抢夺的推定”、“无罪推定”等。我们认为将“精神正常的推定”、“携带凶器抢夺的推定”、“无罪推定”归为推定的观点值得商榷,这种划分过于宽泛,模糊了推定的内涵。有论者将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确立的推定规则统计为15种。认为推定规则大部分存在于制定法之中,既有涉及“明知”等主观要素的推定,也有涉及客观要素的推定,绝大部分具有明显的功利目的。这种观点大致正确,但却未明确列举具体的推定规范。龙宗智教授严格区分了推定与推论,认为“推定是法律问题,推论是事实问题,二者在诉讼中的意义和性质不同。推论是对事实的判定,属于事实问题。而推定是以法律的适用为前提,既为事实问题,也为法律问题,由于推定是依法‘拟制’事实,因此其本质应为法律问题。”宗智教授进一步认为我国刑事立法中的推定规范除了1997年刑法中第282条第2款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或其他物品罪以及第395条第1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两罪的法律规定中存在推定规范,其他持有型犯罪不存在推定规范,在司法实践中对要件事实不得进行推定。亦即,龙宗智教授将推定和推论明确区分,并将推定限定在法律规范层面,不承认事实推定,例如对主观方面的推断不是推定,而是证明。
有论者将推定情形概括为三种:其一,对犯罪主观构成要件要素的推定,包括犯罪故意、犯罪过失、犯罪目的、明知、意图等;其二,对持有状态下行为性质与款物性质的推定;其三,经官方机构依法确认的事实,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扩大了推定的范围。对于第一种情况,对犯罪主观构成要件要素的推定大多都不属于推定,而应当是推论式的证明,否则,推定和推论之间就没有了界限。第三种情况事实上也是一种证明而非推定,我们认为这种证明方式只是简化了证明的程序,即这些事实如同公理一样是不证自明的,为了提高证明效率省略了一定的步骤,如果需要,则可以通过完整的程序加以证明。对于第二种情况,我们认为属于推定,对此,有论者的观点具有借鉴意义,即推定具有规范性,“推定概念极易和推理、推论或间接证据证明等概念混淆,导致推定概念的滥用,对司法实践危害甚大。我们认为,推定是处理证据问题的标准化做法,规范性是其本质特征,也是将推定概念与相关概念区分开来的关键所在。推定是指依据法律直接规定或经验规则所确立的基础事实与待证事实之间的一种充分条件关系(即常态联系),当基础事实确证时,可认定待证事实存在,但允许受不利推定的当事人举证反驳的一项辅助证据证明的标准化规则。判断一项规则是推定还是普通的推论,重要标准之一是该规则是否具有可反复适用性,能否对解决同一类事实认定问题提供普遍指导。”这种观点同龙宗智教授的看法基本一致,即推定包含了事实问题,但根本上是法律规范问题。我们也同意这种观点:首先,推定确立的是基础事实与待证事实之间的一种充分条件关系,即学者们常说的常态联系,这种联系是一种事实推断;其次,推定除了事实上的推断之外,还必须包括法律规范要素。即是能够反复适用的标准化规则,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其次,推定允许行为人举证反驳,即推定包含了证明责任的转移。
三、非法持有毒品罪中推定的具体问题及立法建议
龙宗智教授对持有类犯罪的分析很有说服Z/pgnLOw9bvdigStB+gq4A==力,但我们认为存在一个问题,在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或其他物品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行为人持有的都是合法物品,之所以规定为犯罪,是因为行为人非法持有,即不具有持有的资格,而在非法持有毒品罪中,毒品属于违禁品,即只有少数人才可能合法持有,一般人持有均存在违法嫌疑。因此,对于财产、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或其他物品,刑法规范强调需要行为人说明来源,而这些违禁品则不需要强调,即行为只要持有这些违禁品,达到国家法律规定的量,就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因此。我们认为这类持有型犯罪存在隐含的推定,即通过法律规范推定这类持有行为为非法。实际上,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的持有行为是合法的,则可以进行反驳。同时,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设置是在无法认定其他毒品犯罪如走私、制造、运输、贩卖毒品时对犯罪行为的一种推定,这种推定通过法律条文将其规范化,从而使该罪的认定相比于其他持有型犯罪如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或其他物品罪更为容易。
如果能够证明持有行为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犯罪行为的一部分,则持有行为自动被这些行为吸收,属于典型的吸收犯问题。否则,就需要对持有行为进行单独认定。有论者认为“对于已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行为,同时又查获行为人持有一定数量来历不明的毒品的,目前通行的处理方法是,根据行为人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行为,推定其持有的毒品也属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性质,因而将持有的毒品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毒品加在一起,一并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定罪处刑。”对此,我们持不同意见。首先,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设置看,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对持有行为无法认定的难题,如果按照上述方式进行推定,该罪的设置就失去了意义,同时,该罪的最高刑罚为无期徒刑,配置规格已经足够高,不需要再认定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其次,从行为的危害性以及刑罚规定来看,非法持有毒品罪要轻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因此上述“推定”随意性过强,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从1990年的《全国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到1994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执行<全国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再到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均明确规定了对此类行为的认定规则,因此对上述情形应当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
有学者认为在毒品犯罪中还存在以下推定情形:对明知的推定、对贩运毒品行为的推定、对毒品持有人和所有人、对毒品共同犯罪的推定。从该学者的论证和我们对推定的界定来看,除了对明知的推论由于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作出的具体规定而具有规范性可以认定为刑事推定外,其他推论均不属于推定,而属于一般的推论,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于2005年4月25日公布的关于《毒品案件公诉证据标准指导意见》的通知规定可以运用推定来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观上是否明知:“推定‘明知’应当慎重使用。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可推定其明知,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1)故意选择没有海关和边防检查站的边境路段绕行出境的;(2)经过海关或边检站时,以假报、隐匿、伪装等蒙骗手段逃避海关、边防检查的;(3)采用假报、隐匿、伪装等蒙骗手段逃避邮检;(4)采用体内藏毒的方法运输毒品的。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能否推定明知还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判断:(1)受委托或雇佣携带毒品,获利明显超过正常标准的;(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有物、住宅、院落里藏有毒品的;(3)毒品包装物上留下的指纹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指纹经鉴定一致的:(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持有毒品的。”虽然本规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作出,其效力比法律和司法解释低,但却是对毒品犯罪中主观明知方面进行推定的明确规定。
必须承认,我们对刑事推定的界定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对案件事实的推论证明,从而导致对毒品犯罪中部分隐蔽性很强的行为无法作出有罪认定,降低打击犯罪的效果,但这样界定是为了防止刑事推定的随意性和扩大化,避免出现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侵犯人权的情形。各国规定刑事推定规则是为了应对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高犯罪风险,针对的犯罪类型有一定的限制,往往集中在毒品犯罪、黑社会犯罪、腐败犯罪等危害性大、隐蔽性强的犯罪类型上。同推论这种常规的证明方式相比,刑事推定是一种“例外制度”,必须加以限制。
为了减少侵犯人权的风险,在毒品犯罪案件中适用推定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要慎用推定规则,在无法搜集充分的证据尤其是直接证据证明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时,不得滥用推定规则转移公诉机关的证明责任;其次,在适用推定规则时,要赋予当事人以反驳权,以保障其权益;再次,推定并不意味着推定事实的客观真实性,而是根据法律规范从诉讼便宜的角度认定的事实,因此,推定必须有相应的法律规定:最后,由于推定规则认定的事实在盖然性上的缺陷,在对行为人量刑的时候不能适用死刑。
应当通过完善立法来应对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博弈,即通过修改法律或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增加毒品犯罪中的推定规则。具体可以借鉴我国香港地区的做法,通过立法扩展刑事推定的范围。香港2002年修订后的《危险药物条例》第45条关于毒品犯罪的推定适用情形较多,不仅可以推定明知,还可以推定毒品的持有人和制造人。
考虑到实践中的证明难度。我们建议国家通过立法或以司法解释的方式解决以下难题:第一,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关于《毒品案件公诉证据标准指导意见》的通知上升到司法解释或立法解释甚至法律层面,以提高毒品犯罪中对“明知”推定的效力,明确规定根据犯罪方法、发现毒品的环境、被告人的犯罪前科等推定其是否明知,避免无法证明毒品犯罪行为人主观方面要件的情况;第二,制定明确的推定规则,规定从行为人的行走路线、运输方式、行走距离和毒品数量等方面推定行为人是贩卖、运输毒品还是单纯的持有毒品,避免实践中无法认定行为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行为的情况;第三,借鉴香港的立法模式,规定从行为人实际控制的容纳毒品的容器以及容器的钥匙推定毒品的持有人或所有人,避免因人货分流等原因造成的无法认定毒品持有人或所有人的情况。
注释:
[1]赵俊甫:《风险社会视野中的刑事推定——一种法哲学的分析》,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1期。
[2][法]米海依尔·戴尔玛斯一马蒂著:《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卢建平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3][德]罗森贝克著:《证明责任论》,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页。
[4][美]乔恩·R,华尔兹著:《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弘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
[5]叶自强:《论推定法则》,载《诉讼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51页。
[6]赵钢、刘海峰:《试论证据法上的推定》,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1期。
[7]裴苍龄:《再论推定》,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3期。
[8]劳东燕:《认真对待刑事推定》,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2期。
[9]赵俊甫:《风险社会视野中的刑事推定——一种法哲学的分析》,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1期。
[10]龙宗智:《推定的界限及适用》,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
[11]赵俊甫:《重新认识刑事推定》,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3期,
[12]郑岳龙:《论推定规则在审理毒品犯罪中的适用》,载《人民司法》2005年第7期。
[13]李富成:《刑事推定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0—222页。
[14]郑岳龙:《论推定规则在审理毒品犯罪中的适用》,载《人民司法》2005年第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