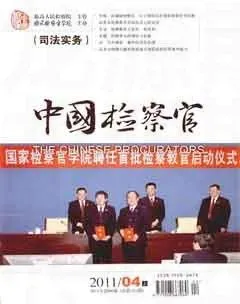销售伪劣商品罪中的刑事推定
销售伪劣商品罪时作为类罪而出现在中国刑法分则之中的。由于销售伪劣商品者并未群手参与伪劣商品之制造。因而其对自己所销售商品之实际质量未必有着确切了解。故此,在销售伪劣商品时,销售商是否“明知”该商品确属伪劣商品,也成为销售伪劣商品罪成立与否的关键所在。借助刑事推定,在具体个案中可以对销售伪劣商品者“应当知道”的“明知”心态予以确定。
一、“明知”属于销售伪劣商品罪的主观构成要素
我国现行刑法典中共有30个条文出现了“明知”一词。总则中的“明知”和分则中的“明知”既有联系但其含义却又各有殊异。正如台湾学者郑健才所言:“刑法总则上所称之明知,与刑法分则上所称之明知不同。前者,系作为基本主观要件之一种基础:后者系一种特定主观要件。犯罪须具备此特定主观要件时,刑法分则之明知为第一次明知,刑法总则之明知为第二次明知。”故此,刑法中的“明知”包括作为主观故意要素中明知故犯意义上的“明知”,即总则中的“明知”。此外,则是基于责任主义所要求的对客观构成要素的“明知”,即分则中作为主观构成要素的“明知”。而依照责任主义之意趣,若缺失此种“明知”,犯罪成立所必须的违法性认识便无从断定,也就更无成立犯罪可言。此种“明知”应体现为对行为性质、行为客体、行为结果、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他法定事实等客观构成要素的认识。由于任何故意犯罪都存在总则中的“明知”,对此刑法毋需特意说明。职是之故。学界对刑法中的“明知”的解释也多集中在分则中的“明知”。
刑法分则中的“明知”作为行为人主观要件构成要素,对犯罪成立与否意义尤为明显。销售伪劣产品罪中的“明知”,也属于分则意义上的“明知”。换言之,成立本罪也要求销售伪劣商品者必须具备“明知”的心态,即“明知”自己所销售的是伪劣产品,假药,劣药,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医用器材,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等伪劣商品。如果不具备这种“明知”就表明销售伪劣商品者没有违法性认识,而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其就不必对销售伪劣商品之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在中国刑法中。作为类罪的生产伪劣商品罪和销售伪劣商品罪虽然共同归属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一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并且诸如生产伪劣产品罪、生产假药罪、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等生产伪劣商品罪的具体个罪,与诸如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假药罪、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销售伪劣商品罪的具体各罪之间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逻辑关系。但生产伪劣商品罪和销售伪劣商品罪在主观构成要素之间还是有着些许差异。作为伪劣商品的生产者,一方面由于存在法定的产品质量保证职责,另一方面又亲自参与了商品生产的整个流程,故其对于其所生产的伪劣商品的性质必然有着清晰明确之认识,因而对生产伪劣商品者不必强调“明知”的主观心态。但对于单纯销售伪劣商品者而言,由于其自身并无法定义务监管商品的制造生产,而是需要经由各种途径从制造商或者代理商处获得商品,因此其对商品质量可能并不知晓。在商品美轮美奂的外包装及光鲜亮丽的宣传册误导下,尤其是在某些口若悬河的职业骗子极具煽动力的花言巧语坑蒙哄骗下,销售商往往不能准确辨明商品之优劣真伪。如在蓄电池经销商从生产厂家购进伪劣蓄电池时,厂方出具了合法的企业注册登记,厂家所供产品均包装完整,标识清楚正规。同时,厂方供给的每块蓄电池均附有出厂《产品合格证》,并能出具详细产品质量检验报告,而且还有“返厂退还”的责任约定。对此,并无检测手段和能力的经销商确实难以辨识其真伪。职是之故,即便该蓄电池经销商销售了伪劣蓄电池,亦不能绝对确定其具备销售伪劣商品的违法性认识。故此,刑法特意对销售伪劣商品罪设置了“明知”的主观构成要素,限制刑事责任的过分扩张,从而避免对因不知情而销售伪劣商品,但却不具备违法性认识的销售者施加刑事处罚。
二、刑事推定与销售伪劣产品罪中的“应当知道”
“推定”(presumption)一词源自拉丁文“sumo”和“pre”。“sumo”意指“事件被当作是真实的”,而"pre”则是“无须其它证明”。“推定”是一个聚讼纷纭难有一致定义的法律概念。早在16世纪,意大利律师Alciatus就抱怨道:“我们即将要处理的是日常事务中非常有用的问题,但推定却总是不厌其烦地扰人心绪;在借助推定进行一般性判断时,法学家和修辞学家都同样会感到困惑。”但事实上,概念之混乱并不影响推定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效用,因为推定本身就是非体系化的日常生活经验而不是以严密性著称的演绎逻辑的产物。推定首先可以归之为一种经验规则,如Waltz在界定何谓推定时说道:“推定的理论基础在于,根据人类共通的常识与经验,基础事实与待证事实经常相伴出现。”其次,推定和从个别性知识推出一般性结论的归纳推理关系密切。在演绎推理中,前提与结论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但归纳推理除了完全归纳推理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之外,从个别到一般的普通归纳推理中前提和结论之间的联系都是或然的。对此,美国前法官Aldisert曾指出:推定是得到并确认一项命题(结论)的过程,而该过程始终始于一项或多项其它的命题。其基于人类过去的经验,有合理的或然率(probability)让我们从做为证据的材料中推导出结论。”同时。由于“经验则大多并不表明命题完全符合事实的必然性,而只表现命题对应于事实的一定可能或频度,即盖然性。”故此,这种作为推定前提的经验规则并非在每个具体情境中都能成立,即它是可以证伪的,允许进行辩驳与反证。
销售伪劣产品罪中的“明知”需要借助刑事推定而予以确认。刑法中的“明知”分为“确实知道”和“应当知道”。其中“确实知道”是指明确、明白知道之意,而“应当知道”则指有合理依据和根据怀疑行为人有极大可能知道。“确实知道”对应着“谁主张谁举证”的过错责任,检方证明负担较为苛重。对于“确实知道”。检方只有拥有充分确切之证据才能予以证实。如在销售伪劣产品罪中,检方掌握的销售者和制假者之间的合作协议,或者获得的销售者承认售假的口供,或者查证属实的销售者已被工商部门告知其所销售的商品属于伪劣商品但仍然予以销售的,或者所销售的面粉已经腐败变质、霉变、生虫,或者销售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物及其制品,或者销售超过保质期的化妆品、农药等事实。只有这些证据事实才能充分证明销售者具备销售伪劣商品的“确实明知”。至于“应当知道”,则对应着过错推定责任。在缺乏充分确切证据时,检方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事实,采取特殊举证方法——刑事推定而予以认定行为人“明知”心态之存在。仍以销售伪劣产品罪为例。如果销售者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进商品,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销售商品,或者所出售的商品没有合格证或其他安全标识,只要经相关质检部门检验证明该商品确实属于伪劣产品,并且具备了销售伪劣商品罪具体个罪的成罪情节。则可推定其具备“应当知道”的“明知”心态,进而追究其销售伪劣商品罪的刑事责任。但若其有证据证明销售者是被不法生产厂家蒙骗的,则仍可排除其“应当知道”之主观心态,而不必对其归罪。
三、销售伪劣商品罪中刑事推定的具体适用
通过刑事推定可以确定在销售伪劣商品罪中售假者是否存在“应当知道”的明知心态,对此相关司法解释曾给予明确之指导意见。同时,除司法解释之外,对于某些销售伪劣商品的案件,适法者还要根据具体案情,以及日常生活经验规则进行实质判断。
(一)销售伪劣商品罪相关司法解释中的刑事推定
由于销售伪劣商品罪是常见的经济犯罪,故此司法解释对其也格外青睐,其中就有刑事推定的相关条款。如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第2条规定:“关于销售明知是假冒烟用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行为中的‘明知’问题根据《刑法》第214条的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烟用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销售金额较大的,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明知’,是指知道或应当知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应当)明知’:1、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进货的;2、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销售的;3、销售假冒烟用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被发现后转移、销毁物证或者提供虚假证明、虚假情况的:4、其他可以认定为明知的情形。”需要指出的是,本条虽然认为销售明知是假冒烟用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销售金额较大的,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但该纪要第6条同时认为:“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经营罪等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由于销售伪劣产品罪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都是销售金额超过5万元的才能构成犯罪,而销售伪劣产品罪法定刑又远远高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故此,销售明知是假冒烟用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销售金额较大的,在一般情况下应当认定为销售伪劣产品罪。故此,该纪要第2条中所确定的几种情况完全可以适用于销售伪劣商品罪,只要销售假冒烟用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者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进货的,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销售的,或者销售假冒烟用注册商标的烟草制品被发现后转移、销毁物证或者提供虚假证明、虚假情况的。都可以推定其具有“应当知道”的“明知”心态。
(二)司法解释之外根据日常生活经验规则而进行的刑事推定
正如上文所称,推定的基础是日常生活经验规则,而日常生活经验规则之内容通常较为笼统模糊,故此不可能会有明晰通透之界定。加之司法解释是一种准立法,在司法解释有限的条文容量下。也不可能包含具体犯罪中所有的可以适用刑事推定的情况。_12]故此,刑事推定本身具有开放性,并不拘泥于现有司法解释的规定。事实上,除了司法解释中所规定的“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进货的,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销售的,或者销售伪劣商品被发现后转移、销毁物证或者提供虚假证明、虚假情况”等事实之外,还有更多情况也可以推定出销售伪劣商品者的“明知”心态。例如,销售伪劣化肥者没有从正规合法手续的生产厂家或供货商处进货,或者无法出具正规的进货手续或合同的:又如,销售伪劣农药者所销售的农药外包装严重破损已经足以影响其内在质量的;再如,销售伪劣电器或压力容器者所销售的电器线头明显裸露在外或者压力容器外层严重锈蚀的;另如,销售大宗伪劣药品者所销售的药品上没有生产日期、生产日期模糊不清或者故意涂改生产日期的。这几种情况均和奉公守法,恪守职业操守的销售商的合法经营行为大相径庭。故此,就这几种情况而言,适法者只要根据日常生活经验规则。结合当时的主客观条件i就可以适用刑事推定,并据此认定销售伪劣商品者在主观具备“应当知道”的“明知”心态,从而以销售伪劣商品者所涉嫌之销售伪劣商品罪的具体个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注释:
[1]请注意作为类罪的销售伪劣商品罪与作为具体个罪的销售伪劣产品罪之间的区别,不要将二者混为一谈。
[2]其中总则部分1处,即总则第14条规定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分则中的“明知”共有29处,属于某些具体犯罪的必要构成要件之一。
[3]郑健才:《刑法总则》,台湾三民书局1982年版。第96页。
[4]周光权:《明知与刑事推定》,栽《现代法学》2009年第3期。
[5]如就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与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而言,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为的前提和基础,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为是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行为的自然发展,是为了实现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的最终目的行为,
[6]WiUiam Mawdesley Best,A Treatise on Presumo—Uons of Law and Fact;With the Theory and Rules ofPresumptive or Circumstantial Proof in Criminal Cases?General Books2010.p22.
[7]WaltzJon R.Introducfion to Criminal Evidence,Wadsworthl997,p275.
[8][美]鲁格罗·亚狄瑟:《法律的逻辑》,唐欣伟译,台湾商周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9]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页。
[10]如就销售伪劣产品罪而言。销售金额超过了5万元的;又如就销售劣药罪而言,销售的劣药对人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的;再如就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而言,销售的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危害人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