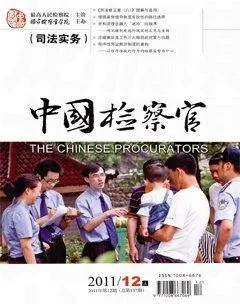雇用犯罪中雇佣双方的罪责认定
雇用犯罪时一方与对方就实施某种特定的犯罪达成协议,一方提供财产性利益或者其他利益,要求另一方单独或者与其共同实施特定犯罪的情形。其中提供利益的一方为雇主,对方为受雇者。根据不同标准,可以雇用犯罪划分为明确授意的雇用犯罪和概括性授意雇用犯罪;纯粹的雇用犯罪和不纯粹的雇用犯罪。
明确授意的雇用犯罪是指,雇主要求受雇者实施犯罪行为,且将构成犯罪事实,如犯罪之客体、犯罪之行为、犯罪之结果均明确告知受雇者。概括性授意的雇用犯罪是指,雇主向受雇者传达犯罪意图,要求受雇者实施犯罪行为时,已经认识到受雇者即将实施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但对犯罪事实无具体确定认识,没有向受雇者传达犯罪行为的具体内容(行为手段、行为后果等犯罪构成要件)。
纯粹雇用犯罪是指雇主向受雇者传达其犯罪意图后,不参与实施具体犯罪行为,雇主成立教唆犯,俗称为“只动口、不动手”的雇用犯罪。不纯粹雇用犯罪是指雇主向受雇者传达犯罪意图后,参与具体实施犯罪行为,雇主即成立教唆犯、也成立实行犯,俗称为既动口又动手的雇用犯罪。
一、雇角犯罪的性质
犯罪的性质就是确定犯罪行为所属的犯罪种类和所触犯的罪名,明确犯罪性质,就为确定罪责打下了基础。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一类犯罪现象,雇用犯罪表现形式多样,故其犯罪性质不可能是单一的。存在着共同犯罪和非共同犯罪两种性质,在司法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认定。
(一)一般情况下,表现为共同犯罪
1,雇主授意后参与实施具体犯罪行为。在雇用犯罪的场合,如果雇主雇用受雇者后,还亲自参与实施了犯罪行为,符合《刑法》第25条的规定。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成立共同犯罪必须要求主观上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客观上具有共同犯罪行为。雇主与受雇者均为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或者单位,二者均可以构成犯罪主体:雇主是犯意的制造者,受雇者接受雇主的授意后,二人即共同认识到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导致危害社会的结果发生,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在此主观心里态度的支配下,雇主与受雇者的行为彼此联系、互相配合,共同指向同一犯罪事实,他们的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2,雇主成立教唆犯的共同犯罪。在雇主不参与实施具体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其雇用行为是一种通过利诱、收买等方式故意唆使他人犯罪,从而实现自己犯罪意图的行为,符合我国《刑怯》第29条关于教唆犯的规定,应当认定雇主为教唆犯。
(二)特殊情况下,表现为‘‘间接正犯,,
当受雇者系无刑事责任年龄或者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受雇者本身不能成为犯罪主体,受雇者完全成为雇主的犯罪工具,雇主与受雇者之间不能成立共同犯罪,雇主构成刑法理论上的“间接实行犯”或者“间接正犯”。
二、雇主与受雇者的罪名的确定
雇主向受雇者授意实施犯罪行为,受雇者接受雇佣后,二者形成犯罪契约,此时,雇佣双方的主观联络的内容即犯罪故意内容是一致的,考察整个犯罪过程,最终可能出现雇用双方罪名不一致的结果,原因在于受雇者的实行行为过限。那么,如何认定受雇者的实行过限呢?
在上文中我已写明按照不同的标准,将雇用犯罪分为明确授意雇用犯罪、概括性授意雇用犯罪:纯粹的雇用犯罪、不纯粹的雇用犯罪。但无论怎样划分雇用犯罪,司法实践中判断是否为受雇者的实行行为过限,还是要区分各自情况下属于明确授意还是概括性授意,只不过在不纯粹的雇用犯罪中判断明确或概括,情况会更加复杂一些,但判断的基本方法没有什么不同,只要明确了明确授意和概括性授意两种情形下受雇者实行过限的判断方式,就基本解决了受雇者实行过限的问题。所以,我将纯粹雇用犯罪、不纯粹雇用犯罪放在明确授意、概括性授意范围内讨论受雇者实行行为过限的认定。
(一)明确授意的实行过限的认定
1,雇主不在场的情形。对于雇主不在场的明确授意的实行过限的认定较为容易,只要受雇者实施了超出雇主明确授意范围的行为,即认定受雇者的实行行为过限。
2,对于雇主在场的明确授意的实行过限的认定。雇主在场对受雇者的实行过限行为未加制止,雇主对受雇者明确授意后,雇主对受雇者超出授意范围的实行行为予以鼓励、默许的,或者事后资助受雇者逃跑的,说明雇主在主观上对实行过限的行为处于积极追求或者放任的状态,属于临时起意的共同犯罪,不属于共犯过限。雇主在场对受雇者实行过限行为制止,雇主在场对受雇者超出授意范围的行为进行制止、劝住、或者设置障碍,而受雇者执意实施过限犯罪行为的,说明雇主主观上没有就受雇者的实行过限的行为达成共同犯罪故意,应视为过限行为。
3,在实践中受雇者的行为与雇主的行为未完全一致时是否认定实行过限。对于表面上违背雇主的具体要求的行为,是否认定为实行过限?试举一例:甲雇用乙砍伤丙的左手,而乙不仅砍伤丙的左手还砍伤了丙的右手。不能认定乙的行为系实行过限。因为无论砍伤左手还是将两手都砍伤,其行为在本质上都是对被害人进行人身伤害,都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健康权,都属于故意伤害的范畴。只要本质上没有超出雇主的授意内容,就不属于实行过限。
(二)概括性授意雇用犯罪的实行过限的认定
依据概括性授意雇用犯罪的概念,概括性授意的范围既包括性质,就是实行何种性质的犯罪、也包括结果,就是雇主希望达到的结果。司法实践中,概括性授意的雇用犯罪有多种形式,根据不同形式认定受雇者的行为是否为实行过限。
1,雇主概括性授意后,没有具体实施犯罪行为。雇主成立教唆犯,如雇主使用“教训”、“摆平”、“整他一顿”、“收拾他,,等模糊语言进行授意。此种授意在行为手段、行为结果方面往往包含多种含义,一是轻伤害、二是重伤害、三是死亡、四是概括性授意,即伤害、死亡都在雇凶者的授意范围之内。在不同场合、不同语境下,可以有不同理解,容易产生分歧,要准确判定受雇者的实行行为是否过限存在一定难度。要结合雇主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性质、授意场合、授意的作案时间、地点以及事后对犯罪结果的态度等方面综合判断。
对于这种概括性的授意,实际的危害结果完全取决于实行行为的具体实施的状况,致人轻伤、重伤甚至死亡的结果都有可能发生,都是因为雇凶者的概括性授意而使受雇者产生的犯意引起的,均可以涵盖在雇主的授意范围之内。因为是雇凶者的授意使被教唆人产生了犯意,实施了教唆内容涵括内的犯罪行为。无论受雇者实施的行为造成何种后果,只要其实行行为没有明显超出雇凶者的授意范围或者希望达到的结果,都不应视为实行行为过限。司法实践中,判断是否明显超出雇主的授意范围的原则是雇主是否已经预见或者能够预见到受雇者之后实施的犯罪行为,如果没有预见且不能预见,则受雇者的行为属于超出雇主授意范围的过限行为;反之,则不属于过限行为。
2,雇主概括性授意后参与了犯罪前的策划和准备。可以通过雇主与受雇者共同准备的犯罪工具判断其授意内容。如准备的砍刀、枪支、炸药等足以致人死亡的犯罪工具,可以判断雇主的授意内容为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致死。
3,雇主概括性授意后参与了犯罪的实行行为。雇主笼统授意后,在参与犯罪的实行行为过程中对受雇者在现场实施的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触犯刑法规定的重罪名的行为没有制止,而是予以鼓励、默许的,或者事后资助受雇者逃跑的,说明雇主在主观上对实行过限的行为处于积极追求或者放任的状态,属于临时起意的共同犯罪,不属于实行过限。对上述行为制止、受雇者不听制止,执意实施的,应认定受雇者实行过限。
综上,关于如何认定是否超出雇主的授意范围,我认为:不管是雇主明确授意、还是概括性授意,认定受雇者实行过限都应当首先考量雇主告知受雇者的内容,分析雇主对受雇者授意时,是否已经预见到或者能够预见到受雇者之后实施的犯罪行为,如果雇主没有预见且不能预见,则受雇者的行为属于超出雇主授意范围的实行过限行为;反之,则不属于实行过限行为。
三、雇用双方在雇佣犯罪中的作用
雇用双方构成共同犯罪时,要准确适用刑罚,除了确定罪名,还应确定雇用双方的行为对社会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危害的大小,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危害大的,量刑重、危害小的,量刑轻。
(一)主犯、从犯的确定
1,雇主均为主犯。在纯粹的雇用犯罪中,雇主成立教唆犯,按照我国《刑法》第29条:教唆他人犯罪,应当按照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对教唆犯追究刑事责任时,借助主犯、从犯的一般处罚原则。我认为,此系对教唆犯处罚的一般原则。雇主刑法地位如何,还要根据其在雇用犯罪中的作用予以衡量,根据《刑法》第26条对主犯的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组织犯是主犯的一种,除此以外,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在纯粹的雇用犯罪中,雇主不仅使受雇者产生了犯罪意图,而且为了实现其犯罪意图,积极为受雇者提供物质利益或者其他利益,在雇用的背后,隐藏着对犯罪后果的积极追求,雇主与受雇者的以利益为纽带的契约关系,保障了危害结果发生的必然性,与一般教唆犯相比,其主观恶性更深,所起作用更大,只能以主犯论处。
在不纯粹的雇用犯罪中,雇主既是教唆犯、又是组织犯、实行犯,在共同犯罪中不仅承担指挥、策划、组织的作用,还参与了实行行为的实施,此行为对犯罪结果的发生必然起主要作用,应认定为主犯,
2,受雇者可能成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雇主只能构成主犯不同,因为受雇者可能是一人或者多人,在雇用犯罪中所起作用不同,其在雇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固定的,其刑法地位要根据其在雇用犯罪中的具体影响,做出不同认定,可能是实行犯、也可能成为帮助犯,对犯罪结果起到主要作用为主犯,仅起次要、辅助作用的为从犯。受雇者在被威胁、强迫情况下亦可能构成胁从犯。
(二)雇用双方同为主犯的情形下,如何区分对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
1,在纯粹雇用犯罪中,直接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受雇者的刑事责任重于雇主。直接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受雇者的实行行为对于刑法保护的法益具有现实侵害性,致危害结果产生的直接原因;雇主的教唆行为的核心是造意,使受雇者产生犯意,但毕竟不是犯罪的实行行为,不具有现实侵害性,被教唆的人既是教唆犯的犯罪对象,又是教唆犯达到犯罪目的的犯罪手段,其主观上想要使危害结果产生,需要依赖、借助于受雇者的实行行为,雇主的教唆行为从属于受雇者的实行行为,是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间接原因,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既然危害结果是由实行犯的实行行为直接导致,教唆犯从属于实行犯,那么,直接造成危害结果产生的实行犯比教唆犯的作用更大。
主观上,受雇者的主观恶性更大。受雇者毕竟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即具有完全的辨认和控制能力,雇主对其授意后,其主动与雇主达成共识,决议实施具体犯罪行为,且受雇者与被害人没有恩怨,甚至彼此不相识,仅为得到雇主提供的利益,即实施犯罪行为,相对雇主而言其主观恶性更大,
2,在不纯粹的雇用犯罪中,要根据雇主的参与程度做不同的认定。(1)雇主在雇用他人后又与被雇者一道积极策划、组织、指挥犯罪行为,由受雇者实施了具体的犯罪行为。如果危害结果是在雇主的精心组织、策划、指挥下发生的,受雇者只是机械地执行雇主的已经精心制定的犯罪计划,那么,雇主的组织、策划、指挥的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具有更大的作用,被评价为更为严重的行为。如果雇主虽然实施了一定程度的组织、策划行为,但此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并没有起到关键性、支配性的作用,受雇者的实行行为更为严重。
(2)雇主在雇用他人后又与受雇者一起实施危害行为或者帮助受雇者实施危害行为。相对于纯粹的雇用犯罪案件,雇主在此情形下的刑事责任相对更重。但也不能当然地认为雇主的作用就一定重于受雇者,仍应考量雇主、受雇者在犯罪实行中所起的作用的大小,如前文所述,实行犯存在不同情形,根据所起作用大小,分为主要实行犯、次要实行犯。当雇主雇用他人后又参与主要犯罪实行行为的,雇主的罪行更为严重:如果雇用他人后,仅实施了次要的实行行为,或者辅助实行犯实施犯罪行为,虽然其行为与危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但原因力的大小远不如危害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因危害后果是主要实行犯直接造成的,雇主的地位次于主要实行犯的地位。
总之,不管是纯粹的雇用犯罪还是不纯粹的雇用犯罪,在构成共同犯罪的前提下,雇佣双方多名被告人同为主犯时,要准确对其进行刑罚裁量,就要准确确定其对危害结果所起到的作用的大小,从主观、客观两方面加以综合分析,对危害结果起到最为关键作用的,量刑最重;反之,量刑相对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