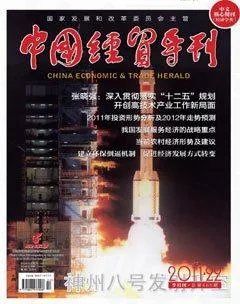加快土地制度创新 促进城镇化质量提升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依托。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到2010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49.7%,城镇人口总规模达到6.66亿,但其中流动人口达到2.21亿,而农民工规模则超过1.6亿。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使其真正融入城镇,是我国未来城镇化的关键。
当前,全国众多地区都在积极探索通过农村土地制度变革,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常见的模式如宅基地换房、承包地换社保等。土地是农民重要但又无法有效盘活的资产,因此,改革土地制度已成为当前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不得不解决的问题,这也是实现大规模的流动农民工市民化、从而有效提升城镇化质量的关键。
一、现行土地制度下的土地“双挤”困境
(一)城镇化加快推进过程中,城乡建设用地同步增加
1、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
2000—2008年,我国经济经历快速发展,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13%,期间城镇工矿以及交通类建设用地增长率约为3.6%,城镇类土地规模扩张幅度超过25%。与此同时,城镇化率由36.2%提高到45.7%,提高约10个百分点,大大低于城镇土地规模增加比重。土地城镇化显著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
2、农村建设用地并未随人口大规模转移而显著减少
1996年,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约为1646.7万公顷,到2000年,达到1655.9万公顷后,开始出现小幅下降,到2008年,农民居民点用地总规模为1653.2万公顷。在此12年间,城镇化率由36.2%上升到45.7%,农村人口则由8.51亿下降到7.21亿,农村人均居民点用地由193平方米增加到230平方米,远超国家上限标准150平方米。根据周其仁的估计,全国1650万公顷左右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中,村内空闲地面积约占村庄总面积的1/8。
(二)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是造成土地“双挤”局面的重要原因
城乡二元的土地管理制度一方面限定了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范围,另一方面,也通过土地用途管制,严格限定了农地转用。这赋予国家城镇建设用地垄断所有者的身份,从而形成了城镇建设用地和乡镇建设用地价格、农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的价格差。农村建设用地、特别是城市规划圈内农村建设用地相对而言较接近国有建设用地价格,而农地转用则存在巨大的管制价格差,这也导致农民有将耕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的冲动,而在偏远地区农民则因土地无法顺畅流转、资产价值无法显化而不愿退出宅基地的问题。
二、农民工的土地情结:难以割舍还是无法割舍
(一)农民工市民化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城推进了城镇化。据统计,2009年,进城农民工占全国人口的比重达12%。1982—2009年的27年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25.5个百分点,而进城农民工数量贡献了近12个百分点。
虽然农民工规模不断扩大,但就户籍角度看,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较慢。1980—2008年,全国非农户籍人口增长约3亿,综合考虑期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因征地以及农村青年通过参军或升学进入城市农村人口数量,实际通过农民工市民化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只有2000万人,占农民工总规模的1/10。未来,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要高度重视城镇化发展质量,而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至关重要。
(二)多数农民工具有在城镇定居的意愿
根据2009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项针对农民工的调查:外出务工者以年轻人为主,30岁以下的占67%,40岁以上的约为12%;从务工者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看,近70%的人在进城前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这也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将是市民化的重点。从实现稳定就业、家庭随迁、从事农业生产时间、年龄等方面考虑,具备在城镇定居能力的农民工占总量的50—70%。在加强政策引导、鼓励持中间态度的农民工落户的情况下,实际可市民化的农民工占总量的比例达75—80%。
(三)资产价值难以实现成为农民工放弃土地进城的一大障碍
总体上,我国当前的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进城农民工的公共服务缺失为代价的,这就使得很多农民工虽然有定居城镇的意愿,但并不敢轻易离开农村。而农村土地资产价值难以实现,更使农民失去一种可以筹集资金进入城市的方式。虽然我国土地权利体系中尚没有土地发展权的概念,但对农村农用地转用的政府垄断和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种种限制,实际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农村土地的发展权。特别是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已经成为建设用地的农村土地,流转也极为困难,土地资产价值难以实现;而农民对集体建设用地的低成本保有(作为集体的一员,农民无偿、无限期地获得宅基地使用权),使得农民不愿也无需放弃土地,这也不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利用。
三、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面临一些有利条件
——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基本进入城镇型社会。到2010年,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按最近公布的“六普”数据,城镇化率已近50%。今后,城镇化仍将较快推进,但相比前一个时期,速度可能略有下降,因此,城镇土地扩张的速度也将减缓,由此引发的土地利用矛盾也会减小,在矛盾有望缓和的时期,加上较强的经济和财政实力,开展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以较好地控制风险。
——综合考虑城乡人口比重,城乡收入差距将逐步进入开始下降的通道,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如果采用反映城乡人口比重和城乡收入情况的泰尔指数计算城乡收入差距,自2007年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下降的趋势,该指数由2007年的0.165下降到2009年的0.16。
——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开始改变,刘易斯拐点可能出现。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变化反映了供求状况,从农民工吸纳“大户”珠三角的情况看,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05年前后,几乎长达20年的时间内,农民工实际工资变化不大。从2007年前后开始,这一状况有较大改变。很多学者也据此判断我国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对此,仍然还有一些争论,但劳动力已经开始出现结构性甚至部分地区是总体性短缺已是事实。工资水平的提高和劳动者谈判能力的增强,将使农民工具有更强的能力扎根城镇。
四、推进土地制度创新,促进城镇化质量提升
(一)试行农地发展权交易,显化农村土地资产价值
探索设立农民土地发展权,城镇用地开发要通过发展权交易,尤其是要赋予城镇规划圈外农村土地发展权,使城镇规划圈外、特别是远离都市区农民享受土地增值收益。同时,完善土地增值税税收体系,调节不同区域农民土地资产收益,避免因征地而产生的不合理的“暴力”和“暴富”。
总结全国各地土地产权交易所的经验,建立土地发展权交易平台,为土地发展权或指标跨区交易创造条件,并借助交易平台,形成土地发展权或建设用地指标的合理价格,显化土地资产价值,为农民是否放弃土地以换取城镇户籍、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提供依据。
(二)加快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按照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切实缩小征地范围的要求,加快制订和完善公益性用地目录。切实完善征地补偿机制,严格按照同地同价原则,给予农村集体和农民合理补偿,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问题,力争使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达到所在区域城镇居民生活中等水平的标准。
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尽快建立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通过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制度。探索农民土地持股进城或以其它参与开发经营的方式,切实保障农民建设用地经营权益。
(三)促进城乡要素双向互动,实施“结构化”城镇化政策,协调城镇发展与新农村建设
加快改变长期以来农村向城市单向输入发展要素的局面,按照稳步试点、风险可控的原则,在严格限定规模的前提下,允许有条件的地区适度放宽城镇资本及人口进入农村的限制,促进农村建设用地市场发育和完善,增强农村发展活力。
针对不同年龄结构农民工的定居意愿,在职业培训、社会保障等各方面提供不同的组合,以结构化政策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同时,通过资金支持、技能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快培养新型农民,增强农村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增强农业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协调促进城镇健康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四)加快社保、户籍等配套制度改革,形成推进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合力
土地、社保、户籍制度是维系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通过土地制度创新促进城镇化质量提升,还需要多种配套制度的完善,其中社保和户籍制度尤为重要。总体思路是强化社保、弱化户籍。
逐步统一城乡社保体系,以所占用土地的增值收益或土地税费充实农民工社保账户,适度提高农村养老金账户统筹层次。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剥离附加在户籍上的各种权益和福利,将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转向大城市,试点大城市户籍制度放开。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