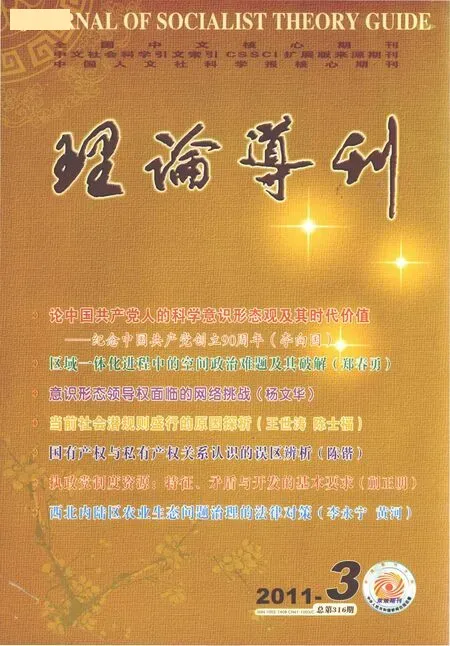中国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和方式
李占乐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郑州450001)
中国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和方式
李占乐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郑州450001)
无论从学理上、参与效果上还是利益取向上,中国公民社会都有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必然性。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可以划分为人大政协、政府机关、公共舆论、个人接触和司法裁决五种。现阶段,不论是中国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还是方式,都存在着单一、不足的特点,呈现出相当的不均衡性。
公民社会;民间组织;公共政策制定
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逐渐兴起和发展壮大,公民社会越来越多地参与了政府的公共政策过程,其中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活动显得更加重要和突出。公民社会即民间组织日益普遍地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今后确定不移的发展趋势。总结当前中国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和方式,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公民社会与民间组织
学术界一般认为,公民社会是指公民在国家或政府和营利性企业之外进行自愿结社和自由交往的社会公共领域,由各种非政府而且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所构成的民间组织是公民社会的主体和构成要素。例如当代西方研究公民社会的权威学者戈登·怀特指出,“当代使用这个术语的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公民社会的主要思想是:它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1]公民社会的发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民间组织的发展水平来衡量。
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民间组织,是指具有共同利益或价值追求的公民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包括公民的维权组织、各种行业协会、民间慈善公益组织、联谊性组织、社区组织、互助组织、兴趣团体以及公民的某种自发的非正式组合等等。学者们一般公认民间组织具有四个基本特征: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相对独立性和自愿性。但在中国,由于公民社会发育的不成熟和特定的国情条件,现阶段民间组织在这四个特征上都还体现得不够充分和完全。在中国,官方一般将民间组织称为社会组织,并将其划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大类;学术界往往将民间组织称为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并经常将其划分为官办非政府组织、官民合作型非政府组织和纯民办非政府组织三类。
二、中国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必然性
公共政策制定是公共权力机关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以达成社会公众意愿的过程。中国公民享有广泛的参与政治生活和政治决策的权利,这被载入宪法和法律,是国家人民主权原则的重要体现。这一价值取向决定了公民必然参与和影响公共权力机关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公共政策及其制定过程以促进、实现和维护公民权利为基本的原则和目标。中国公民社会是公民权利产生的空间,以实现和维护公民权利为价值取向。公民社会和公共政策制定相同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必然性。
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提升公民参与效果的必然要求。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实际效果取决于公民的组织程度。单个分散、无组织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软弱无力和低效的,也会对公共政策制定产生负面影响。公民只有通过各种民间组织形成一种规范性的认同关系,放大其行动的影响力,进而在形成公共议程、评估政策方案、政策方案抉择及政策合法化中形成强有力、有效的和理性的参与。因此,公民必然会通过建立或加入公民社会组织即民间组织来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以增大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效果。
公民社会的利益取向决定其必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维护、实现和促进社会公共利益是中国公民社会的目标和归宿。民间组织作为非营利性组织,是公民基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共利益或群体公共利益而自愿结成的团体。因此,公民必然会通过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向政府提出各种利益要求。公民社会为公民提供了公共利益表达、维护和增进的组织途径。而公共政策及其制定过程也以维护、实现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追求。两者利益取向的一致性决定了公民社会必然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
三、中国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分析
1.中国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关于中国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不论是对于“渠道”如何界定,还是公民社会参与的渠道具体有哪些,目前学术界均没有达成共识。比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团体主要通过民意代表机制即人大、政协制度、行政决策机制和公共舆论机制来参与政治,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2]很多学者都将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分为体制内的参与和体制外的参与两大类型或渠道。本文认为,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是指公民社会通过接触或利用哪些机构或个人来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按照这种界定,中国公民社会为了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直接接触和利用的对象主要包括人大政协、政府、各类媒体、党政官员和司法机关五个方面,相应地可以将公民社会参与的渠道划分为人大政协、政府机关、公共舆论、个人接触和司法裁决五种渠道。当然,这五种渠道的划分只是相对的、人为的划分,经常并不能截然分开。而且由于五种渠道所利用的对象在现实中具有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复杂关系,公民社会在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经常是同时运用多种渠道,以最有效、最大限度地实现参与的目标。其中公共舆论、个人接触、司法裁决基本上属于体制外、非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参与方式一般都是非制度化的;公民社会通过接触人大政协和政府机关来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则是体制内的渠道,参与的方式既可能是制度化的,也可能是非制度化的。
2.中国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渠道的现状。在中国,目前虽然有这五种公民社会参与的渠道,但公民社会对这五种渠道的参与和利用却是相当单一和不均衡的。公民社会最经常使用和最主要的参与渠道是政府机关,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偏重于行政参与。公共舆论、人大政协、个人接触和司法裁决这四种渠道利用得都比较少。以人大的参与渠道为例,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民间组织对人大立法工作的参与呈现出越往基层参与的社团越多的态势,但从总体上看,民间组织对人大立法工作采取活动进行影响的非常少。曾对全国人大开展影响活动的社团仅有23个,占被调查社团总数的1.7%;曾对省级人大开展影响活动的社团有79个,占总数的5.6%;曾对地级市/区级人大开展影响活动的社团82个,占总数的5.8%;曾对县级人大开展影响活动的社团97个,占总数的8.5%。[3]294-295可见,在现阶段,民间组织还很少利用人大的渠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
中国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中政府的中心地位和人大的边缘地位,是和中国当前的政治现状相符的。尽管宪法规定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但现实权力运作中党政机关掌握着实质性的权力,人大更多的是行使程序性的权力。加上目前公民社会参与人大决策的制度建设滞后,只能采取非制度化或制度化水平低的方式进行,更加使得公民社会对人大的政策参与较为少见。反观政府,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政府处于公共事务处理的核心地位,仍是掌握和分配各种社会资源的最重要的核心,因而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居于无可置疑的核心和主导地位,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当然会主要集中到行政参与上。
此外,公共舆论在近年来的重大公共政策制定和调整、民众强烈不满的政策焦点事件参与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和效果。虽然中国没有建立利益团体游说制度,但个人通过写信或当面接触党政官员,向其反映有关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在中国特定的国情当中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人大政协的参与则主要是依赖非制度化或制度化程度低的方式进行,如立法听证、公开征集意见、游说人大代表等,通过政协的参与目前还十分罕见。寻求司法裁决的渠道在中国由于没有建立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司法机关的不独立而受到极大的限制,也非常罕见。
如果我们对这五种参与渠道按照使用频率进行排序的话,从多到少的顺序应该是政府机关、公共舆论、个人接触、人大政协、司法裁决;如果从参与渠道使用的效果的角度进行排序,从近十年的情况来看,公共舆论无疑应该排在第一位。
四、中国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方式分析
1.中国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方式。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方式根据不同的视角可以进行多种划分和分类,对此郑准镐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根据公民社会参与政策制定的主体性,可以将参与方式划分为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根据参与政策制定的制度化与否,可以将参与方式分为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根据参与政策制定的主动性,可以将参与方式分为主动参与和委托参与;根据参与过程中的联合方式,可以将参与方式分为单独参与、联合参与以及与政府合作参与。[4]贾西津将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划分为建设性提议、参与式合作和利益表达即政策倡导三种模式。[5]也有学者更为具体详细地划分,列举出许多种公民社会参与政策制定的具体方式方法。本文认同最后一种对“方式”的界定和划分方法。
本文认为,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方式是指公民社会通过各种渠道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具体形式、手段和方法。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和参与的方式是不同的,渠道是指参与的对象和途径,目前中国共有五种渠道;方式是参与的形式、手段、方法,具体有很多种。公民社会通过每一种渠道参与时都可以使用多种方式,一种方式也可以适用于多种渠道的参与。在现阶段,中国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可能使用的具体方式方法主要包括:参加政府组织的座谈会;提交调查报告或政策建议报告;给政府官员打电话;写信(包括发送电子邮件);发动会员给政府机关写信、打电话等;通过私人关系接触;向新闻界反映情况;召开记者招待会,表明本团体的观点;花钱在媒体上登载广告宣传;与其他团体联合,共同行动;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上访;请愿或静坐;召开群众集会,争取群众支持等14种参与方式。
2.中国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方式的现状。根据前述北京大学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曾经参加政府组织的座谈会的社团占有效回答社团数的53.6%,曾经提交调查报告或政策建议报告的社团占有效回答社团数的53.4%,曾经给政府官员打电话的社团占社团数的49.6%,向新闻界反映情况的社团占社团数的29.1%,通过私人关系接触的占26.1%,写信(包括发送电子邮件)的占社团数的24.1%,采取其他参与方式的社团均较少,比例最高的方式也不超过18%,采取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方式的社团仅仅占总数的7%。[3]296可见,在这些参与方式中前三种方式比例较高,处于使用频率的第一档次,均占到社团总数的一半左右,显示目前中国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最常用的还是这三种比较传统而正式的方式。向新闻界反映情况、通过私人关系接触、写信(包括发送电子邮件)三种方式处于使用频率的第二档次,显示通过公共舆论、个人接触渠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民间组织也相对不少,这也验证了前面我们对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不同渠道使用频率多少的估计与判断。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个调查结果,可以发现目前中国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方式上的更多的特征。第一,根据前文的分析,公民社会参与的渠道中公共舆论、个人接触、司法裁决的参与方式都是非制度化的;人大政协和政府机关渠道的方式则既可能是制度化的,也可能是非制度化的。但前述调查显示,在被问到“各级政府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有关问题,是否向贵团体咨询或征求过意见”时,只有33.7%的社团回答“是”。可见现实中这两个渠道也是以非制度化的方式为主。因此中国目前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方式以非制度化方式为主,制度化方式为辅。第二,中国目前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以合法性间接参与方式为主,直接参与的方式为辅,非法性间接参与方式十分罕见。第三,当前中国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主动性不足,以委托参与或被动参与为主,主动参与为辅。第四,前述调查显示,社团采取“与其他团体联合,共同行动”参与方式的只占总数的18%,可见当前中国公民社会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以单独参与为主,联合参与以及与政府合作参与比较少见。
此外,按照贾西津对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层次的分类,可以把公民社会参与的方式划分为出场式参与、表达式参与、对话式参与和共治性参与四种方式。[6]出场式参与方式只是公民出现在现场,徒具参与的形式,对政府的政策制定并不产生影响,在中国常常表现为动员性参与。目前在中国,公民社会参与的方式以出场式或动员性参与方式和表达式参与方式为主,对话式参与方式还非常少见,只是在某些民间力量特别强大的地方比如温州有所萌芽,共治式参与方式还完全没有出现。因此,与当代西方国家种类齐全、多种多样的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方式相比较,总体上看,中国目前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方式还相当不足和单一,公民社会对现有参与方式的使用也是畸轻畸重,过于偏重某些方式,呈现出不均衡的特点。
五、结语
在现阶段,不论是中国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还是参与的方式,虽然是多种多样的,但都存在实际使用上的单一、不足和畸轻畸重的特点,呈现出相当的不均衡性。今后,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成熟,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将更加广泛、深入和有效,中国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和方式也将逐渐克服这些缺陷和问题,公民社会在实际使用这些渠道和方式上将逐步走向丰富多样和均衡化。
[1]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
[2]张喜红.当代中国社会团体政治参与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04:128-149.
[3]褚松燕.权利发展与公民参与[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4]郑准镐.非政府组织的政策参与及影响模式[J].中国行政管理,2004,(5).
[5]贾西津.第三次改革——中国非营利部门战略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166-167.
[6]贾西津.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条件探讨[C]//.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转型期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国际的视角”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10-28.
D63
A
1002-7408(2011)03-0038-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公民社会对政策过程的影响研究”(05BZZ018)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李占乐(1973-),男,河南洛阳人,政治学博士,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王润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