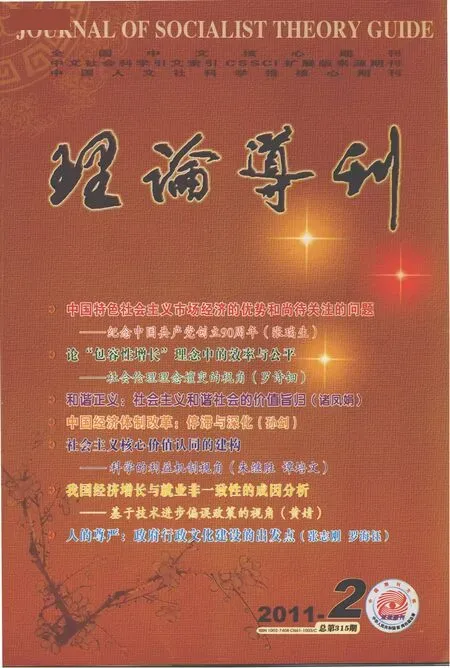“腐败黑数”畸高之文化传统与社会责任分析
曹志瑜
(景德镇市昌江区检察院,江西景德镇333000)
“腐败黑数”畸高之文化传统与社会责任分析
曹志瑜
(景德镇市昌江区检察院,江西景德镇333000)
反腐败是学界及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文化传统与社会责任的分析维度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深刻反思我国的“腐败黑数”问题。对于畸高“腐败黑数”中主要由文化、社会等外在因素导致的行为失范和腐败犯罪,应主要立足于宽容的救赎,而控制和消弥畸高“腐败黑数”的根本出路应是植根于文化基础之上的严密而人性化的制度设计。
腐败;腐败黑数;文化传统;社会责任
“犯罪黑数”(或称“犯罪暗数”)本来是犯罪学研究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社会上已经发生,但由于诸种原因尚未被司法机关获知或者没有被纳入官方犯罪统计之中的刑事犯罪案件的总称。[1]由犯罪学上的概念引申,国际上采用“腐败黑数”来衡量从事或涉及腐败公务员中没有受到查处的比例,指的是确已发生,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被发现,或虽经调查但未被惩处,因而没有计算到腐败案件统计中的腐败公务员数量占所有腐败公务员总数的比例。[2]
我国的“腐败黑数”究竟有多高,在缺少官方统计和权威调查的前提下,只能依赖逻辑推导和经验分析的方法推算。党建研究专家黄苇町在其所著《失落的尊严:腐败备忘录》中说:“有人推算,腐败活动的犯罪黑数保守一些估计也不会少于80%……有人则估计,犯罪黑数达到95%以上。”[3]另据胡星斗教授研究表明:世界平均的贿赂额占GDP的3%,按世界的平均腐败程度计算,中国应查出腐败金额为7000~8000亿元,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2005年查出的腐败金额仅为74亿元,约占应查出的1%,所以说中国的腐败黑数为99%。[4]学界普遍认为,现实中被曝光和查处的腐败案件,只是我国日益生活化、常态化的腐败行为之冰山一角,仅占实际腐败现状的很小一部分,当前的腐败查处数据只能说明国家应对腐败的容忍限度与反腐败的努力程度,而无法反映大面积客观存在的腐败行为。可见,我国的“腐败黑数”畸高,已是不争的事实。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将“公职人员”、“公务员”、“官员”视作同一概念,指代表国家或政府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员。上述三个称谓分别在不同的语境中采用。长久以来,囿于研究旨趣的取向不同,学界对于“腐败黑数”的分析基本都集中在法学、经济学等领域,对于腐败泛滥的文化发生机理,对于“腐败黑数”畸高而腐败查处机制孱弱所蕴含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责任问题,则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关照。显然,我们应该尝试着从一些多维视角来观察腐败和“腐败黑数”问题,否则将难以穷形尽相甚至徒劳无功。笔者认为,“腐败黑数”不仅是一个统计学上的概念,而且是一个社会文化上的概念。腐败的根源和原因复杂多样,难以一言以蔽之,但寻求文化渊源和社会背景的诠释,将始终是认识我国腐败与“腐败黑数”问题的逻辑进路和检验标准。
一、“腐败黑数”畸高之文化传统分析
东西方的历史分流始于国家形成之初。在西方,国家是在突破氏族血缘纽带的基础上形成的。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著作中曾经指出:“国家(笔者注:西方国家)与氏族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照地区划分它的国民。由血缘关系形成和保持下去的旧的氏族公社,……已经很不够了,这多半是因为它们是以氏族成员与一定地区的联系为前提的,而这种联系早已不复存在。地区依然,但人们已经是流动的了。……当它在雅典和罗马能够代替按血缘来组织的旧办法以前,曾经需要进行多么顽强而长久的斗争。”而在东方中国,国家是带有浓厚的血缘关系形成的。学者张光直在其著名的《美术、神话与祭祀》中阐述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途径时曾说:“三代王朝即为姒姓、子姓和姬姓三支氏族所创,王朝的兴亡实际上就成了众多氏族并存的政治疆场上各个氏族命运的盛衰。以血缘纽带维系其成员的社会集团左右着政治权力,这就是中国古代国家显著的特征。”[5]
可见,西方的“国”与“家”是相分离的,而在中国,“家”“国”合一的格局促使无论是统治者还是社会一般成员在行为取舍上都有着浓厚的家族背景,并和家族命运同生息、共荣辱。在这种社会类型的基础之上,出于维护“国”之君权和“家”之父权的需要,后世以“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核心的封建礼教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并日渐发育成长,最终促成了中国社会高度的稳定性和有序化。以礼制为基础的儒学经董仲舒从维护皇权的角度功利化改造以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并一跃而成为正统之学;宋明理学、训诂经学等,都是儒学在不同时代不同政治时期的发展。所以,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的“礼”文化由一家之言而转变为全社会的文化倾向和价值选择,儒学中的道德伦理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遗存和传承,对国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具有潜移默化乃至决定性的形塑作用。
人们普遍认为,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般特征有:人格依附、注重道德伦常,血缘宗法观,官本位思想和中庸的思维方式等。以上几个部分是有机联系、相互融合的,共同构成在世界民族之林独树一帜的中国传统文化。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感慨道:“在中国这样一个以人格依附和信任关系为基础的‘差序格局’的社会里,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什么关系后,才能拿出什么具体标准来。”林语堂先生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是把人情放在道理的上面的。”[6]可见,差序格局的关系往往成为我国官员行使权力时不作为、作为以及如何作为的真正“标杆”,以致在实际的社会生活和权力运作的内容中,“腐败”被视为惯常、必要而有效的方式。在由浙江省纪委、省监察厅向全省2500名普通百姓就当前腐败的现状、反腐倡廉的工作成效、如何进一步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等方面所作的一项随机问卷调查中,在回答假如“您自己拥有某些权力或您的亲属朋友拥有某些权力,能够满足您通过正常渠道无法实现的利益,您是否会利用这些权力?”的提问时,仅有29.72%的人明确表示“不会”,还不到三成。[7]笔者以为,根据对调查对象在敏感问题上的规避心理以及对实际状况的体察,三成的比例应尚属过高;况且,任何官员的角色都是双重的,单个官员在为自己谋取由正常渠道无法实现的利益时,也可能变成有求于其他官员的“百姓”。过去人情关系只限于亲友之间说情,现在已转向学缘、乡缘、官缘发展;过去秘密、私下拐弯抹角说情,现在变成公开登门说情;……过去说情是个别现象,一方找人,现在是双方都找人,有理没理都找人。[8]应当说,为了维系统治的需要,权力崇拜、关系至上等等一些非现代法治思维一直流传在国人的文化基因里,而市场经济中的物质化和唯利化追求更是诱发这些人性中自私、残忍的“魔鬼”一面肆意膨胀、暴露无遗。于是乎,一种奇怪的现象好似成为历史的“周期律”:制度或者规范可以被表面化地确立、修正或删改,甚至于特定情境下违心遵从抑或吹捧,但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将深植于人们的灵魂深处,并始终成为国人价值判断的精神内核及行为外观。从这个层面上说,儒家文化主宰了中国两千多年,而这种文化传统的千年积淀和酝酿,极可能对正式法律及规则的援用构成天然的消解和钳制,自然也包括腐败查处的制度和机制。据胡鞍钢等学者的推算,目前我国公务员腐败被发现的概率比较低,大约在10~20%之间,公务员腐败被发现之后受法律惩处的概率只有大约6~10%之间[2],则我国的“腐败黑数”至少为80%。
二、“腐败黑数”畸高之社会责任分析
当然,文化传统因素落实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则具体表现为社会因素。无独有偶,从现代社会学及犯罪学的“互动理论”出发,社会整体必须对腐败个体的行为负一定的责任,而这种社会责任又是和当前道德伦理的普遍失范以及制度运作的整体失调等因素密切相关的。所以,腐败产生的责任从道义上说并不能完全由腐败者承担。美国学者罗伯特·克利特在其《控制贪污腐败》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有关腐败问题的公式:“腐败动机=贿赂-道德损失-(被发现和制裁的机会×所受处罚)>薪金+廉洁的道德满足感。”基于此,以下笔者将从公职人员的群体生态(即官场)的互动关系与财富资源的相对亏缺性两个方面对腐败的催生关系和对腐败查处机制的溶蚀作用来分析“腐败黑数”畸高的深层原因。
1.公职人员的群体生态的互动关系。前面已经提到,道德伦理对社会个体的思想及行为产生了潜移默化甚至是决定性的形塑作用。那么,儒家文化传统对公职人员的群体生态到底产生了什么具体的影响呢?自古以来,中国官场等级森严、位序严格,俨然成为一个类似“家”“国”特征的自组织系统;上下级界限分明,上级掌握着下级的升降褒贬的主要资源,进而形成一个内部以特定规则流动的金字塔结构,任何违背领导意志的僭越规则的行动都有可能以仕途的损毁为代价;官场内部最讲究的是千人一面,大家彼此彼此、心照不宣,谁也不会冒失地“批龙鳞”、“犯龙颜”,与自己的领导过不去,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以血缘宗法关系为核心在官场生态中的现实反映。权力通过血缘宗法的网络进行流通,极易将正式规范及其腐败查处机制架空。需要指出的是,《乡土中国》中所阐释的“熟人社会”,在计划经济时代又附添了一层强烈的“单位人”的色彩,其影响至今未见有大的削减。受长期的劳动就业体制作用,单位内部成员的关系日益复杂化:血亲、姻亲、上下级、朋友等各种关系盘根错节,单位成员的行为选择不可避免地受到越来越多的关系的牵制以至形成一个任何个体都难以置身事外的关系网,尤其是对于其中的各级领导成员而言。另一方面,国人偏好中庸的思维方式的弊病是因陈守旧、循规蹈矩而缺乏突破创新的自我意识,这种思维模式也是我国文化传统长期塑造下的一个现实映射,其又必将推动传统的自我维系和延续。可以设想,当一定范围内的绝大多数人面对来路不明的钱物或腐败行为保持沉默时,如果有人挺身揭发或“启动”腐败查处机制,这个人将极易被视为异类而为官场所不容。这对于一个实际由上级领导任命产生的官员来说,基本上意味着仕途的终结;将贿赂留下来则要承担受到正式规范惩罚的风险,而由于腐败查处机制的软弱缺位,这种风险相对于巨大的诱惑和群体生态的压力是不足以产生足够的警戒效果的。所以,面临这样的利弊权衡,倘若“经济人”的假设同样适用于官员的话,相信大多数身处其间的官员都会趋向于三缄其口,以致形成一种行为选择的“官场潜规则”。因此,官场中并非每个官员入仕即贪,肯定还有很多正直、廉洁、有责任感的“清官”,但“清官”也必将面临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to be or not to be?而做一个“清官”并非仅仅把赃款赃物上交那么简单,因为这是一种违反潜规则的行为。
2.财富资源的相对亏缺性对腐败的催生关系。占有财富的能力与官员实现其道德和尊严的高位态应该是相匹配的,前者更是后者得以实现的物质前提,道德优势和地位尊严理应在对物质的控制上得到一定的体现和满足。然而,在我国目前这样一个公务员低薪的社会中,清廉者或许难以获得其外在的道德优势和尊荣。企业中的高收入群体与私人资本所有者阶层的兴起,无疑会对其形成一个体制外的道德压力并助长部分公职人员的失落和攀比心理,从而为他们的腐败可能埋下伏笔和祸根。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SSIC)曾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10个城市的居民进行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老百姓对社会上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其中对贪污腐败的原因,被调查者中有88%认为是“由于某些公职人员觉得待遇偏低,心理不平衡”造成的,这个看法在所列举的原因中居于首位。这种政治地位与经济收入的反差容易导致一些人的心理失去平衡,由“吃亏论”产生“补偿心理”,导致私欲恶性膨胀。[9]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改革开放的确是激活了生产关系当中的人的要素,使被束缚已久的生产力得到了解放,但并没有使普遍领域里的生产力获得质的飞跃。积聚财富的往往是那些文化水平较低、道德顾虑较少而又敢于尝试的人,而非真正掌握先进生产工具的人;投机心理、机会主义泛滥以至制劣售假、贩私倒卖、侵吞国有资产等等唯利性的丑恶行径像误开了“潘多拉魔盒”一般,充斥着我们的眼球和生活。这时,不少官员开始“觉醒”和追悔:凭什么那些昔日的无业游民、“进过宫”的人员靠着“无知者无畏”的惊天胆量就可以“一夜暴富”,而自己占有着公权力和大量社会资源却日渐相形见绌。于是,他们在焦灼和失衡之中寻求着或隐或明的致富途径,而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利益无疑是最快捷可行的方式。当然,也有不少人毅然选择了“下海”经商,而先前从政时结织的关系网自是尤可加以利用的资源。这种社会情势下,生存环境和工作待遇的悬殊极易诱发公职人员的腐败犯罪行为。
三、“腐败黑数”畸高之社会心理分析
本文中的“社会心理”,着重强调在文化传统和社会责任的背景下形成的群体心理。群体心理的存在,对于个体在群体中各种行为的生成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其中,对腐败群体中行为人的腐败行为以及形成畸高的“腐败黑数”无疑也起着重要作用。
个人于群体之中时容易产生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并借以消除孤单和恐惧等心理。所以,在明知某件事情是腐败行为或违法犯罪时,一个人可能不会去做,但当该群体中已经有人“身先士卒”,且显然有利可图时,就极易使其他人产生“法不责众”的心理,并加入到群体性的腐败行为中去。曾经轰动一时的沈阳“慕马案”中,其涉案范围和人数令人震惊: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就达66人!包括市府原市长、常务副市长、秘书长以及财政、城建、烟草、国税、土地等政府部门的9名正职负责人和市检察院检察长、中级法院院长及两名副院长在内的一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其中,原市建委主任宁先杰的一段表白很能反映这类窝案、串案背后的心理现象:“认为与领导一起做的事,不会出问题,就是出了问题,有领导在前面抵挡,我只是个随从。”正因为有这种群体归属感的需要,个体在群体中常常会不知不觉地受到群体的压力,而在自己的认知、判断、信仰以及行为上,自觉地修正自己以表现出与群体中多数人一致的行为倾向。研究表明,任何群体都有维持自身统一性的显著倾向和执行机制,对于同群体保持一致的成员,群体的反应是青睐、接受和优待;对于偏离者,群体则倾向于厌恶、拒绝和制裁。[10]因此,任何人不遵从群体都会冒很大的风险——“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等民谚就是此类所谓“不合群者”境遇的真实写照。以此观之,我国公职人员的群体生态中的“官场潜规则”,正是这种群体归属感的典型症候,而任何“标新立异”的尝试都可能为官场所不容,腐败的形成与畸高的“腐败黑数”似乎不可避免。
四、结语
宏观而言,文化传统和社会责任中的“关系”、“潜规则”等因素对个人、小团体或局部地区而言,也许可以达到短期效益的最大化,但对于整个国家社会特别是弱势群体、落后地区来说,肯定是非效率和不经济的。因为仅就单个、独立的腐败行为而言,可能会降低一定的交易成本,而从整个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法制秩序的建立和维护以及公平、公正等理念的养成来看,腐败与畸高的“腐败黑数”却导致国家修复这些社会基础时成本最高。
综合上述对于文化传统、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揣测”:这种畸高的“腐败黑数”,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腐败行为人的一种道德堕落,莫若说是法制与传统矛盾冲突的代价和悲剧。“河边湿鞋”甚或“随波逐流”虽为君子所不齿,但毕竟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举世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并非普世常态。因此,对于畸高的“腐败黑数”中大量主要由文化、社会等外在因素导致的行为失范和腐败犯罪,应主要立足于宽容的救赎而非惩罚性的鄙弃,控制和消弭“腐败黑数”畸高的根本出路将是植根于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的更加严密而人性化的制度设计。
[1]魏平雄.犯罪学教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40.
[2]胡鞍钢,过勇.公务员腐败成本—收益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4).
[3]新余廉政网.“反腐败,你今天焦虑了吗?——读《七个怎看》有感”[DB/OL].http://www.xylz.gov.cn/web/.
[4]胡星斗博客.“中国反腐败学刍议”[DB/OL].http://www.huxingdou.com.cn/anticorruption study.htm.
[5]翟中东.犯罪控制:动态平衡论的见解[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06.
[6]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台湾:台湾综合出版社,1976:72.
[7]袁媛.百姓评说:腐败与反腐败[J],反腐败导刊,2001,(2).
[8]池海平.法治误区论[M].山西:希望出版社,2004:240.
[9]苏满满.腐败心理预防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4:120.
[10]刘邦惠.犯罪心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246.
D035.4
A
1002-7408(2011)02-0022-03
曹志瑜(1981-),男,法学硕士,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研究方向:刑法学、司法制度。
[责任编辑:张亚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