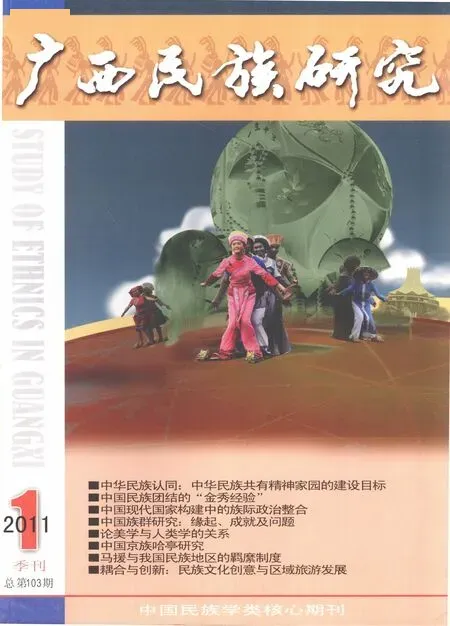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概念、预设与特征*
—— “民族生态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之一
付广华
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概念、预设与特征*
—— “民族生态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之一
付广华
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指的是诞生于美国生态人类学中的一种独特方法,它试图从认知的视角探讨不同民族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对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的概念界定和理论预设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归纳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的本土人立场、民族志方法、认知的视角、关注传统生态知识以及跨学科色彩浓厚5个方面的学科特征。
民族生态学;人类学;美国
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指的是诞生于美国生态人类学中的一种独特方法,它试图从认知的视角探讨不同的民族与其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自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该学科在欧美国家得到了较快发展,甚至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生态人类学中主要的学术思潮之一。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联学术界也以民族 (ethos)为研究中心发展起另一种民族生态学研究的理论框架,我们称之为“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由于中国当时恢复了与苏联的密切关系,因此中国民族生态学的发展初期深受苏联学术框架的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研究也开始影响到中国的植物学界和民族学界,从而开启了最早的中国民族生态学研究。然而,由于同时受到美、苏两种学术传统的影响,中国民族生态学界对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一直未能澄清,这给学科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隐忧。有鉴于此,我们希望此文能够增加国内学者对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的认识,亦为促进民族生态学在中国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一、概念界定
作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民族生态学的概念仍在不断的修正中,这也正表明其研究魅力所在。术语“民族生态学”于1954年为康克林 (Harold Conklin)首创[1]。康克林在菲律宾的哈努诺人(Hanunoo)中进行的植物命名方法的语义学研究证实了民族植物分类的等级本质,真正洞察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认知。不过,康克林与其追随者一样,只是花费很大力气去记述植物和动物名称的清单以及它们的文化使用[2],未能延伸到更深层次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类学家日益对理解人群自己的感受及他们对世界的解释感兴趣,因此他们对人类活动的动因和后果感兴趣的程度远远大于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兴趣。于是以人们自己的世界概念模型为重点,产生了被称为“认知人类学”的领域。鉴于其在方法论上的贡献,人类学家们有时也称之为“新民族志”(New Ethnography)或“民族科学”(Ethnoscience)。刚刚诞生的民族生态学与这一领域不谋而合,在借鉴其方法的过程中,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简单了解民族生态学的发展脉络之后,我们接着来探讨民族生态学的概念界定。虽然康克林没有就“民族生态学”一词给出明确的概念界定,但后来的生态人类学者多次试图去框定“民族生态学”。下面我们就较有代表性的四种界定予以分析,然后结合来自其他学科学者的意见,力争对民族生态学的概念界定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美国人类学家福勒 (Catherine Fowler)是较早地试图从理论上总结民族生态学发展历程的学者。早在1977年,她在为《生态人类学》写作的“民族生态学”专章中叙述了民族生态学的历史、概念、方法论、招致的批评以及其他方面的民族生态学研究。正是在这一专章中,福勒把民族生态学描述为:一种关注本土人环境概念的独特的人类生态学进路,它主要采纳民族科学的方法,尝试证实对应环境的本土术语系统与那些概念化之间的条理关系。从福勒的上述界定可以看出,民族生态学在当时仅仅是人类学的人类生态学的一个分支。对福勒来说,其关键在于要从被研究群体的自观点 (own point of view)去看问题,这样民族生态学就变成了一个群体从其自观出发的生物相互联系的观念[3]。福勒还指出,虽然民族生态学因缺乏关注其方法的行为含义而招致了许多批评,但它却始终坚持自身能够更完全和完整地描述土著人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福勒之后,布罗修斯 (J.Peter Brosius)等人对民族生态学有一个更为清晰的界定。他们认为民族生态学 (ethnoecology)是民族科学的一个亚学科,它研究的是传统群体如何组织和分类他们的环境知识和环境过程[4](pp.187-188)。布罗修斯等人在文章中认为,民族生态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描述和呈现文化内观的知识,而不能止步不前。就像弗雷克 (Charles O.Frake)所言,“民族志学者不能仅仅满足于西方科学式的文化生态系统元素的分类。他必须像他们自己所理解的那样按照被研究者民族科学的种类去描述其环境”[5]。由于该文着眼于如何运用民族生态学去探讨传统农业知识,而不是重在民族生态学理论上的探讨,因此这篇文章的最大贡献也许在于指出了本土知识系统中分享的民间智慧和个体经验组合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本质。当然,布罗修斯等人在文章中亦指出,在以后的民族生态学研究中,要把研究的注意点从名词转向动词。因为动词本身暗示着过程和其语言认知,它对人类适应的概念化也十分重要。
当代英国生态人类学家米尔顿 (Kay Milton)认为,“ethnoecology”一词中“ethno”这个前缀的意思同“folk”差不多,指的是从被研究者的角度 (主位的)界定的而不是从分析者的角度 (客位的)界定的知识领域。这样,关于某一社会的被研究者对植物界的民族分类,便成为“民族植物学”,进而类推出“民族动物学”、“民族医学”以及“民族生物学”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生态学”区别于所谓科学“生态学”,它研究的是特定文化传统的环境知识,而这些知识只在那个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才是有效的。因此民族生态学有助于理解传统群体与其所处环境的互动过程,从而地方生态治理提供本土经验和智慧[6]。
不难看出,上述概念界定基本上都限制在“民族科学”的语境内,因此我们今天看来可能会觉得上述界定似乎跟人类学界最新的理论发展没有什么联系。其实,面对人类学的后现代时代,民族生态学家们多多少少总会有所触动的。如美国民族生态学家纳扎雷 (Virginia D.Nazarea)在1999年出版的《民族生态学》一书中就指出:民族生态学是一种看待人类与自然世界关系的方式,只不过强调认知在框定行为中所起的作用罢了[7]。她认为,作为对自然环境的解释、认知和使用的系统的考察,民族生态学不再忽视文化的代表的与直接的方面的历史与政治基础,也不再把塑造知识系统和最终实践的分布、获取和权力问题拒之门外。民族生态学应该最大化利用其比较优势,结合事无巨细的田野工作,充分意识到历史、权力和风险在塑造环境解释、管理和妥协的重要性。这样一来,民族生态学就会在跨学科研究中做出重大贡献,甚至成为保护、可持续性和平等研究领域的倡行者[8]。从纳扎雷的上述论述中,我们亦可约略看出,民族生态学也在与时俱进中,它不仅坚持其原有的方法论利器,而且还勇于吸收布迪厄等人的知识、权力、风险的新思想,从而为民族生态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与上述人类学家不同,植物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其他学科学者的界定却有着一定的差别。民族植物学家马丁 (Martin)认为,民族生态学包括所有的描述地方性群体与其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因此它包含了民族生物学、民族植物学、民族医药学以及民族动物学等诸多亚学科[9]。无独有偶,墨西哥生态学家托莱多 (Victor M.Toledo)也倾向于扩大民族生态学的研究范畴,他认为民族生态学可以被界定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进路,它旨在探索人类群体如何通过信仰和知识的屏幕来看待自然,以及人类自身形象上如何使用或管理自然资源[10]。无论怎么表述,人类学以外的学者也都想把“民族生态学”这一理论工具延为己用,希望通过这种跨学科的探讨来充实自己的专题研究。
我们认为,民族生态学是民族科学的一个亚领域,它研究的是特定文化传统的人们所拥有的生态知识。这种研究最初仅仅在生态人类学界流行,更像是一种观察人与环境关系的视野或方法。只有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特别是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民族医药学等亚学科促生后,民族生态学才向一门总括式学科的方向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与上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截然不同的是,“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大致在研究范畴上等同于生态人类学,“学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族群或族共同体在所居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谋取生存的传统方式和特点,当地生态系统对人体产生的影响,族群或族共同体同大自然作斗争的特点及对自然界的影响,它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民族生态系统形成和发挥职能作用的规律等等。”[11]由于中国民族学界也曾深受苏联的影响,因此中国的民族生态学一开始就是民族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以民族为中心的生态学方面的研究。它与生态民族学 (人类学)研究对象大致相同,并且其理论方法有进一步融合的趋势。在当代中国的学科分类范畴中,“民族生态学”成为民族学下面自主设置的二级学科,其培养模式与各分支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相似。据我们所知,目前国内名为“民族生态学”的博士点有两处:一是托庇于云南大学民族学研究院,走的是民族学人类学的培养路线,大致等同于生态人类学或生态民族学;另一个诞生于中央民族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走的是生态学的培养路线,实质上是“民族地区的生态学研究”。
二、理论预设
凡是熟悉民族生态学发展历程的人们都知道,民族生态学与认知人类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其一分支学科。按照丹德拉德 (Roy D’Andrade)的界定,认知人类学是关于人类社会与人类思想关系的研究。认知人类学家研究的是人们在社群中如何构想和思考那些组成他们的世界的物和事[12](p.1)。由于认知人类学非常关注分类、认知以及文化的内涵,这使民族生态学也深受其影响,从而使得学科发展中始终存在着两个基本的理论预设①:
1.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其认知状况 (思想、知识和语言)的影响;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影响,不少人类学家认为语言是一个用来组织经验的概念体系,它不仅迫使人们接受一定的世界观,而且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模式,从而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准则。因此,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具有不同的概念体系,因此也就具有不同的世界观、思维模式、行为规范和文化[13]。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人类学家借鉴了语言学家派克的观点,提出要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去了解和记录文化,要把文化主位 (emic,即文化负荷者的观点)和文化客位 (etic,即文化研究者的看法)区分开来。上述两种语言学思想是影响认知人类学发展历程的重要思潮之一。
作为认知人类学的分支领域,民族生态学显然也深受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和派克语言学观点的影响,甚至在学科内部形成了对应的理论预设。民族生态学家们认为,人类是一个特殊的物种,他不像其他物种那样,他具有思维、知识和语言,因此这些文化元素必然会对其与自然环境互动的行为施加影响。人们不会直接地对环境起反应,而只能对那些他们意识到的且语言中已标示的动植物做出反应。在面对环境刺激时,人们会在已有世界观的图式下调动其已有的知识体系,从而做出适应性的行为。对此,瓦伊达 (Andrew P.Vayda)和拉帕波特 (Roy A.Rappaport)曾经在“操作的”环境和“认知的”环境之间做出了著名的区分。所谓“操作的”环境,即所有环境因素的综合,不管这些因素是否得到理解;而“认知的”环境则指的是一个特殊群体的人们所意识到和理解的环境[4](p.188)。在某种意义上讲,“操作的环境”和“认知的环境”之间的区分更像是对来自派克的主位和客位方法的一种模仿。
为了洞察土著人的思想、知识和语言对外部环境世界的影响,民族生态学家经常从语义和分类的角度考察土著人的生物分类体系。他们不厌其烦地收集植物、动物、昆虫、土壤、疾病等方面的土著术语资料,然后按照生物分类学的发展或按照一般化水平对术语进行等级上的安排。通过揭示土著生物分类背后的组织原则,民族生态学家们声称克服外来者强加于土著人既有结构的倾向是可能的[14](p.59)。但是,大部分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成分分析”上,很少能够进一步去思考。事实上,结构化了的动植物分类不仅反映了其环境世界观,而且这种世界观影响到分类结构本身乃至人类行为。这也招致了许多批评,因此不少研究成果被批评者们称为“民族语义学”或者“民族分类学”,而不能够升华到“民族生态学”的范畴中去。
2.由于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和环境的因素差异,不同群体的人们对其所处的外部世界的解释会有所不同。
当今世界生活着各式各样不同的群体。他们采取狩猎-采集、园圃农业、畜牧业、精耕农业以及工业化农业等不同的生计方式。由于生计方式的差别,他们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环境观。不同民族的环境观会因为社会、历史、文化的原因而有所差异,同时自然环境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不同民族对他们所处的外部环境的认知。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每个文化或社会看待外部的环境会一定有着完全截然不同的看法。人类学的田野研究一再表明,不同群体的人们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可能会发展出相似的文化特质,从而在文化面貌上具备一定的相似性。
米尔顿的地球变暖案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来自西方世界的科学家们说世界正在逐渐变暖,人类的活动,特别是那些向大气释放某些气体的活动是造成地球变暖的原因。虽然大家同处于一个地球,但是,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们可能否认地球变暖在发生。或者,如果他们承认有变暖现象,他们可能归因于神灵的行动或神圣造物主。或者承认人类要负一部分责任,他们认为地球变暖是某个更高主宰施加的惩罚,因为他们的社会未能尊奉古老的传统[6](p.487)。之所以对地球变暖这一外部事件的解释会有如此不同,不仅因为他们朝夕生活的自然生态环境有着较大的区别,而且因为他们与自然相处的不同方式的差异直接影响到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虽然我们并不能否认其中存在的文化建构的因素存在,但是这些差异巨大的解释肯定是跟其社会文化和自然生态差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这一理论预设与民族生态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由于不同群体的人们对其外部世界的解释 (认知)会有所不同,当然所有的解释可能都不乏合理的元素,但只有本土人才会对毕生相处的环境做出最为合理的判断,才会有最为准确的解释。这样的理论预设促进了民族生态学的传统生态知识研究的拓展。著名民族生态学家波西 (Darrell A.Posey)等人更是认为本土生态知识 (indigenous ecological knowledge)的研究亦即民族生态学[15]。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传统生态知识研究是民族生态学区别于生态学、环境科学及其他研究人与环境关系的学科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如果把两个理论预设结合起来来看,我们会发现它们实际上讲的都是人类行为和认知之间的关系。第一个预设说的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的行为会受到其认知状况的影响:如果某个群体的人们对某一类型的自然环境认知水平较高,那么他们就会在这种环境中运用自如,如鱼得水;反之亦然。第二个预设则讲的是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他们延续下来的社会文化传统会影响到其对外部世界的解释(认知)。如长期生活在中国华北平原的人们,来到青藏高原以后,基本上都会不适应,因为他们原来生活于海拔较低的地方,对应的社会文化传统难以应付这样的情形,因此会对这种类型的自然环境持否定态度;而原来居住在高山地区的人们则不同,他们拥有相应的文化适应策略,长期以来也形成了应对的身体素质,因此对青藏高原的抵触性情绪就不会那么强,其解释也就自然有所差异。
三、学科特征
作为生态人类学发展中的独特成果之一,民族生态学在欧美学术界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人类学的。由于民族生态学十分关注“他者”,尤其那些仍实践着传统资源利用和管理方式的土著群体,因此它具备一些不同于所谓的科学“生态学”的学科特征。具体来说,我们认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有以下学科特征:
1.本土人立场
本土人立场,亦被称为“主位”立场,是从被研究者本身出发看问题的一种方法。它的出现与文化相对论关系密切。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文化相对论是必须秉持的观念之一。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人类学者常常把自己置于被研究者的立场,从被研究者的时空场景中考虑自己研究的课题,然后再跳出来,结合客位的立场,对文化现象做出正确的解释。作为生态人类学中的一种独特方法,民族生态学必然也要坚持文化相对论,坚持本土人的立场。从学科名称来看,民族生态学(ethnoecology)是一个复合词,它由ethno加ecology构成,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属性,即ethno的生态学。ethno在英语中是“民族的”意思。如前所述,它与“folk”的意思差不多。以此而言,民族生态学就是从本土人立场出发的生态学,其中的“本土人立场”是民族生态学区别于生态学的根本标志。如果在研究中未能采纳本土人立场,而仅仅对土著人的植物、动物、医药进行研究,充其量只是“土著人的生态学研究”,而不能称之为“民族生态学”。当然,如果从“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眼光来看,仍然可以称之为“民族生态学”的。
2.民族志方法
在长期的学科发展历程中,人类学中的观察、参与观察、结构性访谈、半结构访谈、无结构访谈、谱系法等等都民族志方法都得到了极大发展。民族生态学作为一种生态人类学方法,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吸收了民族志方法作为学科的方法论支柱。从20世纪50年代学科诞生之初,到如今蓬勃发展,民族生态学始终坚持民族志方法。事实上,迄今为止,最为杰出的民族生态学研究都是由人类学家来完成的。民族生态学的创始人康克林对菲律宾哈努努人颜色分类和刀耕火种的研究至今仍然是人类学中的经典。为了进行博士论文的研究,康克林从1952年至1954年初一直在菲律宾的哈努努人中进行田野工作。后来,他的研究兴趣转移到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的伊富高人身上去,并为此6次到田野点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实地调查[16]。正如民族生态学家诺兰 (Justin M.Nolan)所言,民族志方法是民族生态学的附赠方法,民族生态学家通过使用参与观察和其他的定性资料收集技术,可以观察到相关生态可能性背景下的不同决策促生的行为模式。这一方法对决定和估测人类行为的影响是不可限量的[2]。民族志方法是民族生态学区别于所谓的科学“生态学”的重要方法论,因此,民族生态学一定要坚持田野调查、坚持参与观察,否则就难以实现其研究目标。
3.认知的视角
作为认知人类学的一个分析领域,民族生态学始终坚持认知的视角,而且长于从认知的角度来分析一个族群与其周围自然生态环境的复杂互动关系。随着认知人类学的发展,对人群概念世界描述本身成了目的,这样正规的采集资料技术就推广到民族生态学中。比如,一位对收集人们怎样对他们的自然环境分类感兴趣的生态人类学者,他会设计出几个层次的问题,从包含事物较广泛的范畴到较小的范畴。刚开始时,他可以问世界上存在着什么事物,然后再依次问有什么植物,有什么树木,有什么药用树,如此逐步缩小范围之最低层次为止。分析者通过向许多提供情况的人按照同样的顺序提出同样的问题,就能得到当地居民对他们自己所处环境的共同认识的总图。这种方法虽然有效,但人类学者逐渐认识到使用这种方法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可能在当地人的文化语境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分类,或者根本没有分类,被调查者就会强行按照自己的逻辑设计出一种分类方法来。这样一来,民族生态学家不得不恢复使用传统的参与观察法[6]。由此可知,民族生态学始终坚持认知的视角,力争从“他者”自身的文化传统去分析其对外部环境的认知,从而为民族生态学的存续提供跨学科的动力。因此,不少认知语言学家、植物学家参与到民族生态学研究中来,运用其语言分析工具和植物学知识,从而更为准确地揭示出“他者”的民族生态学特征。
4.关注传统生态知识
民族生态学自诞生之初,就把传统生态知识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除“传统生态知识”外,生态人类学界内部还有本土生态知识、农村人的知识、本土技术知识、传统环境知识、地方性生态知识以及本土农业知识等类似的术语。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英格利斯 (J.T.Inglis)编辑的《传统生态知识:概念与案例》[17]、贝尔克斯 (Fikret Berkes)的《神圣的生态学:传统生态知识与资源管理》[18]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称之为“本土环境知识”,如埃伦 (Roy Ellen)等3位学者编撰的《本土环境知识及其转型》一书就是如此[19]。通过对传统生态知识的挖掘和深描,民族生态学家可以得知当地人怎样理解他们的环境和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认识,能够纠正和补充某些肤浅的人类生态学的研究。事实上,传统生态知识研究已经发现,一些个人在各样植物、动物以及其他自然资源上要比其他人知道得多,而这是文化内部因素 (如年龄、性别、地位、兴趣、教育以及经验)导致的结果。例如,在女性操控耕作和谷物食品管理的社会,女性很可能要拥有耕作方面的更精细的知识。相反,在男性参与的地方生计的狩猎者中,男性通常操控和交流着野生动物方面的信息。民族生态学家已经从这些发现中获益,可以从中确认哪些个体在具体资源上是最具备与地方生境的物种差异[2](pp.846-848)。这对解决环境问题和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都具有相当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5.跨学科色彩浓厚
如马丁和托莱多所述,民族生态学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跨学科领域,它包含着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民族生物学、民族医药学等多个亚领域。为了学科的发展,民族生态学持续地从生态学、人类学、生物学、语言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吸取营养。事实上,前辈民族生态学家已经在跨学科上给我们做出了示范:美国学者伯林 (Brent Berlin)早就认识到自己学科专业的局限性,因此他长期与两位生物学家合作组成了跨学科团队,最终在民族生态学研究上取得了学术界公认的成就[20]。民族植物学家马丁也提倡这种跨学科团队的合作,生物学家收集和辨认植物物种,语言学家研究地方命名,人类学家记录生态知识,医药学家分析植物的医药价值,动物学家观测动物种群,资源经济学家证实森林产品的价值。不过,他认为,民族生态学家为了获得对传统生态知识的全面认识,一定会经常孤独地工作,因此必然要时常跨越众多学科的边界[9]。可以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由不同学科的学者组成的民族生态学研究团队将会越来越多。
结语
在前文中,我们讨论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的概念界定、理论预设和学科特征。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更像是一种观察视角或一种研究策略。在民族生态学内部分化出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民族医药学等更为专门化的领域后,民族生态学一跃成为一门统领性的学科,与所谓的西方科学的“生态学”遥相呼应。
由于民族生态学家的成果较少为大众所知,而且由于这些研究与早期探险家、牧师和自然史学家联系密切,一些观察家就此认为民族生态学只懂得进行动植物的分类研究,从而得出它是一个老掉牙的学科的错误结论。事实上,民族生态学发展到今日,研究方法和手段日新月异,它不再满足于对动植物名称的罗列。对传统生态知识的系统性研究使得民族生态学家具备了参与农村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资格。由于能够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来观察问题,民族生态学家们更加熟悉地方生态环境特征,同时也深为了解区域族群的社会文化,因此能够为环境问题和环境冲突的解决提供合适的意见和建议。
不过,我们知道,民族生态学仅仅是理解传统生态知识的一种方法,我们不能希望用它来解释所有的问题。同时,由于民族生态学与认知人类学一样,都是以文化相对论为其潜在的思想基础的。居住在同一地区的各个族群对所在环境的特定分类具有一定的差异,这样各个族群的分类只不过是当地环境的一种建构物罢了。最终,民族生态学也只不过一种看待环境的观点而已。饶是如此,深入挖掘不同族群的传统生态知识对维护当地的生态安全还是很有重要意义的,这也是当今民族生态学家们比较关注传统生态知识的深层动因。
注释:
①此两个假设参考了布罗修斯等人的某些提法,参见J.Peter Brosius,George W.Lovelace,and Gerald G.Marten的《民族生态学:理解传统农业知识的方法》一文。
[1]Harold C.Conklin.An Ethnoecological Approach to Shifting Agriculture[J].Transaction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1954(2).
[2]Justin M.Nolan.Ethnoecology[A],In H.James Birx ed.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vol.2)[C],Sage Publications,Inc. ,2006.
[3]Catherine S.Fowler.Ethnoecology[A].D.Hardesty.Ecological Anthropology[C].New York:Wiley,1977.
[4]J.Peter Brosius,George W.Lovelace,and Gerald G.Marten.Ethnoecology: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Knowledge[A].Gerald G.Marten ed.Traditional Agri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C].Boulder:Westview Press,1986.
[5]Charles O.Frake.Cultural ecology and ethnography[J].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62(1).
[6]Kay Milton.Ecologies:Anthropology,Culture and the Environment[J].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1997(49).
[7]Virginia D.Nazarea.Preface[A].Ethnoecology:Situated Knowledge/Located Lives[C].Tucson: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99.
[8]Virginia D.Nazarea.A View from a Point:Ethnoecology as Situated Knowledge[A].In Ethnoecology:Situated Knowledge/Located Lives[C].Tucson: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99.
[9]Gary J.Martin.Ethnobotany:A Methods Manual[M].London & Sterling,VA:Earthscan,2004.
[10]Victor M.Toledo.Indigenous Peoples and Biodiversity[A].In S.Levin,el al.,ed.Encyclopedia of Biodiversity(vol.3) [C].New York:Academic Press,2001.
[11]〔苏〕B·И·科兹洛夫著,殷剑平译.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主要问题[J].民族论丛,1984(3).
[12]Roy D’Andrade.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Anthropology[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13]包智明.语言与文化[A].庄孔韶.人类学通论[C].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
[14]Emilio F.Moran.Human Adaptability:An Introduction to Ecological Anthropology[M].Boulder,Colorado:Westview Press,1982.
[15]Darrell A.Posey,el al.Ethnoecology as Applied Anthropology in Amazonian Development[J].Human Organization,1984(2).
[16]Harold C.Conklin.Language,Culture,and Environment:My Early Years[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98(1).
[17]J.T.Inglis ed.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Concepts and Cases[C].Canada: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1993.
[18]Fikret Berkes,Sacred Ecology: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and Resource Management[M].Taylor& Francis,1999.
[19]Roy Ellen,Peter Parkes,Alan Bicker(ed.).Indigenous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its Transformations[C].Hardwood Academic Publishers,2000.
[20]Brent Berlin,D.E.Breedlove,and P.H.Raven,Principles of Tzeltal Plant Classification.New York:Academia Press,1974.
U.S.Ethnoecology:Conceptions,Assumptions,and Characteristics
Fu Guanghua
U.S.ethnoecology is a distinctive approach in U.S.ecological anthropology,and it tries to study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the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their physical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anthropology.In this paper,the author reviewed the conception definitions and theory assumptions of U.S.ethnoecology,and then summed up some discipline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base,such as indigenous stands,methods of ethnography,perspective of cognition,paying attention to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and thick description of cross- disciplines,in order to supply a measuring criterion for the researches of Chinese scholars.
ethnoecology;anthropology;U.S.
【作 者】付广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生、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81
C95.05
A
1004-454X(2011)01-0069-007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批准号:08CMZ011)阶段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覃彩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