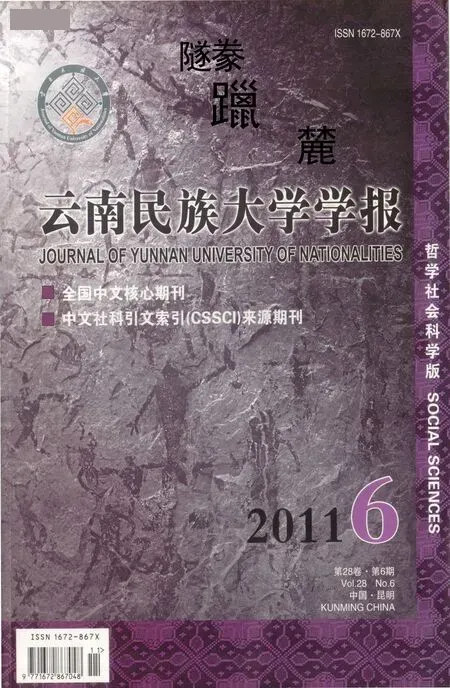羌语支在汉藏语系中的历史地位
孙宏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北京100001)
羌语支在汉藏语系中的历史地位
孙宏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北京100001)
羌语支语言仅仅十多种,使用人口也不足百万,在汉藏语系数百种语言的汪洋大海里,好比沧海一粟。但羌语支现存的许多语言事实,却给我们许多启示。根据羌语支语言的差异,在类型上呈链状演变这一历史实事,我们提出了历史类型学问题,它可能是语言发生学分类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补充。这个命题由汉藏语系音节结构类型、语法结构类型、语序类型和语义分化和改变的历史演变等许多专题研究所组成。由于羌语支语言比较保守,对它的一些语言事实的深入研究也许会对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有一些贡献。
羌语支;历史类型学;语言演变链;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中的羌语支,包括羌语、嘉戎语、尔龚语、拉坞戎语、普米语、木雅语、扎巴语、却域语、贵琼语、尔苏语、史兴语、纳木依语等活着的语言及其文献语言西夏语,有的语言还有差异很大的方言,如羌语、嘉戎语、木雅语、尔龚语、尔苏语、普米语。这些语言的方言,在境外一些学者看来,似乎都是不同的语言。例如羌语分南北两个方言12个土语;嘉戎语分东部、北部和西北部3个方言;木雅语分东部和西部两个方言;尔龚语分道孚、丹巴和壤塘3个方言;尔苏语分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方言;普米语分南部和北部两个方言。
羌语支语言在汉藏语系中是一支比较保守的语言,也是保留古老面貌比较多的一些语言。这个语支主要分布在四川省西部和云南省的西北部,沿六江流域的河谷[1],由北到南的狭长地带。这个地区现在被学术界称为“藏彝走廊”[2]或民族走廊[3],是近20年来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考古学、语言学的一个研究热点。
羌语支语言的调查研究,始于19世纪,首先报导这一带语言的是西方传教士或探险者。20世纪以來,语言学者开始系统记录部分羌语支语言,主要集中在羌和嘉戎两种语言上,对其他语言也稍有报导。20世纪40年代,对上述语言的调查研究进入深入记录阶段,报导的文章也日渐多了起來。深入调查研究羌语支语言,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主要集中在羌语、嘉戎语和普米语上,每种语言各记錄15-35个点,每个点记录了丰富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的资料。20世纪70年代以來,开展了除上述3种语言以外的羌语支语言识别和调查研究,陆续公布了这三种语言的词汇、语音和语法资料,进行了初步比较研究。目前羌语支的所有语言的基本描写研究已经大体完成,《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和《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已经对每一种羌语支语言都有一个基本特点的描述,有的语言还分析了它们的方言资料,如羌语、普米语有“简志”,还有方言专著;嘉戎语、拉坞戎语有不同方言描述的专著,而且已经出版;扎巴语、贵琼语已经出版描写性专著,一般都有25万字左右;木雅语、尔苏语、史兴语、却域语、尔龚语等已经有专著的初稿,即将在年内或稍后定稿出版。纳木依语的调查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专著的撰稿工作正在紧张进行。这些工作的完成,为羌语支的历史比较研究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羌语支的构拟以及他们之间远近关系的论证在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下正在紧张地进行。
羌语支语言北部与阿尔泰语言接壤,南部被彝语支语言所包围,由于所分布的地理位置不同,在类型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不同地区的语言分别向相关的语言结构类型靠近。[4]由于上述原因,羌语支语言在语音和语法类型结构上存在的差异呈链形狀,包括其形态、复辅音数量和结构等许多方面。换句话说,羌语支不同语言或方言的某些特点,分别处在历史演变链的某个链节上。分析和研究这个演变链,不仅对羌语支的历史演变脉络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对藏缅语族乃至汉藏语系语音和语法[5]的历史演变也会有一些启示。下面从语音、语法和词汇等方面举例性质地讨论羌语支研究(有些例证不仅仅局限于羌语支语言,包括藏缅语族的其它语言)在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中的地位。
一、语音
(一)声调问题。声调是汉藏语系语言一个重要特点,但是声调是后起的语音现象,比汉藏语系各语言分化的历史来看要晚得多。羌语支有一些语言,至今没有音位调,只有习惯调,换句话说,声调至今没有形成。有音位调的语言有的2个,有的3个,最多6个。分析羌语支一些语言声调产生的机制,大都与汉藏语系语言音节3个部位的语音要素的性质改变有关,即节尾辅音的演变、复辅音前置辅音的脱落和复辅音基本辅音性质的改变。具体表现为音节各组成要素(包括构词和构形)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出现各种音变现象,如辅音清浊、送气、内爆等现象的改变与交替,元音长短、松紧、鼻化、卷舌、带擦……等各种声学特征的出现与消失。它们最后都与音节音高的产生与改变发生联系。但是,这些语音要素在不同的羌语支语言里,或者说在藏缅语族语言里所发生的变化,对音高所起的作用的次序有先有后,数量有多有少,有的语音现象的改变甚至对音高不起作用。因此,在羌语支乃至藏缅语族语言里,要想建立象汉语那样的调类系统是不可能的。但是羌语支语言声调产生的机制却与藏缅语族乃至汉藏语系语言是雷同的。
(二)复辅音问题。羌语支语言有丰富的复辅音,多的有390多个,如拉坞戎语,其次有200多、100多或数十个不等,有的已经全部消失,如羌语南部方言的龙溪土语,尔苏语的中部方言等。复辅音有2合、3合、4合,个别语言甚至有5合复辅音。复辅音的演变通过多种方式,如弱化、合并、脱落、替换等。演变过程中对辅音格局产生影响,如塞擦音的产生和分化;鼻音和边音的清化;送气音的分化、塞音清浊的再分化等等。大量语言实事证明,复辅音的前置辅音有的來源于词缀,有的基本上没有意义。因此有必要区分有语法意义的前缀(prefix)和没有语法意义的前置辅音(pre-initial)。我曾经提出区分的6条原则:(1)前缀是有意义的语素,复辅音的前置辅音是词根的一部分,它是没有意义的。(2)在一些语言里,前缀和词根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在它们之间是可以插入其他语法成分;而复辅音的前置辅音和基本辅音之间结合得比较紧,他不能插入任何其他成分。(3)前缀的变化只对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产生影响,对词根的语音基本上不产生影响(个别单音素的词缀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对词根的语音产生影响,如S-前缀等);复辅音的前置辅音则不同,在一定条件下,它会对词根的语音发生多方面的影响,例如可能对词根的音高(声调)产生影响,或对音节的松紧、长短产生影响等等。(4)前缀比较活跃,往往出现在一类词或同类语法意义的词形变化之中,在需要的时候,它可以经常被其他词缀替换,也可以从一个词上移动到另一个词上表示类似的语法意义;而复辅音的前置辅音则不同,它不能离开基本辅音而从音节的某个部位游离到另一个音节的某个部位。(5)前缀可能是音节的也可能是音素的,一般來说,成音节的居多;而复辅音的前置辅音没有成音节的。(6)前缀可以添加在与自己相同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词根前面,例如嘉绒语里的使动前缀 [s-],既可加在词根声母为 [s-]的动词前面表示使动,也可加在使动的前缀 [s-]的前面,表示双重使动;而复辅音中的前置辅音则不能和自己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相同的基本辅音相结合。[6]最近我觉得还需要增加一条:(7)前缀由于语法范畴的消失对词根的影响小,或者不产生影响,而复辅音前置辅音消失过程中会或多或少对词根产生影响或留下痕迹。
为什么要区分前缀和前置辅音?首先,问题涉及原始汉藏语的类型学特征问题,是单音节的、一个半音节的还是多音节的?是孤立型的还是粘着型的?其次涉及原始汉藏语构拟问题。如果是前缀,那是形态学问题,在构拟某个词的原始形式的时候不需要构拟它的前缀,只有构拟语法体系的形态成分时才会考虑它;但复辅音前置辅音却不同,它是词根的一部分,构拟某个词的原始形式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考虑进去。
(三)小舌部位的辅音问题。这涉及到原始汉藏语辅音系统的格局问题,从发音部位看,是三分(双唇、舌尖中、舌根)还是四分(双唇、舌尖中、舌根、小舌)。羌语支语言几乎都有小舌部位的塞音和擦音,形成与舌根部位的塞音和擦音音位对立。它不仅分布在单辅音里,而且也出现在复辅音里。①本人在1983年起草《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一书的导论时已经提到了小舌音问题,后來,孙宏开、刘光坤在《也谈西夏语里的小舌音问题》(《宁夏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较详细地讨论了羌语支里小舌音的分布、例证和同源关系。无独有偶,虽然羌语支的小舌音在藏缅语族其它语支的语言里仅仅有零星分布,但是一些专家学者在构拟苗瑶语[7]、侗台语[8]、南岛语[9]时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构拟了小舌音。最近有人主张上古汉语也应该构拟小舌音[10][11]。我们先不去考虑汉藏语系分类之争的各种不同观点:兩分的(汉语和藏缅语)、四分的(汉语、藏缅语、苗瑶语、侗台语)、五分的(汉语、藏缅语、苗瑶语、侗台语、南岛语)、六分的(汉语、藏缅语、苗瑶语、侗台语、南岛语、南亚语)。既然各个语族都构拟了小舌部位的辅音,那么,再往上推测,原始汉藏语是否有小舌的塞音和擦音呢?羌语支语言里的小舌音是否就是原始汉藏语遗存活化石的证据呢?
(四)塞擦音问题。塞擦音比较多,这也是汉藏语系的一个显着特点。因此,在中国化的国际音标表中增加了多个部位的塞擦音。汉藏语系几乎所有语言都有塞擦音,最多的有5套(舌尖前、卷舌、舌葉、舌面前、舌面中),其次4套、3套、2套、1套等都有。羌语支语言一般都有4套塞擦音,少的也有3套,个别的有5套。塞擦音都有清、浊与清送气3种发音方法,与塞擦音配套一般都有同部位的擦音,一般都分清浊,构成复杂的辅音系统,单辅音音位一般都在40个以上,多的达50个以上,如羌语支南支的史兴语,有单辅音53个。汉藏语系里的塞擦音是后起的语音现象,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语言事实,但是它怎样发展起來的呢,我们从羌语支语言方言或语言之间同源词语音对应关系可以提供给我们塞擦音來源的确凿证据。根据分析,羌语支语言复辅音的后置辅音有[l]、[r]、[s]等,这个结构特征也是汉藏语系许多语言的共有特点。它们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受基本辅音发音部位的影响,与基本辅音相结合,构成不同部位的塞擦音。[12]当然,塞擦音的來源不那么单纯,已经有很多文章讨論过。
二、语法
(一)形态问题。汉语是形态不发达的语言,但与汉语有亲缘关系的藏缅语族语言却有比较丰富的形态,尤其是羌语支的语言、景颇语支的语言、喜马拉雅南麓的一些语言等,都有丰富的粘附性形态和屈折性形态,构成各词类丰富的语法范畴和语法形式,其中以动词的语法范畴最丰富。以羌语支北支的一些语言为例,有人称、数、时、体、趋向、祈使、命令、使动、互动、类别、名物化……等,这些表达语法范畴的语法手段丰富多样,它们是原始藏缅语就有的还是后起的,在学术界一直有争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方面的研究逐步展开和深入,羌语支语言里的形态已经在藏缅语族其它语言中陆续有所发现,而且其中有的肯定有同源关系,乃至有的形态成分在汉语中也已经找到一些蛛丝马迹。问题是这些形态成分是各自经过长期语法化的结果,还是原始藏缅语族乃至汉藏语系语言的遗存,这些现象能否构拟到原始汉藏语?例如:
1.使动语法范畴问题。动词使动范畴是汉语和藏缅语族语言普遍存在的语法形式,但大多数语言都是残存形式,只有古藏文②张济川《藏语词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北京),本文有关古藏文的一些资料,主要來源于此书。和部分藏缅语族语言仍然保留着较古老的用词缀(大多数用前缀,少数用后缀,前缀是原始形式,后缀是扩展形式)的方式表达。这些词缀表达使动的形式,在后來许多藏缅语族语言里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其中包括汉语。主要是:主词缀[s-]在一定条件下转换成为其它辅音形式的词缀,部分语言由一个单辅音音素转换成为一个带元音的音节;少數语言转换成后缀,有的逐步分析化,转变为分析形式;[s-]词缀在长期演变过程中受语音磨损逐步弱化,最后到完全消失。在此过程中,它所留下的痕迹是对动词词根的辅音产生影响,使其变清(包括塞音、塞擦音、鼻音、边音等)或变清送气(主要指塞音和塞擦音),有的语言还影响到词根元音的改变(不同部位和性质、长短、松紧等)或音高的改变③有关此问题的详情请参阅孙宏开《论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民族语文》1992年第5、6期);《论藏缅语中动词的使动范畴》(《民族语文》1998年第6期);美国《藏缅区域语言学》第22卷第1期。。我们观察到,这种演变呈链形狀,不同的语言动词所呈现的使动特征处在某个链节上。
2.代词化问题。包括动词的人称一致关系和名词的人称領属关系,它们都是用人称代词的辅音或元音经过长期语法化磨损后成为词缀,缀于名词的前面或动词的前后,构成名词人称領属范畴或动词人称范畴。[13]我们现在所見到的这种构形残存机制可能是汉藏语系语言的一种古老的语法现象。根据已经了解到的情况,动词人称一致关系仅仅在藏缅语族语言里残存着,其中比较保守的语言现在还很活跃,表现为非常丰富的语法形式,甚至扩展到动词的命令式。[14]它和时态、数等语法形式揉合在一起,构成了羌语支北支一些语言(我国景颇语支一些语言和喜马拉雅南麓一些藏缅语族语言也有類似情形)非常复杂的动词语法范畴。那么,这些语法范畴是后起的现象,还是原始形式的残存,一直有兩种不同意見。再说到名词人称領属范畴,比前者范围更窄,仅仅在中国境内的一些藏缅语族语言里有所发现,已经知道的语言不足10个,除了羌语支外,景颇语支和彝语支的语言都有。[15]喜马拉雅南麓的语言里是否有,目前还没有见到详细报导。根据研究表明,人称領属范畴在长期演变过程中,由活跃演变到不活跃,最后留下一些残存形式,最显著的残迹是留下了第一人称的領属词头“阿”,而且主要残存于亲属称谓名词的前面,上海话里的复數第一人称的“阿”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遗存。那么,如果把亲属称谓名词前面的“阿哥”、“阿嫂”、“阿妈”、“阿姐”、“阿舅”、“阿姨”中的“阿”词头看成人称領属的残存形式,那么它的分布面就非常大了。这还需要扩大研究面,进一步详细论证才能够有說服力。
3.动词互动范畴问题。藏缅语族语言都有表示互动语法意义的语法形式,多数用后缀或后加分析形式表达。羌语支语言动词也都有互动语法形式,用动词重叠和添加后缀等方式表达。从构成和來源分析,这可能是比较古老的语法形式。汉语有类似在动词前后加虚词的方式表达互动,但出现较晚,与藏缅语族的互动仅仅类型上的接近,是否是原始遗存,有发生学上的联系,现在还难下结论。
4.量词问题。从类型学上讲,量词是汉藏语系语言一个重要的语法特点,汉藏语系语言里的量词是后起的语法现象,汉藏语系语言为什么要发展量词,这似乎与单音节词根语的语言结构类型有密切关系。在汉藏语系语言里,量词数量经历了由少到多,作用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藏缅语族语言里的量词发展极不平衡,有多有少,有的很发达,有的不发达,有的语法作用很大,有的语法作用很小。[16]10羌语支语言处在中间狀态。量词从少到多,在它发展过程中有许多阶段性特征:如数词与名词的关系问题、量词与数词及指示代词的词序问题、反响型量词问题、名词或动词等演化成量词的意义分化问题、量词语法功能的增值问题等等。揭示量词产生和发展的机制,有利于对汉藏语系共性和特殊性的了解,有利于揭示汉藏语系的本质特性。这与我后面要讨论的历史类型学有关。
5.语序问题。羌语支语言基本上都是SOV型的语言,与羌语支相邻的藏缅语族语言白语、克伦语的语序已经转换成SVO的语言,但是其它藏缅语族语言与羌语支基本上保持了一致的语序,但是与藏缅语族有同源关系的汉语早就是SVO的语言了。人们想论证古汉语是由SOV向SVO转化的,以证明汉语与藏缅语同出一源,但意見难以统一。与此相关的表示句子成分关系的格助词的语序也发生了变化:SOV的语言,格助词一般都是后置;而SVO的语言这种标记一般都前置(介词)。假设汉藏语系语言是由某个原始母语分化出來的,那么他们的原始类型应该是相同或者基本上相同的。在长期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各自的类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研究这种类型的历史演变过程和演变机制,无论是由于接触还是自身动因,对于汉藏语系同源关系的讨论是否也有一定的意义?
三、词汇
(一)疑问词或者疑问语素问题。部分羌语支语言以及藏缅语族语言和汉语有一组疑问词,这组疑问词由一个疑问语素“何”构成,不同历史时期形成“可”、“阿”“曷”等变体。在藏缅语族语言里,我们查阅了近百种藏缅语族语言及方言资料,也有多种语音变体形式,与汉语明显同出一源。它们与指人、指物、指处所、指数量或指狀貌等虚词、量词或名词相结合,构成诸如“谁”(何人)、“什么”(何物)、“哪里”(何处)、“多少”(何数量)、“什么样”(何如)等疑问代词。这种构词方式类似于英语的 [wh-]构成的疑问词。所不同的是这个疑问语素在汉语方言和藏缅语族语言里还渗透到语法层面,做动词和形容词的词头,表示疑问。[17]一个疑问语素渗透到构词和构形兩个方面,不得不引起我们在历史比较研究方法论方面的思考,开阔和寻找新的历史比较研究思路。
(二)关于汉藏语词汇的音节问题。原始汉藏语是单音节的还是一个半音节或是多音节的?这是汉藏语研究领域讨论中经常涉及的一个认识问题。从羌语支语言当前的特点看,多音节词占的比例比较大。但仔细分析,所有多音节词绝大多数是复合词或词根加词缀的词,双音节或双音节以上的单纯词很少,而这些词往往都是拟声词。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重叠词和四音联绵词很多,这不仅是羌语支语言的特点,也是藏缅语族乃至汉藏语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云南民族大学刘劲荣教授收集到拉祜语中的四音联绵词数千条,产生这个特点往往与汉藏语系是单音节自由语素为主的语言有关。
(三)同源词的认定问题。羌语支有一批共同创新的同源词,这一点我在做西夏语比较研究[12]①详情请参阅孙宏开执笔的《西夏语比较研究》中词汇比较研究一章。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该书由李范文主编,实际本人主持了研究工作,并撰写词汇比较部分。的时候已经找到了一批。羌语支语言也有一批与藏缅语族乃至汉藏语系语言同源的词,数量都不太多,要形成严谨的、比较系统的语音对应规律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同源词如何认定?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我曾经提出,要确定某个词是某个语言集团内部的同源词,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在这个语言集团内部是否可以确定大多数语言都同源,语音上是否对应。那么,如果确定藏缅语族语言的同源词,就要看这个词在藏缅语族内部是否大多数语言都同源,语音上是否有对应关系。现在有的人随便拉出甲语言集团的某个语言的某些词(或一批词)和乙语言集团某个语言的某些词(或一批词)说他们有同源关系,我不完全反对这种做法,因为这种做法有时候会根据个人积累的研究经验,可以发现一些值得肯定的线索,但这种论证至少是不严密的,经不起推敲和检验的,偶然性非常大的,因此我不提倡这种论证和研究方法。说绝对一点,论证汉藏语系绝大多数语言都同源的一个词或一组词,要比论证汉语和藏语两个语言100个“同源词”有价值得多。
四、余论
(一)汉藏语系历史类型学问题。与上述一系列问题的讨论相关,我们提出汉藏语系历史类型学的命题。这个命题由汉藏语系音节结构类型、语法结构类型②有关此问题的研究,本人曾发表过相关文章,如《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民族语文》1992年第5、6期);后来又以“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为副题讨论过复辅音、单辅音系统、介音等问题,分别刊登在《民族语文》1999年第6期,2001年第1期、第6期。、语序类型和语义分化和改变的历史演变等许多专题研究所组成。这个研究的理论出发点是:一群有亲缘关系的语言,他们在分化以前或者分化过程中,语言结构的基本类型是一致的,或者說相同或相近的。后來由于分化时间久远,各自演变得面目全非了,那么如果我们把他们演变的脉络搞清楚了,把各种语言的类型转换的过程和原因弄清楚了,把各种语法范畴的语法化过程弄清楚了,不同方言、语言、语支、语族不管是平行发展也好,创新也好,由于语言接触引起的区域趋同[18]也好,构拟不同层次的汉藏语系语言各类特点(包括同源词和形态标记)或总体特点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我们把这种研究语言结构类型演变的课题称为历史类型学。它应该是语言发生学分类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补充。
(二)羌语支语言音节和形态同步演变问题。我们在对羌语支语言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发现,音节类型的改变与语法前缀的消长呈同步狀态。换句话说,音节的复辅音越多的语言,词形变化的前缀也越丰富;随着复辅音前置辅音类型和数量的减少,语法范畴的前缀功能也随之减弱,数量减少,活跃程度降低。这种演变狀态由北向南、由多向少、由活跃到不活跃呈链狀演变。这就是本文开头就提到的演变链问题。构成演变链是从许许多多具体的语言现象中概括出來的,我也曾经想给出一个量化的指标,但不很成功。这方面的想法往往体现在我的一系列文章中,包括列入本文引用的第[12]、[16]参考文献、135页页下注③以及有关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一组相关的文章。
(三)羌语支语言仅仅十多种,在汉藏语系数百种语言的汪洋大海里,好比沧海一粟,使用人口也不足百万。但羌语支现存的许多语言事实,却给我们许多启示。顺便说一句,羌语支语言现存的许多语音形式在原始藏缅语族乃至汉藏语系的构拟中会起到一定的桥梁作用。本人现在正在做羌语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仍然处在资料排比、推断、假设的进程中。当然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的眼睛会注视着藏缅语族历史比较研究的成果,汉藏语系各种语言的研究成果,上古汉语的研究成果等,甚至还注意人类学、考古学方面的新成果。
(四)汉藏语系数据库问题。这个数据库的建设始于1998年,当时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丁邦新教授的支持下完成了130种语言和方言的资料进入数据库。2004年起,在教育部资金的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荷兰皇家科学院合作,又完成一批资料进入数据库。到2009年6月,汉藏语系词汇语音数据库(二期)通过专家鉴定①2009年6月2日,由孙宏开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委)重点项目“汉藏语系语言词汇语音资料库检索系统”通过专家鉴定。专家们一致通过的鉴定意見认为:“本资料库设计思想先进,是目前汉藏语学界资料最丰富,检索功能最强,而且可以和境内外资料交换和接轨的开放性的资料库。”,接近400种语言和方言(包括各种层次的构拟约80万条词目)的资料已经入库,一个开放性的检索系统正在进一步完善②关于本数据库检索系统的详细介绍,请参阅孙宏开、江荻《汉藏语词汇数据库检索系统的价值和功能》载《汉藏语学报》,商务印书馆,第217-225页,2008年。。我们希望为汉藏语系研究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它应该是一个新的研究平台,既可以做各个层次的构拟,又可以检验已经初步论证的同源词是否妥当,还可以检验构拟不同层次的原始语言的语音形式。我们更希望此项工作的完成以及投入使用,能够对汉藏语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有所帮助和推进。
汉藏语系的研究寄希望于21世纪。
(本文在2010年6月24日至25日在台北举行的《21世纪汉藏语系专题研讨会》上发言时得到俄罗斯学者齐卡佳的中肯评价,特此致谢。)
[1]孙宏开.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谱系分类[J].民族学报,1983.
[2]费孝通.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0,(创刊号).
[3]孙宏开.川西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J].西南民族研究,1983.
[4]孙宏开.丝绸之路上的语言接触和文化扩散[J].西北民族研究,2009,(3).
[5]孙宏开.论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J].民族语文,1992,(5、6).
[6]孙宏开.原始汉藏语的复辅音问题[J].民族语文,1999,(6).
[7]王辅世,毛宗武.苗瑶语古音构拟[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8]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9]何大安,杨秀芳.南岛语与台湾南岛语[A].《台湾南岛语言》丛书导论[C].台北:远流出版社.
[10]李永燧.汉语古有小舌音[J].中国语文,1990,(3).
[11]潘悟云.喉音考[J].民族语文,1997,(5).
[12]孙宏开.藏缅语语音和词汇·导论[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13]孙宏开.关于汉藏语系里的代词化现象——一个语法化的实例[A].东方语言学(第3辑)[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14]孙宏开.论藏缅语中动词的命令式[J].民族语文,1997,(6).
[15]孙宏开.我国部分藏缅语中名词的人称领属范畴[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1).
[16]孙宏开.藏缅语量词用法比较——兼论量词发展的阶段层次[J].中国语言学报,1989,(3).
[17]孙宏开.藏缅语疑问方式试析——兼论汉语、藏缅语特指问句的构成和來源[J].民族语文,1995,(5).
[18]孙宏开.丝绸之路上的语言接触和文化扩散[J].西北民族研究,2009,(3).
(责任编辑 丁立平)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 Branches of the Qiang Language in the Sino-Tibetan Fam ily of Languages
SUN Hong-ka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081,China)
Among the several hundreds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there are a little more than ten branches of the Qiang language used by a population of less than one million.Their survival can shed some light on us.Their development is somewhat chain-like and reveals differences in historical typology,a good supplement to the classification studies on genetic linguistics.This study comprises such thematic studies on the types of syllabic structure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word order,and semantic development.Because these branches of the Qiang language are relatively conservative,a further study of them can shed some light on the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branches of the Qiang language;historical typology;language development chain;Sino-Tibetan family of languages
H419
A
1672-867X(2011)06-0133-06
2011-06-20
孙宏开(1934— )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教师,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