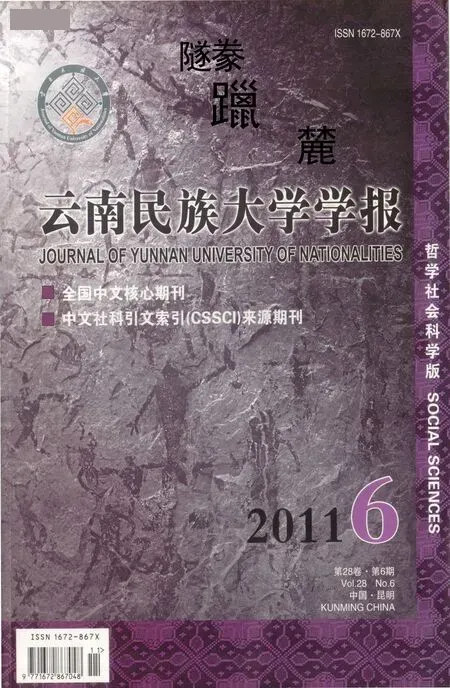小额信贷中社区传统文化的信用约束及创富机制
俞 茹,孟金莲
(1.云南民族大学 学报编辑部,云南 昆明650031;2.云南民族大学财务处,云南昆明650031)
小额信贷中社区传统文化的信用约束及创富机制
俞 茹,孟金莲
(1.云南民族大学 学报编辑部,云南 昆明650031;2.云南民族大学财务处,云南昆明650031)
小额信贷对农村贫困社区的经济发展起着孵化器的作用,但因小额信贷分散、成本高,且无担保,一般化的商业运作模式最终导致资产风险加大,使得追偿成本和难度加大,因此商业类金融机构对小额信贷丧失动力和积极性。若利用农村贫困社区传统文化对信用的约束,挖掘农村贫困社区的群体信用潜能及创富潜力,重视女性传统社会性别角色,构建新型小额信贷模式,可有效地降低金融机构的资产风险。
传统文化;小额信贷;信用约束;创富机制
1997年,全世界的小额信贷客户只有750万,到了2005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1个亿,而其中约有8500万人在亚洲,可见其在亚洲的发展速度非常迅猛。在亚洲,小额贷款用户则主要分布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加起来有5000万人之多,而在中国却只有10万人。中国的2.4亿农户中,1.2亿有贷款需要。与小额信贷在亚洲的发展速度相比,中国显然已经落后了。2009年银监会提出3年全国开设1027家村镇银行的规划,但截至2000年底,在全国仅开设的395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中,村镇银行349家、贷款公司9家、农村资金互助社37家),而五大国有银行动作较为缓慢。到2011年3月底,全国共有小额信贷公司3027家,从业人员32097,实收资本2141亿元,贷款余额2408亿元。[1]而这3千多家小额信贷公司主要分布在城市,对农村社区很少顾及。目前,中国的小额信贷发展基本有三种模式:一种是政府的扶贫基金所发放的小额信贷,如全国妇联、中华总工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中国扶贫基金会是目前借贷规模最大的民间小额信贷组织的管理者,其小额信贷项目、母婴平安120项目、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自强项目、中国消除贫困奖评选表彰活动等已成为国内知名公益品牌。[2]二是由NGO(非政府组织)组织通过吸纳的国际、国内捐赠来发放的小额信贷。这类NGO组织目前在国内大概有300多个。三是由商业类金融机构所发放的小额信贷,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及上述所提到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2005年开始商业性的小额信贷公司等。前两者不算根本意义上的小额信贷,没有合法的借贷经营权,没有持续的资金来源,其收取的利息仅是对借款人还贷的约束,最终目的是扶贫发展和反贫困,而不是获取商业利润。只有第三种才算是根本意义上的小额信贷。比较遗憾的是,在实际操作中,只有NGO能够长期深入社区,充分调查研究社区传统文化习俗,通过参与式发展模式让社区民众参与项目的设计、款项的使用和管理,并取得了较好的扶贫效果和较低的违约风险。而真正的金融机构却忽视了小额信贷的信用软约束内涵,即贫困人口的社区传统文化对借款人的信用约束,过多地强调通过有价资产的抵押等硬约束来防止信用危机和金融风险,其结果是阻碍了小额信贷在中国的发展。
目前,众多的NGO通过社区发展基金机制(CDF)来管理小额信贷,即以社区为载体,以赋权和挖掘社区传统文化中的诚信约束机制,来培育社区村民自我约束能力、自我组织能力和财富创造能力,能有效地结合社区的传统文化特点来提高小额信贷的实际效果。著名的NGO组织香港乐施会,已在云南、贵州、广西、甘肃、陕西等5省区18个县22个乡38个村实施了这种模式,香港乐施会一共给这些村庄的4752家农户贷放本金496.7万元,还贷率93.3%,被覆盖农户每户平均增收3167元。在云南禄劝县运行8年来,小额信贷还贷率平均达到99.79%,比孟加拉乡村银行99%的还贷率还高,创造了政府扶贫和正规金融机构不可能达到的奇迹[3]。但是,通过公益类机构来发放小额信贷并不是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的方向和主流,只有商业类金融机构运作小额信贷,培育成熟的市场,才是将来发展的方向。而商业类金融机构由于缺乏对社区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而过度害怕风险,使得中国的小额信贷停滞不前。同时,由于对风险的过度惧怕,“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小额信贷缺少瞄准贫穷人群的自觉机制”[4],而是把小额信贷过度地投向了农村社区相对富裕的群体,失去了小额信贷的本来意义。因此,商业类金融机构有必要向NGO、孟加拉乡村银行学习对社区传统文化精髓的理解和应用,以提高小额信贷的效率。
一、利用社区传统的紧密结构巩固信用
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简称GB)的五人小组机制(简称GB模式)是其成功的关键。这可以让社区成员互相鼓励,相互约束,虽然其他社区成员没有责任为负有小额贷款债务的成员还款,但如果小组内有社区成员有不佳或不良的还款纪录,整个信用的链条可能会因此中断,这就会影响整个小组以后的借贷额和连续借款。因此,小组内的每个成员或家庭已捆绑为一个信用整体。
与孟加拉乡村银行GB模式不同的是,社区发展基金(简称CDF)机制以社区为载体,以赋权和挖掘社区传统文化中的诚信约束机制来培育社区村民自我约束能力、自我组织能力和财富创造能力。这样的模式所依托的仍然是农村社区紧密的社会联系所形成的社区信用约束。如香港乐施会在云南的“社区发展基金项目”,是村民通过选举组成基金管理委员会,自定利息,督促借款者还款,同时把利息收益投入到社区建设上。在香港乐施会的“五户联保”模式中,由5~8户社区网络关系密切的村民自愿组成小组,互相约束、互相监督、互相帮助,如有一人(户)不能及时还款,其他农户则要帮他垫钱还款,否则将失去下次贷款机会;如果这个组不能及时还贷,整个村就要帮忙,否则全村人也将失去再次贷款机会。在脆弱的贫困社区,获得连续的小额贷款是财富再生机制必不可少的部分,也是农户摆脱贫穷的机会的延续。因此,贫困村民都知道不还款不仅是一个不明智的行为,而且来自社区的其它村民的压力也会很大。社区传统氛围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约束,他们深知,若不能获得连续的、长期的贷款,彻底改善境况的可能性就不大。香港乐施会禄劝县芹菜塘村民用每年100%的还贷率证明了这一点。
在一个松散的社会结构下,这样的还款机制很难实现其最终的目的。但在中国传统社区,尤其是相对封闭和贫困的农村社区,社区结构紧密、家族亲戚关系网络互相交织、宗教氛围浓厚、邻里互帮的传统文化习俗非常典型。通过有效的管理机制,社区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会通过社区紧密的关系网络释放出来,且由于不同农村社区其地域文化呈现不同的特点,对于社区成员还贷出现违约所带来的压力是超乎想象的。宗教信仰、村规民约,甚至社区的流言蜚语都对债务人产生很大的约束力。一些基层村干部、经济学者或人类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点。因此,商业类金融机构应学习并善用社区传统文化中的社区信用约束功能,通过构建社区信用提高还贷率,降低小额信贷的风险。
通过结合家族网络、宗族网络、亲戚关系、邻里关系、宗教信仰等社区关系网络形成信贷项目互助小组,增强他们的抗风险能力,挖掘和激发社区中新的信用约束机制,来构建新型的社区信用。一旦这种社区诚信机制形成,贫困人口不仅能通过小额信贷改善目前的困境,而且还会因财富的增长增加其社会活动范围,减少与其他社区的隔离。由于共同追求财富增长以及担负债务偿还,更增加了贫困群体之间的情感维系,满足了个人和家庭的社区归属意愿,使人们以彼此的社会、经济责任感参与其中,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实现良性变迁。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结构加速变迁,农村社区传统文化的许多积极因子因受外部的影响逐渐消失,特别是年轻群体受社区传统习俗的约束力开始下降。越来越多的年轻群体开始走出农村社区进入城市社区,他们与农村社区的传统社会联系,如亲戚、邻里联系等越来越少,宗教、习俗、村规民约等对他们的约束力渐渐减弱。即便是重新回到农村社区,但其观念已深受城市社区青年的独立、自我等意识影响,传统的农村社区网络关系意识开始淡化。因此,在小额信贷管理中,如何将年轻群体纳入社区信用约束机制,是金融机构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一方面他们是社区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另一方面他们可能又是小额信贷风险的主要来源。
二、理解社区传统文化,构建新型小额信贷管理模式
很多金融机构都把因自然环境、生态所导致的贫困称为“顽固的贫困”,而把因传统文化习俗等原因形成的贫困人群称为“难以触及的人群”。对贫困农村社区致贫原因的了解,是需要走进农村社区理解其传统文化的。现代商业银行远离农村社区,即便是农村金融机构的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其业务网点也大都分布在乡镇。如果不是催还贷款,业务人员大多很少进入农村社区去了解他们贫穷的原因、社区的传统习俗、创造财富的特点等。因此,现代商业银行不仅从距离上远离农村社区,在心理上往往也远离农村社区。一方面社区村民需要付出高额的交通成本到城里去申请希望并不大的小额贷款;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面对城乡巨大的文化、经济差异,与满口都是金融专业术语的商业银行员工打交道。因此,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为取得小额贷款而付出的高额成本,还有巨大的心里压力。现代商业银行往往让贫困社区村民感到高不可攀,其过分讲究金融技术的专业术语和对贫困人群的傲慢,让贫困人群对其丧失了信心。
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认为,每人都是未开发的宝藏,具有无穷无尽的能量。每个人都是一个消费者,他(她)尽情使用地球的资源,但他(她)也是一位为社会作出贡献的生产者,因为他(她)拥有巨大潜能,而发现潜能和找到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办法就是进入社区。2006年他在访华期间说:“我是做小额信贷的,做小额信贷是与老百姓打交道的,在孟加拉国乡下老百姓很穷,很多人是赤脚的,我很大部分时间是走村串户,我已经有拖鞋穿,所以我穿拖鞋来。做好小额信贷,不能与正规金融的程序一样,就像不能穿皮鞋到稻田去一样,一定要穿拖鞋。我是反传统的,小额信贷也是反正规金融传统的。”[2]实际上,孟加拉国乡村银行也是这么践行的。乡村银行系统的运作原则是:人们不应该到银行来,而是银行应该到民众中去。银行职员的工作不是坐办公室,而是与民众融为一体。相反,传统银行要求职员都要到办公室上班,而对穷人来说,办公室让他们畏惧,从而疏远了银行。截至2006年6月底,孟加拉国乡村银行有2185家分行,服务69140个村的639万借款人,而员工总数只为18151人,平均每名员工要服务3.8个村子和352名借款人。
中国农村社区差异性极大,每个农村社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习俗、村规民约等。社区内每个村民的财富创造都离不开社区的公共环境和传统文化特点。对于众多的贫困人群来讲,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小额信贷所提供的资本,更多地是需要融入社区传统文化的金融服务。需要识别社区文化致贫、传统致贫等的原因,有一套针对社区贫困人群和其致贫原因的小额信贷瞄准系统和贫困村民共同建立高效的金融服务支持系统。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对农村贫困社区的深入了解。反过来,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有效的瞄准系统,真正的贫困村民就可能贷不到款,进而转向高利贷,进一步加深贫困。据云南省社科院经济所课题组对云南省昭通市大山包乡调查,借高利贷的农户95%是贫困户[5]。如果金融机构不能提供及时、有效的资本支持,贫困村民就会陷入“贫困——高利借贷——更加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而不能自拨。
三、理解并尊重社区贫困群体的文化特质,挖掘财富创造潜力
贫困人口是一个因独特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地域性贫困人口群。尤其以农村贫困人口最为庞大,因不同的农村社区传统文化习俗不同,这些贫困人口在经济、社会、心理、性格、政治参与上都有着不同特点。但也有很大的共性,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收入水平低、受教育程度低、社会参与意识弱、争取和把握机会的能力差、政治参与意识淡薄,以及缺乏自信心等。但从不同的社区来看,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同社区的贫困群体在社区互助、宗教信仰、社区网络、财富创造动力、社区社会结构等方面又呈现巨大的差异性。因此,普通金融机构以统一的模式对农村贫困社区展开小额信贷业务,一是难以取得较高的还贷率从而丧失信心;二是一些金融机构本身就对这样的贫困群体带有偏见,认为他们缺乏财富创造动力和经营管理能力,从而对贫困群体发放小额贷款没有积极性。
面对有着不同传统文化特点的贫困群体,长期以来的做法是,通过单方面价值转移的贫困补贴来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而这种方法反而加重了财政的负担。贫困补贴只能缓解贫困群体所面临的临时性困境,不是彻底解决贫困的有效办法,其产生的负面效果就是让贫困群体丧失主动性而使贫穷继续存在下去。在中国,有太多的农村社区贫困群体需要小额贷款作为一个起点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实际上在商业类金融机构二八定律的约束下,真正的贫困人口很难贷到款项。这些社会贫困弱势群体,具有诚实、善良、勤劳、正直、吃苦耐劳、注重在社区的声誉、看重社区关系和亲情的优点,但他们没有文化、闭塞、不被人尊重。因没有足够的收入,他们缺乏城市贫困群体所具有的创造财富或者冒险的勇气。即使有创造财富和冒险的勇气,也缺乏基本的技能。这几乎是每一个农村贫困社区的特质。因此传统商业类金融机构往往会选择远离他们。在公益性小额信贷还不能惠及每一个贫困村民时,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需要充分理解社区贫困人群的传统文化的特质,去挖掘具有财富创造潜能的人群,给他们一个支点。除了发放小额贷款以外,还需进行一定的培训和指导,把乡土知识和外来科技、管理经验、理财技能等结合起来,让他们提高创造财富的能力,释放创造财富的能量。而这恰恰是目前商业类金融机构经营小额信贷的弱项,非常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动辄就需要对方提供抵押物,是目前商业类金融机构在经营小额信贷方面的通常做法。然而,有了抵押物,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额信贷。孟加拉国乡村银行自创建以来,至今仍奉行由诺思规定的贷款原则:不用任何抵押物,低收入群体亦能申请贷款;即便是乞丐也能从乡村银行借到款项,且乡村银行每名客户经理至少要发展一名乞丐客户。至2004年末,孟加拉国乡村银行一共有2.6万个乞丐拿到了小额贷款。偿还期还未到,已有近60%的贷款已被偿清。大部分的乞丐都成功转变为小贩,能够自食其力,并感受到生活的快乐与社会的尊重,贫困群体的财富创造潜能被充分地发掘出来。用乞丐们的话来说:“过去总是关着的门打开了,人们见了我们不躲了,好多人还主动搬来板凳,请我们坐一会儿,人活着又有尊严了。”[6]传统文化中的社区自信,随着财富的增长也被释放了出来。
四、重视社区信贷机制中的传统女性社会角色
“社会性别”①“社会性别”由美国人类学家格·如本(Gagle Rubin)于1976年提出。理论认为,男(male)女(female)应从社会、文化的背景去理解,该理论强调“后天”对“先天”影响,指出社会制度、法律、价值观对妇女的歧视而造成政治、文化、经济上的压迫。实现男女平等的道路有待于建设一个平等的社会制度,创造一个平等的文化,并且应把妇女看做是社会经济活动积极的参与者而非被动的发展的接受者。在社会发展中,女性与男性处于平等的主体地位。因此,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财产上,女性应该独立自主,摆脱依赖男性的软弱心理。
目前我国2000多万贫困人口中,有60%是女性②新华社北京2005年1月3日电(记者李薇薇)。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女性由于其性别角色的障碍,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贫困。但男性和女性对于贫困有不同的体验和认知,女性对贫困的感受更加敏感,她们对家庭可能陷入贫困的境地有着深深的恐惧和担忧,对于所经历的贫困,如衣食不保、小孩无钱上学、子女无钱结婚等刻骨铭心,对贫困可能再次降临也有着深深的恐惧。在农村贫困社区,基本上是夫权主导家庭,男性主导社区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服务资源和机会资源的分配,排斥并限制了妇女对这些资源的获取,使得女性在获取资源和整个决策的过程中均处于不平等的位置,成为最贫困的弱势群体之一。而另一方面,农村贫困社区的女性也缺乏对政治、文化、教育等资源的参与和争取的热情,但又渴望通过一定经济资源的获取或支持来改变贫困的命运。因此,现代商业银行的金融服务总是倾向于握有大量社会资源的男性一方和高收入群体,忽视了贫困社区女性对经济资源的渴望、改变贫困的需求和决心,以及比男性更加强烈的通过小资本来摆脱贫困的欲望和动力,而现实恰恰相反,女性则常常处于信贷市场边缘化的地位。
此外,传统文化的惯性又约束着农村贫困社区的妇女,一方面要主内即相夫教子,另一方面又要像男性那样在外承担繁重的劳务来养家糊口。这种男女角色“双肩挑”的生活状态给贫困女性增加了极大的心理和生理压力,即便是在城市贫困社区,女性大多数从事的也是低工资、低技能、社会保险程度较低的工作。而目前的女性问题研究过多的是关注女权、男女平等、性别歧视等问题,较少关注如何通过提高贫困社区女性经济地位从而最终改善社会地位方面。
在孟加拉国,乡村银行97%的贷款人是农村贫困社区妇女,其还款率近99%。该银行之所以把社区妇女作为主要的客户,正是基于对社区传统文化中女性社会角色的充分了解。在农村贫困社区,传统文化对女性的约束依然强大,在这样的社区氛围里,女性比男性更在乎别人对自己看法,更在乎自己的声誉。甚至社区的流言蜚语都对他们产生很大的约束,更何况因信贷可能产生的信用问题。因此,在被称为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社会发展宪法的“16项决定”中谈到“信贷是一种人权”,尤其在对女性的经济赋权方面,乡村银行更是优先赋予女性信贷的权利。使女性和男性一样在经济资源方面赋权,一方面因为贫困社区女性把家庭责任和社会资本的获取看得非常重要,更多地担忧取得信贷后面临的社区信用压力;另一方面,从性别分工和性别关系来看,贫困对男女有着不尽相同的影响,男女对贫困也有着不尽相同的感受,女性对于通过创造财富来改变贫困的心理更加迫切并愿意承受很大的压力,在陷入贫困时,真正站出来为家庭、为子女谋生计的,反而是以母爱为天职的女性。所以通过向农村贫困社区妇女发放小额信贷也可以保证金融机构有很高的还贷率。
社区传统文化是社区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及社区变迁中所形成的物质成果、精神形态以及制度、规约、交往方式、生活习俗和语言、思维方式的总和,在社区群体的代代相传中,尽管也会部分消失或变异,但其中传承下来的部分对社区个人行为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小额信贷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金融标准化工作,而是针对传统文化差异很大的农村贫困社区的个性化金融服务,它体现在深入社区,通过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人信用行为的影响,洞悉农村社区的传统文化与信用之间的机制作用,寻找和挖掘社区传统文化中有利于商业诚信制度的建设的因子,以提高小额信贷的质量。
[1]焦瑾璞.促进中国微型金融规范健康发展[R].在第三届小额信贷机构与国际投资人交流会暨小额贷款公司研讨会上的发言,2011-04-27.
[2]中国扶贫基金会 [EB/OL].http://www.fupin.org.cn/index.asp.
[3]南方报业网[EB/OL]2006.10.30
[4]焦瑾璞.小额信贷与农村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5]赵俊臣.中国农村金融新体系构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6]非比.穷人银行家[J].读者,2005,(13).
(责任编辑 丁立平)
Credit Restraint of Traditional Community Culture and W ealth-producing M echanism:A Study of M icrocredit
YU Ru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YUN,Yunna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Kunming650031,China)
Microcredit is helpful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oor community in the countryside.However,microcredit has much risk by commercial operation because it is costly and has no guarantee.As a result,commercial banks have little motivation in implementing microcredit.If the credit restraint of traditional community culture and the group credit potential as well as wealth-producing potential are brought into full play,a new microcredit model can be established,which can help the women play a better role and reduce possible financial risks.
traditional culture;microcredit;credit restraint;wealth-producing mechanism
F830.5
A
1672-867X(2011)06-0128-05
2011-08-20
俞茹(1965-),女(傣族),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教授。孟金莲(1963-),女,云南民族大学财务处高级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