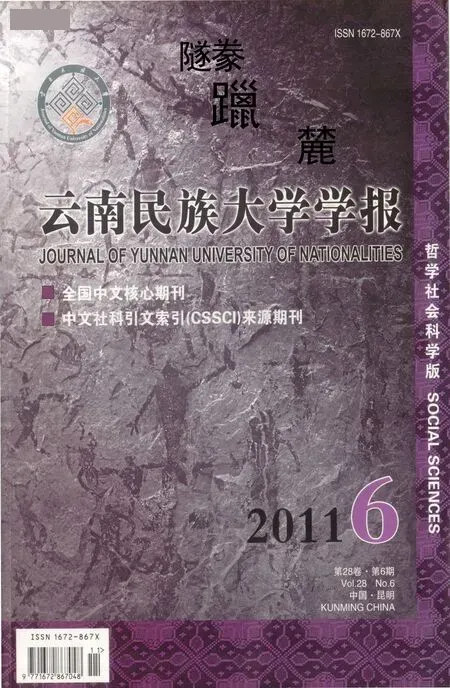论苗族古村落“路”、“桥”生命文化的发生
杨东升
(凯里学院,贵州 凯里 556011)
路、桥是苗族古村落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石级蜿蜒的村落巷道,小桥流水的周边环境,不仅突显着苗族古村落的古朴与闲静,同时也隐含着古村落的独特与神秘,是古村落显著的村落景观之一。
“保命路”、“求子桥”是苗族古村落路、桥最显著的文化特征,是苗族生命文化最突出的表现。村落人们久病不愈或家族富有,久婚不育或缺子少子,都力图铺路造桥,以求延年益寿、富贵腾达、添男添丁、子孙繁衍。古村落这一路、桥生命文化在现代文明社会,仍沿袭不绝。是什么原因保持了苗族路、桥生命文化的活力?作为连接村落与村落,村落与外界而出现的苗族古村落路、桥文化,其生命意义,是如何发生的?目前,苗学界关于苗族古村落路、桥生命文化探究较多,但对其是如何发生的,探究较少,或者说尚无人探究。当然,路、桥生命文化,不仅存在于苗族中,与苗族相邻的侗族也有相似的文化,但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存在差异。本文主要探讨的是苗族古村落,尤其是黔东南苗族古村落路、桥生命文化的发生。
一、苗族古村落路、桥生命文化的特征
(一)建材选择
苗族古村落的路,无论是村落巷道,村外通道,还是山间小道,一般都用石料砌铺。铺路的石料选取非常讲究。取石地一般选在居民认为比较干净或吉利的河漫滩、芦笙场等地方,忌到村寨经常驱鬼、送鬼的鬼场或冤魂屈鬼的坟场周围取石。人们认为,如果到鬼场或冤魂坟场周围取石,会招引鬼魂沿路进村或在砌铺的路上游荡,殃及村民和路人生命。石料选取忌二次用石,曾作过土地庙和佛教堂的石料,是绝对不能选用的。用土地庙石料,会招来横祸,用佛教堂石料,则意味着断子绝孙,等等。
苗族古村落的桥,一般选用杉木、枫木横架。这种选材,除与木材本身的特质有关之外,最主要的是与苗族的生命崇拜有关。杉木耐朽,有韧性,是苗族造桥选材的重要原因,但杉木高大,笔直挺拔,蕴含子孙健壮、刚劲的文化内涵才是选材的主要原因。造桥选用枫木,则完全与苗族的图腾崇拜有关,“它不仅包含了远古蚩尤枫木桎梏的造化,也包含了《苗族古歌》枫树蝴蝶妈妈生蛋造化人间万物的文化内涵”[1],是苗族图腾崇拜的内在要求。
(二)协力建造
苗族古村落的路、桥是个人或家族修建的。修建路、桥一般基于这样的目的:一是主人富有或身体欠安,往往要择路铺石,以求富贵与长寿;二是主人缺子少子,往往要修桥,以求子嗣,这种桥一般较小;三是家族发达,经济富有,为求子孙繁衍,追求富贵,家族往往要修建大路和大桥。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也不论是个人或家族修建,路、桥从取石、伐木、搬运到修建,整个建造过程,都是家族无偿协力完成。这是苗族氏族社会的遗俗。
(三)巫师参与
苗族古村落的路、桥建造,充满着巫术色彩。路段的选取、朝向,树木的选择、砍伐,路、桥的开工、建造,巫师参与了整个路、桥的建造过程。苗族认为铺路与长寿和富贵是成正比的。铺设路段通行量越大、越艰难、越长,则铺设获得的寿富就越多。因此,在铺路选择上,一般以通行量大、崎岖难行的路段为首选,但路向和路段的实际选择要请巫师占卜来确定。路段选好,开工时,巫师先于路段两端烧香化纸,念巫词,宰一公鸡沿路滴血,随后,主人或族长必须亲手在路的一端铺下第一块石块,表示这一路段是主人或家族铺设的,随后,家族共同修建。峻工时,同样请巫师施巫术、做巫事。同时,杀猪宰鸭,八方亲友前来庆贺。
造桥选材,要求必须是树尖不折,枝叶茂盛的杉木和枫木。取材时,先请巫师进山择木。中选的树木,巫师先于树下烧香化纸,祭以酒肉,口念巫词:“山神树神,主人造桥,子孙繁衍,村寨兴隆;子孙强壮,护村护寨;请求许恕,借以林木……”,而后,给树系上麻线。择日,请多子多女,双亲健在的壮汉带人进山伐木。架桥时,备以猪、鸭、蛋、鱼、酒、糯米饭、五颜六色的剪纸花以及锅、盆、碗、筷等餐具。巫师做巫事、念巫词,开始架桥。桥架好后,给桥贴上纸花,在桥面上摆好蛋、酒、糯米饭,并在桥头岸边栽上枫树、樟树、柏树或竹子。栽树的目的,一是希望桥像树常青,二是可供人休息和乘凉。随后,伐木壮汉亲手杀大猪、宰鱼鸭。前来庆贺的亲朋好友生膏火、架大锅、煮猪鸭。过路行人,遇上架桥,是出门逢喜,一般要参与族人共进酒食。酒食后,主人或族长给每位亲朋好友和路人分发两枚红蛋和一包糯米饭,带回家中。巫师参与了整个路、桥的建造过程。
(四)路、桥隶属
苗族古村落的路、桥隶属于个人和家族,有的路、桥还以主人或族群的名字命名,并世代相传。随着家族的繁衍,人口的增长,历史越悠久,其隶属的家族就越庞大,势力也就越强,路逐渐由“家路”演变为“族路”和“宗路”;桥也逐渐由“家桥”演变为“族桥”和“宗桥”。路、桥损毁由隶属者负责维修和再建,时间一般选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或前夕。别人不能在已砌铺的路段或已修建的桥上重新铺路和架桥,否则会引起族际纠纷。苗族认为路、桥是生命的延续、子孙的繁衍、财富的象征。在别人砌铺过的路段或已修建的桥上重新铺路和架桥,无异于夺命、抢子和敛财,是对路主、桥主的侮辱,对族群的蔑视,这是十分致命的。苗族这种路、桥生命文化,是苗族古村落到处是石级小路和小桥流水的真正原因。
(五)路、桥祭拜
路、桥祭拜是苗族古村落文化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路的祭拜,时间不定,一般视需要祭拜,但桥的祭拜,时间是比较固定的。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各家各户带糯米饭、红蛋、鱼、纸花、酒肉、香纸,携儿带女,给村落及周边的家桥、族桥、宗桥进行祭拜。通过年年祭拜,一是让子孙牢记自己的家桥、族桥和宗桥,二是对路、桥赐福赐子表示答谢,三是祈求保佑子孙安康和老人长寿,四是缺子少子人家,祈求恩赐子嗣,添男添丁。若灵验,次年农历二月二则杀猪宰鸭祭拜,以示答谢。
二、苗族古村落路、桥的生命文化内涵
苗族古村落路、桥具有强烈的生命意义。无论是路、桥的取材、建造、隶属,或是巫事、祭拜都充满着生命的文化色彩,表现出接引、延续、繁衍和凝聚的生命文化内涵。
(一)生命的接引
在苗族的生育观念里,认为生育是孩魂归家的原因所致。因此,只要将孩魂招来,便可生男添丁。同时认为,孩魂不在山里,也不在田间地头,孩魂常来的地方是桥头溪边,因为桥头溪边有适宜于孩魂天性的小桥流水。苗族还认为,孩魂不能涉水过河,只有桥才能牵引孩魂过溪,要想将其招来,就必须到桥上求子。于是,缺子少子人家,便带着纸花和孩魂喜用的红蛋、糯米饭,请巫师到桥上招魂求子。求子时,先给桥贴上五颜六色的纸花,意为花一样美丽的通途,随后摆上红蛋、鱼、糯米饭,烧香化烛,接着巫师念词招子:“桥边溪水小玩童(孩魂),你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太阳西斜日将落,天黑地暗鬼怪多,快快找爸找妈去!桥边溪水小玩童,你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天阴云卷雨将来,雨来溪涨鬼蛇多,快快找爸找妈去!桥边溪水小玩童,来来我牵手,来来我背你,背你去找好爹妈,背你去找好人家。”待在桥上发现小蜘蛛,将其逮住,用布帕包好,由巫师背负回主人家中,解开布帕,将小蜘蛛放于卧室床上,表示求子完毕。苗族为何将小蜘蛛作为孩魂的灵显,目前尚不得而知。从桥上求子和巫师的巫词中,桥表现出生命接引的文化内涵。
(二)生命的延续
在苗族的观念里,路与命是息息相通的,人生中的种种不幸就像道路中的坎坎坷坷,只要越过坎坷的路段,前面就是舒坦的大道,于是把生命和路联系在一起。在苗族古村落,当人久病不愈时,便去铺路、修路和祭路,试图通过铺路、修路、祭路获得生命的安康和延续。于是,具有延伸功能,作为联系和沟通外部世界的路,在苗族社会中发生了嬗变,成为生命延续的“保命路”。同样,对于生命的延续,苗族也对桥提出了诉求。苗族认为人来自桥头溪边,当人久病不愈时,认为魂已不再附体,或许已重新回到桥头溪边去了。于是“身体瘦弱,面黄肌瘦,吃不下饭,查不出原因者,便认为是掉魂。于是请巫师来叫魂。”[2](P33)叫魂也称招魂。招魂时,巫师同样带着红蛋、糯米饭、酒肉、香纸到桥上去招魂。并念招魂词:“魂兮归来,爹妈多么疼你呀!魂兮归来,你家多么美好呀!魂兮归来!”[2](P33)当发现小蜘蛛在桥上吊线或爬行时,将其逮住,并用树叶包好,带回家中,放于盛水的小碗,让病人喝下,表示魂已招回。事实上,苗族招魂的历史已非常久远,与苗族同源的楚族,[3]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招魂习俗。先秦文学中,楚辞《招魂》就是例证。是什么原因使这一习俗在苗族迁入西南山地后,变成了桥上招魂是值得深究的。
(三)生命的繁衍
苗族是一个对子孙繁衍具有强烈追求与渴望的民族。由于长期迁徙,发展滞后,好巫信鬼,苗族认识和改选自然的能力低下,从而把种族的不幸,人身的遭遇都归因于外部世界神秘力量的操控,把美好的愿望与祈求都寄于自然物施舍。于是具有接引功能的桥,就成为苗族生命的源处,把对子孙繁衍的渴望都寄于对桥的崇拜。这种崇拜不仅贯穿于整个建桥的过程,同时也展示在桥的祭祀过程中。苗族造桥选用枫木,这无疑包含着枫木蝴蝶生蛋衍生万物的生命图腾,同时,也包含着蝴蝶大量排卵迅速演化后代的偶喻。苗族祭桥时,喜用红蛋和鱼作祭品。红蛋除了具有迎合孩魂天性外,蛋的本身还暗喻着新生命的诞生,是祭桥的直接目的指向。祭桥用鱼,无疑是借助鱼卵的快速繁殖,表达对子孙快速繁衍的期望,具有与蝴蝶同样的生命意义。
(四)生命的凝聚
苗族古村落的路、桥,不仅具有生命接引、延续和繁衍的文化功能,同时,还具有生命的凝聚作用,是族群认同的重要标志。
随着苗族古村落人口的繁衍,族群的庞大,在路由“家路”变成“族路”和“宗路”,桥由“家桥”变为“族桥”和“宗桥”的过程中,路、桥成为维系族群的标志。苗族的许多社会生活如共同祭祖、盟约,重大事项的决定,族内事务的处理,联合对外,维护族群利益等,常常都在以“族路”、“宗路”或“族桥”、“宗桥”为单位的族群下进行。因此,路、桥不仅成为苗族古村落求子、求福和子孙繁衍的寄托,同时也成为维系家族情感和增进族系血缘关系的纽带。苗族古村落人口增多了,家族发达了,往往要分迁他处。这时,迁徙后的族长会告知自己子孙,家族的来处,“宗路”和“宗桥”的桥名。若干年后,子孙携家带眷回归故里,寻找“宗路”和“宗桥”,施行祭拜。届时,故里宗族杀猪款待,几日畅饮,共叙迁徙历史和历途艰辛。来族与宗族相敬如宾,亲如兄弟。
三、苗族古村落路、桥生命文化的发生
作为人们联系和沟通外部世界,具有延伸、接引功能的路、桥,在苗族社会发展中,异化为生命的延续和接引,形成了“保命路”、“求子桥”。这种生命文化的发生,必然存在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和客观的环境条件。
(一)苗族路、桥生命文化的发生是苗族迁徙历史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苗族从炎黄时代涿鹿战败,到新中国成立,从黄河流域到西南各省,由于历代王朝的征讨,长时间、远距离的迁徙从来没有停止过。征讨与迁徙,造成苗族先民游离失所。为逃避战乱,苗族先民在迁徙中不得不跋山涉水、跨沟过隙,这是生存的客观需要。跋山涉水、跨沟过隙,则预示着生存的希望,生命的延续。路、桥是实现跨沟过隙的条件和手段,是生存和生命延续的依托。于是,具有延伸和接引功能的路、桥就赋予了生命特殊的意义,成为生存希望、生命延续乃至种族繁衍的象征——苗族原生的路、桥生命文化。这种原生的路、桥生命文化在历史演变中,逐渐演化为能给苗族带来延年益寿和子孙繁衍的文化认同。这就是苗族“保命路”、“求子桥”生命文化发生的历史基础。征讨与迁徙,被俘与死亡,造成苗族人口的大量锐减,苗族自我保护的力量遭到巨大削弱,种族繁衍受到威胁,从而产生了对种族繁衍的强烈要求。为了种族的延续,苗族不得不选择多生快长的生育方式,以弥补种族人口的不足。这是苗族对子孙繁衍强烈渴望的原因所在,是苗族迁徙历史的内在要求。在上述巫师的巫词“主人造桥,子孙繁衍,村寨兴隆;子孙强壮,护村护寨”中,已清楚地表明苗族对子孙繁衍的目的和诉求。于是,具有特殊生命意义的路、桥就成为苗族子孙繁衍的载体和诉求的表达形式,这是苗族历史的必然选择。
征讨与迁徙,使苗族产生了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为了民族的生存和种族的繁衍,苗族内部必须保持巨大的凝聚力,以获得对外足够的力量。“这种自我保护意识和凝聚力,在文化内涵上,表现为高度的族群认同。文化内涵的外在表现,则需要某种固定的符号特征来体现。这种固定的符号特征表现在宗教上,即是共同的‘祖先崇拜’或‘图腾崇拜’”,[4]表现在路、桥文化上,路、桥则成为苗族族群认同的重要标志,成为维系家族情感和增进族系血液关系的纽带。这就是路、桥在隶属关系上,由“家路”变成“族路”和“宗路”,由“家桥”变为“族桥”和“宗桥”的真正原因。苗族路、桥文化的发生是迁徙历史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
(二)苗族路、桥生命文化的发生是苗族适应西南山地的客观要求。苗族路、桥生命文化的发生既是苗族历史迁徙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苗族适应西南山地的客观要求。西南山地提供了苗族路、桥生命文化发生的地理条件。任何文化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形成、演化和发展的。西南山地山峦重叠,沟壑纵横,斜坡陡峭,雨天路滑,这是苗族路、桥生命文化发生的地理基础。“三苗”时期,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苗族先民,主要从事平原经济,资源相对富足。反映“三苗”时期苗族经济的湖北屈家岭文化,已具有相当发达的农业。[5]春秋战国后,尤其是宋代以来,苗族先民大举进入西南山地,[6]开始了由平原经济向山地经济的痛苦转型。这个转型是以高投入、低产出为代价的,是一个重新选择和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自然界能够提供给苗族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是极其稀少的。迁居西南山地,尤其是黔东南地区的苗族,由于大山阻隔和交通闭塞,在历代王朝征讨的间隙中,获得短暂的修整。“从汉至明,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均实行‘羁縻制’。在黔东南即有‘民不入峒,蛮不出境’的规定”,[2](P97)这使苗族人口获得了迅速发展。人口的发展,苗族对生活资料的需求也就越多。然而,西南贫瘠的山地,不可能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满足不了人口增长需求。《苗族古歌·跋山涉水》就曾有这样的描述:“子孙太多了,吃的找不到,穿的找不到,蕨根当饭吃,树叶做衣穿,……”。于是,为了解决由于人口增多带来的生活资料短缺问题,苗族必须开荒拓土,扩大生存空间。路、桥作为人类生存空间拓展的手段,成为苗族古村落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成为苗族人口繁衍和种族延续的物质来源保障。如果没有路、桥,就没有生产,也就没有苗族生存和繁衍的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路、桥就是生命,生命也是路、桥。于是,路、桥与苗族的生命便联系在一起,成为苗族古村落路、桥生命文化发生的客观要求。
(三)苗族“万物有灵”观念赋予苗族路、桥生命文化以灵性。“万物有灵”是基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形成的世界观。原始社会时期,由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低下,对外在的自然物及其自然力无法认知和驾驭,总是认为自然物都有其自身神秘的力量在左右,并将这种力量人格化,这就是灵魂。形成于原始社会的“万物有灵”观念,并不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同步。尤其是经济滞后的民族,在现代社会中,“万物有灵”仍然存在于人们的观念里,并以不同的形式渗透到各种文化之中。苗族路、桥生命文化产生于苗族迁徙的历史过程,形成于沟壑纵横的西南山地。苗族“万物有灵”观念赋予了路、桥生命文化以灵性,使路、桥成为具有灵魂、具有情感,能与人相通、善解人意和实现诉求的人格化事物。路、桥生命文化的灵性,是苗族赋予的,但却成为主宰苗族命运的外在事物。苗族成了自己塑造的人格化路、桥的奴隶,并把生命的产生、成长和延续都交给了路、桥,从而自觉和不自觉地对路、桥加以崇拜,使路、桥成为能实现苗族生命产生、延续和种族繁衍的生命文化。苗族“万物有灵”赋予了苗族路、桥生命文化以灵性,丰富了苗族路、桥生命文化的内涵。
(四)巫术文化使苗族路、桥生命文化产生虚幻与神秘。巫文化是苗族显著的文化特征。如果说苗族迁徙的历史和西南山地促成了苗族路、桥生命文化的发生,苗族“万物有灵”观念使苗族路、桥生命文化具有了灵性,那么,巫教则强化了苗族路、桥生命文化的虚幻与神秘。
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巫术观念,是幻想通过对自然物或自然力的敬拜和诉求,实现趋利避害的目的。巫术是敬拜和诉求的表达形式,是通过巫师实现人与自然力的意愿表达。苗族“万物有灵”观念赋予了苗族路、桥生命文化以灵性,但这只是对自然物人格化的树立。要实现苗族路、桥生命文化的诉求,还必须通过巫师作中介,通过巫术作表达。中介和表达的需要,促成了苗族路、桥生命文化与巫文化的结合。具有深厚巫文化基础的苗族,路、桥生命文化与巫文化的结合,是苗族路、桥生命文化发展的必然。苗族路、桥生命文化与巫文化的结合,促使巫术中的仪式、巫师和巫词三要素闪亮登场,从而增添了苗族路、桥生命文化的虚幻与神秘。苗族路、桥生命文化与巫文化结合之后,便贯穿于整个路、桥文化的活动过程。无论是路、桥的取材、建造,或是对路、桥的祭拜和祈求,无处不在巫师的参与和巫术的施行下进行。具有灵性的路、桥通过巫师和巫术实现了苗族的意愿表达和生命诉求,实现了苗族从情感到活动的现实体验。巫术文化强化了苗族路、桥生命文化的虚幻与神秘,更加丰富了苗族路、桥生命文化的内涵。
四、结语
苗族迁徙的历史和西南山地的地理环境促成了苗族路、桥生命文化的发生。苗族路、桥生命文化的发生是苗族迁徙历史的内在需求,是适应西南山地地理环境的客观需要。苗族“万物有灵”原始宗教使苗族路、桥生命文化具有了灵性,丰富了苗族路、桥生命文化的内涵。苗族的巫术文化实现了苗族对路、桥的生命诉求和意愿表达,使苗族路、桥生命文化变得更加虚幻与神秘,内涵更加丰富和多彩。正是由于苗族的历史、西南山地、“万物有灵”和巫术文化,才使苗族的“保命路”、“求子桥”这一路、桥生命文化,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仍生生不息,才使苗族古村落的路越修越远,桥越修越多。这也是苗族古村落到处都是石路小路和小桥流水的原因所在。在历史发展中,修路造桥已成为苗族古村落的道德规范和自觉行为。
[1]杨东升.论苗族古村落结构特征及其形成的文化地理背景[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
[2]罗义群.原生宗教与民族社区和谐构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3]伍新福.楚人、楚国与苗族 [J].贵州民族研究,2001,(1).
[4]杨东升.苗族服饰是自源发展的结果[J].凯里学院学报,2010,(5).
[5]伍新福.中国苗族通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
[6]席克定.再试论苗族妇女服装的类型、演化和时代[J].贵州民族研究,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