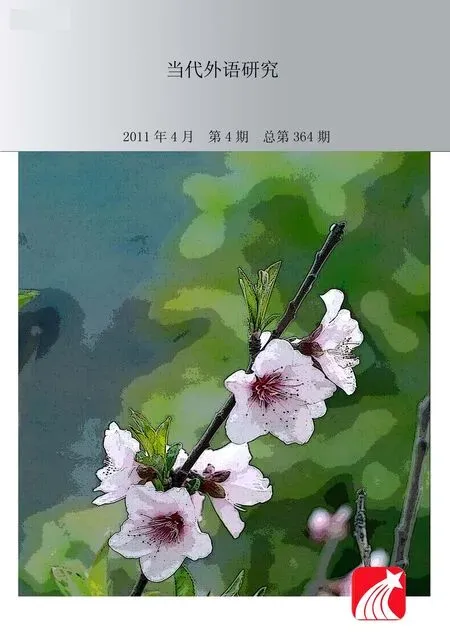少壮功夫老未成
徐盛桓
(河南大学,开封,475001)
1.楔子
来到人世,至今已虚度七十三个年头。想起陆游的诗《冬夜读书示子聿》,感慨良多。我没有做到“学问无遗力”,因而到了老,“功夫”仍未能“成”,只有发出如题目所说的感慨。
陆游又云:“世间万事有乘除,自笑羸然七十余。布被藜羹缘未尽,闭门更读数年书。”进入七十岁以后,我常说自己“年方七十”,就是希望上天能给我时间,从而“闭门更读数年书”,把我想做的事情多做一点。
2.启蒙
1945年,我七岁,正值启蒙开学之年,恰逢抗战胜利,我有机会上学了。
我上的第一所小学在广州光塔路光塔寺内。我当时住在仙邻巷,光塔寺就在仙邻巷对面,所以上学很方便。一双妈妈做的布鞋算是启蒙开学最光鲜的打扮了;衣裤则是爸妈或哥哥的衣服改的,一副寒酸相。最寒酸的是我没钱买课本,我的课本是爸爸用废纸订成本子后替我抄写而成的。好在一年级课本,国语(即语文)、算术都很简单。我记得爸爸还按原来书上的页面简单画了些图,上课用是没问题的。可是,在老师眼里,这样穷的学生,却有点难以接受,平时常常为难我。一次,忘了是因为什么,老师罚我站,我感到委屈,哭了起来。大滴大滴的眼泪滴在课本上,把墨写的课文弄得一塌糊涂;我为了保护课本,想用手去抹干它。谁知越抹越糊涂,课文变成了大花脸,课本也不能用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对不起我已过世的父亲,他花了那么多心血和寄予了那么多希望抄写出来的课本,竟然被我毁于一旦。我多么希望这寒酸的课本能留到现在,作为对我那一生潦倒穷困的爸爸的纪念,并且让我的子孙看看,了解过去日子的艰难困苦。

图1 徐盛桓教授在读书
眼泪洗书这一幕发生了之后,我就没有再去上学;随之,这些课本也因失去了它们本来的作用而被用来生炉子。我因课本事件停学,改为在家“上学”,这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父亲承担起了教我的责任。他要养家糊口,教我当然不是专职,只能在下班之后教教。“课本”是由他编选并抄写“出版”的《论语》、《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千家诗》等方面的内容。他教我认字、习字;习字的“字格”也是他写的,记得有“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床前明月光”之类;还有学习算术的加减,另外他要我背诵九九乘法表——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乘法表有什么用。晚上在油灯下,他为增加家里的一点收入,替人刻图章或写个条幅、画个中堂之类,我就站在他身边胡乱背诵“子曰”、“春眠不觉晓”、“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朱子格言)等;他还检查我的习字,在认为写得好的字上面画红圈圈。
逐渐地,我认得不少字了。白天,我自己在家,就把家里的书翻出来看,有历书、哥哥过去的课本、妈妈的唱本、不知什么时候留下来的书页已泛黄的《江湖奇侠传》等,看得半懂不懂。有一次,刚学习一个标点,是表示上下两个字互换的。我把封皮已经翻脱了的《小红袍》拿出来,在目录上点点画画,十分自鸣得意,等着哥哥放学回来夸我的杰作。谁知他拿起书来,看看画得斑斑点点的书页,嘟哝了一句就放下了,弄得我很没趣。有一次,我看到哥哥桌面上有个小玻璃镜框,里面有一张他写的字条:“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余之座右铭”。尽管我完全不知道“座右铭”、“负我”、“负人”是什么意思,但觉得这肯定是大人(我那个哥哥比我大七岁)书桌的标志,于是我也在经常写字的桌面上做了一个。
就这样,到了年底,一个学期就过去了。爸妈觉得我不去学校上学,始终不是个办法,就让我到另一学校去考一年级下学期插班生。这就是离家很近的广州市第一小学,即现在的朝天小学。那时候我不知道这是全市最好的小学——知道了我就不敢去考了。它由清朝的官办外语学校——同文馆几经改制而成;1945年任校长的梁寒淡是广东高要人,抗战时在澳门从事抗日戏剧宣传活动,胜利才回到广州当校长;他的哥哥梁寒操是国名党元老,曾任国民党的宣传部长。2005年,以梁寒淡名字命名的一所希望小学在他的家乡建成。
一年级插班生有九个人考。考完回家后爸爸问我考得怎么样,我回答说应该没出错。爸爸一点一点问我,我一点一点回忆。有一个问题记不起来为什么要回答“甘肃”,我写成“金肃”,爸爸就说我错了,原因是广州话“甘”、“金”同音。从放榜看到,录取了两名,我考第一。
在市一小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有一个地方是人人可以进来看书、借书的;原来在学校里不光是背诵、串讲、写字,还要唱歌、画画、做手工、跑步;除了在屋子里上课,还会在墙壁上贴上自己画的画、写的字、作的文,比比谁的好。有一次,我给广州一个儿童刊物投了一篇稿,不知为什么,后来文稿竟然抄录得端端正正,贴在学校的壁报栏里,这在当时学校里被传为佳话。我在市一小读了三年多,因为搬家,升五年级时转了校。在这三年多里,除了一次“童军”课小考考结绳,我没把“瓶结”结出来,得了个50分以外,其余的有笔试的各科小考大考,我的成绩都在90分以上;手工、体育、唱歌大概是八十来分。学期总成绩基本保持在年级的第二名。
在市一小,我学会了很多东西,至今仍令我十分怀念。迄今,我还记得在各年级时我的班主任的名字:四年级时,班主任叫谢志群,我曾从他家里借过一套在香港出版的描写一位流浪少年参加东江游击队的小说《虾球传》。后来谢老师生孩子,临时换了一位小伙子高浪教我们。高老师人如其姓,高高瘦瘦的。我对他有特别印象,因为他曾辅导我参加演讲比赛。为了辅导,有一天晚上他甚至留我在学校宿舍住。他人很活跃,课余常常教我们唱歌,如“大家唱”、“团结就是力量”、“古怪歌”、“山那边呀好地方”、“再会吧,香港”等。现在我们知道,这些是进步歌曲。教音乐课的是李老师,她不管我们水平怎么样,教我们唱很多名曲,如德国的“莱茵河的晚唱”、李叔同的“送别”等,至今还记忆犹新。1949年7月,我又由于搬家,升五年级时转到市五十小学。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迎来解放。
五十小学教音乐的何文蔚老师也是高高瘦瘦的青年,在我的记忆里,小提琴拉得不错,嗓音也好,带领我们几个学生教学校附近的居民唱歌。我们这些学生组成了一个合唱小组,曾到当时位于广州沙面的广州人民广播电台演唱。
1951年7月,我小学毕业,考上了广东省立文理学院附中。
3.中学
文理附中位于广州珠江以南当时属边远郊区的凤凰岗,那里曾经是个乱葬岗。我在学校寄宿,还当上广州一个青年刊物《在毛泽东旗帜下》的通讯员。一次,我步行一个多小时到珠江以北的北京路青年文化宫参加通废墟员会议。散会时十点,步行回到学校已经十一点多。途中我经过那些可以看到尸骨的坟地时,嘴里胡乱吼着苏联歌曲“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给自己壮胆,鼓足勇气朝前走。自此以后,多黑的夜路我都不害怕了。
市一小学、五十小学的唱歌经历埋下的种子,在文理附中得到个机会发芽了:我参加了电台“空中教歌”大队,电台每隔十天八天便会给我寄来一张新歌歌纸。一次,我刚收到电台给我寄来的歌纸,同学黄恭义拿过去就唱起来。我很纳闷:这是电台准备下周教的歌,黄恭义怎能马上流畅地唱出歌词来呢?一问才知道音乐人有一种视唱的本领:拿起一首新歌的歌谱,就能马上唱出歌词,先是第一段,之后是第二段、第三段,甚至四部混声合唱中相隔了四行歌谱的第三段的歌词都能唱出来;一边看歌谱,心里想着如何唱,嘴里就要把看到的词唱出来。音乐家会唱的是五线谱,但黄恭义只能处理简谱。这真是一个新天地,原来唱歌也有许多东西可以学。
知道了有什么东西可以学,就有了进取的目标。根据技巧进行学习并不难。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已经可以拿起歌纸就能唱第三段的歌词。在这样的刺激下,我开始学习乐理。通过学习从图书馆借来的许多解释乐理的书,包括五线谱入门的书,我发现自己的自学能力有了提高。我甚至还搞出了“土发明”:五线谱的调号很难记,C调没有#号,G调一个#号,D调两个#号,等等;另外还有b号;此外还分高音谱表、低音谱表等。我发现,把C、D、E、F排列以后,分别把G、A、B插在CDDEEF之间,成为C、G、D、A、E、B、F的排列,中央C没有#号,从G开始以后依次为两个#号、三个#号……,这就很好记了。高音谱表、低音谱表以及b号都有这样的简便记忆法。这个“发明”对我以后的各学科学习有启发:学科的原则、规则、规律是按有关的原理,经过严格的论证、推导得到的,学习时要十分注意这些严格的科学程序,把有关的原理弄通弄透,就能在偶然中找到必然。
就这样,我少年(我那时还是少先队员)的心灵上开启了一扇音乐之门。我继续借来作曲学、和声学、曲式学、对位法之类的书来啃,买来《黄河大合唱》的合唱总谱(简谱)对照学习。虽然当时看不大懂的,而且这些学习注定不会有实质性成果,因为我完全没有任何习乐的物质条件和必要的指导;但这并没有影响我的热情,因为这并不是出于我想当音乐家的奢望,而是我的一种兴趣。
1952年秋季开学,广州市的几个附中合并成为华南师范学院附中,文理附中从凤凰岗搬到广州市中心的中山四路,师资水平、教学设备、人文环境、生活设施都大大改善了。那时候学习苏联凯洛夫的教学法,老师上的每一节课都非常认真准备。用的教材,除语文外,都是从苏联课本翻译过来的。数学、物理、化学的书末附了练习题的答案。考核采用5分制,5分最高,2分为不合格。我们做练习,常常不是满足于答案正确,而是寻找得到答案的多种方法,偶然还居然能证明答案有误。有一点令现在的学生难以想象的是:我们考试不用监考。考试时你想出去走走,休息一下或者去厕所,向老师报告一声就可以。我在附中几年,从未听说有作弊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好作弊的,因为考的东西在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一次物理考试,我只得了70多分。物理老师何尚杰拿我的试卷贴堂,一方面是因为这成绩差不多是班里最高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解题的方法有独到之处。
1953年儿童节前,我给《广州日报》寄去了一篇描写初中生学习生活的3000字的短篇小说,在5月29日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这是我在报刊上发表小说类东西的开始。
还有令我高兴的是,我在这段时间得到了极好的艺术熏陶。1952年底,苏联派出顶尖级的艺术家来华表演。在广州的演出地点是中山纪念堂.离中山纪念堂不远的华师附中于是承担了一项政治任务:每场演出都要派人把空出的座位填满。那时喜好此道的人不多,所以几乎每有演出,我都要去完成这“任务”。对我来说,这任务就是艺术享受,前无先例,后无来者,那真是世界水平啊!苏军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的合唱艺术,乌兰诺娃带领的芭蕾仙女,俄罗斯民歌唱法的女声重唱,大型交响乐队演奏的肖斯塔科维奇的《庆典序曲》、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恰恰图梁的《假面舞会》……我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爱好就是在欣赏这几场表演的过程中养成的。
我们几个同学对交响音乐着了迷,但是哪有钱买设备和唱片啊?后来我们发现,“国际书店”是我们欣赏音乐的好地方。广州“国际书店”即现在外文书店的前身,在北京路,离中山四路不远,主要出售苏联的图书和唱片。有人要买唱片,店里的人就让他试听,我们课余经常去,就站在旁边跟着“试听”。后来我们同一位身材高挑、样貌标致的女店员相熟,她也会给我们一些方便。这样听了一年多,苏联出的交响乐曲唱片也差不多听完了。尽管还不能说是真正的欣赏,但我们这些穷学生也十分知足了。我们一边听,一边练习记谱;看电影时也带根小铅笔头去记下电影音乐的乐谱。这时,我再回想起过去看的作曲学、和声学、曲式学、对位法之类的书,就理解得多一点了。
初中二年级,我的学年成绩科科都是5分,见证了我初中阶段的一个黄金时节。
这些当时只是作为课外的爱好,想不到日后也都派上了用场,助我发表了不少东西。我大学毕业之后结交了一些华南歌舞团的演员朋友。一次,她们要上京演出,希望能预先写好一些文章,以便演出的第二天就能在报纸上发表,对节目作出评介。一位朋友找到我,我在排练房看了她们的排练,帮她们写了几篇东西,后来果然在《大公报》、《光明日报》等发表了。1954年大演革命戏,大唱革命歌,作曲家常为毛主席的诗词谱曲。我通常是在《光明日报》今天读到作曲家为毛主席的某诗词谱了曲,隔天就可以把推介这首曲子的文章写好,寄到《羊城晚报》副刊“晚会”发表。大约是1956年,中国实验歌剧院来广州演出大型歌剧《草原之歌》和《刘胡兰》。我看完他们的演出后写了一篇评论发表在作协广东分会(现广东省作协)的文学刊物《作品》上。
1957年我们高中毕业。我们几个一直对音乐有兴趣的同学,特别是从文理附中一起走过来的同学商量,在毕业晚会上演出器乐小合奏《托儿所的早晨》和《玩具波尔卡》。《托儿所的早晨》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台常播放的一首器乐曲。高中时,宿舍播音室早上播的起床曲就是这个曲子,伴随我们的生活多年了。我们分头记谱,秘密排练;乐器是我们当时条件下所能有的牧童笛、口琴、箫、三角铃、儿童手鼓,还加上了口哨、人声。演出受到极大的欢迎,也许是因为那旋律太熟悉了,唤起了同学们对这几年学校生活的回忆。我们一边演奏,同学们在下面一边唱和,气氛十分热烈。我们用手鼓突出了《玩具波尔卡》中的波尔卡舞曲的强烈节奏,既有点诙谐,又有点专业。
高中毕业后我考入华南师范学院外语系,攻读英语专业。入学时,我人在外语系,名却于中文系,因为我在上海的《文艺月报》(《收获》的前身)发表了一篇评艾青诗的文章。现在来看,文章写得并不成功,拘泥于某种意识形态,但它反映了我在中学学习期间的积累。
4.热身
大学学习和毕业工作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我学做研究的热身阶段。
那时华南师院在广州石牌,属广州东郊。学校的校舍是低矮的平房,礼堂是一个大草棚,学校旁边只有三两间老百姓开的茅寮小吃店。外语系全部电化教学设备就是一部磁带录音机、一部手摇唱机另加一套“灵格风”唱片。就是在这样简陋的设备条件下,外语系给我们提供了尽可能好的教学条件:英语一年级二十六个学生,分两个班,每班配备了一位主讲的教授和一位助教。我们只有一、二年级,一部分学生来自港澳和东南亚国家,英语起点已比较高,但基础不够扎实。老师狠狠地抓我们的基本功训练。
二年级的任课老师刘桂灼教授曾留学美国,是一位十分严格细致的学者。他在我们用词和造句上的许多细微之处指瑕,弄得我们既害怕又佩服,为我们打下了非常难得的扎实基础。三年级的老师吴英树教授曾留学英美,原来不是读文学的,却特别喜欢英国的散文。他认为英国十八、十九世纪的散文用词严谨、句式多变但常又表现出一个特点:单词、短语、分句排列为三项式排比,读起来很有韵味。他是我们几位同学的导师,指导我们将英国历史学家、散文家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名著《英国史》(TheHistoryofEnglandfromtheAccessionofJamesⅡ)当文学作品来读。他讲解起来十分投入,特别是讲到原文的三项式排比句时,一边朗读(常常几乎是背诵),一边拍着桌子“砰—砰—砰”,真是激情澎湃。我记得有这么一句: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during the last hundred and sixty years is eminently the history of physical, of moral, and of intellectual improvement...
当他“背诵”到the history of...,of...,and of...,我们也跟着拍着桌子读起来,大家陶醉在英语散文的三项式排比意境里。这时的学习,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思考,帮助我在二十年后构建了一篇论文《英语三项式排比结构分析》(《外国语》,1984,2)。
我在一、二年级课余时间翻译了苏联出版的英文版《苏联文学》上的一些儿童小说,在《羊城晚报》副刊“花地”发表。后来增加了一些未发表的,结集寄给了一个出版社以求出版,而出版社都已来函我系党总支了解译者的政治面貌,但因中苏关系出现了变化,这事就被搁置了。跟我同年进入华南师院的同学章以武,考上了中文系。我们分别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因而有些交往,两人曾商量结集出个小说集,后因我的东西太单薄而作罢。八十年代,章以武因电影《雅马哈鱼档》编剧而蜚声大江南北,后当选广东作协副主席和广州作协主席。作为广东作协会员,我以有同学当上副主席而感到高兴。
四年的大学时间其实很短。一年级上学期先是开展“反右”运动,接着二、三年级开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到农村去插秧收割水稻、去工厂劳动、去修铁路、下乡办公社等等。还有一个学期差不多全部时间我们都在乡下参加“四清”运动,专业学习的时间不多,我们对时间特别珍惜。
1961年大学毕业,我留外语系任教。由于大学期间政治运动和劳动占去的时间较多,1962-63年,学校让我们这批年轻的助教“填平补齐”,就是把在大学期间该学而未学的东西,通过自学和请老教师指导来补充完善。我在这段时间读了一些书,除一批英美的文学作品和英美文学史的著述外,还读了Otto Jesperson的AModernEnglishGrammaronHistoricalPrinciples和PhilosophyofGrammar;Daniel Jones的AnOutlineofEnglishPhonetics和ThePronunciationofEnglish等描写语言学的一些经典著作,学识略有长进。1965年,我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第2期发表了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评〈英美文学欣赏〉(第一集)》。现在看来,这篇文章的观点还是有点幼稚,但同样也反映了我在英美文学方面的一些知识积累。不久,“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开始,所有的学习都停下来了。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进入到复课闹革命的阶段。七十年代中、后期,国家给许多高校布置了翻译联合国文件的任务,华南师院也同样成立了联合国文件翻译小组,叫我任组长。小组的成员许多是留学归来的教授,尽管不一定原来是学英语的,但英、汉语水平都很高。小组成立之初,翻译工作难度很大,原因是我们都不懂联合国的运作,对世界各国也不太了解。翻译的时候闹了很多笑话,就是交上去的译稿及已经出版的定稿,也有一些误译。至于专有名词、术语的翻译,不标准之处就更多了。
为了完成任务,我急需提高自己。
这时,文化大革命不再是以急风暴雨式的运动方式进行,教师可以开展一些业务性的学习和工作。大学阶段的英语教学走的基本上是“文学路线”,学生学的基本上都是英美文学作品,做的研究是文学作品的解读,所以我在1965年写的第一篇较长的论文就是文学评论。那时文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形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评价常以某种立场、某种意识形态来划界,工人作家的作品、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作品受到吹捧,但很难提升为一种文学理论。所以,我就把研究兴趣的重点放在正在进行的翻译工作上面。
当时我对翻译的认识也很简单:翻译就是中外文字兑换,原文是不能解读错的,换成的汉语表达要清楚可读,有时还有点文采——这就完成了翻译的任务。组织这一工作的中央领导部门对译文的要求也就是“准确、通顺”。我们大体就是以这种认识来完成联合国文件翻译的任务的。幸亏联合国文件的文体风格比较单一,用上述标准对待文件的翻译也还应付得过去。因此,那时我对翻译的研究也只是总结一些移译的文字技巧,如《汉语外位成分在翻译中的运用》(《现代外语》1978.1)、《歧义与翻译》(《外国语教学》1980.1)、《也谈句法与翻译》(《现代外语》1981.1)。对翻译的研究在联合国文件翻译告一段落之后还在继续。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开始走上一条复兴的道路。1977年,广州外语学院的桂诗春教授前往美国访问归来,给我们带回了美国语言学研究的信息,包括那时已经有了二十年历史的“乔姆斯基革命”。我读大学的时候,中文系开设“语言学概论”课程,内容主要来自苏联学者编的普通语言学教科书的章节,没有涉及当代语言学的内容,而且我没有选修这门课,所以对桂老师提到的信息非常陌生,感到既新鲜,又很吸引。我在我们系的资料室寻找,意外找到了文革前我们系定购的美国的一些语言学资料,甚至有乔姆斯基SyntacticStructures那本著作。我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初读一点都不懂,因为一直没有接触过语言学的东西。硬着头皮读下去,一遍、两遍地反复读,开始半懂不懂,慢慢知道了一点皮毛。我觉得语言学理论比文学分析实在,与我们的经验也更贴近。毕竟我有几年学英语语法的体会、长期运用自己母语的感受、还有教学生学英语语法的经验,所以这些语言学理论表面的一些东西还是能读进去一点的,尤其是那些同表面的语言经验比较接近的内容。经过一番研读和思考,写了《卓姆斯基的转化语法》(《华南师院学报》1978.1)、《转化语法在外语教学中的运用》(《华南师院学报》1978.2)两篇文章,算是我涉猎语言学之始。当时听桂老师介绍的时候只有Chomsky的发音,我把他的名字翻译为“卓姆斯基”。这两篇论文可能属于我国文革后介绍乔姆斯基理论最早的几篇,虽然还很初级。以后我还撰写了《深层结构与英语教学》(《外语学刊》1981.1)一文。这样,我在进行翻译研究的同时,开始了语言学的学习、思考。在学习转换生成语言学后还写了《汉语主位化初探》(《华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4)、《空范畴初探》(《外语教学与研究》1984.4)、《语言的生成性》(《华南师范学院学报》1984.4)等文。
后来翻阅我国文革前出版的语言学资料,我发现大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国已有人简单介绍过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一书的部分内容。不过那时凡是介绍西方的理论,必然要戴一顶“批判”的帽子。现在看起来,这种批判一方面不伦不类,另一方面又影响介绍的全面深入。一些有理论深度和新意的东西往往欲言又止,谈不到要领;或者为某些认识偏见所左右,介绍得变了形。不管怎么样,“乔姆斯基革命”可能是文革之后最早吸引我国语言学界注意的国外语言学研究动态。
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流派、各学科的语言学理论的引进越来越活跃,我接触到的语言学理论流派也越来越多。系资料室购进了韩礼德(M·A·K·Halliday)的著作ExplorationsintheFunctionsofLanguage和LanguageasSocialSemiotic:TheSocialInterpretationofLanguageandMeaning等书。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很贴近人们运用语言、进行社会交际的心理和惯例,比较容易理解和运用,读起来很有意思。我读了韩礼德的著作,并参考了苏联篇章语言学关于超句统一体的论述和德国语言学家、阿姆斯特丹大学语言学系主任Simon Dik教授的功能语言学的理论,结合自己教学和翻译的体会,写了《主位和述位》(《外语教学与研究》,1982.2),开始了我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进行的语言研究。我研究语言学起步晚,但我的认识是,早晚只是比较而言;只要起步了,就比还没有起步早。
5.积累
我的语言学知识根基浅、基础薄弱,所以此后从1982年到1992年这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定位在积累。十年的积累确实成为我日后研究的重要基础。
1984-1986年期间,我有机会到澳大利亚访学,读了悉尼大学图书馆里重要的跟语言学相关的著作,其中有三套多卷本的系列丛书,一套是当时已出版十三、四卷的“语用和语义”(书名已记不清楚,以下两套同)研究系列。几乎所有同语法、语义、语用研究有关的重要文章都收录了进去。例如,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我就是在这套丛书里读到的。另外两套叫“New Horizon”和“New Trends”之类。我记得里面许多文章是关于计算语言学、数理语言学、形式语义学、语言逻辑、语言统计、语言运作模式的建立的,它们成为我认识上的“新的地平线”。例如,我以前已经自学了一般的统计学,而在这里还读到了“语言统计学”,通过词汇的统计来研究文体。这些书,在当时的国内,至少在我所在的学校里一时还读不到。我做了许多的笔记,开拓了日后研究的多方面的视角。
我还切切实实地研读了索绪尔(F.Saussure)的《语言学教程》的英译本和我国出版的高名凯的中文译本、美国的几位语言学家分别写的《语言论》(Language)、美国和欧洲语言学家的功能语言学著作、三四十年代布拉格学派的重要著作、美国描写语言学的重要著述,及其他语言学论文。
我在悉尼还有机会较早读到R.Quirk等1985年编撰的AComprehensiveGrammaroftheEnglishLanguage这本大部头的语法书,并且读到了名家们对它的评论。考虑到国内可能得到国外图书资源之不易,我还作了很详细的笔记。
悉尼大学图书馆顶楼有一个小小的“东亚图书馆”,里面放的主要是中文的图书。1949年之前出版印行的汉语(中文)语法(文法)和修辞著作在这里找比在国内找方便多了。《马氏文通》以及陈承泽、吴瀛、杨树达、金兆梓、陈望道、方光焘等人的汉语语法著作,我都是在那里读到的;还有后来的吕叔湘、王力、赵元任等的著作。那里还有台湾出版的用汉语写的语言学著作,包括研究古汉语的、现代汉语的、甚至还有研究英语的。1949年以来,我们对台湾语言学研究一直了解不多,我在这里增加了对台湾语言学研究的了解。台湾的同行接触美国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机会比我们早,他们的研究有很多长处,对我有很好的启发。
有时我也去听课、参加研讨会,吸收韩礼德最新的研究成果。
除了上述语言学内容的学习以外,在我转入理论语言学学习和研究之前对文学作品所进行的思考以及所从事的翻译研究,也对我的积累很有帮助。例如,文学作品的结构和语言特点同作品的主题思想的辩证关系的分析,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翻译中译文遣词造句的各种考虑,其实也跟语言的运用有关。甚至作曲学、曲式学所谈的模式,都有可能为语言的运用提供有意义的范式。真是“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
这十年的积累涉及的语言学理论和语言学科比较多,我写的东西内容也比较杂,包括生成语言学、各流派功能语言学、语法、语义、语用、语篇、语言研究方法等,发表论文约五十篇。其中有一篇叫《认知框架在中国英语教学的应用》,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英文刊物《中英语文教学》(1983.2)。回想起来,那时好像有语言教学的认知研究,但还没有“认知语言学”这个名称。
6.给力
1993年之后的语言学思考,多是围绕语用推理的展开而进行的研究。这里触发的动因,是因为我注意到语用学有一种理论值得重视,这就是关于“常规关系”(stereotypical relation)的理论。“常规关系”这个概念既联系着传统的语用学语用推理研究,又同认知研究和现代逻辑推理研究相通。我对语用推理的研究,断断续续持续了十多年,并且生发出一些有意义的研究。
1987年,列文森(S.Levinson)在JournalofPragmatics发表Pragmatics and the Grammar of Anaphora一文,认为即使在“约束条件”(binding conditions)下,语用推理也可能要参照常规关系,这就使转换生成语言学所说的“约束条件”的“先天性”受到挑战。列文森根据Grice的合作原则的量准则,提出了新格氏的语用推理三原则,其中的“信息原则”(the Principle of Informativeness)提到,要以符合常规关系作为话语理解的一项指标。1991年,列文森在JournalofPragmatics发表Pragmatic Reduction of the Binding Conditions Revisited,再次提到对“约束条件”的“先天性”的挑战,再次论证了话语理解对常规关系必须的依赖,并且把他所提出的“三原则”称为“新格氏语用推理机制”,常规关系就是新格氏机制里的一个重要概念。我的许多研究就是围绕新格氏机制和常规关系展开的,这构成了我在1993-1995年研究论文的主旋律(详见我在此期间发表的论文)。
1995年,我从广州的华南师范大学(学院)调到河南开封的河南大学工作。两年后,河大外语学院获批博士点。
通过这一段时间的研究,我认识到:含意是话语的本体的一部分,而语言的运用包括运用话语的含意性和运用含意思维。我写了《含意本体论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3)以及《话语的含意性》(《外语研究》,1996.3)、《话语含意化过程》(《外国语》1970.1)、《论含意思维》(《外语学刊》,1997.2)、《含意的两种形态》(《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1)等文章,将含意看成是话语本体的一部分,同目前我正在进行的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中把话语信息作三分的看法相一致(《感受质和感受意》,载《现代外语》,2010.4)。
默认知识、默认思维是近十多年来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研究的重大发现,并且已经发展出默认推理、合情推理、常规关系推理等重要推理模式。在语用学的语用推理中引入常规关系,与在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中进行常规关系推理研究的思路一脉相承。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将常规关系研究同认知研究联系起来,写了《常规关系与认知化——再论常规关系》(《外国语》,2002.1)一文,从而进入到认知语用学的研究。我在研究中试图建立起语用推理的常规关系的心理模型,著文《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外国语》,2007.3)。并将常规关系同句法、话语(包括文学话语)、修辞等研究联系起来,努力建立一些使用比较简便而又稳定的生成和理解的机制,并运用这样的机制进行研究,写了一些“为什么可能”系列。
在其中的“隐喻为什么可能”的研究中,我系统地讨论了同比喻中的本体和喻体有关的概念的内涵、外延之间的关系,用内涵、外延的传承来说明隐喻发生的机制,这就是“内涵外延传承说”(《外延内涵传承说——隐喻机理新论》,载《外国语》,2009.3)。
在比喻的研究中我发现,有一些喻体是“以偏概全”的。如转喻以竹子指代“箫”就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竹子都能做箫的原材料。有些成语、诗词、话语也有这样的情况。这引发了我对指类句的研究(《指类句研究的认知——语用意蕴》,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2)。
近一年来,我开展了一项新的研究: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语言研究的心智哲学视角——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之五》,载《河南大学学报》,2011,期未定)。
心智哲学是21世纪的第一哲学。心智哲学研究的是身心关系,是形而上的研究。但在讨论物理事件与心理事件的关系时,揭示的是一些人们心理活动的重要规律,如属性二元论、心理随附性、心理感受的涌现性(emergent property)等,并且可能体现为某些具体的心理活动。有些是在所谓“民间心理学”(folk psychology)中有过很多的讨论,或者体现为我们通常所说的格式塔转换。这些都可能作为语言研究的理论资源。另外,研究揭示,语言表达,基本上是表达人类的感知和感受。这方面的研究,同语言的认知研究是有可能相似的。
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是个新课题,我和我的团队才刚刚开始研究,必须假以时日才有可能深入下去。现在的研究才只是一个大致的框架,许多细节还需要费力加以补充,例如可参照认知科学表征和计算理论。设想如下几个计算和表征的的步骤:
(1) 在语言运用中,感觉和知觉的过程是从什么开始的?
(2) 在这过程中哪些主要的变量在语言表达中起作用?
(3) 这些变量如何组合成为计算模型?
(4) 计算过程和结果是如何在大脑表征的?
(5) 大脑的表征又是如何被语言表征的?
这里的每一个步骤,甚至包括其他一些步骤,都需要深入的研究加以充实。
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是我七十岁以后开始的一项新研究。我深知,这样的新研究或者其他什么新的理论,同已经在国外发展了几十年的语言学理论相比较,在有些人眼里,是完全没有竞争力的。我只希望上天能假我以年,让我和我的团队一起尽量多做一下深入细致的分析、推论、证明、甚至证伪,看看心智哲学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对语言研究有参考价值。我已年老体衰,唯寄希望于年轻人。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语言研究的趋势是:越来越重视人的因素在语言中的作用,具体来说是人的大脑功能和认知状态对于语言的形成和运用的影响;越来越关注心智与语言关系的解说,以说明意义是如何建基于更具生物学意义的心脑关系之上的。参照心智哲学研究进行语言研究,就是看能不能在这方面对语言的认知研究有所推进。
7.献疑
当前困扰我国语言学研究的最大难题可能是创新问题。创新可以分解为要不要创新、怎样叫创新、创新如何做等几个子问题。核心问题是要不要创新。
语言研究作为人文学科的重要内容,首先兴起于近现代欧洲。索绪尔、叶斯柏逊、高本汉这些欧洲人的名字,将永远彪炳在语言学研究的史册里。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为了记录濒危的印第安语言的资料,系统地发展出美国本土的描写语言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欧洲的人文科学家移居美国,为美国的语言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如果说,这时的研究主要还是就语言研究语言,发展出研究语言本身的一套严格的程序,那么二次大战之后,随着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研究的开展和深入,语言研究成为认知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当然,敏锐的语言学家也想到,认知也能够揭示语言的很多秘密,语言的认知研究揭开了语言研究的新篇章,这就是认知语言学。上世纪五十年代以降,美国已为建立在世界贡献了两个有世界影响的语言学理论,这就是第一、第二代认知科学基础上的两个语言学理论,前者为转换生成语言学,后者为认知语言学。这些语言学思想,为美国人赢得了世界声誉。
有一种说法认为:一流国家产生思想,二流国家产生品牌,三流国家产出成品,四流国家加工成品。我们不妨衡量一下,就语言学研究而言,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处于几流?
奥裔美籍经济学家熊皮特(Joseph Schumpeter)说,任何创新都是分工的结果,都是具体的人基于自身利益和成本而进行异化的创新。这里有几个关键词:分工,异化,自身利益,成本。
语言学研究要创新,就要在研究中有分工,有“异化”。大家一窝蜂地赶潮流,都往“主流”堆里扎,都是用某种理论零散地研究汉语、解释汉语的某个现象,而不去思考这里面可能体现什么语言学的思想或心智现象,这就很难形成自己的语言学理论体系。古语有云,“善弈者谋全局之胜,不善弈者谋数子之得”,而“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在赶潮流中,用汉语把原来用英语写的东西转写就能出一篇论文,或者综述、译介以及简单的应用,就已能获得重要刊物的重视和高被引,那么又何必花精力去思考新的理论问题呢!因为那是可能要付出被认为是非“主流”而被革除的代价的。
因此创新问题关键是提高对要不要创新的认识。
相比于经济的发展、大型活动的成功举办,外界可能更为关注一个社会发展的模式,比如这个社会的模式能不能有利于创造力的发展、有利于科学家形成思想和创新理论、有利于人的有所作为,为人们研究的可持续发展铺路。为此,我认为,现在要从学生抓起,抓硕士生,特别是博士生,让他们一开始踏入研究之门,就要有创新意识,就知道研究不是坐享其成,不要谋求走捷径、走现成的路,不是想尽千方百计挤进“主流”,而是要为创新而甘于受冷落、坐冷板凳,会被人看不上,要进“地狱”,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要用成功举办奥运、世博、亚运,成功地研制出两弹一星的经验来激励自己,用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临终前的叮咛鞭策自己:“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归根到底,就是要为发展我国的语言学研究献出一分力,使我国的语言学研究水平同我国的国力发展相匹配,使我们能够同世界的同行平等对话交流。
我们的硕士生、博士生并不缺乏聪明才智,问题是我们不要光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引导到套用一两个说法来发一两篇小文章的小打小闹中去,而要把他们的聪明才智集中到思考大问题、全局问题的大智慧上来。启发人们创新的是自由思想和一种鼓励兼收并蓄的全局性的学术眼光和学术器量,而不是知识。光是学会了、学透了某一门派的理论也还是激发不出多少创新的思想的。因此,要在语言学界,尤其是青年学者中,提倡一种多元并存、多元竞争、多元发展的学术氛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尊重。目前,禁锢学生的学术思想的,很可能是老师们有意无意地流露出的话语,因为这些话误导学生以为语言研究中不存在其他可能性、不知道还有其它路子可走,以为老师介绍的就是金科玉律,就是解决问题的津梁。
因此,我对自己的博士生有八个字的要求:平等、无畏、快乐、创新。平等无畏是为了鼓励创新,快快乐乐地创新。我要求他们注意进行如下的学习模式的转换:
1.引进吸收之后要转换为对观点的研究;
2.理论知识的接受之后要转换为研究思路的训练;
3.知识的高积累之后要转换为创新思维的培养。
作为语言学研究者,吸收、接受、积累都是需要的,对观点的研究、对研究思路的训练、对创新思维的培养,也是需要的,后者似乎更为重要。只有不断学习借鉴,才能够保持开放的心态,获得别样的视角。也只有常怀全局之念、创新之心,别样视角才能转化为创新的大智慧。这样,在平等的条件下,有了无畏的精神,不成熟的创新遇到批评也能转化为促进思考、改进所得、获取进步的契机。
有人认为,我们的语言学研究对外影响太小,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东西翻译出去。这种想法很可能来自我们中国人自己思维的认识。现在信息交流那么多、那么快,有好思路、好理论,人家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有些青年作家,国内褒贬不一,人家了解得一清二楚。几十年前,苏联的巴甫洛夫、维果茨基、巴赫金,不是在西方都有很多知音吗?我们有些论文,我们自己都不看,翻译出去就能扩大影响?还有些论文,在国内影响很大,给后学以很大的启发,但究其所以,其源有自。多翻译一些出去当然非常好,但关键还在于有自己的创新。我期待着我国语言学研究的复兴。
8.结语:薪火相传
语言学研究的复兴是薪火相传的事业。我自己很幸运,在我起步的时候,得到一些甚至还不曾有幸谋面的先生的指导、扶持、提携。这里要特别提到北外《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许国璋先生的提携和上外《外国语》编辑部朱纯、刘犁先生的扶持。那时我工作在地处南方一隅的华南师院,外界对它少有了解。记得应是在1983年的寒假,朱、刘两先生不避严寒,专程南下,看望在广州的王宗炎先生和桂诗春先生,顺道也屈尊来到我家,对我说了很多鼓励的话。1987年初,我突然接获许国璋先生电报,询问他们寄回来要我修改的《论语句的“中心”》文稿的下落,等着要在1987年第一期发表。但是不幸,邮递员当了洪乔,我没有收到。后来,在许老和编辑部的关怀下,文章终于能在第二期发表。还有一件事就是华南工学院外语系(今华南理工大学外语学院)郭杰克教授无私的的关心。1987年夏,我申请正高,郭老师担任广东省高校外语学科专业职称评定小组组长。当时有熟人找他缓颊,但他既不偏袒我,也不轻信别人,而是把情况在组里作了说明,正常按学术成果数量和质量把申请正高的人排队,使我得以全票通过。由此,我深切感受到语言学界的前辈对后学的关怀和提携,体现了他们切望我国语言学研究复兴得以薪火相传的热心。

图2 徐盛桓教授在指导学生
在前辈示范作用的感召下,现在我也竭尽所能给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以帮助。有一些谋面、未谋面的青年充当了我的“编外”博士生、博士后。他们中有的人说不知如何感谢我,我说:不用感谢我,你就用同样的精神去帮助需要你帮助的人;同时,加入我的团队的研究,也就是帮助了我。
通过这样一代一代的薪火相传的努力,我国的语言学研究一定能够复兴。此乃余心之所善,虽九死其犹未悔。当此年方七三之龄,期望老当益壮,不移白首之心;暮年益坚,仍系青云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