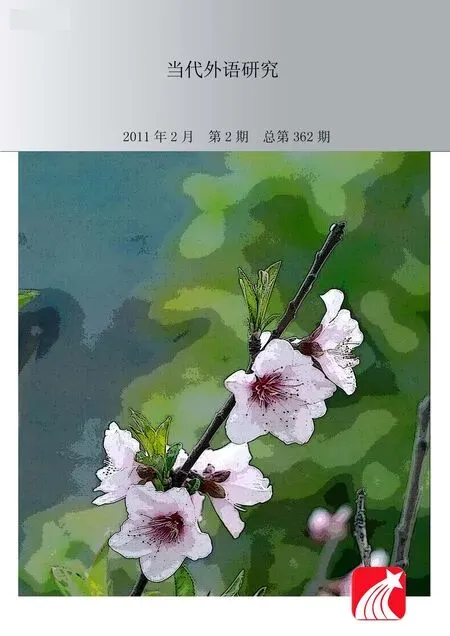治学就是自学
——回顾和思考
桂诗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510420)
《当代外语研究》索稿于我,请我写篇关于个人治学的文章。我觉得这个题目不大好写,生怕写得不好,会贻害别人,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道路不同,打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别人很难复制。现在恐怕只能“姑妄言之,姑妄信之”,希望读者持批判的眼光对待,不要依样画葫芦。
每个人都是他时代的产儿。如今读报,常看有所谓90后、80后的人怎样怎样,而我是30年后的人,和他们相差大半个世纪,横跨了两个不同的时代。对我自己来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明·袁了凡语)。不对自己的过去作一点回顾,很难说清我是为什么和怎样走上这么一条自学道路;而做一番思考和梳理,我愿将夕阳作朝阳,让阳光撒在共同奋进的大路上。
1.我的家庭
我于1930年出生于广州东山区。呱呱坠地没有多久,日本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不久建立伪满洲国,并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内战基本结束。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华全民族抗战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在抗日志士奋战于黑山白水之间和中国政局瞬息万变之际,我开始了我的童年。
我的父亲是陕西官费留日生。他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于20年代初携日本夫人花子回国,在广州广东大学(即现中山大学前身)医学院任外科教授。他和文艺界的郭沫若、郁达夫及成仿吾都是老同学、好朋友;和郭沫若更有过一段相同的经历:一起上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升入和毕业于九州帝大医学部、都娶了一个日本夫人;两人在广东大学也曾短期共事;两位日本夫人(花子和安娜)更是情同手足。大概是在1927年间,父亲携花子夫人回日探亲,谁知花子感染斑疹伤寒,病死于途中。父亲后来娶了我的母亲,才生了我们四兄弟。

父亲是个很勤奋的学生,在中学阶段,各门功课优异,才能考取官费留学。可是他对我们的教育却不大过问,母亲也没有受过很多教育。所以在家庭教育方面,我们既非“书香门第”,更无“家学渊源”。
我的中小学教育是残缺不全和支离破碎的:大概七、八岁前还算接受过一点正规教育。1937年后,为了躲避逐步蔓延到南方的战火,我们举家迁往香港;父亲则在粤港之间来回上下班,后来则随着中大内迁云南,就更少回家。我在香港的中小学阶段,前后变换了五、六间学校,没有拿过一张小学和初中的毕业证书,其间还因为日寇占领香港,我们只能停学在家。也曾延请过两、三位家庭教师,但时间不长,且教学均不系统。
2.我的启蒙教育
我们这一代人既不像上一辈人那样接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也不像后一辈人那样在正规学校完成了普通教育。在日寇侵华战争的狼烟战火中我随家人颠沛流离,时断时续地接受了初级教育;初中阶段是在日寇占领(三年零八个月)下的香港(包括元朗)度过的;1945年日寇投降后,我按自然的年龄段进入高中,先后在九龙华仁书院、拔萃书院、香港华仁书院读书。其间因为得肺病停学一年,最后才磕磕绊绊地取得香港会考的毕业证书。这是我中小学阶段唯一的证书。在这段时间里,我从来都不是“规矩的”好学生。
在香港沦陷初期,家父和另一位姓崔的留日归国医生在香港联合开了一家诊所,两家住所就在诊所的楼上。崔医生与妹妹崔载瓦同住。崔氏兄妹的父亲为澳门望族,受过传统教育,而且爱好书画金石。崔载瓦从小跟他学习,写得一手好书法。她成为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首先要我练书法,又教我读《说文解字》。她自己其实也没有受过严格训练,只是按部首一个一个字来教,对其中的注解也没有什么讨论和解释。她还要我背唐诗三百首,但方法有点奇怪,连题目和作者也一起背,如“临洞庭上张丞相[孟浩然]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从此以后,我就对书法(连同篆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练王(羲之)赵(文敏)的书体,而且乐此不疲地看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经常到旧书摊上去淘宝,看有些什么极品,居然给我买到了《淳化阁帖》的复印本,还淘到了一本被康有为列作“神品”之一的明拓本《石门铭》和明代最后一位宰相王道周(石斋)的扇面真迹。我曾经许愿到退休之后再来专注书法和篆刻,未曾想退休后还有那么多吸引我的眼球的东西,只好把从第一个老师那里培育起来的个人爱好搁置一旁。
我的第二个启蒙老师是一位在香港机场工作过的文员。这位老师大概在香港的书院读过英语,受过一些传统教育。他每周两次到我家来教我们几兄弟。我算上初中,弟弟们就算上小学。他每次上课既教中文,也教英语。汉语强调背书,英语则强调弄清情节。中文课本是《古文观止》,但只是选读其中一些名篇,以散文、骈体文为主。英语课本是Lamb的TalesfromShakespeare。但其教学方法比较单一,只是逐句解释,不作太多的延伸。
我的第三个启蒙老师是一位中学英语老师,他是我们举家迁往元朗后的邻居。课本是我自己提供的。那时我在旧书摊里找到一本名为China的书,是一本给外国人看的介绍中国的书,谈的是民国初期的中国,有些插图里的中国人还拖着长辫子。这位老师比较强调语法,也让我写些作文给他改。
因为时间短暂,这两位启蒙老师的姓我都已记不起来了。但我真正的老师其实是自己,因为在这段时期,我们都躲在家里,不大敢外出。小孩子没有什么去处,就只好读书,而且饥不择食,什么书都看,但因为缺乏指导,看书有点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小学时期我就开始读四大名著,最爱看《封神》、《水浒》,感到《三国》文字过于古雅,而《红楼》又太婆婆妈妈。对《七侠五义》、《施公案》、《隋唐演义》这类演义小说也十分爱好,有时早上醒来,就赖在床上看书,直到中午吃饭才起床。英文书也看,主要是简写本,当时香港坊间有很多Michael West为印度读者而编的《新法读本》(TheNewMethodReader)辅助读物,都是英美小说名著的简写本,像TheTreasureIsland,OliverTwist,JaneEyre,ChristmasCarol,TheVicarofWakefield和Ivanhoe等等,只要能找到的,都以一读为快。
3.我的书院生活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在战争中停办的学校逐一恢复招生。家父觉得要呆在香港,非学好英语不可,就要我们报考英文书院。我有点忐忑不安,因为之前从未听过真正英美人讲的英语,对于究竟能否在书院读下去,我心存疑虑。我们住处附近有一所拔萃女校,报名招考的那一天,我跑去看热闹,听到那里的老师正在用英语向考生宣布一些注意事项,我居然都听懂了,于是信心大增。因为那是女子学校,所以我就改报了也在附近的一所男校——九龙华仁书院。几个弟弟也一起去了这所学校。
香港的书院有公办的、私办的、私办公助的和教会办的几种。所谓“名校”多是公办和教会办的。教会办的又分为天主教和基督教办的两大类。当时的华仁书院有两处,分别设在香港区和九龙区,大本营在香港薄扶林道的半山区,都隶属爱尔兰天主教教会。华仁书院的教师大都是爱尔兰神父,不过九龙华仁的校长是中国人,叫林海瀾,为人刚烈,对学生很严格,我们背后称他为“林老虎”(Tiger Lin)。他自己不上课,但碰上有老师请假,不管什么课他都能顶上。我记得有一次语文老师请假,他就代课,教我们念一首英诗“Some Halluciations”(可能是Lewis Carroll为儿童而写的那一首);还有一次是代数学老师的课,教四则运算,他自己带了一把大尺子上课,示范怎样做演算,要求每一道题都必须用尺子来划线,绝不能马虎。
在华仁读书时,我曾经转到拔萃书院去读了一个学期,但因为该校在一座小山上,离家较远,又转回华仁。为了复学,我曾当面去找过校长。他最初有点犹豫,后来看了我的成绩单也就收读了,并且说了一番话,大致意思是办学的宗旨在于育人,把学生教好,只要有空缺,他都会接纳;有些学校专门去挑一些好学生来教。好学生何必要你去教?把不好的学生教好,才是教育呢!对照这位老校长的崇高理念,我真不知道现在那些千方百计地争抢好学生的学校有何感想?
应该说,我的正规教育是从战后的香港书院开始的。当时书院的培养目标是文员,即政府和工商业机构里的底层办事员。如果学生有前途,就让他升第二班(即大学预科),然后考为数不多的大学或师范学院。大学毕业后,就从管事做起,一直留在政府部门供职。不管从那一级做起,只要老老实实,就可以保住铁饭碗。每年的工资会增加一点。
我的同学大都走的是这条道路:有的毕业后直接当了文员,有的则考取大学,毕业后再去当高一级的文员。我在香港华仁读完第三班,成绩平平,就有一个神父问我要不要到某政府部门去做文员。当时文员的工资是210块港币,勉强可以生活。但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走这条道路。
4.我的读书生活
当时香港学校(包括书院)基本上没有一个像样的图书馆,教师好像也不甚鼓励学生多看书,我看这便是人说“香港是个文化沙漠”的缘由。我从小喜欢看书,没有书看,就只好到旧书摊去淘,可以说是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包括麻衣柳庄、占卜问卦、武术防身、散文、武侠小说、文艺小说、诗词歌赋等等,无所不看,当时可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所谓语言学这样的东西。有时无书可看,就去读《辞海》条目。后来懂得一点英文,也看一些掐去半页的原版杂志(有些过期杂志出版商不愿回收,只收半页封面,卖书小贩则会将封面剩下半页的杂志降价卖出),如Reader’sDigest,Coronet和一些关于刑侦破案的杂志。战后一些给美国大兵看的书籍(叫做GI Edition)也流到市面上来,价格非常低廉。其中也不乏佳作,如Whitman的LeavesofGrass,Fast的CitizenTomPaine等。在旧书摊里,我专门找那些平装纸面书(paperbacks),它们价钱便宜,且携带方便。我最喜欢侦探小说,Conan Doyle,Agatha Christie,Ellery Queen的作品是我的首选。应该说我最初的读书生活漫无目的、而且“不求甚解”,实不足为训。
当时我爱上了集邮,通过笔友会结交了很多笔友,用通讯方式来交换邮票。我喜欢收集英属殖民地的邮票,因为上面有很多风景秀丽、颜色鲜艳的图案。有一次在笔友会里找到一个在Rhode Island的笔友,以为又是一个英属殖民地,就主动与之联系。结果收到一个大包裹,里面有一封信,还有很多美国邮票和一些读物、地图。写信的是位老太太,她告诉我Rhode Island是一个美国小州,不是英国的殖民地,要我看看地图和其他读物。当时我的笔友有几十人之多,遍及全球。在通信中除了交换邮票外,往往介绍一些当地的风俗人情。通过交友,我既增长了地理知识,也提高了写作能力。因为要在薄薄的一张信笺里写更多的东西,我便养成这样的习惯:直接把信笺放在我那破旧的打字机上来写信。这样做的坏处是打下来就不能改了;好处是培养了思维能力,用什么样的句子讲什么话,都事先想好,然后打下来。我觉得好处比坏处大。
读书还诱发了我的写作欲。我曾模仿冰心、郭沫若的自传体的散文和小说来写我的童年;因为看了《青城十九侠》、《蜀山剑侠传》而去写武侠小说,但因为没有生活,写了几回就辍笔了。战后香港的中文报纸慢慢多了起来,家里订了一份《新生晚报》,该报的副刊每天都登一篇《怪论》,我用“你唔知”(广州话“你不知道”)的笔名写了一篇对香港殖民地生活不满的文章,居然给采用了。从此我开始给该报投一些源自国外杂志(如Coronet)里的奇闻杂趣,因为篇幅不大,适宜于当“报屁股”,也多半为编辑所采用。后来居然还把我编写的一篇关于宋美龄在美国生活的较长的文章作为副刊头条连载。其实我在这个时候所发表的东西都是半写半译,均非独立创作。这大概是在1946~47年间,用的是笔名“明磊”。
1947年以后,我参加了一个由香港进步团体新民主出版社举办的读书会,只需交一笔钱,他们就把新出版的一些进步书刊寄到家里来。我又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在我面前展开一个新世界的读物,这包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等等,也开始订阅进步报刊《大公报》、《文汇报》、《周末报》。在文艺书籍方面,鲁迅的杂文也取代了巴金的小说和冰心的散文,成为我的至爱。总之,我开始“赤化”了。我首先自我反省,开始批判自己在《新生晚报》写的那些“帮闲”文章,然后学习写鲁迅风格的杂文,还订阅前苏联的《苏联文学》(SovietLiterature)和美国共产党主办的《群众与主流》(MassesandMainstream),并开始改用“史村”的笔名向《文汇报》、《大公报》投稿,多半为杂文,居然也有些被录用。
书院的课程枯燥无味,我觉得在书院的局促生活里自己的思想像一朵鲜花难以绽放。当我感到书院难以容身时,便开始逃学,自己跑到一些公共图书馆去看书。这个时候我已经立下志向,要当文学家或翻译家。《苏联文学》那时发表了青年作家冈察诺夫写的小说《金色的布拉格》(TheGoldenPrague),写的是二战中苏联反击纳粹的故事,气势磅礴,十分感人。我于是着手把整本小说翻译出来,谁知刚一脱稿,诗人袁水柏的译本就已经上市发行了。我等于做了一次练习,算是完成了我当“翻译家”的梦。这包译稿我保存至今,因为那是我踏入新征途留下的印迹。
这个时候我去了一所为进步人士办的夜校——中业学院学习,学院的董事长是郭沫若,校长是成庆生。该校遵循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将他的话“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印在学生的结业证书上。课程按文学、经济等专业分类,每晚上两节课。我报了文学专业,上课的老师有楼栖(文艺理论)、司马文森(中国现代文学史)、黄秋耘(小说)、黄宁婴(诗歌)等,都是当时华南著名的文艺界人士。我参加的不是第一期,据说在第一期里,郭沫若和茅盾都去讲过课。学校就在我家附近,于是我白天到书院学习,晚上就到中业进修,那里有很多追求进步的同学。当时我们几个爱好文艺创作的青年还办了一个“春泥社”,大家自掏腰包合办了一本叫做《春泥》的同仁小杂志,我还走访过楼栖和黄秋耘,约他们为杂志写稿。楼栖应约写了一篇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杂志上还登了我从前苏联出版的《高尔基选集》里找到的一篇散文,名为《同志》。这个小杂志没有什么知名度,读者不多,我们几个人又都是穷光蛋,难以为继,出了一期就夭折了。
当时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已胜利结束,随后南京和上海解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广州也解放在望。香港进步青年都渴望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谁都无心呆在书院里过那种晨钟暮鼓的生活。我这个一心要当文学家的青年,渴望立即扑向新生活,可是却没有什么可以引领我的人脉关系。后来听从一个临时在新华社落脚的青年的劝告,我于1950年回到刚解放的广州,参加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当时我对考试并没有什么信心,因为实在没有经过多少正规的中学教育,而且香港的书院在理科方面的教学远不如内地中学。例如在当时香港中学会考中只有数学和初级数学两门课可供选考,而内地已教到高等数学。我在香港会考中选考的是初级数学,因此在内地高考的数学科交了白卷。
由于对内地大学的情况一无所知,我随意报考了两所学校:北大和武大。考北大是因为它在首都,考武大是因为招生广告宣传珞珈山非常漂亮。我也想报考青岛大学和杭州大学,但它们的考试和武大的在同一时间段。我在报考的两个学校都榜上有名,北大在广州只录取两人,我是其中之一。武大没有按地区排名录取生,后来我到武大报到,才知道自己是外语系录取的第二名。同学们告诉我,可以去教务处查分数,结果查出我数学0分,化学7分,最后得分主要靠英语和语文、历史。我舍北大而奔武大,并没有太多原因,主要是武大的体检通过,而北大要求我再作一次x光检查,我则因为痔漏开刀,已经请了两周的假,怕耽误时间。
5.火红的大学生活
我平生第一次只身外出,来到武汉珞珈山,马上就被解放后那火红火热的生活所吸引,积极投身于各种政治活动。
武大当时的秘书长(实际上是党代表)就是后来被鲁迅批判过的徐懋庸,他给我们上《社会发展史》,从早上一直讲到晚上(中间休息两次吃饭),我们在大礼堂坐着小板凳听得津津有味。后来又开展资产阶级思想改造运动,我被任命为校刊《新武大》的副主任委员,当跑腿,管点具体事务,包括校对、去排字房看老师傅改字粒和拼版、分发报纸、和把徐懋庸的发言(或社论)校样送给徐家秘书,等等。偶尔也写点报道或小评论。当时的运动席卷全校,很多老教授都卷入其中,《新武大》也出得越来越频繁,有时甚至隔天一期。课堂教学则处于半开半停的状态,英语课程的内容很浅,老师袁昌英教授倒是十分开明,要我不用来上课,爱到高年级去听哪门课就听哪门。我听了一下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又恢复了自学。因为文艺创作搞不成,我决定转而自学文艺批评,于是捧着一本前苏联出版的俄罗斯文艺理论家杜勃罗留波夫的选集到图书馆去看,同班同学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我在武大两年多,其中有一年因为查出有肺病而被迫停学卧床休养。当时没有什么治疗条件,而武大一位身染肺病的副校长是靠卧床休息、加强营养而治好的。他就采取行政措施,让所有染有肺病的学生休学一年,就地卧床休养,免费吃营养餐(三荤一素,另每天加一个鸡蛋)。所以我在武大的两年多,不是搞运动就是修养,学习上无大的进展。后因为院系调整,武大外语系和中南区的几所高等院校的外语系一起合并到广州中山大学外语系。到中大一年多,虽然小运动不断,但读书学习的环境大大改善,在戴镏龄、骆传芳、蔡文显、王多恩、谢文通、骆夏露德等教授的教导下,我完成了高年级的课程,在大四两个学期,全部课程都得了5分。这是因为中大所开的各门课程都和我的志愿比较吻合,上述教授又都有真才实学,而且教学认真负责。
在这一段时间,我和另一个同学经常被省外办借调到广州去做英语翻译,少则几天,多则一月有余。我记得尼赫鲁第一次访华时,有一个印度报业集团的记者代表团为他打前站。他们先来到广州,参观了几天,我负责全程陪同,最后一起坐火车到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到首都,免不了要到各个仰慕已久的景点参观,从故宫、颐和园到鲁迅故居,然后才坐火车回穗。因为回校后等着我的是谢文通教授的莎士比亚课的考试,考试内容是《威尼斯商人》,考试题目是拿出其中的几段话要我们诠译成现代英语,这可是实打实的,而我拉了几次课,不能靠胡诌几句就能敷衍过去,于是在归途的短短两天中我就在火车上突击看莎剧。回校后参加考试,居然在以严厉著称的谢老师手中得了个5分。在我所得的众多5分中,这确实是我最弥足珍贵的一个。
解放前和解放初期,我国外语系的办学方向大都是“走文学道路”,我就是这条道路的产物;所以我毕业后留校当助教,正是延续这条道路的最佳注解。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我读书生活的延续。
6.自学路上的种种求索
毕业前填写志愿时,我本首选新华社,因为我梦想能够利用自己的语言(包括汉语和英语)知识和能力当驻外记者,写些新闻和专题报道。走向教师岗位我不无遗憾,但再一细想,在高校任教可以很大程度上满足我的读书欲,可以跑图书馆,“座拥书城,听雨打芭蕉,”不也是我追求的生活境界吗?
我当助教不久,中大就把我作为特殊培养对象,多发了一张特殊的入库借书证给我,准我进入图书馆的珍藏书库。这样我就有了两张借书证,一共可借40本书。在中大15年,我起初从事基础课的教学,教过精读、泛读和写作,后来才教文学,包括外国文学和英国文学史、英美文学选读和文艺理论等课程。好几门课程都是我没有学过的新课。平心而论,对所教的东西,我本谈不上有什么深刻的研究;能够开出这些课,多半是靠自己的努力和自学。记得叶启方教授为中大中文系开设外国文学课程,他要我协助他改写讲稿的头一部分希腊罗马文学。这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领域,所以只能从原著的英译本入手,读Homer的两大史诗,读希腊Aristophanes的喜剧、Aeschylus,Sophocles和Euripides的悲剧,还读Dante的《神曲》,最终写出了几万字的讲稿。1970年以后,中大外语系合并到广州外国语学院,我又转向搞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也都是自己开书单,一本本读下来,然后开课、写讲稿,走的还是自学为主的故道。我在别的地方已谈过自己为什么转向,限于篇幅,在此集中谈谈我是怎样依靠自学而实现这一转向的。这些个人的局部认识和体验不一定适合每个做学问的人。
6.1 专注不可少
专注就是对自己所选择的目标培养浓厚的兴趣,充分认识“路漫漫其修远兮”,坚持“上下而求索”。专注的精神就是“发烧友”的精神。我见过种种发烧友,音乐的、画画的、集邮的、电脑的,他们目标不一,但精神却一样:为了达到所设定的目标可以不问个人的利益得失、不计较所花的金钱和时间、不在乎上下班和休假与否。当然这种“精神”只是相对而言,不是在任何时间里都那样做,而是该睡觉时睡觉,该吃饭时吃饭;只不过有时也会“废寝忘餐”。这也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钉子”精神,包含“青山不改”(执着),“绿水长流”(永恒)的意思。其实这种精神源于奋斗目标的高尚与否。有人在发财梦的支持下不断敛财,也是专注,但那是卑下的,丝毫比不上“宁肯一人臭,换来万户香”的掏粪工人时传祥那样高尚。
在了解到应用语言学学科对我国外语教育的重大意义后,我发愿要把这个学科引进中国,并让它在中国的国土上生根发芽。这样的目标很有意义,可以为我的专注“给力”。我不像后来者那么幸福,可以到国外去攻读硕士、博士,或是师从于某位专家学者,取得重要业绩。我国曾在向苏联派出留学生后,向英美派出第一批留学生,我毕业后被中大外语系推荐为留学候选人,资格评选方式是由系主任戴镏龄老师命题,要我写一篇讨论Robert Tressell的TheRaggedTrousseredPhilanthropists的文章。这部小说很长,有几百页之多,写得有点拖沓,幸亏我早已看过,所以交了一份自己感到满意的答案。谁知当时的教育部执行极左的阶级路线,政治审查下来,说我有海外关系,不能出国。这对我来说,与其说是打击,不如说是激励,更坚定了我走自学之路。
直到1973年我才第一次有机会作为中国教师代表团的团员访英,那时我已迈入不惑之年,而且出访时间只有3周,我带回来一堆英国各学校应用语言学专业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就凭这些资料,我们在当时的广州外国语学院筹建起一个应用语言学专业。最初我只能开设一门非常笼统的课,浅浅涉及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等方面的内容,说不上有什么分量。后来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分化,开出应用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课程,并陆续写了几本关于应用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教科书。全靠自学和专注精神,我才能逐步掌握这门学科。
我第二次(1988)访英是受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到Lancaster,Edinburgh,Reading几所大学访问。每到一所大学,我首先钻到图书馆里,有目的地寻找关于语言学方法论的书籍,发现这方面的书并不很多。回国后,我觉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让语言学在我国扎根,必须讲究其研究方法,于是我又专注于普及方法论,最终和宁春岩教授一起完成了《语言学方法论》一书。
从1978年我在《光明日报》的“教育·科学”副刊上发表的“要积极开展外语教学研究”开始一直到2011年我将要在《外国语》上发表的“应用语言学家的责任和良心”,前后30多年,我在不少场合上都不厌其烦地提到,要把应用语言学(外语教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要了解科学、尊重科学,按科学的规律而不是按长官意志、个人的局部体验或商业化所编造的神奇广告来办事。
6.2 以革新为道
我常爱引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话“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来作为我的座右铭,意思是要自强不息,走革故鼎新的道路。革新是人类认知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是因为我们处在信息数量和流量不断增加的信息革命时代,人类知识的老化率也随之增加。从放射性元素、血浆、药物到科学文献都有半衰期(即有一半成分老化)。在工业经济时代,一个人在4年大学里所学到的知识可以受用终生,只有很少一部分会过时和老化。知识经济时代则不然,数据分析显示高级工程师的知识半衰期为3年,工程师的知识半衰期为5年,一般技术人员的知识半衰期也只有7年。以平均知识半衰期6年计算,一个大学生毕业时,其4年所学知识可能有30%已经老化。根据Burton和Kebler的老化方程式计算,科学文献的半衰期为5年,如果一个人大学毕业后5年的知识不更新,他就有一半的知识老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类知识的半衰期更是大为缩短,有人认为,一个互联网资源的半衰期只有6个月。更有人估计,人一生中用到的知识,只有20%是来自学校,其余80%来自其它渠道,所以必须通过各种办法(包括自学和再进修)来更新。这是“以日新为道”的主要理据,也就是庄子所叹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和《四书-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含意。朱熹则有更形象的说法,“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活水”就是不断吸收新知识。
这是就人类的整体认知而言的。从个人认知角度看,新与旧的关系却是相对的。自己所不知的东西都是新的东西,而自己所已知的东西,却不一定都是新的。因为未知的东西层出不绝,所以“革新”也带有“更新”的味道,我们决不能满足于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正如韩愈所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我们只能活到老,学到老,自强不息。从历史的角度看,越是变革的年代,学科之间的联系越密切,文艺复兴时代出现了Da Vinci那样的百科全书式人物,我们现在所处的信息(后信息)时代也呼唤着跨学科的联系,一个学科的发展往往会催化别的学科发生变革。比如牛津哲学家Austin对语言行为的研究就触发了语用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发展;而语言基因FOX2P的发现对了解物种起源、人类进化、语言的产生、语言缺陷治疗、语言教学也会发生重大影响。对猿猴学话的观察和研究会对我们研究人类交际系统(特别是利他性行为和合作性原则)提供许多启发。描述新世纪各学科的相互作用时,不妨引用一句常用的成语,那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至于怎样才能走革新的道路,倒是需要多说几句的。(1)革新源于历史发展,新和旧其实是一种继承的关系,要通过扬弃旧的来发展新的;革新不是漫无目标地标新立异,找一些“噱头”。(2)革新需要实践、观察和深入思考,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在的研究生培养非常强调创新精神,有的研究生也很想在研究中提出一些新意,但是他们往往抄袭别人的思想,换一个名目或说法,其实只是换了一顶“新”帽子,就说自己有创新了;还有的研究更是只根据一点点局部实验和观察,就着意于提出一个全局性的新模型,甚至说什么多模态(multi-modal)模型。我认为创新不是拍脑袋的遐思,也不是没有真实内容的“皇帝的新衣”,更不是没有经过历史检验的痴人说梦。(3)要有敏锐的能力。新鲜事物处在萌芽状态时是不容易发现的,所谓“风起于青苹之末”,大思潮往往萌发于不易察觉之处。但是新鲜事物是否真的永远“新鲜”?还仅是昙花一现?这需要审慎的判断能力,是认知科学和管理科学中所谓不确定情况下判断的问题。
革新应该深入研究者的骨髓,成为指导研究者终身实践的一盏指路明灯,这便是“以不息为体”的真谛。人类的认知是不会有顶峰的,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我们要达到的也许不在于哪个高峰,而在于“攀登”本身。
6.3 广博与专攻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韩愈),做学问可以有先(师)后(生),但是专攻则无先后之分,能者为师;所以“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但这些话未触及广博与专攻的关系。
广博就是“杂学”。由于种种原因,我从小就养成了爱看杂书的习惯,回粤升学后,我买了一本解放后刚出版的《翻译通报》合订本,看到里面有好几篇翻译界老前辈写的关于“杂学”与翻译的关系的文章,深有同感。我曾做过业余口译,也翻译过一些作品,痛感知识面的宽窄与翻译水平的高下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杂学”这门复杂的学问,尽量多看专业以外的“闲书”。此处不妨举一两个例子说明“杂学”的作用。
1956年,我被借调到北京当北京杂技团的英语翻译,到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等国访问演出九个月。在印尼时我陪同团长去参观一个当地的土特产展览会,团长被一种手工艺品所吸引,就停下来问它的原料是什么。印尼的主人说了一个我听不懂的印尼语,我无法找出它的英语对应词,只能按发音来说。结果团长反问,这是不是海南岛的什么什么?我既没有去过海南,更不知道那什么什么是否就是印尼的什么什么,当场就卡壳了。
文革后,商务印书馆约请广外的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William Manchester的《1932-1972年美国实录》(即《光荣与梦想》),我负责翻译第18章《分裂之家》。刚好这一章谈的50年代朝鲜战争时美国的生活场景,那时电视剧刚露头角,所以书内谈了不少电视广告和当时生活时尚的东西。我们在翻译此书时已事隔数十年,对抗美援朝间的美国人的生活一无所知,不少时尚的东西又往往昙花一现。这一章原作者提供的注释只有4条。经过请教翻译大家王宗炎先生后,我弄懂了不少文中内容,增加了注释57条。但是有一处始终没法弄懂,就是“Outside Detroit the market offered those who had everything solid gold toothpicks,whiskey-flavored toothpaste,and His and Her submarines”这句中的submarines是什么东西?翻遍手头所有的英语词典,我都只能找到“潜艇”一个意义,那么潜艇为何还有男女专用的?而且在市场上就可以买到?我无法解开这个疑窦,只好硬着头皮把它们译成“男用和女用的潜水艇”。直到最近我才偶然从一则外国广告里发现,submarines原来是指一种紧身泳衣或潜水衣,男装和女装不一样,男的只有一条三角裤,女的则是两点装或三点装,并有图说明,而submarine更有可能原是一个商标名。我这才恍然大悟。
广博与专攻是互补的,那就是要在广博的基础上专攻,所以胡适有言:“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提高”。广博就是拓宽自己的视野,Bacon曾谈到读书对人的塑造的种种好处,“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王佐良译)。我从小就爱看杂书,倒不是为了做人,而是无书可读,有书就读,反而受益匪浅。
广博和专攻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打外围战和攻坚战的关系,两者都不可少,但是它们的战术却不同。广博要杂而不乱、粗中有细,特别在当今信息爆炸的社会里,信息管理成了核心问题,所以Negroponte在《数字化生存》里强调“少就是多”,我们需要的是像英国管家管理一大家子仆役那样有条不紊地管理信息,内外皆心中有数,强调关注关于信息的信息。我的具体做法是以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作为专攻的目标,而把那些支撑科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统计学……)作为外围,每个学科都选读一些有关的基本读物(教科书),每个学科都看几本,有的只看目录(即史树清所说的“书皮学”),有的从头到尾大致翻阅,基本做到凡谈到某学科便知晓有哪些读物可以参阅。专攻要读透其内容,挖地三尺,直至“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必要时要能够做到用汉语转述其内容。对一些学生我就要求他们用汉语写读书报告。用汉语写出来就是强迫学生把书读透,就表示经过咀嚼和消化,学生已经拥有了个人体会;这和在书本上画条横线,做个记号,甚至搬字过纸,很不一样。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验,因为习惯泛读杂书,有的书虽然看过两三遍,但很容易跳过一些关键的表达语,不得要领。只有硬着头皮一句一句地用汉语来表达,才能了解到作者为什么这样说,而不那样说,达到了“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境界。
6.4 知与行
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对知与行的关系已有过许多探讨,我无意在此作哲学遐思,只想谈些自己在自学路上的考虑。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这是针对我喜欢读杂书却会碰到以下问题而言的:一是书读得多而杂,虽然可以拓宽知识面,但在使用知识时,却又常有捉襟见肘之感,这说明人类的认知像海洋那样渊博,恰是“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读书不能漫无边际。二是文科出身的人往往着重形象思维,而忽略理性的、逻辑的思维。但从精确科学(exact science)的角度而言,语言学是文科中最接近数学的一门科学,在我转向语言学的时候,往往会被以前养成的思维方法影响,没能进行最精准的研究。
为了克服这些问题,我觉得要强调动手能力的培养,很多事情都必须亲自经历。例如我从学统计学到教统计学,再到应用统计学,完全是靠自己动手。我国的考试中心和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即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有过一次关于考试的等值(equating)问题的学术交流,该中心派了统计部当时的负责人Livingston等人前来讨论。而美国并不了解我国高考的情况,他们要求提供一些信息。可是国内只有我们广东建了一个模型和一套主观题等值的做法,我有一篇英文稿,就先发给他们。在会上他们认可这个模型,我也对这个模型做了一点补充,发言中首先声明我是讨论会中唯一的没有经过统计学训练的人(当时我国考试中心的许多年轻人都是心理统计和教育测量学专业毕业的)。会后Livingston赞许地对我说,“你虽然没有经过训练,可是你是唯一做成功的。”其实我完全是摸索出来的,连很多表达方式用汉语应该怎样说都没有弄清楚,经常担心自己会讲一些外行话。
知与行应该是相互补充、互为因果的,不必讲究其先后(如朱熹的“知先行后”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但是对我们这些文科出身的人来说,强调“知易行难”,却是有必要的。我们经常关注的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生物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等都强调研究来自实践的行动,而不集中进行思辨性的交锋(虽然它也十分重要)。我们不要做“坐在扶手椅上的语言学家”(armchair linguists),要亲自动手做实验,按现代科学研究的精神提出和验证假设。
6.5 尽信书不如无书
书读多了很容易产生拘泥书本、迷信书本的情况,应该防止。外国人写的东西多半是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归纳出来的,虽然可供参考,但往往不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所以读时不能全盘接受、一概照搬。这方面有几种不同的情况:首先,读书必须吃透原书的精神,而不能拘泥于片言只语。有很多经典的著作不是读一遍就能完全看懂的,要反复结合时代背景、历史渊源、成书意图,甚至作者的其他相关著作,才能领悟其精神。其次,对书本既要采取批判的眼光,也要“设身处地”,具备换位思想。例如荷兰人根据他们本国学习者学习英语的情况而总结出来的模型不完全适用于我国的英语学习者,因为各自的母语和英语的历史渊源不一样。有许多研究既有民族性、本土性的一面,也有国际性、普遍性的一面。必须对它们进行独立思考,吸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第三,我们有时会把外国人设计的实验(包括素材和方法)在中国学习者身上重复,但往往得不到相同的结果,例如在中国人身上做智力测验,可能因为没有很好地控制实验的内部和外部变量,使得测验结果不一样。
“尽信书”仅是做书本的奴隶、教条的信奉者。“无书”并不是无需看书,而是经过多番“寻寻觅觅”,最后才蓦然回首憬悟过来而达到的那种最高境界——顿悟。正如武侠小说所说的“手中有剑、心中无剑”,只有真正把书读透了,才能做到“心中无书”,做书本的主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谈到人生和治学的最高境界为“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正是这番心情的真实写照。我并不认为自己已达此境界,充其量算是达到了“图书管理员”水平。作为图书和读者的中介,图书管理员一直在和图书打交道,热爱、收藏、介绍和整理图书,传递着知识和文明,使人类文明的香火得以延绵。能够向读者介绍和推荐一些好书,是功德无量的事。但我总是在向读者推荐图书的同时也不忘善意地提醒他们:尽信书不如无书!要学会驾驭书本,不要被书本所驾驭!
7.我的教训
拉拉杂杂说了上面几条,无非是在自学道路上跌倒而又爬起来的一些体会。在读书方面,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成功人士”,《礼记-学记》说,“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越看书越发现自己的不足,越教书越发现我的无知,世界太广博,而个人又太渺小,我只试谈一些个人教训,与青年们共勉。
首先,我的理科基础没有打好,特别是数学没有学好,常引为终生憾事。我曾多次想自学高等数学(微积分),终因基础过于薄弱,学了半天仅得皮毛。现代实验科学需要很多统计学知识,我在自学和教授统计学过程中,碰到了统计学中多元分析的许多问题,特别是需要亲自动手的方面,没有高等数学知识就做不下去。
二是未能多学点逻辑学知识。不管是形式逻辑,还是模态逻辑,都和句法学、语义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及计算机编程技术的学习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逻辑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科学,我自问这门科学没有学好。
三是未能完全掌握一门计算机语言。未来学家Nasbitt所写的《大趋势》说过,“要想真正取得成功,你必须要懂三种语言:流利的英语、西班牙语和电脑语言。”我最初购买个人电脑时,也曾学过一点Basic语言,并试图编写一些程序,感到获益良多。因为懂得了计算机如何运作,就知道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可惜的是程序语言层出不穷,我终究未能再接再励学些更高级一点的语言,常以为憾。
四是年岁越增,越脱离教学实践,对学生在英语学习中所碰到的问题缺乏亲身体会。
我已年逾80,回首前尘,实在说不上有多大学术贡献,只能说点读书的经验和教训,确实和苏轼有同感,“昔之学者,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希望后来者多读书,不管是纸面的,还是电子的。我不相信书中有什么黄金屋和颜如玉,但觉孔老夫子所说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倒是我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