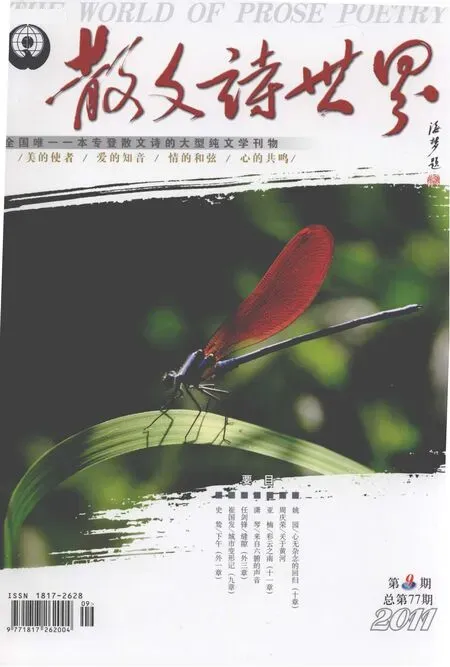中国元素
广东 陈计会
土
大地是疼痛的。面对孕育、裂变与涅槃。在盘古的利斧下纷落成块,成尘,又被女娲抟土或挥绳舞散落成人子,其中历经多少疼痛与希冀。在你回望的那瞬间,得得的马蹄将尘土扬起,淹没往昔的岁月和故事的细节:那群血色渗白的面孔,在秦王的大铲下面等待罪恶的覆盖;那些被驱逐离开国土的流亡者,他们的背影为大海的波涛所遮蔽。你被人缠在裤带,攥在手里;或被卷进地图,包裹着匕首,图穷之际,又是一场杀伐。硝烟、战车、马队、奔走的脚步……黄土的铜镜里是历史的倒影。你孕育了人群、五谷、河流、山川、宫殿、城池……转瞬又将其覆盖。西风残照,萋萋荒草蔓满时间的原野。我常常惊讶于你在烈火中端坐,涅槃成一尊如玉般的女子。在瓷质的光芒里,你细腻、莹润的肌肤,犹如贵妃出浴。一轮满月,升起山野之间。然而,又有谁参悟你内心历经炼狱般的痛楚?穿过历史的风云,骊山脚下那泥土烧制的八千无辜陶俑,被迫捍卫着专制的王权,它们又是多么渴望回归泥土的自由。岁月之外,大地倾斜。我终生在大地上奔走,滚着西西弗的石头,最终为大地所收藏。内心仍然扬溢着泥土的气息,犹如泪水和血液,它是我存在的见证。一个人仅有的秘密,被大地紧握在手中。
火
大地之上,火焰越升越高,像血液穿越我的内心,暗红、灼热。火光中,交叠涌现的是燧人氏惊喜的面孔、普罗米修斯刚毅的神色、佛佗涅槃时的安详……来自事物深处和遥远的天庭的两种思想在火焰中交融,成为一个整体,真实而虚幻,与黑暗和寒冷对峙。我看见有人持着火把从远古走来,越过波涛与壕沟,点燃大地上的灯盏;正如一种思想的流布,穿过漫漫长夜,让人看见火鸟黎明前那滴血的吟唱。然而,人们往往在拨开漆黑的灰烬,才能发现盗火者烧焦的脚印,燃到最后的内心。火是自由而热烈的,而罪恶往往来源于点火的双手。我们无法忽视这样的镜头:焚书的火焰高过秦王猩红的双眼;烈火吞噬着华丽的阿房宫和圆明园;纳粹在焚尸炉前嚣张。这一切是那样的清晰,让人看见沾满鲜血的双手,以及灵魂中的阴鸷。在火焰中,闪现更多的是脸庞:父亲被砖窑炉火染红的沟壑纵横的脸庞;普罗米修斯燃烧成图腾的脸庞;嵇康被铁炉锻红的脸庞,他的锤下是一块叛逆的钢铁,四溅的火花,让魏晋阴云低垂的晚空留存几许亮色;布鲁诺的脸庞犹如黑暗中世纪里一朵熠熠闪光的向日葵,它盛大的光芒覆盖了我今夜的眺望。盗火者的背影永远留在历史的坑道里,只有高擎的灯盏,成为黑暗时代的缺口,或证词。对于卑微的人生,我们往往以一根火柴的姿态来诠释:擦亮,并且燃烧,成为惟一的途径。
水
窗外的雨水依然敲打着大地之琴。
我禅坐成一株青葱的树,想象着清凉的水流搬运着血液和思想,从根须上升到叶脉、花朵,并且贯穿着我的一生。水统治着整个世界,包括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渗透进命运里的,不只是水、酒精、血液,还有泪珠和汗滴……水开拓着我们的视野——从低洼之水上升到寒光闪闪的冰川,从涓涓的细流奔腾到浩渺的大海——并始终引领着我们的思想飞翔:在善与恶之间,在滋养与泛滥之间。水在打开与合拢间,让人看见堤决、舟覆、人亡……在起义者眼里,一个旋涡,就轻易吞没一个朝代。汪洋大海,一滴水找不到自己的脸孔,同时也难免沦为罪恶的随从或帮凶。透过雨雾,不远处的河岸,两位先哲杳无踪影。逝者如斯,人如何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倏忽的闪电。一道穿越时空的流水:穿过我的内心,并且带走青春、花朵和梦想。那一刻,我感到被流水淘空了命运,血液将以另一种方式,推动时间的脚步。前行:在摇篮与墓地之间。
金
说它本身就是岩石的一角。我常常听见铿锵的声音从岩层深处传来。当炉火燃旺,我沉浸于历史的辉煌与暗淡之间:盘古舞着两把金光闪闪的斧头,关羽挥着青龙偃月刀,更有月黑风高时,那“嗖”的一声射向八仙桌上的飞镖……在岁月的烽火硝烟里,有人大刀阔斧,所向披靡;也有人折戟沉沙,败北而逃。所有这一切,都定格在它沉稳、坚毅的面孔上,仿如历史的铜镜。在镜中,它让人的手臂加长了,以长矛,以铁锹,甚至以箭镞,以子弹……让事物在空间增长,以铁塔,以楼宇……让道路向前延伸和拓展,以桥梁、火车、轮船、卫星……它充当人类的工具或武器,推动脚步向前,也让人类互相残杀:制造金戈铁马。制造司母戊大方鼎。制造奴隶主的钢鞭。制造广岛的蘑菇云。制造火星探测器。在远方月下,我看见挖泥的父亲,铁锹的寒光将他黝黑的膀子镀亮;五金厂尘埃纷飞的车间,金属的冷光颤荡在打工妹疲惫的脸上。其实,在铜镜中,更多的是人类思想的反光,它曾照亮这片漆黑的岩层:揭竿而起的人群攻陷巴士底狱;闪闪发亮的内燃机车拉动一个时代的步伐;联合国讲坛上熠熠闪光的麦克风发出异质的声音……它包含了太多的秘密、思想和血液,一个时代的悲歌或礼赞。人们往往在钟声敲响之际徐徐回眸。
木
当我行走在现代都市,我希望逢着一株卓然独立的大树,它以超然淡寂的神态面对喧嚣的市声,仿佛一位得道的高僧,不为滚滚红尘所动。它每一片鲜嫩的叶子都闪着神秘的光芒。然而利斧无时无处不在,自从它诞生之日起。坎坎伐檀的声音从遥远的《诗经》传来,它在后世演绎成斩草除根式的杀戮,让漫山遍野裸露无法弥合的伤口。风沙肆虐,洪水滔天。那行走于山野之间的木铎仿佛在为此招魂。透过大树旋转的年轮,我看见历史展开它内心的奥秘:扶犁而来的古人,将汗水磨滑的犁柄交到父亲粗糙的大手里;难以上青天的蜀道,诸葛亮运粮草的木牛流马川流不息,远远望去,神龙见首不见尾;包公勃然大怒,惊堂木一拍,令多少贪官污吏闻风丧胆……木,往往与金结合在一起,打造成犁、耙、耜、锹、镰刀、斧头、铁锤……甚至成为一个政党的图腾,砸向一个个腐朽的王朝。然而,这仅仅是工具,执工具的人往往会被工具所伤;或成为牵线木偶,被自佯掌握神谕的人操纵,成为一则悲剧的主角或配角,让历史发出木已成舟的浩叹。此刻我正伏在木质结实的书桌上,凝视着变幻的木纹,仿佛听见远处的林海涛声,听见树木内心的吟唱,它的屈辱和光荣会为多少人理解?当我们的斧头举起之际,谁在喊痛?树耶?人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