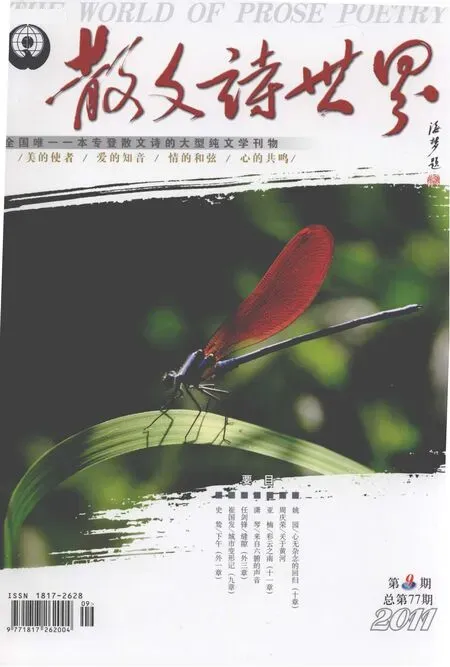城市变形记(八章)
安徽 崔国发
古城墙
让大风说出,一截城墙的裂缝。
让浮动在风沙上的残照,说出一个个朝代朴素的余晖。
时光的白垩,在古老的瘢痕里脱落。
遍地的砖堞。
它是回溯性的,一个多泥浆的名字,在源初的蛮荒里,看见天空的深邃。
幸好那些烽火台差不多都在。
记忆的褶皱,又怎样追念一个个不知名的灵魂?
疲倦而久远的护城河水。
仿佛可以渗透、融化与复归:是谁在词语的铿锵中诘问?是谁在几何学的矩形上雕刻不安之书?又是谁,循着岁月的足迹忍不住默默地流泪?
唔,那些历史的急雨,那些疾驰的闪电,那些深沉的奔雷……
那些全身散发着芳香的白鸦,在秋天的迷茫与斑驳里飞。
(报告:有人在古墙上涂写“办证”的字样)
连绵的城墙,符号的城墙,欲望的城墙,蜕变的城墙。
也许它的曲折不同于我的曲折。
已经无数次地考证:
荒凉中的寂静。内心的安宁。一些更为隐秘而难以揣摩的遗存。
词和它的影子,一直延伸出苔藓的句子,孤独与存在的诗。
那些突然从星星变为石头的真。
那些突然从污点变为神迹的善。
那些突然从沧海变为桑田的美……
酒吧间分手的情人
情人对坐于酒吧。今晚的温馨和醉,不属于他们。
两个人的烛火,于心事的默读中熄灭着,迷人的夜色。
阴影移转,美神虚无。
会流泪的红蜡烛,在光源的交织中,绽开苦涩的花蕊,一个夜晚所含的余烬,潸然落下。
他们有一样的酒浆,有一样的火盏折射出的分裂的幻象。
这时候的花,那一朵怪异的玫瑰,那一朵病态的玫瑰,好像是假的。
就好像那些用硅胶垫起的乳房是假的一样。
在与不在的蝴蝶。
变与不变的星星。
闪闪烁烁,闪闪烁烁。
纷繁的心绪,被时间的碎片,撕破了月亮空悬的面影。词语与所配置的情态之殇,在爱的不确定性里,涂上了一层凝重的颜色。
许多的事情,在心灵的黑暗之上浮现。此时守夜人的灰烬潸然落下,曾经迸发的那一缕缕激情。
月的幽凉。烛的幽凉。心的幽凉。
分手是一种明白。缘来缘去的梦幻,曾经缠绵心头的一段柔肠。
哦,今晚的月色。今晚的酒吧。今晚的温馨和醉,不属于他们。
红灯区的蚊子
那一夜,一只又一只感性的蚊子,在红灯区里徘徊。
这些一到夏天就解禁的蚊子,在美色的诱惑中,沉湎于赤裸的体香。
嗡嗡嘤嘤,嘤嘤嗡嗡。
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行踪诡秘的蚊子,陌生的蚊子,总是在人不经意的瞬间,出没于迷离恍惚的包厢,显得饥饿而贪婪。
把她放倒在沉醉里,循环往复,叮咬或吸吮,融入她鲜红的血液,她那浑圆的乳房,她那忍不住的快乐尖叫,她沉沦的肉体,她的血色之痒。
窗前的初月,挥霍灵魂的初月,倏忽迭碎了纯洁的光亮。
嗡嗡嘤嘤,嘤嘤嗡嗡。
那些在阴影与暗黑中呻吟的蚊子,它们在柔软的耳根上叫醒,那内衣敞开的、躯体润滑的、逢场作戏的女子最深的梦幻。
肉搏空虚,苟且偷生,然后彷徨于明暗之间,作影的告别。充满血腥的蚊子,心在颤抖的蚊子,在夜色里飞。
似乎只有爱的扭曲与笑的渺茫。
一只蚊子悲叹:“这血是属于你的,我来日无多,已感染上艾滋了。”
另一只蚊子,则在淡淡的血痕中答道:“我的身上本来没有病。吸的人多了,也便成了病!岂能无恙?”
嗡嗡嘤嘤,嘤嘤嗡嗡。
红灯区的蚊子,悔之已晚。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带血的死火,眩目的死火。它们只仿佛觉得,眼前有火花蓦地一闪、一闪……
成人用品店
龟缩在逼窄的裤裆巷里,让人体验出持久的浪漫与风流。
纵深曲折的小巷,如醉汉的步态一样歪歪扭扭。
店牌上的“神你油”,在风中颤巍巍地晃悠。
半遮半掩的门,羞答答的。
花花绿绿的世界。挑逗人的丰乳肥臀:壮阳药、大补丸、避孕套、自慰器、充气娃娃……飘飘欲仙的风姿,飘飘欲仙的引诱。
亭亭玉立的美女,丝绸裹不住,她曲线的丰腴。
饮鸩之渴,在波浪的起伏中,怎么也饕餮不尽,她的姿色与清秀。
湿漉漉的赤裸:冲动,狂欢,心的自足。
野性的勃兴,一如人性的坚韧与温柔么?
半遮半掩的门,羞答答的。
夜,已隐藏起爱与欲的文明。
夜的隐藏,两个人的梦,当如金瓯一样玲珑剔透。
夜的隐藏,也有见不得人的,比如“鸡”与“鸭”,在暗处的交易让你捉摸不定:桑拿、敲背、淫荡、性的轻薄,玫瑰的毒瘤。
夜的隐藏:一棵出墙的红杏,在树梢上悄悄地挂着、挂着——
那是晚风中成熟的果子,还是一身的附赘悬疣?
T型台上的妖娆
美人的细腰,是一尾水蛇吗,在时尚T台上,悠然地游动迷人的线条。
一朵朵可爱的七色花,开了。
彩妆的蝴蝶,飞来飞去。让人一见倾心的蝶儿,在华灯的映照下恣意怒放:
无穷无尽的妖娆。收腹,再收腹,双峰的突起,紧身衣的疯狂绽裂,是凸显一片圣洁的世界,还是迎合人们心底的畸爱?
争奇斗艳,百媚千娇。一次次帅气的华丽转身。
轻熟的摩登感。时装的新潮。扮酷的宽檐帽。橘红色的编织包。
温柔小资。明星搭配。雅典娜还是夏娃?俏皮,浪漫,典雅,似裸非裸,悄然张开一袭梦的霓裳,星的羽衣。晶莹的饰品,缤纷的色调,熠熠闪耀出大牌的华美。
清纯活泼的模特儿,披一头风的长发,在天使般的微笑中,充满了不羁、魅惑与风骚。飘逸的月光之妖。飘逸的气质与风度。飘逸的秀与时髦。
气场十足:狂欢的性感与眩晕的唿哨。
以真实的曲线接通了灵与肉、忧与乐,以及观众台上那一个个眼神里惊愕的符号。
仿佛向人们敞开了一本神秘的身体使用手册。
“请你用圣洁的目光,把我生命的胴体拭亮!”你说。
可有谁能够保证,台下直勾勾的凝眸里,没有三两位淫荡的开阖呢?
假奶粉
奶粉的变形记。它被充当在封闭的铝筒里,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
异质的细末。
在无限的欲望中,不知被谁的阴谋,渗入一种巨大的虚妄?
超标的三聚氰氨:你的在场,让嗷嗷待哺的孩子健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三聚氰氨,让那些丧尽天良的头颅,在心灵的天平上一下子就失去了重量。
曾经给人补钙的奶粉啊!曾经赋予人的魂骨以至坚而至诚的奶粉啊!
我仿佛听见,磨盘碾过良心的声音。
我仿佛听见,婴儿颤巍巍的,在琥珀色的杯中品咂的声音。
(一对对父母,抱着年幼的孩子坐在沙发上哭了。)
是的,没有人会相信,就是这些奶粉,这些被杂交与混合进假字的奶粉,竟然被人在暗地中贪婪地溶入,最瑟缩的一滴。
你又怎能想到,琳琅满目的大商场里,货架上摆放的竟是某些人的利欲熏心!
杯子空空的,没有奶粉,也没有孩子们饥渴的吮吸。
“妈妈!我渴!”孩子在说着梦话呢。
父母被孩子的哭声惊醒,一行行泪水在无休止地滴落、滴落……
断臂的铜姑娘
手臂断裂了,在街心花园,在某一个暗夜里,遭遇粉碎性骨折。
我看见长长的椅子上,靠着的那位铜姑娘,曾经栩栩如生的,美的维纳斯。
我更没想到,她的手臂这么快,说断就断了。
黑洞洞的夜,一群穿着黑衣裳的小偷,居然对她肌肤丰润的手臂下了手。
(是卖到废品收购站里吧?)
被锯开的伤口。流着血的伤口。被野蛮的解构。
一个不太和谐的音符,在无情的切割声里,发出沉重的叹息。
抚摸:那伤残的手臂,不曾有过的颤栗。
一个颤栗着的,裸露的手臂,在展开,青铜的残骸。
青铜是沉重的吗?就像姑娘的心,坐在那里,如一团凝固的火,消受着断裂和痛。
萧瑟的夜,姑娘的手臂不见了。
让花园里的二裂叶,在风中唏嘘时间的尾曲。
这是焦虑与欲望的对话:青铜的忧郁,青铜的荒原,青铜的烧灼,
穿越城市的梦魇,那些苍白的灵魂,在深深的暗地里,长出了星星的霉点。
都市的噪音
就像乡村夜间狗的汪汪连成片那样,城市里的一个声音总是连着一个声音,让人的耳廓,总是招架不住——
马达的轰鸣。机床的喧闹。小区拾荒者午间的吆喝。开市大吉的鞭炮。工地上的搅拌机。酒店包厢的划拳令。卡拉OK飙歌城五音不全的高吼。车站广场像蚂蚁一样旅人的话柄。街头流动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一楼那户人家用来看家护院兼作宠物的狗,半夜那一声声的吠。列车车轮的轧轧。
剪碎宁静的声音!
在风中鼓噪起口弦,一种晕眩的,呼啸的,亢奋的,旋转的,簧片的爆裂。
(人不堪其扰,而又奈之何也!)
嗥叫人的一声呐喊,在响亮的声带上,激活过我们过于敏感的听觉。
闪电和雷,在一瞬间即能扼住命运的咽喉。
然后呻吟出,城市的咏叹调,散乱的词,飘然而去,飘然而去。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彻底挣脱那噪声的绞索呢?
总是掠不过,城市的噪音——
一声又一声,不厌其烦的分贝,
在我们的头顶,炸响:快节奏的哗然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