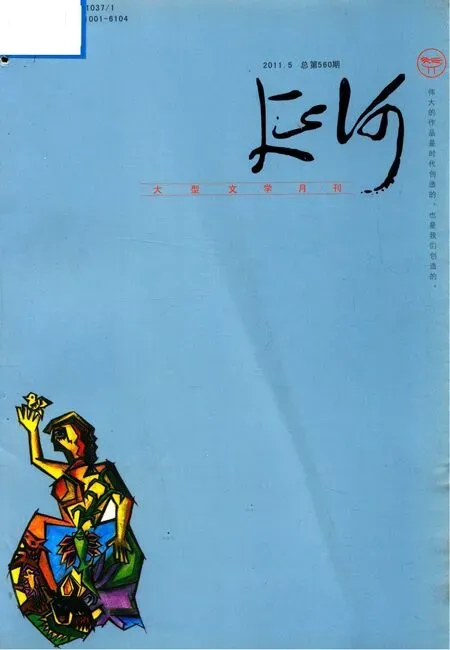在孤独中灿烂
认识孔奇很多年,感觉他腼腆,不善言辞。凭感觉,这样的人从事艺术,没有选对行当,则很难成功。譬如当歌星、影星、主持人等,都是会耍嘴皮子,眼睛会送秋波,眉毛也会搞笑的角色。假想把孔奇推到强烈的镁光灯下,塞给他一支麦克风,面对台下黑鸦鸦的一片人头,让他说一句:“朋友们,你们好,我今天给大家唱一首……”他只怕要晕过去。庆幸的是,孔奇从不想当荧屏上的宠儿。他选取了画家的职业。每日于画案上,鼓捣几盒颜料、几支画笔。那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何有于我哉”的悠闲,使他的生命在孤独中灿烂。
楚地的绘画,虽没有像岭南、吴中、新安、浙中、长安等画派那样以集团军的力量,向世人展示出美学追求以及不趋俗流的魅力,但依然在中国当今的画坛,占有一席虽不太显赫但却十分独特的地位。
何谓独特,即鄂省的绘事虽然发达,却从未形成某种为世人瞩目的流派。究其原因,乃鄂省人的性格,儒者多侠气,莽者多匪气。所谓侠者,都是排斥集体的智慧而刻意彰显个性的光芒。这种超凡绝俗的心态导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迈,也导出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信。唱一点颂歌的话,则侠的形象支撑,一在豪迈,一在自信。而侠的令人不愉快的一面,则是老子天下第一,对谁也不服气。
基于此,鄂地之文学艺术界侠气弥漫,仗剑走天下的英雄代不乏人。但这些英雄相互之间,轻者彼此陌生,重者势同水火。
如果从精神层面来谈,这些英雄恩怨实在不值得一提,它的后果是“为伊消得人憔悴”;但从艺术层面来探究,则大可赞颂。性情中人大都有独特的品质,其独特又恰恰是艺术的根本。
孔奇既然腼腆,自然就不是好战分子。事实上是一个老好人,完全没有那种“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天赋。但于绘事,他却有着藏巧于拙的异禀。
孔奇的绘画,可分为两个方面:一在人物,一在山水。真正的“左牵黄,右擎苍”,两手皆辛苦,两手都浪漫。若细究,亦可看出分别,他的人物重“显”而山水重“隐”。我们知道,唐诗总的美学底蕴是“显”,而宋词是“隐”。显者,明白如话也;隐者,曲径通幽也。所以,我们称李商隐是诗中词,辛弃疾是词中诗。说孔奇的人物画为“显”,并不是以毕加索为坐标,有人物的素描与变形之分,而是他描绘这些人物的目的性很明确,他渴慕美而欲宣泄心中的压抑。画每一位女郎,他的脑子中先已有了“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意境。而他的山水画却不一样。生长于九宫山侧的他,从小接受鄂南山水的熏陶,晨岚夕雾、春花秋月都曾是他生命中最好的营养。同样一支画笔,画人物时我们可以看见线条的刻意;画山水时见到的却是线条的率真。如果说,人物画中的女郎是他的渴慕,那么,山水画中的苍岩深壑则是他生命的本身。欣赏他的山水画,你会产生“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的那份物我两忘的优雅情怀。
孔奇的巨幅山水已为人民大会堂、中南海怀仁堂、中国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多家重要单位悬挂和收藏。可见,他的绘事已进入某种高度。虽不是洛阳纸贵,却已经名传遐迩了。
前面已经说过,孔奇是一个在孤独中求灿烂的人。相信他的灿烂会保持下去,会从簇簇芳菲进入满山杜鹃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