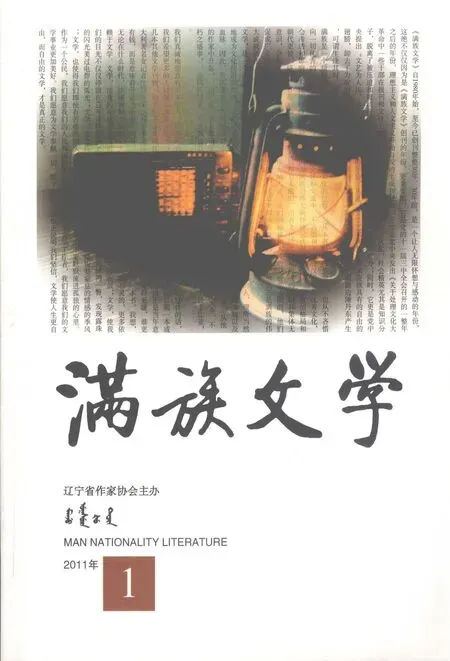时间见证的激情与成长
——评邱华栋的诗集《光之变》
李霞
时间见证的激情与成长
——评邱华栋的诗集《光之变》
李霞
在很多写作者的记忆中,诗歌常常是他们最初的经历和深刻的体验,诗神从雪地的尽头逶迤走来,将写作者的心灯点亮,他们享受着第一次被文学照耀的幸福。诗歌凝聚着文学的至高品质和感性的魅力,哪怕写作者奋斗一生,通过其它体裁的写作,攀上文学的峰顶,他还是愿意被人们称作:这是一个诗人,仿佛只有诗人的命名,才能准确估量一个真正写作者对文学朝圣般的情感。事实上,一个胸怀志向的作家往往终生怀揣一个诗人的梦想,像岁月的农夫,不事声张地在自己的田里,埋下诗歌的种子。
邱华栋十八岁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而作为邱华栋的另一面——诗人的写作经历却湮没在小说家的盛名之下。邱华栋诗歌写作最集中的1990年至1992年,整个诗坛开始渐渐转入低潮,但他对诗歌的至情与诗歌运动的潮起潮落无关,他有一种“将诗歌进行到底”的偏执。为了见证曾经的激情与成长,邱华栋以编年的形式,将他1986年至2008年期间的诗歌作品汇集在一起,以《光之变》这一时间的总题,纪念一个行吟诗人曲折而执着的行迹。
邱华栋的诗歌经历了三个阶段:史诗的欲望、轻盈意象的抒情篇章和大诗的雍容气象。
史诗的欲望: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寻根文学试图向民族的本源文化寻求突破。诗歌大潮中的寻根运动,表现出对建构东方史诗的强烈诉求。这一时期,邱华栋对史诗的“根性”的理解是返回创世神话的现场,拭去文化附着在上面的概念灰尘。在他最早的史诗《皮匠之歌》中,“后羿射日”的经典定义被解散,只留下一个朴素的故事原型,成了“皮匠”一系列行为中的一个举动,多少个“后羿”集合在一个大写的生灵的身上。这是一首抒写开天辟地的伟力的英雄史诗,它力图回到洪荒年代,以一个亦人亦神的生灵高贵的死,宣告人类婴儿的隆重诞生。这位大地上的先行者攫取江河日月的精华,承担神性的使命,用沉着的大步“丈量通往彼岸的路”,最后仆倒在火山口,“堵住岩浆之通道”,完成了生命“最后一次的搏杀”。这首诗中,诗人以民族整体人格的主观视角,在一个高大的个体形象中,融入了整个东方民族的性格和故事;营造冷峻的意象和原始粗陋的自然场景,为人物大起大落的情感变化提供舞台空间;运用大规模的数词和量词组合,渲染气吞山河的史诗气概。七十七只黑鹰、三百只青鸟、百万匹野马、千万彩蝶、八十八处岩浆、九十九条闪电、千百炷祭香、两千只紫风,形成意象句群的魔阵。对东方史诗创作的异乎寻常的热情,应和了邱华栋边疆之子的精神气质。诗人后期的史诗创作《盐》是诗人这一阶段的高潮之作。诗人在创作中既身居其外,又深入其中,他以冷眼旁观的姿态藐视、以不能自己的激情诉说屠刀的无耻和屠刀之下人类的愚盲——“你们都是盲者,看不见鹿和蛇的影子/你们惧怕清醒而浸泡于酒浆/你们活着,你们又纷纷死去/你们用白纸购买爱情,谋杀所有的星光/你们互相询问着对方的死期/一个人掌握着另一个人,形成了食物的链条/在人人饱食的过程中和流沙一起抵消,灭亡。/你们渺小而又喧嚣,像岁月深处的海浪/旋即被历史的肛门排泄/你们活着只是为了在石碑攀附/你们这些绵羊啊,多么驯服/把脖颈——这世界中最软弱部位/呈献给鹰和苍狼”,“在每一个人的眼里 你可以看见城堡/在每一个人的背上 额顶 你可以看见城堡”——我们从中看到诗人来自于自身文化的清醒与讽刺和来自于自身品性的刚正与愤怒。诗人站在东西方文化搭建的高梯上,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审视自己的国家文化。诗人后来放弃了史诗写作,但他把史诗的厚重品质保留下来,转化成新的诗歌再生资源。
轻盈意象的抒情篇章:一种新的美学元素注入到邱华栋的诗歌创作。1989年末,一首《葬礼》表达了邱华栋对早逝的年轻诗人海子的深深敬意,我们不能回避海子对包括邱华栋在内的一两代青年诗人的巨大影响,海子来自村庄的青春诗意,给当时过于凝重的诗歌取向,带来了轻盈的启示。邱华栋感受到了自身的微妙变化,青春、诗歌、死亡、爱情,被诗人敏感的心放大,在诗人营造出的孤傲之死的幻象中,他对语言恢复了雪花飘落般轻柔的质地,“没有人看见我的影子/被青草放倒在地面上”,诗人的倒下,像影子般轻柔,而且是被柔弱的青草帮扶着,这是怎样一个怀着爱意的生命的消失(《逃亡》)。爱情的光临,助长了邱华栋诗歌的轻盈气质,组诗《草莓》是邱华栋诗歌个性化的一个里程碑,一方面是果敢前行:“为了你!我开辟着新的一种精神”,一方面是柔情婉转:“亲爱的,因为你/我必须先把自己看得轻些”,在年轻诗人身上,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姿态。“献诗”在邱华栋诗歌题目中出现,通常意味着这是一种深情表达的开始。他的“献诗”的对象从故乡、父母,开始越来越密集地转向心中的情感恋人:“你从山坡上骑车俯冲下来/想象把世界撞成重伤”,多么清新、纯美的意象,世界仿佛是青春的“敌人”,青春所独有的自由、无畏、肆意、狂放,都在这与世界的一“撞”中爆发出来,在年轻人的眼里,青春的一举一动,无不联动着“世界”这一大的概念——这是青春期的非常体验,它传达出青春的豪迈与单纯。
这一时期,邱华栋的抒情篇章吸取了前段史诗的厚重,与这种厚重形成内外呼应的是,“土地”元素频繁地进入他的意象空间。而诗人对“土地”的情感认识,从最初的深深的眷恋——“想象我是一把镢头”,“深深咬住泥土”(《农事诗》),到一代人对“土地”使命承担——作为“土地”的“儿子们”,“在土地里扎根,在地面上挺拔/成为泥土和空中两面蓬勃的形象”(《感恩》),再到《大地》一诗中所展示的爱与怨的情感纠缠,情感层面日趋复杂。《大地》虽是一首短诗,但却大气、直截而包容,“大地”引起我们很多“能指”的联想——人民、母亲、民族、家园。此时,邱华栋面对的“大地”是现代化压力下的民族象征。一方面,她所承受的千年苦难过于沉重,身为一员,我们只能无语仰望,她是“一面永不落下的旗帜”,是所有炎黄子孙的精神归属,另一方面,她对“大众和天才”一视同仁的“喂养”和“掩埋”,让诗人感到一种抱负不得施展的失落。诗人处于“进退两难”的情感困境:“为什么我这么迅速地向你奔来/却永远不得靠近”?诗人渴望母体的怀抱,然而对她又感到陌生和距离,坚强的诗人终于抵御不了内心温柔的潮水——“坚硬的泪水夺眶而出”。复杂情感的进入,使邱华栋的抒情视角越来越广阔,抒情层次越来越丰富。
大诗的雍容气象:自1993年开始,邱华栋的写作精力在诗歌上只做短暂的停留,而他对诗歌不间断坚持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对语言的惊觉,以抗拒叙事写作中容易发生的语言惰性。这期间,小说的叙事品格与他对国外译诗的体会,转过来影响了他的诗歌。文体之间交叉写作的经验,使他2003年到2008年间的诗歌出现了一种雍容的气象。它的最大特质是解析对象的不同层面,从容展开多极化的联想,凭借流荡在意象与意象间的整体诗意,经验与想象间的互涉,厚重与轻盈之间交织的美感,显示出一种开阔而无限延展的大诗的体量。《航空港:大地回收她金属的儿子》以“金属”与“儿子”这一肉身与金属的形象组合,透射出一种后工业时代的反讽诗意。诗人通过对飞机起落过程的体味和观察,发现了现代人被机械的快捷与方便所遮蔽和异化的生存本质。诗人从夯实的细节处提取诗意,笔触在经验与想象之间游走,“人们整齐的排列,或坐或站/像是等待机器灌肠 流水线把他们/填充进候机室和飞机舱/使人们成为飞机的内脏”,一边是人们按照程序登机的画面,一边是食品车间流水作业的想象,美国学者斯金纳说过二十世纪两种荒诞现象:“一是机器看来愈来愈像有生命的东西;二是生命有机体越来越像机器”,透过诗中交叉的隐喻画面,我们是否意识到现代人被机械体制异化进而宰割的悲哀?诗人从具体场景入手,看似写实,实则是一步步酝酿和拓展诗意空间,蓄势待发,在不经意间展开一次形而上的飞翔。这个“金属的儿子”并不能解除生活本身的痛苦,只是把人们“送进更远的冲突,更广阔的阴影”。《哀悼死于克拉玛依大火的孩子们》单纯从题目上看,使人想到大诗人狄兰·托马斯的《哀悼死于伦敦大火的孩子们》那首诗,但邱华栋选取的只是诗人的主体视角,内容书写完全是邱华栋身处当下现实的悲愤情绪。诗人将审判的矛头锁定成人世界,成人世界教给了孩子们什么?如果前提是,成人世界注定是一片黑暗,那么死难的孩子们在“即将进入灰暗复杂的成人世界之前陨灭”,“是该庆贺,还是应该诅咒?”——这是诗人激愤的反语。诗人在对大火中成年人可耻行径问责的同时,指出了他们无处躲藏的伦理困境:“除了黑暗,我不想让他们被别的颜色包裹/除了火焰,他们收不到别的礼物/除了冬天,他们也不会拥有别的季节”,这是怎样的一种漫长的不幸?余下的时间全都是压抑,自我囚禁在这单调的人生颜色中,与死亡何异?诗人预言这种灾难的后果无人可以幸免、逃逸,它延宕到每个人身上,“仿佛是我自己的耻辱,是我自己的丧失,是我自己的死亡”。
《壶口瀑布》是邱华栋诗歌这一阶段的集大成之作,它显示了邱华栋在诗歌散文化方向上卓有成效的探索。诗的开始就是一种洪钟大吕般沉实的语调:“我曾经见过很多瀑布。那些大型的、小巧的瀑布,/人工的、季节的瀑布/它们一直在我的记忆里喧嚣。”后面是一组散文倾向更明晰的铺排,“我曾经坐船穿行过声势浩大的尼亚加拉瀑布”,“我也见识过河水的颜色像血一样的红河瀑布”,“我见识过劈头盖脸冲下来的黄果树瀑布”,接着,是冰岛瀑布、人工瀑布、家中的盆景瀑布,直到“见到壶口瀑布,黄河上最壮观的瀑布”,从前几十条有关瀑布的记忆——“白色的、红色的、黄色的、青色的”瀑布记忆全部被激活。
为什么是“壶口瀑布”而不是别的瀑布激活了诗人的记忆?这与诗人以及华夏子孙的黄河情结有关,与诗人的成长经历有关,它跟诗人的东方史诗的写作、轻盈的抒情篇章在情感取向上一脉相承。“壶口瀑布”是黄河之眼,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它容纳了“时间、永恒、河流、人民、历史、人类/这些巨大的词汇”,尽管我们处在一个精神去魅的时代,“一个铜臭的时代”,但“壶口瀑布”带给诗人的依然是一种震撼,是效仿唐代诗人陈子昂的天地感叹,诗人在哪里能躲避它巨大的声音启示?我们不能不承认,诗人在骨子里深藏着一个有担当的东方诗人的使命。
巨大的诗歌体量,像河流入海处沙粒形成的冲积平原,它是邱华栋诗歌生涯中最重要的收藏。二十多年的诗歌写作似乎都是在朝着这个方向行进,时间终于在新世纪见证了邱华栋诗歌的裂变,见证了大诗的雍容气象。
〔责任编辑 丛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