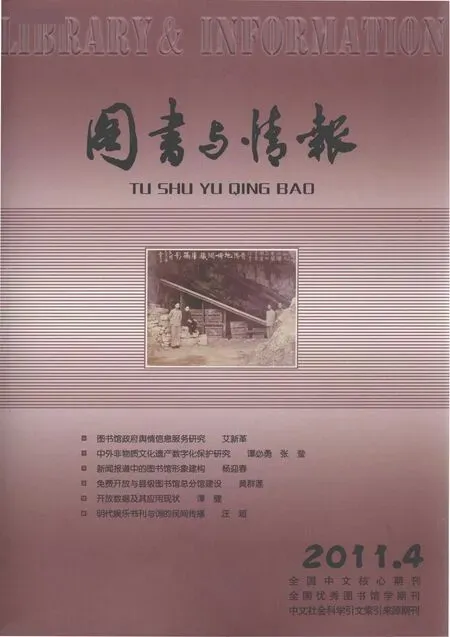藏文古籍文献的科学保护与抢救
李万梅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 甘肃兰州 730030)
我国的藏族文化历史悠久,丰富多彩,颇有民族地域特色。从历史发展的实践看,最能代表藏族文化的当属藏文古籍文献。藏文古籍卷帙浩繁,数量惊人,内容广博,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珍宝和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藏族先辈学者对藏族社会发展历史实践和历史文化的研究与记录,为我们研究古代藏学提供了第一手原始资料,其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可以想见。藏文古籍文献一般包括吐蕃时期的敦煌古藏文历史文献和历代各个历史时期的藏文碑文、铭文、档案文书、全国各地藏传佛教寺院珍藏的各种手抄版与木刻版的佛教显密经典、高僧和著名学者的传世著书、保存在藏族民间个人手中的族谱史、地方志、部落志以及数千年来在广大藏族民间口头广为流传的口传文献等等。
1 科学保护与抢救藏文古籍文献的现实意义
藏文古籍文献是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自产生以来,全面、系统的保留了藏族精神文化思想的精髓,凝聚着千百年来藏族人民的智慧,它不仅是藏族文化的宝藏,而且也是全人类共同享有的文化与精神财富。当今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电子技术、网络通讯技术和数据处理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广泛应用,图书馆文献管理与服务工作已经向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转变。在这样的网络环境下,采取高科技手段对藏文古籍文献进行科学保护与抢救,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进一步研究民族历史,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振兴民族经济,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推进民族教育事业又快又好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 藏文古籍文献的收藏情况
2.1 国内收藏情况
我国藏文古籍文献内容丰富,数量仅次于汉文古籍文献。但是藏文古籍文献收藏分散,大部分保存在佛教寺院、博物馆和各民族高校图书馆。据调查显示:西藏、青海、四川、内蒙古、新疆、辽宁、吉林七省(区)档案馆就收藏了元、明、清、民国时期的藏文档案文献300余万件;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拉卜椤寺收藏经卷达6万多部;青海省塔尔寺不仅保存了举世罕见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而且还收藏了其它类型的藏文古籍文献3341函;西藏拉萨布达拉宫收藏藏经2万多函,10万多册;中国民族图书馆藏文古籍文献8000余函;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文古籍文献达3500余函;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文古籍文献有1500多函;[1]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不仅收藏着最具版本价值和史料价值,采用金粉、朱砂、墨汁三色,历经明万历至清道光年间抄就而成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105函,3000余种,而且还收藏了其它版本的藏文古籍文献4000余种。
2.2 国外收藏情况
由于历史的原因,使我国的大量藏文古籍文献流失国外。据统计,目前,日本除藏有藏文大藏经的各种版本外,还收藏了大批敦煌藏文文献和11世纪以后的藏文典籍;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敦煌藏文古籍文献约5000卷;法国国立图书馆藏的藏文古籍文献达2500余卷;前俄国收藏藏文古籍文献1000多件;匈牙利人乔玛个人就收藏藏文古籍文献38种。[2]
从收藏情况来看,藏文古籍文献内容丰富、种类齐全而收藏分散,跨越地区广泛,这给科学保护与抢救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3 藏文古籍文献的科学保护与抢救现状
近几年来,随着科学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国家对古籍文献的科学保护与抢救给予了高度重视,颁布了许多相关政策。2005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又颁布了(国办发[2007]6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3]与此同时,国家民委根据国务院《关于抢救、搜集、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精神,成立了由西藏自治区、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北京六省(市区)藏文古籍工作协作领导小组,并先后召开八次协作会议,协商有关藏文古籍文献的科学保护与抢救事宜。与此同时,全国各有关收藏机构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藏文古籍文献的科学保护与抢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2007年8月首届“全国民族高校图书馆藏文文献(即藏文古籍)整理研讨会”在甘肃省兰州市西北民族大学召开,参会专家认为:藏文文献特别是藏文古籍文献是藏族千百年来文化积淀的结晶,是一座尚待开发的文化宝藏,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并在藏文古籍文献的联合编目、数字化加工、数据库建设等方面达成了共识。这次会议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新华网、人民网、上海图书馆网、中华佛学网、中国西藏信息网等海内外数十家新闻媒体和网站作了专题报道。另据报道,自1988年以来,国内已抢救、整理出版了600余种藏文古籍文献,内容涉及历史、宗教、语言、文学、哲学、天文历算等多种学科,版本有古籍原版、注释本,汉文译本、英译本等。[4]西藏自治区先后整理出版了《更登群培著作集》(1-3)、《西藏简明通史——松石宝串》、《德吴源流》等;青海省民委古籍办公室抢救、整理、出版藏文古籍文献20多部;甘肃省民委古籍办抢救、整理、出版藏文古籍文献25部;四川省民委古籍整理、出版藏文古籍文献105万余册;云南省民委古籍办抢救、出版《格萨尔·加岭传奇》;北京市抢救、整理出版藏文古籍文献达23种114000册。[5]
4 在藏文古籍文献科学保护与抢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如上所述,近年来,虽然有些藏学研究单位在对藏文古籍文献进行科学保护与抢救方面做了一定工作。但是,由于客观原因,还面临许多问题和困难。
4.1 藏文古籍文献收藏分散,内容残缺
藏文古籍文献大部分收藏在佛教寺院和全国各地的民族高校图书馆,部分又流失国外,还有一部分保存在民间私人手中,由于保存不当,许多古籍的内容已经残缺不全,这种现状使藏文古籍文献的科学保护与抢救遇到了许多困难。
4.2 藏文古籍文献本身的状况令人堪忧
长期以来,由于遭受了自然和人为因素的损坏,再加上存放时间久远,大部分纸质版的藏文古籍文献的字迹、颜色、纸张等已经受损严重,加大了保护与抢救的难度。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稀世珍宝藏文《大藏经·甘珠尔》(手抄本),历经沧桑,纸张已经发黄变脆,色泽暗淡,字迹模糊,经不起反复翻阅和利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档案馆收藏的藏文古籍文献中有20%的古籍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失去了原貌。其他一些寺院、民间个人收藏的藏文古籍文献同样面临这种现状。
4.3 藏文古籍文献毁坏严重
在动乱年代,藏文古籍文献同我国其他民族文献一样遭受了一次大劫难,甚至有些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版本价值极高的孤本也被付之一炬。现存的古籍也破损严重,残缺不全,已经不能形成完整的内容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档案馆从1961年开始收集藏文古籍文献,到1996年初,只收集到3000多卷,并且内容残缺不全,纸张破损;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拉卜椤寺收藏藏文典籍22万余部,后在“反封建”斗争及十年浩劫中,收藏的藏文古籍文献大量被毁,至今仅存65000余部。[6]
5 藏文古籍文献的科学保护与抢救对策
藏文古籍文献浩如烟海,博大精深,其本身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它和文物考古资源一样,是不可再生的宝贵文化财富,一旦毁坏就无法挽回。由于客观原因,目前,许多藏文古籍文献还不能得到有效的科学保护与抢救,特别是一些收藏机构的人员“生在宝山不识宝”,缺乏应有的保护意识,一些珍藏的古籍文献长久“沉睡”在书库。因此,如何全面、系统的进行科学保护与抢救,使藏文古籍文献资源转化为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资源,是值得认真思考和探讨的课题。
5.1 增强科学保护与抢救意识,建立长效机制
从目前状况来看,各收藏机构对藏文古籍文献的科学保护与抢救的意识比较淡泊,普遍认为藏文古籍文献是珍稀文献,只要拥有了就是一种实力,在科学保护与抢救方面做的不够,导致极具价值的文献资源发挥不了作用,极大地浪费了资源。因此,为了全面、系统的搞好藏文古籍文献的科学保护与抢救工作,一定要转变观念,改变重“藏”、轻“用”的思想,将忧患意识、全局意识、责任意识和现代意识融入到实际工作中,尤其是要做好以下几点。一是为了克服藏文古籍文献在保护与抢救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国家要从长远利益出发,建立全国性的协调机构,统一协调这项工作顺利开展。二是组织专家深入民间、藏传佛教寺院、民族高校图书馆等进行详实调查和摸底,掌握具体收藏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为保护与抢救提供依据。三是采取有效形式,加大宣传报道力度,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四是完善和健全行之有效的科学保护与抢救制度。众所周知,藏文古籍文献的科学保护与抢救工作程序繁杂,是一项非常庞大和专业化的系统工程,非一朝一夕之事,不仅要把好质量关和技术关,而且要将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人,并要以行政手段对其安全性和可靠性进行全程监控,全力避免出现纰漏。因此,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与之相制约的长效机制,才能为藏文古籍文献的科学保护与抢救保驾护航,提供机制保障。
5.2 采用先进的缩微复制技术,对藏文古籍文献进行科学保护与抢救
采用缩微复制技术,是科学保护与抢救藏文古籍文献的一种最先进、最富科学性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通过高科技手段对藏文古籍文献的全文进行缩微复制、电子扫描等,使藏文古籍文献的全文转换为数字化格式,读者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检索,从而保护了纸质版古籍,减少了被反复利用而造成的损坏。这种方法对珍贵的藏文古籍手抄本有非常好的保护作用,既能减少对古籍的损坏,又能吸引读者,方便广大读者使用方便,提高了对藏文古籍文献的利用率,更好地为广大读者服务。近几年来,部分文献收藏单位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取得了明显效果。如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不但创造了良好的典藏环境,而且利用缩微复制的方法,拍摄藏文古籍文献,使藏藏文古籍文献得到有效保护与抢救。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对馆藏藏文古籍文献的典藏条件也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善,目前正在对馆藏藏文古籍文献进行全文扫描,为读者提供网络化服务。但从总的情况来看,对藏文古籍文献采取的缩微复制,在技术上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规范的体系,这种做法存在很大的不完整性。应该成立一个权威性的缩微复制中心,该中心负责制定复制的具体步骤和方法,组织全国各收藏机构分工协作,避免重复工作,为日后开展联合编目和建立数据库提供可行的依据。这种方法既可以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又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共享。
5.3 建立藏文古籍文献数据库
建立具有特色的数据库是信息化时代开展网络信息服务的基础,没有可靠、稳定和方便的数据库就无法实现网络检索服务。随着现代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图书馆工作应用软件的开发,国内一些大型图书馆已经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已经建立了汉文古籍文献数据库。南京市图书馆已建立了40多万条汉文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辽宁省、浙江省图书馆也建立了富有特色的汉文古籍文献数据库。[7]另外,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互联网上能够检索到的汉文古籍文献数据库已经达到近百个,古籍数字化形式也经历了光盘、数据库、网络版等。与之相比较,藏文古籍文献数据库的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因此,为了好地为读者提供藏文古籍文献的网络检索服务,也为了更科学地保护与抢救藏文古籍文献,各有关收藏机构应从自己的馆藏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先进经验,对藏文古籍文献进行数据整合,建立藏文古籍文献数据库,合理配置数字化资源。由于语种的特殊性,在建立藏文古籍文献数据库期间,难免会遇到数据库的标准及应用、技术等难题,需要多方合作,联合攻关。首先是要注重加强基础业务建设,完善现有馆藏目录体系,摸清家底,力争编辑出更准确、更完善的书本式目录,其次通过对书本式目录的筛选,相继编制全国性的联合目录,在此基础上通过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对各种藏文古籍文献进行彩色扫描和数码拍摄,最终将其变换成JPG格式,然后保存在电子存储器上,使图、文、声、像融为一体,形成数字资源,读者可以利用计算机查阅藏文古籍文献的全文,从根本上解决“藏”与“用”的矛盾,杜绝对纸本藏文古籍文献反复利用而造成的损害。
5.4 做好藏文古籍文献的修复工作
对藏文古籍文献进行修复是对藏文古籍文献进行科学保护与抢救的重点。各收藏单位要集中力量,有计划、有目标地对馆藏破损藏文古籍文献进行修复,尤其是对一些孤本和濒危古籍作好修复工作。修复工作是一项非常细致而科学的技术性工作,对所做的工作一定要求科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并要将修复工序进行翔实登记,建立修复档案。在修复过程中,要不断改进技术,对已经破损的藏文古籍文献采用传统修裱技法和现代修复方法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修复,防止藏文古籍文献的纸张发生进一步的损坏。
5.5 加强对藏文古籍文献的科学保护与抢救力度
如前所述,藏文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具有巨大的社会和文化价值。为了使其长久地保存下去,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发挥更大作用,必须保护与抢救好作为物质形态存在的古籍载体材料。首先要改善存放环境,最大限度地降低藏文古籍文献因储藏环境所引起的纸张材料老化。其次要采取人为措施去除古籍纸张材料中不利于长期保存的因素,如通过去酸、去污等技术,使纸张材料保持稳定,防止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质。另外,要做好防火、防盗、防潮、防虫蛀工作,并对破损的藏文古籍文献要及时抢救、整理、分类、编目、定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与抢救藏文古籍文献。
5.6 加强横向联系,实现资源共享
要搞好藏文古籍文献的科学保护与抢救,必须克服各自为政,闭门自守的做法,一定要加强横向联合,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协商合作,共同保护与抢救古籍资源。首先要在充分挖掘各收藏单位馆藏藏文古籍文献的基础上,按照统一标准,先建立各自的馆藏藏文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然后再将馆藏藏文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提供给各收藏单位,编制藏文古籍文献的联合目录。其次,根据联合目录,对本馆没有的藏文古籍文献进行数字化处理,最终建立全国性的藏文古籍文献的科学保护与抢救数字化系统,真正实现藏文古籍文献的资源共享。
5.7 加大资金投入,为藏文古籍文献的科学保护与抢救创造有利条件
长期以来,经费不足是制约古籍文献的科学保护与抢救的一个问题。因此,政府要高度重视,要加大投入力度,为全面保护与抢救藏文古籍文献提供资金保障。一方面要通过法律法规来规范政府部门的财政拨款行为,保证专款专用;另一方面应该建立一种激励机制,争取社会团体、个人、企业的捐助,并对捐助者给予相应的奖励。有了足够的经费保障,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善典藏环境,还可以购置保护与抢救的先进设备。
5.8 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工作队伍
加快工作队伍培养是对藏文古籍文献进行科学保护与抢救的关键所在。藏文古籍文献的科学保护与抢救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和专业性,对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藏文古籍文献的科学保护与抢救方面的人员极为匮乏,导致大量的藏文古籍文献得不到及时、有效地科学保护与抢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收藏了4000余种珍贵藏文古籍文献,主要有木刻本和手抄本,其中木刻本占绝大部分,手抄本属于珍贵文献,有的是罕见的孤本,由于各种原因,至今仍然沉睡在“藏经阁”,在保护与抢救方面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培养一批热爱藏文古籍文献事业,具有高度责任感和事业心的职工队伍,显得越来越重要。
在培养专业队伍方面,一要加强对各级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藏文古籍文献收藏单位现有人员的培养,并发挥有关学术机构、高等学校、社会团体等的作用,互相联合,逐步建立一支专兼职结合的工作队伍。二要通过外派进修的方式,进行脱产学习,注重加强新技术、新知识、新方法的学习,开拓创新,使藏文古籍文献的科学保护与抢救工作更快、更好地得以实现。三要积极开展工作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加强藏文古籍文献的科学保护与抢救的研究,拓展藏文古籍文献的科学保护与抢救的思路和视野,逐步培养一批具有高水平的保护专家、鉴定专家、修复专家和整理专家。
总之,藏文古籍文献是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藏文古籍文献进行科学保护与抢救应该遵循“在建设中保护,在保护的同时开发利用”的基本原则,使藏文古籍文献在加快精神文明建设,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1][2]包和平,包爱梅.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的收藏与研究现状[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4,(6):9-10.
[3]刘冬青.探析科技文化创新环境下古籍文献的保护与修复[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7,(2):92-93
[4]李海秀.藏文古籍研究工作取得丰硕成果[N].光明日报.2002-10-24:(2).
[5]阿华.六省市区藏文古籍工作成果展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办[J].中国藏学,2003,(1):114-115.
[6]包和平,何丽.民族古籍保护及其策略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5,(6):22-83.
[7]马滴滴.浅谈高校图书馆的古籍管理工作[J].高校图书馆工作,2007,(5):9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