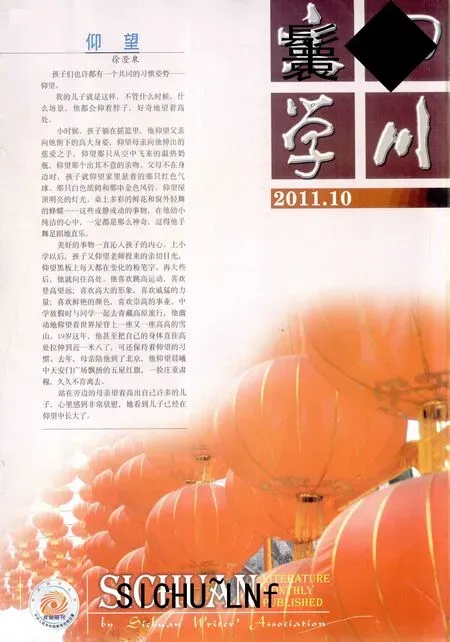真英雄出自真市场
□廖保平
最近,关于企业的新闻,我关注到两类。一类是企业虚假宣传、虚假广告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了一片。达芬奇家具明明是在国内生产,硬贴上“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标签;味千拉面的“骨汤”被爆是兑制而成;肯德基的“醇豆浆”被曝是豆浆粉冲制而成;之后,又有永和豆浆和真功夫两家知名快餐企业被曝使用豆浆粉调制豆浆。
另一类是企业倒闭现象被热切关注。有媒体报道广东东莞有两家公司突然倒闭,引发了舆论对广东中小企业新一轮的“倒闭潮”猜想;浙江温州由于信贷收紧,关于温州中小企业出现“倒闭潮”的传闻也不断。之后,一些媒体和专家认为,中小企业“倒闭潮”言过其实,但中小企业利润受到挤压,生产经营确实处于困境。
前一类新闻归结为企业诚信问题,后一类新闻归结为企业生存问题,把两者摆在一起,并不能直接得出,中小企业生存困难,所以降低成本,以次充好,以假当真,欺骗消费者。且以上弄虚作假的企业多数是知名公司,并非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中小企业。
但是,企业的诚信与企业的生存常有内在联系:企业诚信危及企业生存;企业为了生存会突破道德底线和法律红线。在残酷的市场竞争里,中小企业议价能力差,一旦融资困难,就会发生资金链断裂,生产难以为继;一旦成本上升,又无法有效转嫁出去,利润大幅减少甚至亏损,只好关门大吉。一些中小企业宁愿倒掉也不愿意使用“老千”的手段,比起前面所列的知名企业,显得悲壮而有良知。
这当然不是说,能够生存发展下来的企业就是靠赚黑心钱,也绝不是鼓励中小企业弄虚作假以求生存。一个国家的经济最终不能靠这样的企业支撑起来,也不可能走得远,诚信守法,把消费者放在第一位,才是企业的生存之道,国家之福。
中小企业动辄倒闭,当然有资金、技术、管理等诸多原因,而公权力对微观经济干预过深,也是重要原因。在法治不健全的社会,权力介入微观经济越深,越容易出现权力寻租,形成隐蔽的腐败成本,并成为企业绕不开的成本,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比如,企业要想拿到挣钱的项目、资源,很少有不请客送礼找关系的,以致在本国遵纪守法的跨国公司跑到中国来也要行贿。
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曾做过的一个课题,认为开发商利润里头有15%是支付给贪官的“腐败费”,可惜没有人能统计出企业平均支付的腐败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壮大起来的企业,敢说自己一身清白的值得敬佩,而有多少人陷在首富黄光裕式的怪圈里难以自拔——想把企业做大,就用利益输送的办法亲近权贵,获取资源,于是违规违法,留下耐人寻味的罪与罚。
倘若需要缴付“腐败费”才能获得更好的“生路”的话,企业急功近利地挣快钱几成必然,它要在权力的赎买期内尽快实现利润最大化,不然权力换手又得重新“付费”;又要将“腐败费”这个成本转嫁出去,只好压缩其他成本,降低产品质量。忽悠一个算一个,捞一把就闪人,虚假宣传、制售假冒伪劣就是这些逻辑下的行为。我们当然要把板子打在不诚信的企业身上,但更深层的原因,也需要去省视。
可是在德国,办企业的腐败成本是极低的。创办企业不需要批准,只要备案就行,也没有工商、警察、卫生、防疫等找你要这要那的钱。工商只管注册,没有其他权力;除非办案,非受邀请,警察不能随便登企业的门;卫生检疫部门必须在收到举报时,才可以去企业检查。这些部门要想企业送点好处,一来没有什么机会,二来不敢,民众和媒体都盯着呢。德国企业家只要把钱挣了,把税交了,把工人安抚好就可以了,企业办不办得好,主观因素很大。
这种自由而纯洁的环境,人们愿意去做实业。与之相反的是,中国一些地方大力提倡“全民创业”,给予种种政策优惠,可大学毕业生七成以上不是选择创业,而是去考公务员,正好与欧美等国的情形相反。这与做公务员旱涝保收,甚至来钱更快更舒服,而做企业太难、风险太大不无关系。
要给企业创造更适宜生存发展的阳光、空气、温度和水,重要的一条,就是说破了嘴的话,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不越位,不错位,做市场的公正裁判员。有真正的市场,就会有真正的市场主体,真正的市场主体会尽一切努力去经受市场的检验,成也坦然,败亦无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