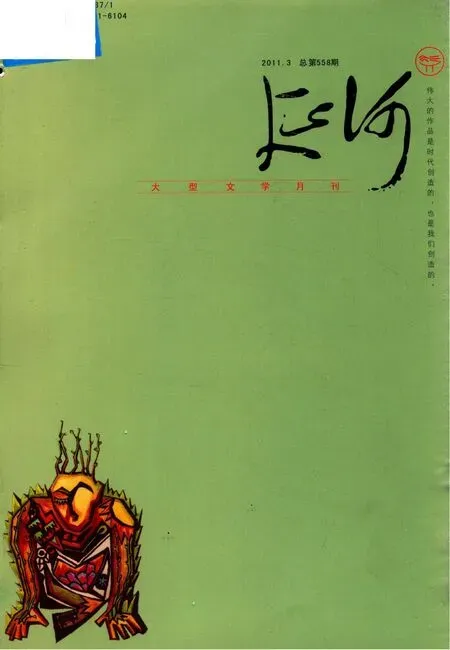中国出了个晃晃叫李更
中国出了个晃晃叫李更
一
我与李更相识已有三十余年。记得1980年春天,湖北省作家协会在我的故乡英山县桃花冲林场招待所举办一个小说笔会。参加者有鄢国培、祖慰、周冀南、王维洲、王继等人。组织这次活动的,是当时省作协驻会副主席李建纲。桃花冲处万山丛中,离县城六十余公里。县城每日有一趟班车到达一个名叫红花嘴的小镇,自此进入桃花冲还有十五公里,虽有简易公路,却无班车可通。一日午饭过后,李建纲忽然对我说:“我儿子今天从县城搭早班车来桃花冲,按理应该到了,怎么不见人影?”一干作家,只有我是当地人,于是自告奋勇沿简易公路去寻找。当时的青年作家王继陪同前往,因为只有他认识李公子。沿林场招待所下行大约五公里左右,忽见一位瘦若麻杆的少年正对着路侧一处山洞出神。王继喊了他一句,麻杆少年冲着他一笑,说:“这洞内有泉水流出,还有燕子飞。”样子稚气,却满脸兴奋如科考工作者。
这位麻杆少年就是李更。
从那以后,就算认识了李更。但来往不多。其因是他太小,还是一位高中生,但与他父亲李建纲却过从甚密。建纲是著名小说家,代表作有《三个李》、《坐火车玩儿》等,文风朴实而幽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湖北文坛,占有重要的一席。
说实话,认识李更的时候,只把他作为李建纲的儿子看待,并未意识到这麻杆少年日后会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文人。
记忆中,李更大学毕业就去了珠海,在《珠海特区报》谋了一份编辑的差事,并且一干就是二十五年。论资历是元老级的人物,论职位还是一名普通编辑。在别人看来,他这际遇似乎有点蹭蹬。但人各有命,岂可一概而论。不必美誉他“安贫若素”,也不必说他“不求闻达于诸侯”,只能说他“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作家的造诣,相比于他的小说家的父亲,完全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二
李更开始写文章,大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其时正是我文运蹇滞下海经商的时期。我那时不读任何文学类的报刊杂志。所以,对李更早期的文章知之甚少。记得有一次,一位作家老朋友地我说:“你还记得李建纲的那个儿子李更吗?那家伙可是文学界的一根刺儿,看谁不顺眼就扎谁,大家都躲着他。”听到这番评论,我心存疑惑:难道当年那个站在山洞前一脸兴奋的麻杆少年,竟成了牛二式的泼皮?
三年前,我与《文学自由谈》的主编任芙康先生同时担任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赏读入选作品之余,常得暇聊天,有一次他问我:“你认识李更吗?”我立刻想到关于“刺儿”的评论,便回答:“李更的爸爸是我老同事,老朋友,听说李更文章写得犀利。”任芙康说:“李更经常给《文学自由谈》投稿,他的文章从不趋炎附势,有自己的见地。”听到这番评价,我内心高兴。因为芙康自己就是一个不趋炎附势的人物,他的评价可谓惺惺相惜。
去年,我在《文学自由谈》三月号上读到李更的文章《大声公》,第一段就把我吸引住了:
那天在凤凰卫视的窦文涛节目里看见德国的汉学家顾彬,他果然是敢于说话的。但是我在他身上没有看到德国人的严谨,倒很有一点当年党卫军的严厉和战败国的忧虑。
果然犀利,果然泼辣,果然无所顾忌。在好好先生大行其道的当下文坛,李更果然是一根“刺儿”,但他并不是逮着谁就咬谁的疯狗,而是有的放矢、对当下文坛的不正之风始终保持着批判意识的独行侠。
三
李更的杂文,在读者中影响广泛,仇者仇之,亲者亲之,不用我更多的绕舌。但是,作为诗人的李更,对熟悉李更的读者来说,恐怕是个新鲜的称呼。日前,我收到李更寄来的他将要出版的诗集,附上不到一百个字的便条说:“你看看这些诗值不值得你写几句,如觉得不够格,就不勉强。”
在李更的内心中,有亲情而无权威。他不大看地位、名头,但绝对要看交往的“舒适度”。读了便条,我随手翻开他诗集的打印稿,只见以下这些句子:
哪一天自己也会像他们那样
白发苍苍坐在那里
固执地把交易所
当自己的养老院
《悲壮》
在中国房价
像长征火箭一样升天的时候……
买
还是不买
这不是一个
哈姆莱特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像买自己的棺材那样
赶快作出决定
《海伦堡》
四十八年以前
在这个叫蒋家墩的地方
呼尔嗨哟
中国出了个晃晃叫李更
《红钢城》
我们已经比不了官大官小
也比不了钱多钱少
我们只有比谁比谁能熬
《我们终于熬过了2008年》
其实
小人是有素质的
你如果
不具备那种素质
再怎么努力
再怎么花钱
都做不了小人
哪怕装也装不像
《小人是天生的》
我们认真活下去
已经不是为了享受生活
而是为了看到一种结果
想知道结果离真相有多远
《自言自语》
四
读到以上这些诗句,相信读者会有一个判断:诗人李更还是那位杂文家李更,同样的调侃,同样的冷峻。
杂文诗在中国素有传统,古人不说,单是新中国成立后,杂文诗就出过不少名篇。如袁水柏先生的《马凡陀山歌》,赵朴初先生的《某公三哭》,聂绀努先生更是杂文诗大家。有句俗语说“嬉笑怒骂,堪成文章”,移植到杂文诗中,便是“嬉笑怒骂,皆成诗趣。”但是,近二十年来,写杂文诗的人已越来越少了。不是社会上值得批判的东西大为减少,而是文学批判社会的功能大为减弱。李更僻居珠海,却是“位卑示敢忘忧国”,说忧国太大,忧时可也。浏览诗集中的作品,没有士大夫的优雅,也没有小文人的闲适。处处流溢的,既有草根阶层生活的窘迫,也有对庸俗生活的讥讽。即便是怀旧,也是“苦恼人的笑”;即便是向前看,他也认为“把世界交给陌生人”有点让人担心。
李更诗作中的妙处,在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我只是想引导读者来读读这本诗集,至于评判,还是那句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李更在诗中自嘲地说:“中国出了个晃晃叫李更”。晃晃是武汉的新方言,有无所事事,管管闲事,做不了正经事,无事找事等诸多意义。当然,上述种种还不能概括“晃晃”之妙。在日常生活中,晃晃为贬义,说某某人是晃晃,大家就会对他敬而远之。李更自称是晃晃,依我看,这是对那些“正人君子”的巨大反讽。就像他的这些诗作,不能登上被一些“大师”们控制的“大雅之堂”,但是,置于另册,相信还是有不少读者会喜欢它。
2011年元月1日于闲庐
责任编辑:阎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