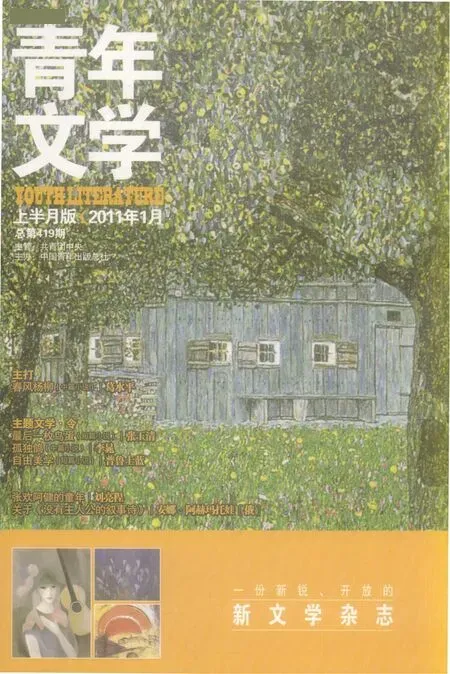凰兮凰兮
文/笑嫣
1
可不可以让胸怀更宽,宽过犀利透彻的海;
可不可以让热忱复燃,儿时的黄昏,乡村怀抱着夕阳,火烧云直落大地,漫卷神话飞书;
红枫林,在三十年前泛出迷梦的血色,脚面上翻涌的何止是爱。一地红叶,一地知秋。
像我早熟的忧伤尖锐的少女时光。
藏起来,藏起来,在人群中,谁也看不到谁的人群中间。一只鸵鸟不见首尾,刺在梗中,梭行沙漠。在字里行间,贪婪地抚摸和吞噬,我血脉贲张。
只有阅读。汤姆、鼹鼠、山庄、新岁的钟声,在幽闭和扼腕中,从不肯闭上眼睛,
转瞬经年。
这是盛世的丛林。我在其中,又常常迷途,今夕何夕,此地何地。我的、我们的,灵魂与肉体的栖息之所。我耋耋老矣的土地,千年书万年书的智慧。
我看到一个壮汉,在田间起来,他快步疾飞。
我惧怕的飞逝、渺小的力,除了热爱,我一无所有。
除了追随。
2
没有面孔的城市,只有声音。不绝于耳的声音,无所不在的声音,就连最深的沉默之夜,金鱼在鱼缸里,也要有气泵的喧嚣才能活的声音。
一片又一片的海,所有的人都在,所有的鱼,在鱼翔浅底的梦中。
抵达。就真的抵达了吗?
我点燃诗稿的灯。它和我俱燃。如果,能烧出一片静。
静是更可怕的止。
是更大的恐惧。我慌,不择路。还是走吧,在原路、在去路,在来时路、在转角路,在单行路、在高速路,在铺满鲜花的路,在遍插荆棘的路……在数不清辨不明的一条又一条的路,上路。
尽管上路。只要上路。
3
这是伟大的时代,盔甲们金光闪闪地炫耀战绩。山妖们极尽美色,脚下的土地随时可能塌陷,鸟儿都被扑棱棱惊出山林。
豹子在山顶接受阳光之浴,它皮毛熠熠,强者之音,风鼓动起叶与枝的琴瑟主旋律;路边不时有狐狸和豺狼出没,炯炯的眼神。更多的蚂蚁在知足知命地爬行,表情幸福神往。
我的国和家,我还能感受到它们的温度,曾经的温文尔雅。
它们的温雅在速度的底下发酵。
我想要抓住一双手,或者哪怕一只,却被一座山峰横截,推开我,说:去!
每一个字都是冷的。我从冰里钻燧取火。狂奔,哦,燃点!!!
请赐我羽翼。
4
我还会飞吗?
一座正在翻建的层峦叠嶂。哦,不,是一座又一座。
顶峰之顶遥不可及。
还有一挖再挖的地下,生命的秘所被剥光了衣服。
开足的马达和赤膊的肉体。惜若珍宝的工业温情,行色张皇的人群。废气尾气里求生的喘息和呼吸。词句和灵肉混在一起批量生产,乘坐光缆的车,难分真伪。
语言们也在悄然梳妆,必须要改头换面。巧施粉黛。
如果,能烧出一片光明。我的骨骼在暗中歌唱,耐不住的寂寞。
还有我的心,深邃之空里的射手,日落后,一只持箭的人马。
请赐我锦绣衣。
啊,竹子,我必须要吃掉那些节和气。
5
一个吹箫的美少年。
天若静水,琼树白冰,繁星如雨般下落。
我的眼睛湿润了,此时此景人生夫复。
是的,我唯美的夜晚、爱情、世界、宇宙、野兽、虫蠡……
我柔身战栗,手捧蚕衣,看时光软软地化成水,任凭温香从耳边吹拂。
在鼻翼和唇际。
当柔弱时爱情是我们唯一的逃离。
6
我看到衣食丰足、爱欲尽享。
一只物质的肥硕的汁水饱满的乳房下,数不清的婴孩在迷醉地吸吮。一些肉白色和一些金银色。抚摸的手,渴望的手,要求的手。
在追索中制造,头顶想象的桂冠。
在酒精里彻夜,唇欲达旦;无休止地爱狂,溺毙。
这些人间景象,这些昨天、今天、明天,我置身其中,又恍如隔世。
一条蜿蜒的蛇,或者是河。我不再走。蹲下来,在镜中洗手,手指分明在日渐僵硬,骨骼嶙峋凸起。
衰败的藤蔓迅疾地攀附在镜子的边缘,不管我的瞠目结舌。
死亡将是最后和最特别的聚会。青冢连天。
拼命地抓取,想方设法逃离。我得到,却看到失去在一点点走近。
7
无数吹箫的少年。翠绿地肃立。我蓦然而生敬畏。
修罗玉面,白衣胜雪,剑指长安。那里是一场真正的盛宴吗?
江水在吞云吐雾般长啸,千里烟尘绝迹。宝马和雕车排成庄严的长列。
有百草的气息在弥漫。
如果心灵渺小,又如何能写出伟岸的诗句?
继续上路吧!
没有牙齿的喙。
我必须精雕细琢。
在前往朝拜的路上,修整还嫌单薄的羽翼。
用热切的汁液消解一切粉尘,请原谅我无比热爱,而且只有它。
8
无法摆脱这些箫声的指引,它是我的瘾。
我的癫狂时刻,现在和现在分离。必须承认,它是我的瘾。
那些最新颖的爱情,那些描绘爱意的不知羞耻的大胆的词句,那些我不曾经历的极地,将遭致嫉妒和艳羡的投予。我承认了,并努力从内心发出宽容的歌颂,努力心怀有你。
一盏台灯亮了,节能的,就像一个男人的爱。我的房间不再黑,小小的温暖也很暖。一只手被握在另一只手里。
你的眼睛在我的羽翼上停留一秒,它便长宽一寸。
这多么神奇。
你说:爱情是要拿在人前炫耀的。那些秘密的,是私情。
那么我可以大声表白了,秦楼之上,我像月亮一样献着殷勤。
秦楼之下,是那片孤高的竹林。
我今晚的爱情,给那少年。低回委婉的箫音拉长的道路,指向那路引领的方向。
9
我爱上了悲伤,这比悲伤本身更令人悲伤。我回到了虚空,于是一次比一次更觉虚空。
一只灰鸽子在脚边,小身子在光滑地涌动。“来呀,这些食物给你。”草坪的长椅上两个陌生的男女将因此结缘。
他们看不到我的羽翼。我的声音在云翳中泯灭。
在冗长的仪式中险些忘记了自己。
我拼命地臆想着那些秘密,练习不开口,这是一种快乐。
拼命地,不要绝望地睡去。
10
是那些花环吗?绚烂的舞步,隐约的裙角。
当我一眨眼,所有的色彩消失,水汽在阳光下苍白地游离。
一棵树被晒干了,笔直地等待枯死。一只蜥蜴爬过来,捉到几只倒霉的飞虫。
知了从来没有停止它的唠叨。
云朵慵懒地在天空散步。
多少人来到过,探望过你,爱戴和憎恨。
哦,你,寂寞,这巨大的时刻。我也曾来。陪伴你如同陪伴自己。
但终将离你而去。
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采摘那些棉花和丝麻。苦艾酒绿、樱桃红、胭脂粉、蓝紫……这样一些缤纷,我熟知这些色彩的性格。
编织我的锦绣衣。
希望和毒药是同一种颜色。忠诚是蓝色的。
我一路走,一路编织,也许是茧,那也是美丽的。
11
冰冷的夜晚,我会偶尔站一站,为一只萤火虫的路过感动。
在寥廓下痛感渺小,向劳作深深地鞠一个躬。
一次次被割裂成许多的碎片,一片给过去,一片给未来;一片给父母,一片给幼子;一片给兄妹,一片给你、你、还有你。剩下腾空的躯体留在现在,用诗意来填满。
我用尽所有的力气,也只能照顾到自己。
我一路走,一路驻足,在每一场薄暮里预测自己。不再拿一朵花做无谓的相较,不再丢掉打开家门的钥匙。在瀚漠里能够一眼找到绿洲。
看啊,那些小兽站起来了,竖起上身,向那些斑痕点点的针叶和阔叶,山岚倏忽黯淡……
在每一个神话里,干旱总会到来。
12
大地出现裂痕,小草在泥土折断的岩壁上飘摇。它的叶尖儿在泛黄。
向下看,是梦中惊惧的深渊。
琼浆有多少,饥渴就有更多;狂欢有多少,悲泣就有更多。
高贵和富足是如此的不堪一击。那些矫揉的情调。
活下来的,是一丛肯微微低下头的灌木,它们长久地关注土地。
谷物、食盐、空气。我们需要的,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呀!
还有水,从自然的胸怀里慈悲地流淌,所到之处生灵鲜嫩,鹿角旖旎。我无数次用最绚烂的诗句赞美你,并将一直赞美下去。
13
觅食是人类永恒的姿势。
绽放和陨落都是注定的,这中间的过程我们不能超越。
我停下来了,用最卑微的屈膝,把全身的温度集中到唇喙,聚光灯在头顶悲悯地看着,我看不到它。我在心里默念:“我是美的。”
我需要两粒米。
一粒给孩子,一粒给自己。
如果有幸找到第三粒,我会把它种下去,用虔诚的泪水灌溉,并献出贮藏的光芒。如果需要我孤独,我也会考虑的,尽管我摒弃和鄙视它。
我在梦中看到过这样的景象:漫山遍野的金黄,翡翠般累累的果实,孩子们在田间嬉戏追打,少女们用玉米缨扎成花冠。一切弱的,一切成长的,一切美的,要加倍快乐。我爱。
14
无路可循了吗?或者我已经接近了真理……
完美是错的,贪欲是错的,得到是错的。饥饿是对的。
当你瞭望远方,无垠的宽阔、崇高。海洋、草原、群山,拾阶而上的巍峨,皑皑白雪的峰顶……我们必须要被震慑,在一生的某些时刻。
我将穿越墓地。
最后一次,被彻底地义无反顾地震慑。
15
我狂饮、沐浴、浇灌,翻云覆雨。
用全部的身体和感官感受你。水,我的母亲,源,起点和终点,蓝天之蓝和碧海之蓝,只剩下一些最俗不可耐也最珍贵的词句了。用赞美来引诱你。
如果可以,我出卖自己,赤裸的羞惭。丑陋与平凡。
一株桦木上有片潮湿的苔绿。
是你吗?食指小心地浸润,你的甘美直透肺腑。
那么请拥抱吧!土地已经等待很久。你的臂膊足够长,爱意足够广。你无分巨细和富裕贫贱,你的世界混沌一片又黑白分明。
我看到我的伙伴,它们振荡翅翼纷飞相告。
我将指给它们看,那些粮食。
麻雀跳起了节奏布鲁斯,电子鼓和蓝调混合映衬着高亢的女声。从毁灭金属到华丽金属,苍鹰粗暴鲁莽的低音泄露着喜悦,漂亮的红嘴鸥浓妆出场。
我的羽毛在一片片丰盈,闪烁着感恩的水光。
16
是的,它们还需要水,这生命的最初真实形态。它们还需要!活过来。
最大的巢是金属做的。还有那么多在长空横亘而过的金属的翅膀。
最珍贵的矿藏都来自于土地、植物、尸体。
这就好。我们没有分离,没有理由分离,从来不曾分离。
我们躲在房子里,但打开窗户接受雨、风、阳光、偶然的尘埃、遥远的乌啼。
我曾经穿戴朴实、很不显眼。平常心做着平常事,一路飞来飞去。青春貌美大把挥霍毫无遮掩。
而今,即使身披火一样的光明,依然只配食竹果腹。
我自命清高的胃啊。
凤翔、岐山,以及太阳升起降落的天边,这些嵌在大地上的神秘的字眼。西边,在爱琴海的上空,俊逸的阿波罗王子赶着他的七色马车每天昼夜穿梭而过。
嘈杂的人声、脚步声。复杂的目光。繁茂的林语,爱管闲事的枝枝杈杈。
嗯。我有我的去处。你有你的。
17
一棵端直的树。该用薄荷绿和柠檬黄的诗句来描绘它。在年轮的密码里,悄然破译我的前生。
树干挺括,树皮青色,光滑的纹理。圆锥形的叶脉上,爬满豌豆粒一样的心事。
未遭亵渎般寂静。
在北方的冬天,如果有洁白的树挂,它就是我的新娘。
穿百羽衣,衔青木枝,我找到了,生存的状态和飞翔的意义。
有些东西永不可丢弃。那一截苍翠的祥瑞。
那么,请赐我声音。
雍雍喈喈。
让我不开口,也能一路纵歌长鸣,一路独孤无惧。
18
我躲在漆黑的黑里。
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我乃良禽,欲择木而栖。端庄的梧桐,忠实的梧桐,承担的梧桐,玉树临风的梧桐。使我的眼睛睁开来,就能看到光明之光的梧桐。
在雷声炸响爆鸣的刹那,撕开胸膛接纳呼喊的梧桐。
红褐色的树枝饱经风雨,紫藤花那么亲昵地搭着他的肩头远眺。他像自然的长子,繁华梦中保有一颗矍铄与温软的心。
在秋华将近、寒冬贲临,幽默地坦然一笑的梧桐。
你是父兄、姐妹,你是母亲。我还记得滚动的车轮,那些漂洋过海的长信,灵动笑语撞击着树干,桀骜的美貌,消融泪水和悲伤的房子——家。
……那经年累月的脚步声,早于朝阳,早于我。
19
一些风吹过整排的棕榈,有加利在你身边挺起了高峻的身躯。
我无意知晓他们的交谈,那些除你之外的任何话语。
我的梧桐。
相对于窗外那株古槐,我听得还不够多,可是已经足矣。
一株蔷薇花会比我说得更多吗?它沉默,但偎依。
今夜,我愿收起枝枝蔓蔓的心思,安心地环枝而卧,只倾听你。
20
我从爱情那里来,沦落为一个诗人。
群山、江湖、负重而行的人群、万物,活的和死的,都是我的背景。
我在其中,
又似乎不在……
一只麻雀侧身飞过,踏实地聒噪一声。
丛林里的生活照常有序,早餐、午餐、晚餐,星星已经从夜宵的盘子里被撤出很久了,生活变成一座旋转餐厅。
灯火通明,使我怀念黑。
我们不敢直视太阳,无节制地贪迷于各种灯光。遗忘了月亮。
每一个早晨醒来,只能看到眼前这一点儿繁忙。
并蒂莲无规则地盛开,在脚下。它们的快乐与情欲令我艳羡。我心无芥蒂,或许可以化身为一棵蒲公英?带一点儿小小的感伤。
不曾存有半点侥幸,不曾偷懒。我,只是一直在等……等待……
21
可以了,是吗?是那座山。
我将念诵《给活的十四行》,以你想象之外的醇美。我的声音。
——曾遭遇爱情、安逸、迷乱、灾难、饥渴……还有一些,我说不清楚都是些什么;
——长久背负着爱、责任、亲情。你可以诅咒,但无法摆脱的字眼。
——是的,是孤独的,都是我的错。
——从没有路那里来……
一只大鸟悲鸣,它打断了我。那双伤残的翅膀使我倍感亲切(看啊,我也有一些伤,我忘记了都来自哪里)。
是他吗?将击中我?
他制止了我。哦,是,你是对的,我们无须忏悔。
丛林中我是心灵干净的鸟,只是不甘心平庸,从未背叛过飞翔。
所以,放你的马过来吧!还有一切。我不会躲开,相反,我心存盼望。
22
火光。
曾经在那古老的阿房,面对一场毁灭手足无措。在梧桐带雨的梦乡。
火光。在岐山之上。
熊熊的燃烧,寒殿冷袖,竹节噼啪,来不及了。
我植下种子,却眼看着它们长出邪恶的嫩芽。
而我无能为力。
那些打开的盒子极尽恐怖。还有那些酒,五百年或者更长时间,它们也还没来得及酿成佳醴。我啜饮一口,让火在胸怀里燃起。
这不是一道选择题,我必死无疑。
那些焦急的奔赴,哀怨的鸣叫。汗血马扬蹄嘶呖。
都无法挽留了。我们总是一直被堵在路上,无视我们的心跳出胸膛。它们滚烫地舞蹈,却恰好留给了思想、死亡和复活以时机。
23
我享受这些燃烧的时刻,欣赏灵魂在火苗的尖儿上踮起脚眺望。
这是告别也将是永生的形式。
我愚钝的身心,需要狠狠地着一下。
我是甘愿的,这一次。把自己扔进火中,在盛世之光下,将那些怯懦、惰性、观望、痴癫、孤独、无妄的天真,一一洗劫。惊叹于千娇百媚的焰火之妖。
仙乐缭绕,在光的映射下它的兰指不断扣动,一再追问。我知道,那是诸神在索取我的心。
而我的心,已经四散成原野的暗香,在每一个陷阱的深处长袖善舞。
当你不再爱我,美丽是件多么无所谓的事情。溪流婉转地顺山颊淌过,鸟儿们啊,我的伙伴,不要告诉他我哭过。
当我的忧伤划过时空,并不是为了和这个世界失之交臂……不是的,不是的……
每一次和这一次,我所为何来?没有什么比这更令我忧伤。
24
那是失落的声音,恍如隔世。
这是凰,浴火的样子颇似一只殉情的琉璃,山林肃穆。
凤鸣即即,凰鸣足足,我恍惚听见锵锵的和鸣。
这一次,是真的了,灰烬、余温、花冠、美酒。玫瑰花娇艳地卖弄风情,在姑娘们的头上。每一个女子都是公主和皇后。绿色的霓裳,向西陵作舞。手臂中清脆撞击的杯盏……百鸟们欢喜焦急地在低空逡巡,它们召唤着更大的奇迹。
我是凰,身披五彩华衣。
确实需要这样一种恢弘吗?
或者,只是一个美的瞬间假定,还不够吗?那么多幸福一下子都赶过来了,那么多。
我原以为它在这一生都要错过我。
凤鸣即即,凰鸣足足,我分明听见锵锵的和鸣。在重生的刹那,在奇迹终于发生的时刻。
25
是真的吗?我血性的叛逆,悲喜交集,注目着你更血性的诺行?
血性啊,你这前世的神话。
忧郁的大鸟,你的翅膀为谁而折?伤情的大鸟,你又因何而浴火?
这一片盛世的土地。你啊,我的凤,原来一直都在,在身边、在心里。也许原本便是一体。
有爱,即是一体。
我可以相信吗?这用于自欺的信仰。我可以相信吗?我能看到的是一切又重新开始。从时间开始。
从来不指望无名的眷顾,从来不。
也许,我们曾一起出发,却久久失散;也许,直到在无知觉中,一体。自己。
26
我真的无法确定。世界依然险象环生,平安符在车窗下左右摇摆。空虚从来都在,藏在歌舞升平和爱恨情仇的底下,伺机而发。你稍不小心,当爱情一闪身,它便出来。
男人、女人、小孩子,仰起的脸庞是那么的晶莹剔透,如此打动我。我活过来了,并将继续活着。莫名沉醉,依然不懂得拒绝快乐,用寸肤寸肌去知觉美。
然后,让痛苦为快乐的寻求负责。这是我活的宿命。
而我伟大的山林,每一缕叶脉都吸附着血、热汗、甜蜜、拥抱、无边无际的智慧的沙砾……
在山冈上,我回望那树,充满大地的璀璨。
谷物金黄,踩着欢欣的鼓点。
你们看到了我,我的衣履极尽奢华,我的心在渐渐变化,变成七彩石。绚烂且坚硬。
我是凰,将以石的方式得到灵之永生。
27
你们看到了我,在广袤的天穹之下,我远成微妙的圆点。在这伟大的时代是这样微不足道。
奇迹与悲恸无时无地不在发生,在这盛世的华年。
我的一点点灼痛是暴雨中的一串水珠,落地无踪。
我将自己全部呈送,也不过是一片羽。一切的虚幻都仰靠阳光的加冕。
在一片静如处子的林中空地,我脱下金光闪闪的羽翼,依然是那个容颜素朴的女子,向自身寻找着存在、爱、永生,与自己。
我的国,我的父,我的兄,我无上威仪的大鸟,当你以欣然的颔首迎接我的再生,我却瞩望着你的伟岸瑰丽。无言以对,难以述说的虔诚。
我的国,我的父,我的土地,我的母性是你的赠予,敬畏自然、力量与速度是我唯一的本能。在每一个清晨无所遮蔽地醒来,深深呼吸,将嘴喙缠绵婉转地朝向无所不能的生活之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