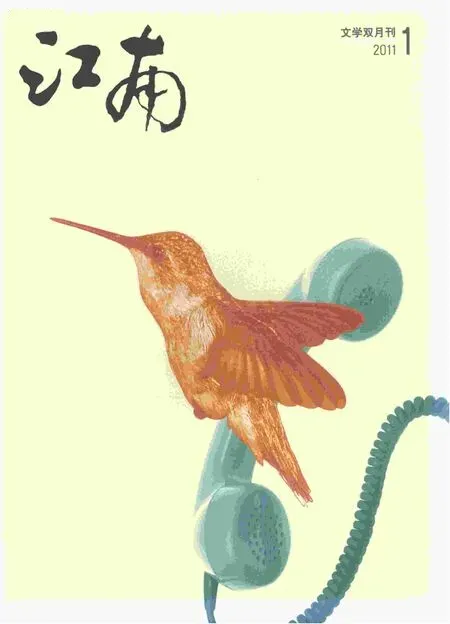心灵的故乡和你的家
◎洪 峰
心灵的故乡和你的家
每一次回故乡的日子里,我都会产生出很漫长的激动,这种激动往往产生出很好的小说。我一直想知道我的激动怎么就不产生诗歌或者散文,我想这大概就是我和其他人的不同:我一旦激动了就写不出自己期望讲的话,只在激动过去之后才可以坐下去慢慢想心事——只有这个时候写在本子上的话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比如“我的故乡没有春天……”
我所熟悉的作家中,几乎每一个都有很重的故乡情结。当代中国作家里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莫言,还可以加上贾平凹和刘震云,女作家中首推迟子建。莫言写作和故乡相关的小说应该是非常出色的,他的优势是具备了想象力。我格外喜欢有想象力的写作,比如他的《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对莫言小说的欣赏肯定来自于他的这一类写作,它们给了我很多遐想,没有什么比这个叫人愉快了。
如今许多作家都开始习惯他乡是故乡的生活了,但好作家一直只能活在故乡的文化中。即便他已经生活在大都市里,他的心和记忆都和这个都市关系不大。都市文化说到底是一种个性趋同的文化,不论你如何特立独行,但最终还是要相互湮没。或许是人们太渴求都市文化的绚丽色彩了,所以他们义无反顾地拒绝了那些苦难和艰辛。没有谁喜欢苦难和艰辛,所有在乡村文化土壤上诞生的人都只能在挣扎中暗示自己可以成功;都市生活给每一个乡下人都显示了机会,虽然大部分人只能成为少数人的参照和陪衬。你很容易看见这样的场面:在台上竞争的超女快男自己还没有什么大动静呢,台下的拥趸似乎已经疯狂起来了:他们泪流满面,他们狂呼呐喊,他们昏厥他们幸福和快乐。我的疑问是,这一切和他们自己的人生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悲剧和不幸就产生在这种状况下:一个成功的范例会激发起大部分平庸者的联想,他们把别人的成功看成是自己的未来,还欺骗自己说这是理想主义和心怀梦想。于是无条件支持自己的偶像就相当于保护了自己成功的梦想,为了这个难能实现的梦想不灭,即便是丑恶的行为也是可以原谅甚至可以被赞美。比如说偷盗在日常生活中会让你痛恨不已,在文学和写作中同样属于下作和违法,但为了保护自己的幻想,这些人可以赞美偷盗:换作你你还偷不了这么好呢?有本事你偷一个试试?道德和公理就这样被消解了,大家在虚假的个性演出中形成了共同的时代性格:为了成功可以不顾一切!这种精神状态与巴尔扎克展示的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物欲横流何其相似,21世纪的中国人原本已经退回100年去循环一种人性丧失的生活了,却还在那里自欺欺人地宣布时代进步了。
时代的事情想不清楚,还是想我自己的事情。
我至今还是不能完全清楚故乡对人的一生究竟都意味了什么,你可以说它生你养你是你生命的根,但这似乎都不是我真正想寻找的答案。每次要重回家乡,心里就免不了一团乱麻,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接下去的日子是和同学聚会,那些中学时的伙伴都成家立业,大大小小还做了官,他们有能力请我吃馆子。每个人差不多都能安排一顿,肚子撑得很大,脑袋里的想法都撑光了。这个时候我又恨不得马上离开,马上回到我自己的小家里去。
他们送我上火车,火车开了,我心情放松了很多;火车继续开,我又开始莫名其妙地想念他们了。我不能回忆每次都想到了什么,反正一路上的心情很坏。然后是开始重新整理自己的心情,开始慢慢感受和体味那些往事;于是本能地开始记录,于是开始形成小说。
现在想来,这大概就是几十年时间过去,我依旧不敢写一写故乡的缘故了。我始终觉得一旦把自己的那些记忆完全展示出来,写作就终结了。
故乡如今已经没有我的至亲了,父亲母亲早在1981年就去了内蒙古的通辽。父亲就死在那里,那是一个和故乡一样风沙经年不休的城市。我一直觉得父亲和母亲生活的地方才应该是真正的故乡,于是我试图把通辽当做我的第二故乡。但我没有成功,我没有办法在梦中和它相见,它一直远离我的思念。1987年父亲在那里离世,1993年母亲随着哥哥去了济南,妹妹如今也在济南生活了将近20年了。母亲去年春节前也去世了,很少听母亲说起父亲,但哥哥说母亲还是想与父亲合葬。这不奇怪,她一定希望在土地下面与父亲会合。既然生前不能共同进退,死后相互关照总是可以实现的。对活着的人来说,合葬是一种象征:两个装了骨灰的盒子放在一起埋了,你想象他们可以得到新的安慰和幸福。哥哥说他把墓地已经选好,在通榆。初冬的时候他和嫂子一起到了通榆,老燕的治疗几乎每天都要进行,我们只能在家里听消息。
又多出一个问题,济南是不是应该成为我的第三个故乡?很难,哥哥说他很快就要去上海,他在那里有自己的事情。嫂子大概还会留在济南,问题是她距离我的记忆模糊而遥远。妹妹也还在济南,但她有自己的丈夫和女儿,她为自己的女儿几乎倾注了全部心血,我一直不清楚她到底在女儿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什么未竟理想。前两天老燕接到妹妹的短信,上边说她的女儿在上海的一次全国性少儿钢琴比赛中得了银奖。难道说我的妹妹曾经想成为一个钢琴家?
我问老燕:“是自己花钱的吗?”
老燕说:“只是自己出路费宿费,再交20元参赛费。”
我说:“那就祝贺她吧。”
她就祝贺,妹妹那边就谦逊,似乎所有事情都是发生在她自己身上。我看见过妹妹女儿的照片:不是很漂亮,但看上去不傻。这就行,人不能要求太高。太高了就要心理失衡,成大事就难。
我在通榆总共生活了大约18年,后来在长春大约8年,又到北京4年,又到沈阳,在沈阳期间到云南住了将近3年……几十年的时间就这样瓜分了。故乡的概念就这样飘来飘去,始终不能降落。梦里边经常是故乡的乡间小路、青纱帐、大都市的高楼大厦、无声的飞机和奔跑的小毛驴混合在一起,醒来之后总有某种不能述说的悲伤,好像自己被什么最喜欢的人或者事情抛弃了。
今年的夏天和秋天还有这个冬天,我经常梦见吉林省西部的那个镇子,还梦见了住了18年的土坯房子;还梦见下了大雨,我父亲撑着一把藏青色油纸雨伞——他脸上流着很多雨水,笑嘻嘻地咳嗽。醒来之后我清楚那个场面不是虚构的,它是我记忆里的事情。那是父亲打着雨伞去我的班主任老师金耀人家,他私下告诉我的老师,说洪峰的眼睛不好,他看不见黑板上的字,他请金老师在考试的时候写完试题之后把那张底稿给我。许多年前我就是这样上学读书的,我只是听老师讲,就这样听完了小学中学和大学。我庆幸如今的孩子考试都有印好的卷子,我猜他们中间也一定有看不清黑板的人。还有,如今戴眼镜的孩子多起来了,给人嘲弄的机会就少了。不知道这算不算时代的又一个进步。
梦见家乡之后的日子,我就会喋喋不休地讲述少年时的事情给老燕听。她这个时候也会说起自己的家乡,她说的那些事情总是让我对她更加心疼,我感觉到那些大山里面掩埋着更多的苦难和梦想。我知道她和我一样想家,但估计她很难回去:那里的人对亲人的态度比较奇怪,他们似乎更愿意以伤害的方式表达亲人之间的感情。我们所能做的是努力感受家就是两个人相互支持和一同建设的世界,我们只需让这个世界温暖和健康。
我不是很清楚她是不是对我的故乡有兴趣,但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又开始梦见那个地方了。
我开始问自己:是不是又该回家了?家呢?
童年经验
每个成年人都能从自己的童年经验中寻找到自己生活的出处,童年经验从一个人生命的最底层规定了一个人的全部生活。童年的梦想执着并且辉煌,它使一个人幼小的心灵充满了焦灼和向往。童年的世界游离于成人世界之外同时又被成人世界所扼杀,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便是放弃梦想的过程;当梦想被成年后的日常生活吞没时,人最美丽的生命便宣告了终止。
巴乌斯托夫斯基在他的小书《金蔷薇》里这样说:“对生活、对周围的一切赋予诗意的理解,都是童年时代给予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谁不忘记自己的童年,他就是一个诗人。”
童年经验对每个人都有所不同,不同的经验会唤醒生命中某些特殊的情感。这些情感是生命历史中积淀下来的人类共同财富,它们以封存的方式保存在每一个生命个体之中。不同的经验如同若干把钥匙,相应地打开某一个保险箱,放飞出美丽或者丑陋的情感。
在我童年的梦想中,一直想当解放军,这种梦想直到今天依然以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有朋友说:“你好像对战争背景的小说很感兴趣啊。”我不置可否,他不可能知道这种兴趣产生在几十年之前。那此后的几十年中,我也一直比许多人更愿意读战争小说并且研究战争史和兵器发展史。甚至可以这样讲,在理论上,我几乎比许多职业军人更能理解战争,更能宏观地把握战争的趋势。
当解放军的梦想肯定源于那个时代所受的教育,它使“解放军”抽象成为一种威力、一种强权、一种战无不胜的象征。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可读的书越来越多,我开始读到德国作家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太阳照常升起》,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格拉斯的《铁皮鼓》,冯尼格的《五号屠场》……所有这些书籍和我曾经读过的那些小说是那样不同,比如说《林海雪原》《战斗的青春》《烈火金刚》《红岩》……在那些异域文学大师的笔下,我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恐怖和罪恶,也开始领会战争没有胜利者的深刻含义。在这种时候,童年时的那种梦想带给我的快乐变成了一种忧伤,一个成年人的梦想变得更加虚无缥缈起来。在许多时候,我的眼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战争爆发了,我的亲人还有许多儿童跟随着他们的亲人颠沛流离、缺吃少穿,时时被枪炮声从睡梦中惊醒……我于是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喜欢和平的年代。在这个和平的年代中,我甚至愿意承受一些贫穷和平庸。我把自己的意愿表达在自己的作品中:《和平年代》《东八时区》《喜剧之年》。我还意识到了和平年代给人造成的精神伤害比起战争毫不逊色,所以说几部书都不同程度地摧毁了我童年的梦想。但必须说,那种由童年梦想所唤起的学习热情和探究毅力却始终是后来写作的缘由。
当我们离开讨论写作的时候,我们还会发现一个人成年之后的许多习惯和生活准则都和自己的童年经验不可分割。
在童年的记忆里,父亲每天大约要喝二两老白干,大约需要两角五分钱,偶尔花五角钱买四两酒。每到月底的时候,家里的钱就花光了。父亲就要命我去邻居家借上几元钱,一般都是十块或五块。我最害怕的就是这种时刻,每到月底我总是心惊肉跳。我祈祷能躲过这个难堪的任务,但很少能够如愿。那年头大部分人家都没有余钱,跟人家借钱就是给人家凭空增添麻烦,更何况又不付利息。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是能回想起债主的神情。年仅六七岁的我在那个时候开始体验到尴尬和羞辱的滋味,每次我都恨父亲恨不得把他的小酒壶砸烂了。
成年之后,我几乎滴酒不沾,虽然我有足够的钱买酒喝。在许多宴会上也因为不喝酒经常使同席的人大为不满,还有因此对我深恶痛绝的。我评价一个人的好坏甚至有了一个奇怪的标准:凡死命劝酒的人我一概认定为坏人,凡酗酒者和馋酒者我一概看成是无赖。其实这样的人并不见得坏,相反,他们一般都觉得我是一个不好结交不好相处的人。如今的情况有了一定的变化,我不再用喝酒不喝酒的标准去衡量他人,但也渴望喝酒的人给我一份尊重:我应该有不喝酒的权利,这是我的心灵死角,我可以不去打扫它,并不碍别人的事。
再回到写作实践中,这种心理障碍也影响了表达:我很少写到喝酒,看见赵本山在电视剧里不停地喝酒,不停地大舌头,就感觉那是一种很下作的生活。真实的情况可能不是这样,人家需要喝。
从借钱中、从喝酒中,我体验到的是人对尊严的内心需求。我还联想到人都需要各自的尊严,因而保持自身的尊严一定要以不损害他人的尊严为前提。这虽然只是人类精神中很小的一个部分,但它可以帮助一个人在其他领域里走向人类共同理想的彼岸。
正如巴乌斯托夫斯基说过的,作家和其他人的区别就在于他在成长过程中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童年的梦想、欢乐、痛苦,还有伙伴、父母、原野、学校……从心灵的角度说,他的一生永远是童年世界的延续和扩大,他永远不会走进成熟,他的内心永远单纯、脆弱并且幻想不灭,梦想不灭……
生命之度:轻重贵贱和长短粗细软硬
最近几年关于作家早逝的报道很多,数来都是有知名度的人:周克芹、路遥、邹志安……关于路遥,很多文章大都讲他的清贫——“早晨从中午开始,午饭是一个馒头加一根葱,他用自己生命作血本去拼搏。”文章都有很多如果:如果路遥的处境好些,“路遥的路不该这样短。”
很富有同情心的善良人的想法。
也是最近,读到了拉美“爆炸文学”主力作家多诺索的一篇文章,他介绍说当今世界文学大师中除了马尔克斯等少数作家之外,大部分优秀作家的生活都相当清贫,甚至在贫困线以下。相比较而言,中国作家的日子无论如何要好过些。我严格区分了作家的品位,好作家的日子大部分时间是处于贫困线以上的,基本过得去。至于打着作家旗号做大款的,随着人们逐渐智慧起来,这些江湖术士最终会暴露出本色:写作不是明星事业,它的存在就是为了给明星和富有做一种现实性陪衬。如果一个写作者不甘心如此,出路还是很多的。写作者毕竟比常人多出些技能和手段,只要操作得当,成为明星并不难于登蜀道青天。
问题只在于这个过程不可避免要损失和丢弃写作的良心,能狠下心来的一定是大有人在的:时代变化着,人们正处在打烂一切传统而新传统无从建设的时刻,正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没有什么比现世享乐更有魅力了。
说起天才艺术家,我们都会想到凡·高、高更、晚年的伦勃朗和俄罗斯“巡回画展派”的衣食之窘;在古代中国有绕城踏步取暖的吴敬梓和贫困之死的杜甫,当代中国有了一位四十二岁便英年早逝的路遥。如果说到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有年轻的郁达夫和萧红。
其实这没什么大不了。人总要死,三十岁八十岁都免不了死。死人这件事本身很平常,不平常之处是生命的社会价值出现了反差。我们心疼路遥心疼高更心疼萧红,是因为我们以为这些人的生命更有价值,大家都觉得有用的东西总该存在得长久一些才好。问题是从生命本身的意义讲,三岁儿童的夭折和百岁老妪的寿终正寝都是人类的损失,它都证明了人类整体的脆弱和渺小。任何一种职业都不能提高或降低生命对个人的价值,艺术大师也罢,拾破烂的老头也罢,在生存和死亡的尺度上是对等的,天堂和地狱同时对他们洞开,说不好谁进哪个门呢。约翰·唐恩有诗说:“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
说到生命价值,生命个体的价值只对他自己和亲近的人产生意义,和社会的评价没有关系。还有,路遥的早逝不会给世界带来变更,只有他的亲人和爱他的人才会有真实可靠的内心悲伤。其他的人,伤心来伤心去、说东说西最终还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活着的庆幸。说得更刻薄些,没有谁愿意跟着死者进火化炉子,死者的亲人包括爱死者的人也还会很努力地活下去并且努力活得更好。说那是对死者尊重是对死者最大的安慰,胡扯淡!
我的意思是说:生死不是平常事但只能是平常事,有人死了你还活着不是罪过,但过分去寻找这个那个活着的理由说服自己还说服别人,这种人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还想,在人们感慨唏嘘咿哩哇啦的时候,死去的人不见得在那边活得吃力。
我猜测,高更路遥吴敬梓虽生年吃了很多苦,但高更安息,吴敬梓安息。路遥呢?路遥也安息。说起来也简单,他们清楚自己一生善待同类也善待这个世界。
无论怎样,这些人确实不该贫困,但他们贫困。
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写作者之爱
每个人都有成为各种大师的机会,就如同谁都有机会成为英雄和败类一样。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存在着人世间所能展示的全部才能和愚蠢,任何人的成功和失败都潜伏在他生命的深处。只是成长的过程中丧失了某一部分,成为让人羡慕的大师的可能就变得有些渺茫。这种丧失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可能是在自我满足的收获中,可能是在与人奋斗的其乐无穷中,也可能在持续努力之后的疲惫里……任何的成功都伴随着其他领域的失败,只是专注于特定领域的痴者才有更多的机会在某个领域里获得成功。
比如说作家,我指的是那些文学史意义上的作家(不是自封的和几个人吹捧中诞生的,是文学历史淘沙后的产物),他的成功得益于他放弃世界和生活已经显示出的其他机会,他只专心于文学的劳动。从最普遍的意义上看这些作家,他们在很多领域里都是低能儿。这种情况和他们的智力无关,他们太过专注于单独的领域了,大部分人生经验都用在表达精神和心灵了,这和科学家哲学家的低能殊途同归。
更多的人喜欢文学而不能成为文学的继承者和创造者,不是因为才能和愚蠢与他人有什么多寡的不同,主要的也就是爱好太多需求太多欲望太高分神太多。想要的东西太多了,最大的可能就是在文学领域一无所获。当然,把写作看成一种爱好,如同你喜欢足球但踢的是那种穿胶鞋小场地的足球:它可以给你的生命增添些许乐趣和活力,也是一种成功。我所说的成功和这种成功是两回事,和爱好无关。
现实世界中的好东西非常多,金钱、美女、酒宴、高档服装、卡拉OK、奔驰轿车……对哪个人都有十足的诱惑力。写作则不同了,它的诱惑非常抽象并且和艰辛与孤独相伴,它暗示了一个人的生命消耗和生活享乐不成正比。写作者大部分时间自绝于如火如荼的现实享乐,他被自己所设想的人类前途和同类命运折磨得困苦不堪。在世人眼中,此类作家要么愚蠢至极要么精神偏执,况且文学艺术史又提供了无数例证:比如说茨威格和海明威的自杀,比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分裂,比如说卡夫卡的逃婚和托尔斯泰的晚年弃家出走,比如说萧红的英年早逝和普希金的决斗……从精神和心灵的意义上讲,成为文学家的内在条件是他和他所处的时代生活以及时代精神呈某种对抗状态,它的反面是随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共同行走的人意味着丧失了成为作家的可能。再强调一回,我指的是人类文学史意义上的文学大师,和洪老汉这个层面上操作文学的人毫不相关,后者最大限度是喜欢球赛的人。
我的想法很单纯,不要轻易告诉别人:“我爱文学。”这就如同不能随便说“我爱你”一样,它必须是你内心的一种深切感觉,甚至涉及了一个人的生命品格。和“我爱钱”不一样,作家也爱钱,每个人都爱钱,因为它能从实在的生活兑现出吃喝穿用和生命体的延长。爱文学则不同了,你愿意用五百元的稿费损失十年的寿命和能见的快乐么?
西北的一位作家有一个正读中学的女儿,这一天家人看电视,看歌剧《白毛女》。演到大年三十杨白劳躲债回家,从怀里掏出红头绳比划给女儿看,女儿喜儿大喜。爷儿俩你唱一段我唱一段,大意是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我没钱不能买,现在只能扯了二尺红头绳,扎呀嘛扎起来呀!
这时候作家女儿突然说:“穷成那个熊样子,还不嫁给黄世仁干啥?”
作家一时间被女儿的评论弄得无话可说,过了半天才说:
“你……我……那……大春怎么办?”
在那个当代中学生眼里,喜儿有点死心眼儿:放着有钱有势的黄世仁不嫁,却偏偏为穷小子大春海枯石烂不变心。21世纪的小姑娘着实不理解喜儿图个什么,这怪不得孩子们。在当今的时代,爱情和性之间的联系比较疏离,中学生处女数量骤降便是证明。当然这篇文字没有“救救孩子”的念头,我只是用这个细节转喻作家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也算是写作者的职业怪癖。
文学就是那个穷小子大春,写作者就是那个痴情傻瓜女子喜儿。跟了大春有吃不完的苦有受不尽的穷,但喜儿只爱大春,于是什么都认了。
没地方说理去的类型。
一个爱情故事的结尾
大约是在2003年初秋的一天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个女的。“你还记得我吗?”她问。我没有回答,我讨厌有人这样在电话里问我。
“我是小梁啊!”那个瞬间我觉得记忆恢复了,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大眼睛圆脸皮肤白皙的姑娘。我说:“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小梁你好吧?”她说:“我很好,你呢?你也好吧。”然后我们说了很多话。
此后的日子里,我们经常通电话。
她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老杨的朋友。用现在的说法定位:是老杨曾经的情人。
姑娘留给我的印象很深,不仅仅是因为她长得漂亮,更因为她是那种非常安静非常体贴的女人。记得我和她的情人下棋的时候,她会静悄悄坐在一边看,夜深的时候她会把冲好的方便面端过来。当时他们住在一个学校里,正因为是同学,他们才爱上了。那年头刚刚开始时兴这样的爱情,所以离婚的也比较多。现在进步了,该爱爱该家家,两不误。那会儿还比较不进步,所以我这个朋友和他的情人就私奔了。他们一家伙就跑到海南岛了,90年代初的海南岛还是冒险家的乐园,大部分在内地活得不如意的人都跑了去。他们在那里生活了三年但一直没有过上很好的日子:他们经常吵架,开始文斗最后发展到武斗。武斗一开头就意味着两个人的关系到了结束的时候,他们结束了。男的回到自己家里,女的没有回家,她一个人去了广州。
我想说后来的事情。
后来,后来我的朋友老杨得了癌症,胃癌。做了几次手术,效果不错,再后来就转移再做手术。小梁从一个朋友那里知道老杨的情况,就从广州赶到上海。老杨那时候在上海的一家医院里做化疗,他看见小梁的时候先是张着嘴巴,然后就哭了。小梁也哭,她后来跟我说她哇哇地哭,一点也不管周围的人用什么眼睛看。
他们哭啊哭哭完了,老杨说:“小梁,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
小梁没有回答,她还沉浸在悲伤里。
老杨继续说:“等我的病好了,我们一起去广州,再也不分开。”
小梁连忙停止悲伤,“你不会是真的这样想吧?”
老杨说:“我真是这样想的。”
小梁看着老杨发了一会呆,说:“不行!我现在也有自己的家了。”
小梁后来跟我说:“老杨怎么可以有这个念头呢?我去看他不是要证明我还在爱他。”
后来老杨还给小梁打过几次电话,小梁说不行老杨,已经不是过去了。不行。
老杨问:“为什么不行?你不爱我了?”
小梁说:“不爱了。”
老杨说:“你为什么还要去看我?”老杨沉默了一会儿,在电话那边哭了。
小梁在这边也哭了,她说:“你连这个也不明白,我当年爱你算是瞎了眼。”
后来我在云南的时候,小梁也去了云南旅游。小燕和我去机场接她,她先是和小燕亲热了一会儿。小燕去找车的时候,小梁对我说:“你不知道吧?老杨已经去世了。”
我不知道,我有几年没有见过老杨了。我非常难过,他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在沈阳的时候我们会经常聚在一起下棋,也会时不时聚在一起喝茶。离开沈阳之后,我几乎断绝了和那里同行和朋友的联系,也包括老杨。
小梁说:“刚刚去世不到半个月。”
我看着她,她说:“他去世前几天还给我打过电话。”
我看着她,她说:“他说他一定要去广州找我。”
我看着她,她说:“我没有答应。”
我看着她。
她说:“我要是知道他就要不行了……我会答应……”小梁的眼泪流下来,她把脑袋搁在我胸前,身体哭得抽搐。我摸着她的头,我也哭了。
“但我真的已经不爱他……”她抽泣着说。
“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