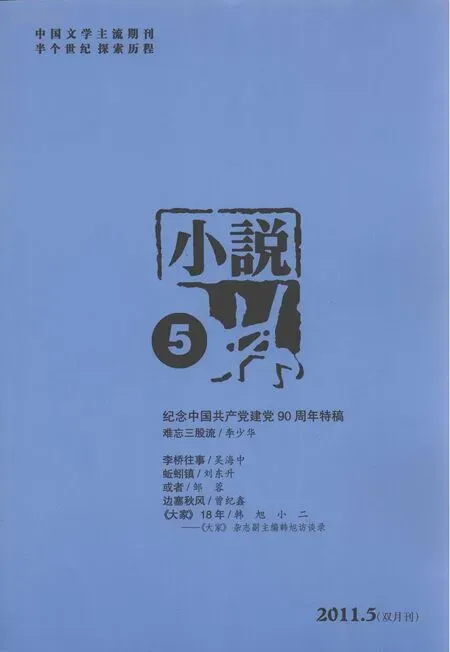重 雾
■陈孝荣
1
早晨从屋里出来,太阳还没有醒来,依旧在东山那边发芽。只有雾霾扣住锁扣,将整座城市锁死了。我一头扎进雾霾里,发现雾霾依旧是过去那副小人德性,浓成稀粥,得意洋洋。我的眼睛几乎等于零了,无法看清百米之外的任何物体。身边街道上的车辆也基本瘫痪成泥,傻在雾里一动不动。偶尔擦身而过的行人则一如进入雷区,小心翼翼,举步维艰。
我也同他们一样,小心谨慎地朝单位走去。大脑中的意识则如数空掉,不让它们再增添一物。就这样走着走着,突然一栋陌生的建筑物就闯进了眼帘。几乎是嘭地一下,某个开关就错了位,我就傻掉了:怎么搞的?难道我走错了路?
但随即,意识很快清醒过来,刚刚升起的疑惑也被扔到一边。因为这条线路是我上班的路,我在一次次的重复行走中,已经焊进了生命的每一条缝隙里,即使是闭上眼睛,也不会错。
可是怎么突然钻出这么一栋陌生的建筑物呢?
抬眼细细打量方位,发现依旧没有错。陌生建筑物的位置就是过去夷城法院的所在地。街对面的凤兰商店、夷城电器维修部、护栏、绿化树、花坛等等依旧完好无损地待在那儿。再打开记忆的盖顶,发现关在记忆深处的法院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过去的法院是一栋三层楼的老式房子,患有多种重病。笨重而老式的门窗严重哮喘,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墙体又患风湿骨病,大多数墙面的搓沙脱落,在风光里伤心、出丑败相。过道、花坛、护栏等等,全都是破罐子破摔,灰头土脸,心灰意冷。这么个地方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栋崭新的房屋呢?
再细细打量新的建筑,发现它已是浓妆艳抹了。加到十多层的楼房,高傲地挺在雾霾里,不可一世。瓷砖砌的墙面,洁白、高贵、目中无人。大理石铺成的地面和柱梁,气派、雄壮、拒人千里之外。不锈钢的大铁门,欧式的玻璃窗,明亮、霸气、不食人间烟火。
这还是法院吗?它是什么时候返老还童的?
疑惑牵着我往前走了几步。接着,“夷城县人民法院”几个金色的大字就跳入了眼帘。没错,这里依旧是法院。
但更大的疑惑却又爬上高坎:法院怎么变化这么快呢?尽管我知道,我们夷城近几年的发展是坐上的喷气式直升飞机,拔地而起的高楼似乎是吃了什么激素药,眨眼间就吞下了我们熟悉的环境,让政绩带着巨大的轰响。可是法院也不会这么快就变得如此壮观吧?
再搜索记忆,发现记忆里的每一个房间、抽屉、角落里也并没有保存法院整修时的任何时间,任何迹象。但眼前的事实却又比铁还硬,它显然不是某个夜晚用吹火筒吹起来的,而是经过了建筑工人精心打造之后才呈现出的这副浓妆艳抹的装扮。难道是我太粗心了?竟然对身边的变化毫无感觉?
看看四周,发现也并没有解开疑惑的任何扣子。行人照例在小心地进入雷区,无一个熟人可以打听。泊在重雾里的车辆照例瘫痪在地,也不会开口。我只好暂时地放掉疑惑,抬腿朝单位走去。
来到单位,还没有迈进大门,太阳就喷薄而出了。金色的阳光带着热量与正义,一下子就将雾霾横扫一净,夷城又露出了它的清秀面容。整洁的街道、漂亮的楼房、来往的车辆、匆匆的行人,来自生活里的各种声响又同时摆到了眼前。我的心情也同时打开了另一扇门窗,好了起来。因为我知道,我们这座临江的城市,无论雾霾多么不可一世,终归见不得光亮和热量。只要太阳一出来,聚积在空气中的水蒸汽就不可能小人得志。
爬上台阶,再打开办公室大门。办公室里的桌椅、沙发、饮水机、空调等等,也都同先前一样,照例在等着我。往办公桌前一坐,望着洁净的办公桌,这才发现我的意识并没有回来,它依旧被疑惑牵住了手脚:法院到底是什么时候整修的呢?为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
再环顾一眼办公室,发现沙发依旧坐着,饮水机依旧站着,空调照例悬着,没谁能回答我。我便站起来朝旁边的办公室走去。
一进去,就发现两个同事的脸上都栽满了笑容:“你们说什么好笑的话?”
“陈作家呀,坐坐坐。”
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唉,你们晓得法院是什么时候整修得那么漂亮了?”
“法院?”
“嗯。今天来上班,走到法院前不敢相认了,以为我走错了路哩。”
“我说你呀,还是在家里待的时间长了,已经整修起两个多月啦。”
“两个多月?”
“嗯。”
“两个多月为什么我不知道?难道是我粗心没有发现?”
“你怎么这么关心法院?是不是里面有老相好?”
“我都半老头子了,哪还有什么老相好。”
“那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呢?喝不喝水?”
“不喝,你们忙。”
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出去,再回到自已的办公室,突然发现意识里的另一个阀门已悄然打开,一个叫周伦的老同学走过阀门,来到了意识的天空下。哦,原来我关心的并不是什么法院的整修,而是那里的周伦。看来,周伦还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死结。
重新在办公桌坐下,顺手拿过摆在旁边的文件。但只看了一眼,发现所有的注意力都被周伦牵了去,那上面的文字无一字可以与意识对接。来到意识天空下的周伦,则在独自表演。我便干脆将整个身子靠在沙发椅上,让周伦尽情地表演。
2
周伦是我高中时的同学。
新入学的那天,我们在学校报名处报到后,父亲背着箱子和被子走在前,我背着生活用品走在后。走进被学校指定的高一班男生宿舍,发现楼板上的位置早被占满了。楼板的两边分别铺上了各色被面的铺盖,一床挨着一床,类似于新铺成的苕床。同学的木箱就一个挨着一个放在床头,放成了两排,只有楼板中间留出了一条过道。有的同学正在铺着铺盖,有的则在整理木箱。各种声音都似乎打着赤脚,轻轻地掠过,生怕惊扰了什么。只有贫穷、寒酸、羞涩、陌生挤满了所有的空间。
扫视一眼,发现里面靠墙的位置还空着,我和父亲走进去,问正歪在那里翻着箱子的同学:“这里有没有人?”
那同学头也没抬:“没有。”
我和父亲便卸下背篓,将铺盖散开铺上去,再将箱子摆好,父亲便背上空背篓说:“我走了。”
“您在哪里歇呢?”
“到你姑爹家住一晚,明天就回去了。”
“噢。”我便站起来送父亲出屋。
“你回吧。自己照顾好自己。”
“嗯。”
但我没有立刻回去,而是站在楼道口目送父亲走下楼梯、走过操场,一直看见前面的农户掩住了他的身影才回屋。
回到自己的床铺前,发现刚才那个同学没再翻箱子了,而是坐在木箱上埋头吃着玉米饼。再细细看他一眼,听不见的一声闷响就在心头轰然响起,我一下子就傻了。因为眼前的这个同学类似于一个隔了气的馒头,没有发育开,似乎还是个小娃子。倘若如此也罢了,他竟然还是个鼻涕糊,长长的鼻涕爬出来,一如两条长龙挂在那里,他连擦都不擦一下。上唇和两腮处则结了一层硬壳,类似于农村女人做鞋的那种硬布壳,硬邦邦粘贴在他那黑瘦的脸上。身上穿着一套蓝色的卡叽衣服。衣服早被洗得发白,被磨破的胳膊处打了两块黑色的补丁,肩膀处打了一块灰色的补丁。脚上则穿了一双破旧的布鞋。他无声地坐在那里咀嚼着,一如一只癞蛤蟆,或一个被虫蛀过的包谷棒子,可怜、龌龊。
接着嘭的一声,内心里的同情与厌恶就同时在我心里泛滥起来。我便脱掉鞋子,在床头趴下:“你叫什么名字?”
“周伦。”
接下来,我俩再无话了。他依旧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既没问我叫什么,也没有望我一眼。
就这样,周伦就以这样一种形象闯入了我的意识。
之后,他的这种形象不仅没有丝毫改变,反而是把他的龌龊与可怜又涂得更厚。因为接着我们就发现,他身体里的自卑比他的鼻涕还多。他几乎不与同学们发生任何往来,无论是下课、自由活动时间,还是吃饭、归寝,他一如一孤魂野鬼,默默地来,又默默地去。那身破旧的衣服也似乎从没有换洗过。只是到了冬天,里面多套了一件棉袄而已。因而他的身上常常散发出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酸臭气息,一如来路不明的病毒,吓得人人都不愿意接近他。有些女生偶然与他碰面,甚至如临大敌,赶紧逃也似的逃开。甚至发出一声轻微的惊叫声。就这样,他的自卑就垒成高高的山峰,重重地将他压扁了。不敢抬头走路,不敢与人合群,不敢大声说话。看人的眼光一如盗贼,扫过一眼就赶紧将视线移开。也就这样,全班五十多名学生几乎没人把他纳入视线之内,将他彻底遗忘了。
两年的高中生活转眼结束,各自不同的命运又振翅把我们带到了不同的方向。
毕业后我一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曾经生起的渴望在流逝的时间里一点点枯萎。突然有一天,邮递员站在屋外大声喊我:“笑容,笑容。”
“唉。”
应声出来,邮递员说:“你的信。”
激动迅速翻山头,占满心空。
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信,只看了一眼封皮,啪地一下,刚才翻出的激动就被彻底打入了冷宫。因为来信不是录取通知,而是我的恋人蒋丽写来的。
赶紧拆开信:
笑容:
我们分手吧。
蒋丽
即日
意识还没来得及做出愤怒的姿势,我就被迎面泼来的冷水冻成了冰棒,傻在门前失去了知觉。
三年后,我通过招干考试,被聘成了乡镇干部,分在一个叫五尖山的乡里从事办公室工作。第二年与被同时招聘上来的一个叫田英的女孩子结了婚。生活的轨道算是铺成了一条简易的钢轨,在最基层进行简单而重复的运行。曾经被人抛弃的伤痛,因为新的生活而修复。
第三年五月的一天,时间的脚步迈到下午五点多钟,快要下班的时候,突然电话响了。抓起一听,乡里分管计生工作的郭副乡长就在那头说:“陈主任,县法院的法官已经在村里执完法,现在正在返回途中,请你帮忙接待一下。”
“好的。”
放下电话,检查了一下开水瓶,发现早晨打来的开水还很满。再检查一下茶叶,茶叶也还有大半盒。茶杯则早洗干净了,只要人到了,随时都可以泡茶。郭副乡长要我接待,也无非是泡一杯茶就算完事。
昨天,我就从妻子田英嘴里得知县法院执行庭的法官们来乡里执法了。因为我们五尖山乡的命运不好,边远、偏僻、无人疼爱,是鄂西最穷的一个乡。全乡仅一万多口人,但山却大得如同橡皮,需要吹多大就可以吹多大。刚刚摆脱温饱的农民依旧把脱贫的希望寄托在多生育上。因而计生工作成了第一难。分管计生工作的郭副乡长常年带着计生办的人到乡下攻多胎,收罚款,却常常是碰的铁钉子。直到碰得头破血流,脸色乌青,工作也依旧毫无起色。因而他们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起讼生效后,夷城法院执行庭的法官们,就于昨天声势浩大地来到了乡里。只是当时是计生办接待的他们,所以我就没与他们碰上。
检查完刚刚一坐下,就听见屋外传来了汽车的刹车声和喧闹的说笑声。声浪刚刚一扑进来,我就赶紧站起来朝外迎去。一出屋,就发现大院里停了一辆警车、一辆小车和一辆汽车。警车里下来的是县法院的法官,小车里下来的是乡里的郭副乡长等人,汽车上则装着二十来个民工。他们的脸上一律插着胜利的旗帜,笑容灿烂得装满整个院子。显然,他们大获全胜了。
接着,走在最前面的法官迎面向我走来,一下子就劈出了我的意外。因为那张脸与记忆中的周伦有某些相同之处,但又不敢确认。因为保存在记忆里的周伦是癞蛤蟆,是虫蛀过的包谷棒子,脸小而瘦,眼光躲闪。可是现在的这个法官却是发育良好,略显发福的身体里散发出的是满满的坚定,胖脸上的那双眼里溢出的则是满满的自信。
“你是?”
身后的郭副乡长说:“执行庭的周庭长。”
“是不是叫周伦?”
周伦依旧将一张灿烂的脸面向我:“你是?哦,想起来了,你是小陈。”
咔的一声,我的笑容冻在了脸上。心里的不快迅速翻越山头:怎么是小陈?我比他还大一岁呢。
郭副乡长说:“你们认识?”
周伦说:“我们是高中时的同学。”
我只得将冰冻的脸赶紧融化:“屋里请。”
迎进屋,周伦并没有再理我,而是坐在屋子中间的位置上,将袖子和裤腿高高地挽起来,然后手舞足蹈地对着郭副乡长等人说:“那个钉子户并不是你们说的那样,没什么了不起嘛。见到法官就成了软柿子,大气都没敢出一下嘛。下了瓦,拆了屋,牵了猪,赶了羊,抬走了家具,他们不是半个屁都没放出来。”
郭副乡长及其他人都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那是,那是。”
“法律就是法律,谁都硬不过。”
……
那脸上的巴结,都成了厚厚的青苔。
我也没再与周伦接嘴,赶紧给所有人一人泡了一杯茶,就在旁边的一把空椅子上坐下,依旧把笑容僵在脸上。
坐在那里的周伦则依旧居高临下:“帮你们拔掉这个钉子,你们今后的工作就好开展了。”
郭副乡长说:“那是。这次你们辛苦了。先休息一下,喝杯茶,马上就开饭。”
周伦没有马上回话,而是拿起放在桌上的茶杯看了一眼,又望着我说:“小陈,给我加点水。”
又是咔的一声,心里的厌恶就快速地翻了上来。但我也只得忍着,站起来给他们一一加水。
加过,周伦说:“你怎么在这里工作?是招聘进来的?”
“唉。你呢?”
“高中毕业后去读了几年大学,毕业后就分到了夷城法院。”
“这么说来,我们那一届就你混得最好了。据说当时考上大学的就你和班长。”
周伦没有回话,脸上的旗帜则更加鲜艳。
给所有人加完水,将开水瓶放回桌上,我又望着周伦问:“结婚了吧?”
“结了,孩子都一岁了。我老婆你认识。”
“我认识?”
“就是蒋丽。”
“蒋丽?”
轰隆一声,心里所有的一切全部炸毁,所有的秩序全部坍塌,便不敢再看周伦脸上的旗帜,对郭副乡长说:“这里再没我的事了吧?”
“等会儿帮陪陪客。”
“好,我先回去一下。”说过,就大步朝外走去。
回到家,厨房里传出了田英做饭的声响,生活的足音依旧踏遍所有的空间,但它们却再也扶不起我心里的秩序了。往沙发上一坐,伤心与愤怒就将我彻底淹没:
原来,竟然是这个家伙抢了我的心上人。
周伦离去后,内心失衡的秩序才在时间里渐渐修复。那个周伦,那个蒋丽均在接下来的生活里被一一抹去,我依旧滑行在过去的轨道上。
这样又过三年,我的一个远房叔叔于这天敲开了我的房门。
一进来,叔和婶就苦着一张苦核桃脸对我说:“笑容,不好了,出了大事,我们是来求你的。”
“求我?什么事?”
叔说:“三个月前,我们被人给打了。当时我跑得快,只受了一点轻伤。可你婶却被人用镰刀和锄头把头打破了,住了三个月院。最后医学鉴定,是三级伤残。”
“谁这么下死手?”
“就是我们的邻居陈家富。”
“陈家富?都是一个族的人,怎么能弄成这样?”
婶说:“事情也不大,就为一小块山林。但现在我咽不下这口气,官司就是打到天边头,我也得让陈家富那王八蛋坐几年牢。”
“这事找我,我能有什么办法?”
叔说:“你有没有法院的熟人。”
“法院?”接着,周伦的形象就又在意识里复活出来。曾经的伤痛也开始发作。但面对被欺负的叔和婶,我只得收起我的伤痛,把脊梁弯下来,对他们说,“法院倒是有我一个同学,但我们很少有往来。”
叔和婶一听这话,苦核桃脸立刻换成一副灿烂的笑脸:“这事儿你一定要帮帮我们,出多少钱都可以。”
“陈家富呢?当时你们没报案?”
“报了。派出所也去查了。但陈家富一直逃到现在,连个踪影也没有查到。”
“好吧。我先查查他的电话,联系上了再说。”
“那行,那行。”
我便站起来走进卧室,打通县委办公室秘书科长的电话,问到周伦的电话号码,然后又挂通了周伦的电话:“老同学,你好呀。”
“哦,小陈呀。好呀,好呀。你呢?”
“还算行吧。我现在有个难事儿得求同学帮忙。”
“你说。”
“是这样,我一个叔与人发生山林纠纷,被对方打成了三级伤残。凶手潜逃,案子一直到现在都没了结。他们想通过法院起诉,这事儿怎么说也得靠你帮忙了。”
“三级伤残?”
“有医学鉴定。”
“那没问题,这事儿包在老同学身上。这样,你叫你叔直接来找我。”
“好的,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老同学,客气什么呢。”
放下电话,悬着的心也咚的一声落入了深潭,被抢夺了心上人的不快与伤痛也随着轻烟消失在了一个看不见的领域,我便对叔和婶说:“我那同学叫周伦,是县法院执行庭的庭长,你们尽管去找他。他答应一定帮你们打赢这场官司。”
“这下就好了,这下就好了。”叔和婶一听这话,激动迅速冒出来,多得连屋子都盛不下。
可是过了不到半年,叔又上家来说:“你那是个什么同学?”
“怎么啦?”
“我们给他带的猪蹄子,羊胯子,给的钱他当收的全收了,可是他只帮我们引荐了一下,之后就蒸发了,怎么找也找不到。”
“怎么会这样?我来给他打电话。”
“没用。他不接电话。”
“怎么会。”说过,我就拨了周伦的电话。
可是电话通了,就是无人接听。再拨,那头依旧无人。
放下电话,我又对叔说:“那你们可以上他家去找呀。”
“找了,没有用。”
“他说什么呢?”
“叫我们不着急。你说我们能不急吗?返还县城几百里,这样耗下去我们怎么耗得起?”
“那也没办法,只能按他说的办。”
叔再没说话,站起来无声地走了出去,只把伤心留了下来。
之后,叔再没来找过我。他们的官司也打了整整六年。六年马拉松跑下来,叔原来还算殷实的家就被一场官司给生吞了,只留下了一贫如洗的一栋空屋,还有他们无法卖出的伤心与绝望。尽管最终的判决是叔赢了,凶手陈家富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但那个判决连最起码的安慰都不是。因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没有捉拿归案。所以叔的官司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只有上帝才能说得清楚。
再后来,叔再看见我,几乎不同我说话,只有眼里的不屑堆得比锯末还厚。所以也就从那以后,我就把周伦那个同学从心里彻底擦掉,就连擦掉的刷子都不知扔到了哪个空间,根本想不起他来。
3
内心里的周伦表演结束,我的意识依旧回到了现实世界。摆在眼前的还是安放在那里的沙发,悬挂在对面的空调,站在墙角的饮水机,以及内心里爬上来的厌恶。
坐正身子,看了一眼摆在眼前的文件,文件上的文字依旧傻着眼,无法进入大脑,而意识则在自我运行:对呀,我关心法院的变化不过是意识的一个借口,其实真正关心的还是蒋丽。由此看来,这么多年过去,扣在蒋丽身上的死结并没有自动解开,而是越拧越紧了。
继续通往意识的深层,发现扣在蒋丽身上的死结并不是用恨、怨系上的,而是对蒋丽的关心。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无论当初蒋丽是怎么狠心甩下的我,还是周伦用怎样的手段抢夺了我的心上人,都显得不重要了。曾经的恨与怨,伤与痛都进入了记忆的历史博物馆,不会再对我构成任何威胁与伤害。然而,作为曾经的恋人,我却是自高中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留在记忆深处的她依旧还是高中时那个清纯、美丽、活泼可爱、小鸟依人的样子。然而我知道,现在的蒋丽显然不是那个样子了。流失的岁月肯定在她身上做过很多手脚。她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过得幸福吗?
再环视一眼办公室,发现办公室的一切都呆呆地望着我,就是不给我答案。再抬头朝窗外望去,近处的建筑和远处的天空,也都是傻呆呆的,根本无法回答我。重新敲敲意识的所有门窗: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我和蒋丽就一直没有正面相遇过呢?是不是她一直躲着我?因为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人生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我在爬格子中开辟出一条路,成了一个小作家,从乡镇调到了夷城文联。如今进夷城也是数年时间,可我就是从来没与蒋丽正面相遇过。周伦也从过去的庭长爬到了副院长的位置上,算是风光无限了。但这并不代表蒋丽的幸福。她真的生活得好吗?
然而这一切,均没有答案摆到我的面前来。重新看一眼摆在眼前的文件,发现内心里还是有许多说不清的情绪在里面盘旋着,涌动着。显然,这个样子是无法处理该处理的事情了,我便干脆将文件放回原处,拿起报纸来看。
但报纸上的文字也同文件上的文字一样,没一个字能配合我。将报纸放回报架,再翻开电话通讯录,找到周伦的手机号码,拿出手机将他的号码拨了出去。刚响了一声,意识的大门突然打开:不行,不能联系周伦。他们的法院就是装成了皇宫也与我毫无关系。便又赶紧按下了取消键。
看了一眼手机,手机很不幸,各种功能均哑着,不知道它自己犯了什么错。便将手机装回口袋里,站起来走出办公室,又扣上大门,就大步朝屋外走去。
一进入街道,喧闹的生活就强行赶走了意识里的一切,什么蒋丽,什么周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自己的生活。我便走入另一条街道,沿着清江朝家里走去。
清江照例醒着,不知道对谁风情万种。亲水平台照例鲜艳,不知道对谁脉脉含情。抬头看看天空,天空也照例无所事事,连一朵云彩也没有。我便加快步子,回家打开电脑,重新又进入了创作之中。
这样写到中午时分,开门的声音就突然切断了我的思维,我便站起来走出书房,发现妻子田英下班回来了,脸上依旧是生活的单一表情:“田英,问你个事。”
“什么事?”
“法院装修后你看见过没有?”
“我天天上班,哪有时间逛街呢。”
“法院装修得真气派,到时你上街真得好好看看。”
“再气派与我有什么相干?我又不找法院。”说过,妻子就进了那边的厨房。
望着她消失的背影,心里刚刚爬起的一点喜悦就又潜回了深处,便又转身进屋,继续进入创作之中。
新的一天不露声色地来到眼前,昨天泛起的情感没有再出现。吃过早饭,妻子继续去上班,我依旧坐在电脑前继续牵着思维进入到创作之中。就在灵感汩汩涌动,屏幕上的文字不停地跳着舞蹈时,手机突然响了。打开一看,发现号码有些陌生:“喂,哪位?”
“你是老陈吗?”
“是呀,你哪位?”
“我是周伦。昨天你打过我的电话吧。”
“哦,可能是打错了。”
“最近好吗?”
“好呀。你呢?”
“好哩。我一直说找个机会我们老同学聚一聚,就是穷事太多,一直没有机会。这样吧,我接你们夫妇到我家来做客。最近我们装修了房子,来看看吧。”
“这样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呢?这也是蒋丽的意思。”
“蒋丽的意思?”
“当然,主要是我的意思。”
“好吧。你住几楼?”
“八楼。”
“我们一定专程来拜访。”
“拜访经不起,我们老同学之间也应该常走走。我们有几年没有见过面了吧?”
“是呢,怕有十来年了吧。”
“我们在家里恭候你们。”
“好的,到时给你打电话。”
放下电话,发现创作的思维被彻底切断。望了一眼屏幕,发现屏幕上的文字都傻着眼,无法与思维接上。倒是犹豫大步来到眼前: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去吧,这个周伦不地道,他身上没有一缕气息可以与我对接。不去吧,似乎又抽不出一丝拒绝的理由。
这样等到中午时分,一听见锁扣的声响,我就赶紧从书房出来,对刚刚进门的妻子说:“田英,法院的那个周伦你还有没有印象?”
妻子脸上还是单一的生活色彩:“有呀。他不是你的同学吗。”
“是,他今天打电话接我们去他家玩。”
妻子关上大门,走进客厅,一边放挎包一边问:“去他家玩?”口气比清水都淡。
“你说去不去?”
“你去吧,我不去。”
“还是去吧。他是接的我们两个。法院能多一个朋友对我们也不是坏事。”
“那好吧。”
“你说什么时候去?”
“得等我下班。”
“行。”
妻子没再说话,转身进厨房做饭去了。
吃过午饭,妻子继续去上班,我则继续写作。一切都完好地运行在过去的轨道上,并没有因为即将见到蒋丽而受到任何影响,理性照例稳稳地站在生活的岸堤。
这样到下班时分,妻子一到家,又简单地补过妆,我们便出来打的朝法院奔去。
坐到车上,妻子突然问:“我们就空手去?不给他买点什么?”
“等会儿下车了再看吧。”
妻子没再说话。的士无声地向前滑行。车外鲜活的现实生活被一片片扔到身后。理性照例站在岸堤,激动没有泛起。这样,车到离法院不远的山野礼品店前,我便对司机说:“就在这儿停吧。”
的士无声地停下。我们付过车钱,和妻子一起步入礼品店。但在柜前站定,只看了一眼琳琅满目的礼品,思维又无法整理出一根清晰的线条了:“买点什么好呢?”
妻子没有回答我,问店老板:“酒鬼酒多少钱一瓶?”
“四百。”
妻子又转身问我:“那就买一瓶酒?”
“一瓶酒是不是太少了点?”
“还买点什么呢?”
“搭条烟吧。”
店老板问:“哪种烟?”
我说:“就把三百的黄鹤楼拿一条。”
店老板拿了酒和烟,妻子付过钱,我便提着酒走在前,妻子提着烟走在后,朝法院走去。
刚一走到法院门前,身后就响起了妻子激动的声音:“是气派,是气派。”
“我没骗你吧。”
妻子没再做声,我也没再说话,继续朝前走着。洁白的墙面、光滑的地面、闪亮的门窗,似乎都张开了欢迎的翅膀。走进一楼,发现一楼空无一人,只有正面墙上八个金色的大字“公平公正,执法如山”,对着我们信誓旦旦。每一间办公室的门都紧闭着,寂静歇满各处。显然都下班了。扫视一眼,发现一切也都一如精美的瓷器,完整、高贵、典雅,无一丝裂隙。
走到电梯前打开电梯,再进去关上门,又摁下数字8。电梯便带着我们无声地上升。站在对面的妻子望着我,单一的表情换下,补上了微笑的妆扮。
上到八楼,从电梯出来,摆在面前的并不是那种单元式的设计,而是一条长长的甬道。朝东西两边各望一眼,发现只有做工精良的玻璃漆陌生地望着我们,并没有一条清晰的线路摆在眼前:“我们该朝哪边走呢?”
“电话里你没问清楚?”
“他只说他在八楼,没说在哪个房间。”
“打电话问。”
妻子的话提醒了我,我便掏出手机,拨通了周伦的电话:“喂,老同学,我们已经到你门前来了,现在就站在八楼的电梯口,你到底是住东边还是住西边?”
“你朝西边走,第九个房间就是。”
“好的。”
合上手机,我对妻子说:“西边,第九个房间。”说过,就大步朝西边走去。
一一数过一道道房门,来到第九个房门前:“就是这儿了。”说过,我就上前按了一下门铃。
听见门铃发出了歌唱,我便退回到妻子站立的地方,与妻子并排站在一起。焊在心里的激动则从内心里的各个出口涌出来,一起在心空下聚集:想必蒋丽的变化一定很大吧。
可是等了许久,面前的大铁门依旧乌青着脸,就是不开口。
“难道没人?”妻子的声音里裹满了焦急,还有一丝的不快。
我没有回话,又上前按了一次门铃。内心激动的旁边则又站下了坚定。因为刚才才通的电话,不可能没人。听见门铃发出了歌唱,我没有再退回去。静等片刻,见门依旧没开,便又连续按了两次。
可是,时间的脚步大步走远,铁门依旧不开口。刚才站出来的坚定又缩回了脖子:“难道搞错了?”
妻子说:“绝对没有。过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一个房间数着过来的。”
望了一眼妻子,发现她的脸上倒是站着坚定。我便转回身,抬起手用力拍铁门:“周伦,周伦。”
铁门发出的吼叫比我的喊声更响。但响声滚过,铁门依旧清高,就是不开启一条缝隙。倒是身后妻子的耐心被刚才的吼叫涨破了:“再给他打电话。”
转身望了她一眼,发现她的脸色依旧还在正常状态铺展着,我只好退回来,带着我的疑惑重新返回去一道道数着铁门。
一一数过,没错,刚好是第九个。再一遍遍数回来,还是没错,依旧是第九个。我只得放下疑惑,掏出手机,重新拨通了周伦的电话:“喂,我们到了。按了门铃又敲了门,你怎么不开门呀?”
“笑话,我把门打开了。一直等着你呀。你是不是上错了楼?”
“绝对没错。电梯上的数字显然的就是八楼。”
“那这样,你们退回到电梯那儿,我出门来接你们。”
“好的。”
合上手机,我拉了妻子一把:“走,周伦出门来接我们。”
重新走到电梯口,与电梯一同站在时间里等着周伦的到来。我俩也都没再说话,甬道里只有无处不在的寂静。妻子的脸色依旧还在正常状态。只是我的激动如数潜回了,心里只有一片平静的湖,连一丝波纹也没有。
这样又等一会儿,我的手机又响了。是周伦打来的:“你来没有?”
“我们就等在电梯门前呀。”
“你肯定是上错了楼。我就站在电梯门前,这里根本没人。”
“什么?你是八楼吗?”
“是呀。”
“那就巧了,我的电梯门前就写着‘8’字。”
“那这样,你们再回到法院的大门前,我到那里去接你们。这样就不会错了。”
“也行。”
合上手机,内心里爬出的无奈,冲开了我的笑容。我无声地笑了一下。
“他怎么说?”妻子的眼里则爬满了疑惑。
“他叫我们退回到法院门前,他到那里去接我们。”说过,我就上前按了一下电梯上升按钮。
电梯没有出现意外,乖乖地升上来,对我们敞开了怀抱。
走进电梯,我和妻子一人一边靠在电梯里。电梯依旧听话,带着我们无声地下降。望着眼前的妻子,我的心里依旧是一片平静的湖。
这时,妻子突然笑起来:“你说是不是见鬼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笑容在妻子日渐衰老的脸上细细地绽开,向着两颊奔去。但它并没有带动我的笑容,也没有激活我的思绪。我也没有回话,而是抬头朝我们的头顶望了一下。
只是望了一眼,复杂的情绪就蜂拥而出了。因为我突然发现,电梯顶盖上映出了我和妻子的身影。但我和妻子的身子均不见了,只有妻子清晰的头皮盖和我的那张脸。妻子的头皮盖竟然是那么小,可怜地贴在那儿,似乎是想粘牢什么。我的那张脸则是那样陌生,似乎来自天外。他就那么望着我,眼里铺满的全是奇怪的神色。轰的一声,怜悯、虚无、恐惧等情绪就一起朝心头涌了过来,似乎还有巨大的呼啸声。
我吓得赶紧收回眼光,发现妻子没再望我了,而是在另用一只手掸她身上的灰尘。她的姿势很优雅,类似于优美的舞姿。其实这只是她习惯性的动作,那件米灰色的风衣是我们出门的时候她特地换上的,不可能有灰尘。她的另一只手里提着那条烟。烟用黑色的塑料袋包着。黑色的塑料一片黑暗,没有任何前途。我手里的酒也用黑色的塑料袋包着,照样是没有前途。
不过妻子习惯性的动作把我召回到了眼前的现实,我这才发现,刚才出现的情绪毫无道理。清醒过来的意识就又将它们一一请回各自的房间。
但随即,另一种疑惑又爬了出来:我们来见周伦本来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为什么用黑色的塑料袋包着礼品呢?还有,我们明明是上的八楼,为什么就找不到周伦呢?
疑惑还没来得及铺展,电梯门开了。我只得赶紧将疑惑塞回体内,一步迈出了电梯。
刚一出来,就又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因为突然发现,法院里涌满了人。看样子来的人非常多,一楼所有的空地全部插满了人。而且外面还有人在继续朝里面插进来。扫了他们一眼,发现他们都是普通的劳动者,穿着极为普通的衣裳。那一张张脸都被阳光和重体力雕刻过,全都是沧桑的木刻。但那些木刻脸上却正在燃烧着愤怒,个个都义愤填膺。发出的怒吼塞满每一个空隙,并在一点点榨紧,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爆炸。他们或许是乡下的农民,也有可能是下岗工人。显然是集体来找法院讨一个什么公道。
赶紧回过身望了妻子一眼,妻子脸上的惊讶也多得溢了出来。我便拉上她,奋力从人群里朝外挤去。
好不容易挤出来,刚刚在屋外的一根柱子前站定,手机又响了。还是周伦打来的:“老陈。”
“你下来了吗?”
“实在对不起,今天不能接待你了。法院里来了不少人,我现在有事要办。这样吧,我们改到下次再见面。”
“那没问题。”
“那就这样?”
“好的。”
合上手机,我拉了妻子一把:“走,他今天有事。”
妻子没做声。
我俩挤出人群,来到街上,招了一辆的士坐了上去。
车刚一启动,我的疑惑重新复活,问妻子:“你说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们怎么就找不到他的门呢?”
“先晓得是这个情况,我真不该跟你来。”
我没有回话,扭头朝前方望去,却突然发现浓雾又铺天盖地来了。接着,重雾就扣死了锁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