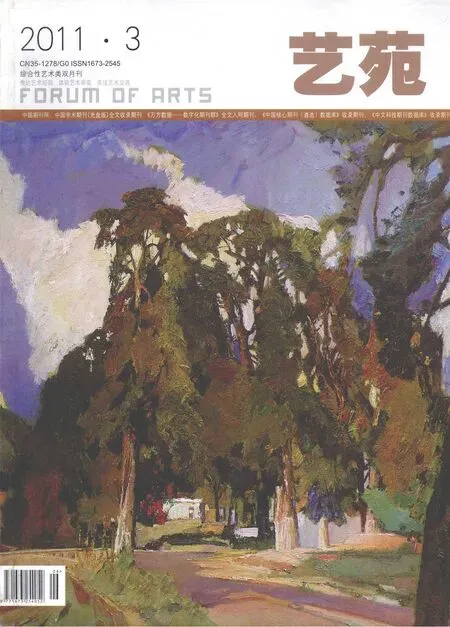遥远的回响——从《英国病人》中的“倾听”说起
文/代金存
伟大的电影都相似,但又各有各的不同。这些电影都描绘了人世间的爱与恨、罪与恶、真与善,但又因那些伟大的导演杰出的叙述及演员精湛演技而千变万化,华丽无比。英国著名导演安东尼·明格拉的《英国病人》(以下简称《英》)因其杰出的电影业绩无疑可以位列其中。
对电影《英》的评述不胜枚举,有的深入剖析了男女主人公之间凄艳绝美、让人扼腕叹息的爱情悲剧,有的深刻地揭示了战争给世间平凡众生带来的身体与心灵的创伤,有的详细论述了刻画得入木三分的人性善恶,有的义正言辞地批评了法西斯领土扩展带来的灾难,有的客观而不失公允地探讨了社会“身份”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有的科学地分析了其巧妙无比的电影叙事。这些评述都是就电影文本而展开的,较多关注的是电影文本的故事情节、叙事技巧、历史背景、社会意义等,较少从文本接受这一角度来论述。不朽的电影有其独特的魔力磁场,它会一层一层向外散射其无与伦比的魅力,每一层的捕捉都会给影评者及观众带来一次魅力之旅,而如何捕捉这恍惚不定、若有若无的魔力光环,也是一项蛊惑人心又让人醉心不已的任务。
任何一个文本都有其接受者,不管是显或隐。电影因其独特的呈现方式,即图像与声音的结合,而区别于传统的单纯文字文本、图像文本和声音文本。因文字的符号性质,纯文字文本阅读会诱使人寻找一个个能指符号后的所指意义,虽会带来思考的快感,但也难免会陷入思虑的疲乏。图像的直接呈现虽直观可感,但过多的图像犹如走马观花,留人心者恐怕是少数。当然,耳朵的过度使用恐怕也会带来听力的疲劳。电影将这些文本的优势合并,重新创造了一种可读可听的文本,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与其他电影不同的是,《英》的电影文本中有众多的“倾听者”,即在文中就是作为接受者而存在的,这些接受者对电影文本意义的生成就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它与外于电影文本的现实的接受者,即观众,共同完成了文本的意义生成。本文就这些数目众多的接受者展开分析,再一次回溯这部伟大电影在接受过程中的意义生成之旅。
电影《英》中的各主要人物艾马殊伯爵、凯瑟琳、护士汉娜、工兵吉普、卡拉瓦焦(曾经的间谍现在的小偷)之间互为倾听者,一个人的经历在对另一人的诉说中呈现。作为诉说者,是对过往事情的一种回忆性讲述,由于讲述的内容发生在过去,历尽了时间的淘沥,再加之个人性经验的累加及对事件后续性的感悟,在诉说的当时就会有情感性的流露以及掺杂一些评说。而作为倾听者,在倾听之前就有包括自我独特经历、性格、兴趣等在内的接受前见,他(她)倾听到的内容一方面可能会因为一些契合在自己心中引起共鸣,另一方面也会因为迥异于自我的经验而产生一种全新的体验。故倾听的过程,包括诉说者对过往经历情感性的体认和反思,也包括倾听者对诉说内容情感性的认同和自我经验的全新建构,是一种全新的意义生成过程。
艾马殊伯爵是影片着力刻画的一位人物。这位匈牙利贵族才华横溢,风度翩翩,通晓多国语言,钟情于历史、地理,致力于考古及沙漠探险,流连于荒无人迹的沙漠中数年之久,憎恶占有与被占有,心中没有国籍,眼中没有边界。在沙漠考察中结识了已为人妇的凯瑟琳,被其谈吐、学识、智慧及不羁的个性吸引。在交往中情愫互生,最终相恋,但各自的个性及凯瑟琳已为人妇的事实让这段情感纠结缠绵。战争的爆发,让每个人不能免于其中,得知实情的凯瑟琳的丈夫基夫在绝望之余用飞机驾着凯瑟琳冲向了艾玛殊,凯瑟琳的丈夫当场死亡,而凯瑟琳也因此受了重伤不能走出沙漠。艾玛殊把凯瑟琳留在沙漠中的古洞,只身走出沙漠寻求救援,但事不遂人愿,艾玛殊的身份及口音让盟军认为是德国人,不仅被拒绝提供救援反而将其抓捕。艾玛殊最终逃走,用自己绘制的地图在德军哪里换取飞机赶回沙漠,但时间已过去得太久,凯瑟琳已在黑暗的古洞中孤独死去,艾玛殊肝肠寸断地带着凯瑟琳的尸体驾着飞机穿越沙漠,但飞机又被误击,在一片大火中,艾玛殊面目全非、伤痕累累,也失去了记忆,最后被沙漠中游走的本地人所救送到了盟军的医院。因身份毫无,记忆丧失,他又因口音被安上了“英国病人”的名号。护士汉娜在战争中死去了爱人、朋友,她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照顾到伤者的工作中,因不想艾玛殊在转移的过程中受苦,单独将其留在战争中破旧的教堂中照料。艾玛殊用地图与德军交换飞机的举动使德军得以长驱直入地进攻,与他同时绘制地图的好友都铎因此自责而自杀,同时间谍卡拉瓦焦也因此而被德军逮捕,双手致残。卡拉瓦焦为复仇,一路寻找艾玛殊来到了教堂。而拆地雷的工兵印度人吉普为汉娜拆除了钢琴中的地雷后,也驻扎在了教堂。
战争中伤痕累累的四个人相遇在了教堂,一个拷问心灵的地方。在寂静而残败的教堂里,百无聊赖,只剩半具躯壳的艾玛殊靠注射吗啡苟延残喘,一阵风吹,一声响动,一个眼神,一张残纸,一个音符,一句问候……都会让他陷入回忆。卡拉瓦焦来到了破败的教堂,在他咄咄的追问之下,艾玛殊将往事道出。沙漠之中有他的激情,有他的洞穴,有他的地图,有他的爱情,而这一切已随凯瑟琳留在了无垠的沙漠,大火之后残存的肉身不能承载他的灵魂了。一丝游魂残存,仅以回忆度日。艾玛殊的经历在对他对卡拉瓦焦的诉说或者可以说是解释中,多了一份流恋,加了一份反思。如果说事情发生的当时还来不及感受与思考那份炽热、感伤、痛苦、迷茫,那么在对回忆诉说之时,一切都加倍地涌过来,百感交集!失去手指的卡拉瓦焦在倾听艾玛殊的诉说中也陷入了往事,他那颗饱受战争摧残已不再相信他人的心也开始有了同感:我们都是战争中的伤者。而卡拉瓦焦对艾玛殊的倾诉,也让艾玛殊陷入了对好朋友因他而死的自责中,往事又开始涌现,情愫又开始翻滚,本来已是置身于战争之外,没想到最终还是处于战争之中。
汉娜对艾玛殊朝夕相对,护理细致而周到,对艾玛殊的事情不可能不知。同是失去了爱人与朋友,汉娜对艾玛殊又多了一份感情,她为艾玛殊朗读那本与他形影不离,陪他度过生死的希罗多德的《历史》,翻阅记录艾玛殊与凯瑟琳爱情的残片。艾玛殊在与汉娜的交谈中,得知 “爱她的人因她而死”。而在艾玛殊的往事中,爱他的人也因他而死,凯瑟琳,都铎都离去了。往事在现在的生活中又在别人身上得以呈现,似乎是自己过往的翻版,现实中汉娜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提醒他那若记若忘的往事,往事中他肝肠寸断,相信现实中的他不会因为躯壳残存而痛苦减半。对汉娜而言,爱他的人都离去的现实并没有在工作中忘却,艾玛殊对往事的追忆与记录也在时时深撩着她敏感而痛苦的心灵,她不仅要在艾玛殊与凯瑟琳的爱情中深味自己的过往不幸,也要在艾玛殊与凯瑟琳的爱情中担忧自己现在的爱情。战争中的爱情注定是个悲剧,与先前艾玛殊与凯瑟琳的爱情一样,她与吉普相遇、相知,虽然没有古洞中神秘的岩画,但他们却有教堂中那些温暖而肃穆的壁画,一切那么相似,那结局会是什么呢?感受在当下的汉娜不得不想。就这样,各自在倾听中回味着过去,思虑着现在,一切的一切继续着。
电影《英》中还出现了倾听者叠加的场面。当艾玛殊向卡拉瓦焦诉说凯瑟琳如何死去的时候,汉娜也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倾听着他们。让生留于世的人来讲述爱他的人因他而死的场景是如何的残忍。有人说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生离死别。在讲述中,现实中孤苦无依的艾玛殊又一次回到了他与凯瑟琳“死别”的现场,悲痛欲绝。卡拉瓦焦在倾听中神色凝重,个人的仇恨似乎在艾玛殊巨大的痛苦中得以释怀,同为伤者,同为往事,能计较的又有什么呢?而此刻他们旁边的汉娜看到的、听到的却是两个男人过往的爱恨情仇,一个人的经历足以发人深思,如果是两个人呢?在艾玛殊与卡拉瓦焦的过往中,能左右他们的并不是他们自己,他们被残酷无情地卷入了战争,失去了爱人,失去了朋友,失去了身体,汉娜也意识到自己不能例外。个人终究压不过现实,该来的终究要来,该走的终究要走,汉娜最终还得面对当下与吉普的“生离”。
而最后,电影《英》中一切的谈话,最终的倾听者还是作为观众的我们,对电影全知全能的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又作何感想?我们是电影中每一场谈话的另外一个倾听者,虽然并非每个人都是战争的亲历者,有些想法、有些情愫还是会产生的。除了战争对人与人性的戕害之外,在轰轰烈烈的时间之流中,在广阔无垠的大地之上,标榜自由、憎恶占有、反对疆界、留恋爱情、珍惜友谊、为信仰而献身、为梦想而痴狂、为复仇而执著、为利益而争夺,这一切历尽岁月的冲洗,能留下的是什么?人类是书写着历史,还是只是历史中的残片?是人在时空中流浪,还是时空抛弃了人?是利益掠夺了人心,还是人心蛊惑着掠夺?痛苦是滋养着生者,还是埋葬着死者?战火是焚烧万物的恶魔,还是涅槃人类的火种?地图的疆界是秩序的界定,还是人心的藩篱……一切的意义、一切的哲思绵延开来,文本意义也绵延开来,这一切的呈现使电影《英》承载了无限的东西,但它又能给每一个倾听者插上飞翔的翅膀,自由地飞翔开来,整部电影也充盈起来。
电影《英》中众多的倾听者生成了文本的意义,后来的每一位倾听者又各自在倾听中回味着。毫无疑问,这带给电影《英》无限丰富的内涵,也是电影《英》精彩绝妙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