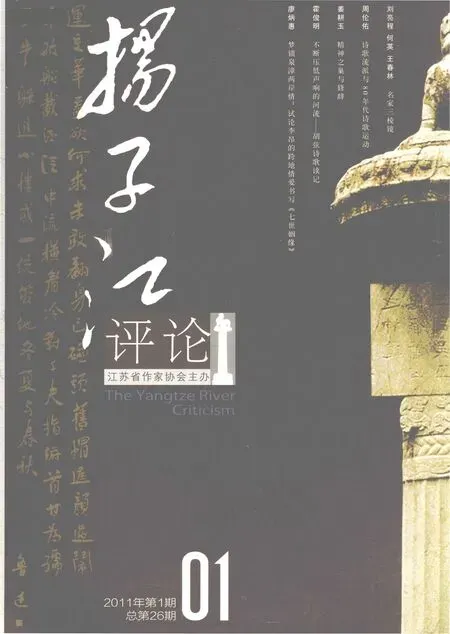“返乡”之路
——关于新世纪乡土小说中“返乡”主题的思考
刘铮
“返乡”之路
——关于新世纪乡土小说中“返乡”主题的思考
刘铮
乡下人“进城”与“返乡”贯穿了百年中国乡土小说叙事。以鲁迅、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小说作家的创作始于“进城”;1949年以后一大批解放区作家整体进城;上世纪70年代末,伤痕、反思作家群再一次掀起了“进城”高潮。如果说“进城”的动力源于乡土中国的现代性冲动和焦虑,而“返乡”则体现为对乡土文明的依恋及由此衍生的现代性误读和错位。然而,从上世纪70年代梁生宝、高家林、陈焕生等人物的返乡到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文明交错下的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农民工的“返乡”,更是体现出“返乡”在方式、广度和深度上的深刻变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的推进,现代化的诱惑和自身困境的双重牵引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背井离乡,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来到如霓虹一样光彩陆离的城市,追寻梦想。他们在城市的生活境遇被越来越多的作家所关注,进入作家的视野和表现领域。“返乡”缘何屡屡成为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重要主题,这一点颇值得思考。“返乡”一词所对应的是农民的“离地”、“进城”,即离开乡村,脱离土地,进入城市谋生,成为“城市异乡人”。①他们是城市的建设者,却难以成为城市文明的受益者。他们做着最艰苦的工作,吃着最廉价的食物,有时甚至自觉地将人格和尊严放置一边,担负着远在家乡的妻儿老小的生计——那是他们在城市生存下去的唯一动力。
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家的概念是深入人心的。外面的世界再精彩,必定不是生我养我的土地。更何况,家里有日思夜念的亲人。即使远隔千里,也要回家。然而能在除夕与家人团聚这一小小的心愿,打工者郑大宝(罗伟章《我们的路》)实现它整整用了五年,并且经过了反复的思想斗争,以舍弃两个月辛勤工作的血汗钱为代价,终于在农历的正月初四回到了家。何以五年才达成这一小小的心愿?一是回家路费对打工者来说是昂贵的,谁会舍得把汗水换来的一点血汗钱拿去做了盘缠?二是假期太短。路上耽搁的时间太久,耽误了返岗的时间老板就会克扣下欠发的工钱。于是宁可除夕孤独地在异乡熬过,也要省下钱寄给家里以维持生计,这就是大部分进城务工农民生存的真实写照。当然,也有不愿回家,被迫“返乡”的。在刘庆邦的《回家》中,矿工的儿子梁建明大学毕业后求职屡屡碰壁,又被传销组织欺骗被囚禁,最后把衣服撕破结成绳子才得以逃生。此时,只有家是他的避难所,是他期待疗伤的唯一地方;春妹(《回家的路》)为了哥哥能够继续读书,十五岁辍学进城打工。有限的文化程度和年龄问题都成为她得到一份哪怕最普通工作的巨大障碍,无奈之下只得在洗头房靠出卖肉体赚取哥哥的学费。当受骗怀孕生子后,生活更是举步维艰,无奈之下回到家乡,为的是“孩子起码能有一口饭吃”。荆永鸣的小说《大声呼吸》里,王留栓和妻子一同进城打工,然而妻子却怀了城里人的孩子。他在讨回公道的过程中,被抓进了派出所。极具讽刺的是,最后把他从派出所里救出来的,竟然正是欺负自己妻子的那个城市男人。最后王留栓和带弟只能踏上返乡的火车,城市仿佛在他身后发出着鄙夷的嘲笑,他要和妻子加速离开这里,“离开城市的火车,逃跑似的奔驰在广阔的原野上,一直向西”。这是一种对城市的逃离,也是一种对现实的无可奈何的逃避与妥协。“返乡”之路变成了一条灰暗的充满了辛酸和眼泪的逃亡之旅;李锐的《扁担》里,在北京打工遭遇车祸失掉了双腿的金堂,丧失了劳动能力,无法继续在城市生存,“硬是用双手把自己仅剩半截的身体挪回了家乡”;贾平凹的《高兴》中,五富直到死亡都没有能够回家看看,最终他的骨灰和满头白发的妻子一起被送上了火车,和与包工头顶撞后不幸摔死的贺兵一样(《回家的路》),实现了自己的“返乡”之旅。
“返乡”之路如此艰辛,回到阔别的家园,就找到避难所和栖息地了吗?答案是悲观的。梦中之乡已不复存在,梦中之人也已变了模样。贾平凹在谈论自己的长篇小说《秦腔》时,不无感慨地说:“这几年回去发现,变化太大了,按原来的写法已经没办法描绘。农村出现了特别萧条的景况,劳力走光了,剩下的全部是老弱病残。原来我们那个村子,民风民俗特别醇厚,现在‘气’散了,我记忆中的那个故乡的形状在现实中没有了。农民离开土地,那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将无法继续。解放以来农村的那种基本形态也已经没有了,解放以来所形成的农村题材的写法也不适合了。”②当郑大宝回到家乡,满眼的景象破败不堪,老奎叔撕心裂肺的咳嗽和荒凉的屋舍都使他归家的喜悦瞬间荡然无存。看到自己五年未谋面的妻子,二十六岁却苍老得好像四十岁,女儿已经长大,看到自己却害怕地叫着妈妈。末了,大宝躺在床上静静地想:“从没出过门的时候,总以为外面的钱容易挣,真的走出去,又想家,觉得家乡才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最让人踏实的地方,觉得金窝银窝都比不上自已的狗窝,可是一回到家里,马上又感到不是这么回事了。你在城市找不到尊严和自由,家乡就能够给予你吗?连耕牛也买不上,连付孩子读小学的费用也感到吃力,还有什么尊严和自由可言?”现实家园的破败加上生存的艰辛使这个汉子不得不重新踏上进城的路。春妹本以为回到家乡起码会有一口饭吃,可乡亲和家人却无法接纳她和未婚生下的孩子。一方面,家人对她一分钱都没带回来给予了无声的责备,对她未婚产子也觉得羞于见人;另一方面,受传统的中国伦理道德影响的乡村,这样的事情是大为值得“嚼舌根”的,连大宝的妻子金莲都觉得春妹不是个好女子。如此这般,春妹只得再次离乡。她回了一趟老家,再次背井离乡之后,她会以什么样的眼光和心情看待外面的世界?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未来的人生?城市会如何接纳这样一对归来的母子?她们的生活究竟会怎样?一切令人不忍想象。
刘庆邦的《回家》中矿工的儿子梁建明冒死回到了家乡,家人却惶恐多于惊喜。一直以来背负着父母的希望读书、上学,父母都希望他能通过读书来光耀门楣,跳出农门,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他们认为只要儿子读了大学,就成了公家人,以后就可以端公家的饭碗,这是他们一生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在煤矿上当临时工的父亲没日没夜挖煤挣的血汗钱全部支付了儿子高昂的学费,勤俭持家的母亲更是节省得连一个鸡蛋都舍不得吃。连亲戚介绍的女朋友都“老担心建明会把她甩了”。此时怎能如此落魄地出现在乡亲面前,又如何对女朋友交待?无奈之下,家人把他关在家里,他就像只老鼠一样,只能在夜晚的时候才走到院子里来活动一下。最终,母亲也无法接受他一直待在家里,因为村里的青壮男人都出去了,潮流就是这样,好像只要出去,就是目的,就是成功,不出去就是窝囊,就是失败。梁建明走了,他对自己说:“我再也不回来!死都不回来了……”就这样又一次踏入了城市。可以看到,乡土中国商品化、世俗化之前的数千年,乡下人进城的主要方式是“学而优则仕”,必须通过十年寒窗来谋取功名,进入统治阶级,成为人上人,达到进城的目的。时至今日,“学而优则仕”仍然是乡下人进城的理想途径。梁建明走了,成为众多城市漂泊者的一员,继续着也许和父辈们相似的人生路……“返乡”之后是更大的失落和悲伤,无奈的返乡动作之后是更加无奈的背井离乡。
现实的返乡之旅是悲伤的,精神上的还乡依然是哀伤的。在项小米的小说《二的》中,主人公小白虽然获得了在城市里衣食无忧的日子,但却深深厌恶城市的压抑感,虽然生活在城市中,她的记忆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回到乡村,靠着这种特殊的精神层面的返乡,来完成对自己所遭受的压抑的释放。离家前未曾在意过的风景在厌倦了城市生活之后,被发现竟然是那么美丽和弥足珍贵。这种怀恋带着无法言说的悲伤,那是一种回不去的不舍和依恋。这种精神层面的回归过去,还代表了主人公对当下、对城市的强烈不满。主人公只有哀伤地回忆着梦中故乡,以此作为无奈对抗现实的一种方式。
可以看到,新世纪乡土小说中虽然仍旧不乏“返乡”这一意象和主题,然而这样的“返乡”却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点。首先,与充满深情地回忆诗性栖息地和理性地表述乡土自然风貌的返乡不同,新世纪乡土小说返乡的主体是“城市异乡者”,他们的双重身份(在城市是打工者或其他职业者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以及种种差别待遇使他们在城市不可能获得归属感,因此对家的渴望更甚。新世纪乡土小说以异乡者的叙述视角来开展叙事,以期从细节和变化中,发现农民工个体独特的返乡感受。其次,返乡之旅充满了艰辛。他们的返乡并非轻松愉悦的,除了对家乡的思念和眷恋,更多的是对城市压抑的一种疏解和释放,也有被迫与无奈。城市再大,没有容身之处,城市再繁华,只能躲在繁华背后。面对城市文明的多彩与强势,他们如履薄冰,动辄得咎。当现代性以不可阻挡之势淹没了乡土文明,侵占了乡土社会的最后一块壁垒,农民触碰着、感受着新鲜的同时,已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现代性的漩涡。历来一种文明在代替另一种文明的时候,这种反应是正常不过的。只是具体在当下的中国,在以乡土文明为基本内核的中国,这种反应表现得是如此剧烈,势不可挡。这种返乡正是表达了当下中国作家集体对现代性的忧思。再者,返乡之后发现的家园缺失。不仅包括记忆中美好家园被残破的、荒凉的景象取代,还包括农民自身精神家园的丧失。乡土文明被侵蚀的结果是传统文化和精神之厦的沦陷和坍塌。如果说,以前文人式的返乡用美学和艺术向现代性的城市发难,那么农民工主题的返乡则靠的是困难和个体挣扎、人道主义向现代性的城市发难。回家之路如此艰辛,也许是社会转型期必须经历的阵痛。社会结构的每一次重要变革必将带来社会关系的改变和重组,注定要有社会成员或阶层做出利益的牺牲或付出相应的代价。就像郑大宝临走时心里对孩子讲的:“等你长大了,你就会理解,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城市和乡村是如此对峙又如此交融,我,你母亲,还有你,包括像你春妹小姑这样的所有乡里人,都无一例外又无可挽回地被抛进了这对峙和交融的浪潮之中。为此,我们都只能承受。必须承受。”
新世纪的乡土小说以近乎残酷的笔触叙述了乡下人“进城”之后身心经历的现代性裂变之痛。他们来到城市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但在离开乡村的瞬间,家园荒芜了,那片精神乡土也不复存在。回到家乡的结果是不得不再次出走,无奈的痛苦抉择形成了进城——返乡——再入城的怪圈,这是一个轮回复始的现代性漩涡。回家之路何以如此艰辛,曾经的家园今在何处?不可避免地卷入现代性浪潮的乡土文明是否会终结?这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然而农民有了差异性的进城经验,返乡后的回归也将不再是简单的回到城市的原点,和他们一起归来的还有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文明。从这一点来看,返乡之路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悲剧和苦难,裂变的阵痛与希望同在。
【注释】
①丁帆在《“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关于文明冲突中乡土描写的转型》(《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一文中提到:“农民工”是一个广义的称谓概念,它囊括了一切进城“打工”的农民,“农民工”的定义似乎还不能概括那些走出黄土地的人们在城市空间工作的全部内涵,因为游荡在城市里的非城市户籍的农民身份者,还远不止那些从事“打工”这一职业的农民,他们中间还有从事其他非劳力职业的人,如小商小贩、中介销售商、自由职业者、代课教师、理发师、按摩师、妓女等许多不属于狭义“农民工”范畴,他们比那些真正的“打工仔”更有可能成为城里人。当然,在阶级身份层面的认同上他们仍旧是属于广义的“农民工”范畴的。因此,无论从身份认同上来确定这些“城市游牧者”阶层,还是从精神层面上来考察这些漂泊者的灵魂符码,我以为用“城市异乡者”这个书面名词更加合适一些。
②贾平凹、郜元宝:《秦腔和乡土文学的文来》,《文汇报》2005年4月10日。
┝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