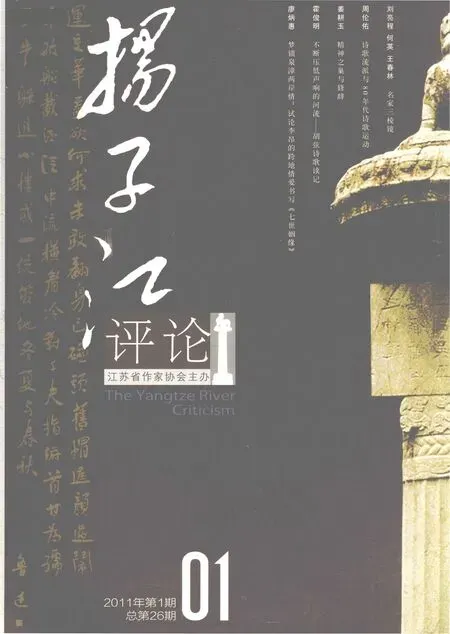边地现实的别一种思索与书写
——论《凿空》兼及刘亮程的整体文学写作
王春林
边地现实的别一种思索与书写
——论《凿空》兼及刘亮程的整体文学写作
王春林
带着一种异常沉重的阅读感觉,从刘亮程长篇小说《凿空》(作家出版社2010年4月版)所营构的艺术世界中走出来已经好一段时间了,但我却一直找不到有效进入这一部长篇小说的解读途径。虽然在对刘亮程小说的阅读过程中,我的心灵世界确实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然而,究竟以怎样一种方式,才能够把我的阅读感觉准确到位地表达出来,一时之间真的成了缠绕于我脑际的一个重要问题。一直到现在的这个标题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我才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才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可以有效进入并深入理解刘亮程《凿空》的一种路径。什么是路径?路径就是道,是“道可道,非常道”的那个“道”,就是那条只有沿着它才可能切实抵达目的地的道路。虽然说,对于“道可道,非常道”的那个“道”,学界很可能会有许多种不同的理解方式,但毫无疑问,“路径”或者说“道路”,应该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理解方式。说实在话,也真的是在找到了本文的标题之后,我才强烈感觉到了什么叫做“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如果说,是上帝之光的存在,照亮了整个世界,那么,也就可以说,是这个很不容易才被找到的标题,照亮了刘亮程《凿空》的整个文本空间。
说实在话,我之所以有机会在这里谈论刘亮程的《凿空》,并得以由此而进一步兼及他整体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我的鲁院同学、新疆籍批评家何英的力荐。一方面,或许是因为刘亮程那部《一个人的村庄》影响很大并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的缘故,所以在我的心目中,刘亮程一贯是一个优秀的散文家形象。长此以往,这自然也就成为了刘亮程的一种形象定位。另一方面,在当下时代的中国文坛,其实也还少有优秀的散文家同时也是优秀的小说家这样一种现象出现。所以,虽然早就知道刘亮程有长篇小说《凿空》出版,但内心里却一直有所排斥。当然,也就不可能去主动寻求阅读。一个偶然的机会,与何英聊到了刘亮程,聊到了他的这一部《凿空》。何英说《凿空》绝对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优秀长篇小说,要求我无论如何都要认真地读一下这部小说。何英是优秀的批评家,审美感觉非常到位,有了她的力荐,我自然会找来《凿空》认真阅读。但谁知,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只有在认真地读过刘亮程的《凿空》之后,我才明白了一个人的审美偏见会有多么要命,才真正地意识到,在没有接触文本之前就做出的判断会有多么不靠谱。正是对《凿空》的阅读,从根本上改变了刘亮程在我心目中的惯常印象。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刘亮程之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同时也还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的事实,方才得到了有力的确证。
在我看来,要想准确地厘定刘亮程长篇小说《凿空》的思想艺术价值,就必须把它同时置于刘亮程个人纵向的创作历程与同时代其他优秀长篇小说横向的坐标系之中进行相对深入的比较分析。因为此前已经认真地阅读过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于是,就又专门找了作家《凿空》之前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虚土》来读。很显然,《一个人的村庄》、《虚土》以及这部《凿空》,这三部作品可以被看做是到目前为止刘亮程最重要的三部文学作品。因此,要想较为全面地理解把握刘亮程的创作历程,对这三部作品的阅读分析,就自然是必不可少的。首先当然是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刘亮程之在中国文坛的暴得大名,实际上正是因为这部上世纪末写出的散文集的缘故,也正因此,他才获得了所谓“乡村哲学家”的美誉。在经过了已经有十年之久的时间检验之后,我们发现,当时的文学界从《一个人的村庄》出发而把刘亮程看做二十世纪末中国最后一位重要散文作家的理解定位,还是相当准确到位的。然而,在承认这种理解到位的同时,我觉得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当时的批评界实际上还是多少存在着一些对于刘亮程的误读。具体来说,这种误读主要表现在当时的人们过分地注意到了刘亮程散文浪漫诗意的一面,而明显地忽略了作家在其中关于新疆地区不无严酷的现实生活的深入思考与表达。关于这一点,我以为,只有在时过境迁之后的现在,进一步联系他最新的长篇小说《凿空》,我们才能看得比较清楚。
刘亮程之由散文家向小说家的转型,一个标志性的文本,就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虚土》。应该说,早在《虚土》出版的当时,我就已经注意到了这部长篇小说。之所以没有去阅读这部长篇小说,其实是明显地受制于自己某种审美偏见遮蔽的缘故。那就是,既然刘亮程是一位优秀的散文作家,那他的小说创作恐怕就好不到哪里去。关于《虚土》,一直到目前为止,我所读到过的最具力度的批评文字,就是何英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上的一篇批评文章《刘亮程:〈虚土〉的七个方向》①。不过,也正是何英的文章,似乎在某种意义上证实支撑着我优秀的散文家未必同时是优秀的小说家的判断。那就是,虽然同样地是以一个村庄为自己的主要表现对象,但刘亮程的《虚土》却具有着某种十分鲜明的凌空蹈虚性质。不仅如此,刘亮程的《虚土》还很明显地存在着与《一个人的村庄》的承接之处。关于这一点,何英在她的文章中曾经有过清晰的描述:“规避一切现成的知识,呈现一个直觉和心灵中的乡村世界,这应该是刘亮程主要的创作动机之一。他营造了一个与世隔绝、自然生长衰亡的奇幻的村庄。在这个村庄里,一切和谐共处,人与天地自然共生,乡村的知识和经验足够应付生活。与土地的面对面、与自然的朝夕相处使人们眼界开阔,立意高远,树叶在风中的走向、蒲公英开散的地方、一场风一般的命运、一粒沙枣花对应的那颗星星——人与自然的亲密与依赖还原到人类的童年”。然而,需要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却是到了《虚土》当中,被称作“乡村哲学家”的刘亮程,开始逐渐地背离了对于现实生活的谛视和关怀,正如他自己在搜狐网谈及《虚土》时所说:“如果《一个人的村庄》是这个村庄的大地和墙基的话,我认为《虚土》是这个村庄的屋脊,有抬升的势态。”只有在认真地读过《虚土》之后,我们才可以确认,刘亮程所谓《虚土》较之《一个人的村庄》“有抬升的势态”,其实是在强调小说更多地思考表达着某种抽象的人生哲学命题,因而也就具有了非常突出的隐喻象征意味。这就意味着,如果说《一个人的村庄》是一部兼容现实关怀和浪漫诗意的优秀散文集的话,那么,到了刘亮程的《虚土》当中,作家所延伸发展的实际上就只是其中浪漫诗意的那一个部分。虽然我们并无法否认《虚土》也是很有艺术个性的小说文本,但如果按照我自己所认同的小说更多地应该是及物的,应该以具象事物为主要表现对象这样一种艺术观念来判断,则《虚土》的艺术缺陷显然是十分突出的。所以,尽管《虚土》自有其特定的思想艺术价值,但在我看来,却并非是小说写作的正途。在我看来,只有到了写作《凿空》这样具有着强烈现实关怀特征的长篇小说的时候,刘亮程方才真正地寻觅到了小说写作的正途,方才真正地体现出了一位优秀小说家的艺术创造能力。关于这一点,只要与同时期的其他边地长篇小说略作比较就可以明显地见出。
应该看到,在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长篇小说创作热潮的持续高涨,确实有不少汉族和原住民族的作家,把自己的创作视野投向了与中原地区相比较存在着极明显的政治文化差异的中国边疆地区,投向了在这些远离中原文明的边远地区长期生活劳作着的原住民与非原住民身上。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而言,诸如阿来的那部采用了花瓣式结构的《空山》,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杨志军的《藏獒》三部曲,范稳的《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红柯的《乌尔禾》等作品,就都可以被看做是以边地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代表性长篇小说。然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从表现对象上看,刘亮程的这部《凿空》同样也可以被归入到边地长篇小说的范围之中,但从我个人一种直接的阅读感觉来说,刘亮程的《凿空》与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较,却又极明显地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说到底,我之所以会形成一种一时之间难以进入《凿空》所营构的思想艺术世界中的强烈感觉,其根本原因或许也正在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标题中所谓的“别一种思索与书写”,所欲强调说明的,实际上也正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与那些同样以边地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同类长篇小说相比较,刘亮程《凿空》的“别一种”意味究竟何在呢?在我看来,虽然以上的诸多作品都具有现实主义的基本品格,都在努力地追求着对于边地生活的真实还原与表达,但是,相比较而言,如果说其他的那些小说更主要地是着眼于文化的层面,多多少少都带有着某种文化猎奇或者说文化展览的意味的话,那么,刘亮程《凿空》的值得肯定之处,就在于,小说一方面固然也带有强烈的文化意味,但在另一方面却又明显地突破了文化层面,更多地把自己的笔触探入到了边地的现实社会政治层面,对于当下时代的边地,具体到刘亮程这里也就是新疆的社会政治状况,进行了一种堪称是刻骨真实的思想艺术表现。或许正因为其他同类作品更多地着眼于文化层面的关注展示的缘故,在阅读的过程中,便总是感觉到有一种不无浪漫色彩的诗性弥漫于其间。然而,尽管说刘亮程早期那部曾经使他一下子暴得大名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确实也是以充溢其中的浪漫诗性而著称于世的,但是,到了他的这一部《凿空》中,那样一种多少带有一点刘亮程标志性色彩的浪漫诗性却的确已经了然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我以为,实际上正是长期生活于新疆地区的刘亮程对于新疆现实生活一种简直可以称得上冷峻而又内在深刻的观察与书写。笔者注意到,对于《凿空》,实际上仍然有一些批评家,比如雷达先生,所一力强调的依然是小说的诗性色彩:“《凿空》在恢复小说的诗性建构上做了有成效的努力。好的小说有一个很高境界就是诗性,很多作家的成功都证明了他们的作品因诗性而赏心悦目。”“《凿空》也是如此,我们能感到他在表现人的一种精神向度,一种下意识的渴望,一种向未知世界索取和刨根问底的固执。”②从雷达先生的行文过程来判断,就不难看出,他如此一种结论的得出,在很大程度上是顺延着对于刘亮程散文、小说一贯的评价发展而来的。虽然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可以被称作是一种诗性的建构,但是,具体到刘亮程的这一部《凿空》,我以为,除了语言层面上的诗性存在之外,作家曾经的浪漫诗性,实际上确实已经荡然无存了。雷达先生的看法之所以没有能够抓住《凿空》的要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能够及时地注意到刘亮程小说写作其实已经发生了某种耐人寻味的变化。
就我个人的阅读感觉来说,相对于中国的小说家们普遍缺少思想力度的这样一种文学现实,刘亮程《凿空》的重要价值,突出地表现在深刻思想内涵的具备上。具体说来,《凿空》的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刘亮程以一种一般作家所不具备的非凡勇气和识力对于当下时代新疆地区的社会政治现实状况进行了足称深入的思索和表达。在这一方面,需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一方面固然是小说中关于张旺才一家与阿不旦村之间明显不和谐关系的描写上,但在另一方面,却也表现在作家关于“东突”这一社会现象的艺术审视与表现上。“东突”的存在,是一种客观不易的社会政治事实。要想全面真实地以长篇小说的艺术形式表现当下时代的新疆生活,肯定不能忽略“东突”问题的存在。刘亮程的令人敬佩之处,正在于他以一种不无象征隐喻意味的表现方式,对这一点进行了特别真实的描写与展示。无论如何,“东突”这一社会现象的出现,乃在很大程度上表征着新疆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矛盾碰撞的客观存在。脱离开这一层面的新疆书写,当然就是一种极不真实的艺术书写。应该注意到,在写到张旺才与阿不旦村民之间的隔膜时,刘亮程曾经一再强调他们之间语言的无法沟通。这样的一种发现与描写背后所潜藏着的睿智,是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于,“洪堡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生存所必须的‘呼吸’。是它的灵魂之所在。通过一种语言,一个人类群体才得以凝聚成民族,一个民族的特性只有在其语言中才完整地铸刻下来。洪堡在这里所说的语言,不是作为人类表达手段的语法意义上的语言,他从根本上把语言看作是精神的创造活动,或者说,是‘精神的不由自主的流射’。因此他强调说:‘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人们的任何想象’。”②既然语言对于一个民族的存在拥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那么,刘亮程能够抓住语言的层面来表现新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凸显出的就是作家一种特别的艺术智慧。
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意义上,刘亮程的《凿空》促使我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曾经荣获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来。或许正是因为帕慕克所置身于其中的土耳其地处欧亚两大洲交界之处,切身感受到了穆斯林文化与基督教文明之间不乏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缘故,帕慕克小说创作的一贯主题,就是对于不同文明之间文化碰撞的审视与表现。换言之,帕慕克小说所一贯关注表现的,乃是一种对于现代人而言十分重要的“文化认同”或者说是“身份认同”问题。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之所以在授奖词中特别强调帕慕克的文学创作“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只要认真地阅读帕慕克业已被译为中文的那些作品,就不难发现,贯穿于其中的一条基本思想线索,正是关于东西方文化关系深入的思考与表达。我们注意到,有论者在谈到帕慕克的小说《新人生》时,曾经指出:“把这本充满神秘奇异和嘲讽的书读到底,才明白这本幽默的书其实很沉重:主人公兼叙述者‘我’,是首先被揶揄的对象,帕慕克也在嘲弄自己,嘲弄土耳其。这个夹在东西方之间的国家,既是欧盟成员,又是伊斯兰国家,年轻人东倒西歪,无所适从;帕慕克是伊斯坦布尔的良心,这个落在欧洲的亚洲城市,恐怕是世界上精神分裂之都;帕慕克的祖父是铁路投资者,父亲是西化不成功的商人,他的家庭东不成,西不就。把《我的名字叫红》读成歌颂西化,恐怕没有明白帕慕克作为土耳其作家心中的痛苦。”④我认为,论者的这一段话,差不多可以成为阅读并深入理解帕慕克作品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可以用来诠释帕慕克的全部作品。事实上,正是因为置身于土耳其这样一个东西方文化直接激烈碰撞着的国度,所以,帕慕克才会对于“文化认同”或者“身份认同”的问题,有着如此感同身受的真切体验,并把这所有的体验都有机地融入了自己所有虚构或非虚构的文学作品之中。对于这一点,同样有着丰富小说创作经验的作家莫言的看法是极为精到的。莫言说:“在天空中冷空气跟热空气交融会合的地方,必然会降下雨露;海洋里寒流和暖流交汇的地方会繁衍鱼类;人类社会多种文化碰撞,总是能产生出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因此可以说,先有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然后才有了帕慕克的小说。”⑤这一点,在对帕慕克作品尤其是那部为作家自己所特别钟爱的长篇政治小说《雪》的阅读过程中,可以得到有力的证实。在其中,我们所强烈感受到的,正是作家内心世界中一种突出的精神撕裂感。说到底,如此一种精神撕裂感的产生,很显然只能是拜帕慕克所置身于其中的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文化地理位置所赐的结果。说实在话,作为一位长期生活于新疆地区的汉族作家,刘亮程肯定也如同帕慕克一样,感同身受地充分体会到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尖锐矛盾冲突的存在。在我看来,作家虽然很难简单地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做出优劣与否的判断,但是,能够如实地把新疆地区所客观存在着的不同民族文化之间某种严重的分裂状态呈示出来,所充分体现出的,就是刘亮程那种难得的文化良知与写作勇气。
其次,刘亮程《凿空》的思想内涵,也表现在对于新疆地区普通民众生活苦难的展示与描写上。这一点,最集中地体现在小说第三章的“艾疆”一节。在这一节中,刘亮程以一种冷静客观的叙述语态,把政策的不正常变换带给南疆地区普通民众生活的损害,极为详尽地展示在了广大读者的面前。阿不旦的村民早些年本来“只种麦子玉米,白面苞谷面掺着吃,没有钱花,也不饿肚子”。但从乡上县上来的干部,却动员农民少种粮多种经济作物,并且还给村民们主动带来了五块钱一棵的果树苗。结果到了第三年的时候,“村里苹果丰收,巴扎上摆的到处是苹果,两毛钱一斤都没人要”。到了第五年,乡上县上的干部又来了,“这次是动员农民把苹果树砍了,种梨树。这个项目是县领导在山东考察带回来的,是山东人专门针对新疆开发的新品种,说是把梨树嫁接到苹果树上,合成苹果梨,再把这种苹果梨嫁接到杨树上,产生的新品种叫苹果杨树糖心梨”。结果呢?果子倒是结下了,而且产量也还不小,但“就是嚼到嘴里没味,像嚼木头一样,不是人吃的东西”。“那以后,没人再管农民种啥果树的事情了,只听说县上几个干部倒卖果树苗发了财”。“还有一个实木家具厂,靠制作高级果木家具赚了钱”。然而,还没有安静了两年,上头的干部们就又不安心了。“这次是动员农民种棉花。龟兹以前是南疆有名的小白杏子大县,后来领导要把它变成苹果大县,变成苹果杨树糖心梨大县,都没变成,现在又要变成棉花大县”。但是,如此一种努力的结果,却仍然是普通民众的被伤害。“村里人用好几年时间,学会和接受了种植棉花。开头几年,只是当任务去完成。麦子是自己的,棉花是种给县上的。后来,村民逐渐从种棉花中尝到甜头,开始拿出更多土地种棉花时,棉花价格却变得不稳定,许多人种棉花亏本了。没吃的了”。表面上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要为老百姓谋幸福,要发展阿不旦村,发展南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实际上,却不仅构成了对于当地本来合理的经济体系的极大破坏,而且更是那些昧良心干部私利的一种无耻满足。就这样,当地普通民众本来平静自如的生活,反而被政策的不正常变换搅成了一团糟。就这样,一种人为制造的苦难,凭空地降临到了无辜的普通民众头上。在这样一种貌似平静的叙述背后,我们所读出的,一方面是刘亮程人情味十足的悲悯情怀,另一方面,则是作家对于错误的决策与主宰者一种无声然而却坚决异常的抗议与批判。
应该注意到,在对新疆地区普通民众的苦难生活进行冷静展示的同时,刘亮程也把自己的艺术思索与表现视野投注到了新疆地区的现代化问题上。在这一方面,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小说中那条非常重要的坎土曼线索。就我的阅读感觉而言,坎土曼在刘亮程的这部《凿空》中,一方面的作用,在于通过考古学家王加的出场而指向了遥远的过去历史。另一方面的作用,则是成为了刘亮程现代化问题思考的一个有效载体。小说刚刚开篇,关于石油管道与坎土曼之间关系的描写,就作为小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因素,开始强烈地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今年没人打镰刀了,从开春到现在,铁匠铺打的几乎全是坎土曼”。为什么呢,因为特别引人注目的“西气东输”工程终于开工了:“电视上天天讲这个事情的重要性,说这个工程就像铁路一样,是新疆连接内地的又一个重要通道,要求各地方各行业都要给它让路。”虽然政府并没有公开说明要全县农民都准备好坎土曼,但“从老城巴扎上传来的小道消息说,这个几千公里的石油输气管,龟兹县的坎土曼全上去都干不完,恐怕全部南疆地区的坎土曼都要上。这是靠坎土曼挣钱的一次大好机会。错过这个活,往后一百年二百年,一千年两千年,坎土曼都不会有大用处”。从此之后,对于坎土曼与石油管道建设之间的关系描写,就一直草蛇灰线隐隐约约地贯穿于文本的延展过程中。然而,令当地的农民倍感失望的却是,到头来,他们望穿秋水般地期盼着能够用坎土曼去挖石油管道的一桩大活儿,居然泡汤了,居然被大功率的现代化挖掘机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
从主流的观念来说,所谓的“西气东输”工程,确确实实是近年来与新疆有关的一个格外值得注意的大事件。无论是从新疆未来的整体发展而言,还是从促进新疆现代化的角度而言,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转换一个角度,从如同阿不旦村民们这样的新疆普通民众的角度来看待“西气东输”工程,情况恐怕就没有这样乐观了。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刘亮程借助于小说人物之口所发出的一种议论。这样的议论,出现在小说的第十章“叮咛”中。“坎土曼肯定还有活干。听说我们这里的油气,十几年就会抽空,那时候,炼油厂停工,油井关闭,井架拆掉,石油人撤走,石油卡车开走,为石油人修建的那些高级宾馆停业,跟石油来的都跟石油走光。但是,埋在地下的石油管道拿不走,挖掘机和推土机再不会对它们感兴趣,那是留给我们坎土曼的。……这些埋在地下的废输油管是石油人留给我们的最后财富。他们抽空油气,把管道留下。当然,不会白留下,会按米卖给我们。让我们自己去挖,挖出来当废铁卖。”就这样,不仅无法使用坎土曼去挖石油输气管道,而且,更进一步地说,除了把新疆地区蕴藏千年的宝贵资源挖走,除了给当地人留下一堆埋在地下的管道,从当地普通民众的角度出发,我们真看不出“西气东输”工程还给这些坎土曼们带来了什么。如果一定要说,那只能是宝贵资源的被无情剥夺,只能是自然环境的被严重破坏,只可以说是一种人为的灾难。必须看到,伴随着所谓的现代化越来越快速地向纵深处发展,敏感的思想者们已经发现了这样的一种发展思路所必然附带着的严重负面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如此一种以人类生态环境的被严重破坏为惨重代价的发展思路与发展模式,将会对于人类所赖以寄身生存的这个地球带来毁灭性的巨大灾难。正因为如此,包括文学界在内的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在以种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开始思考并传达着对于生态环境被破坏的深深的忧虑。仅就文学界而言,生态文学创作与生态文学批评,之所以能够在近几年来迅速地异军崛起,其根本原因或许正在于此。刘亮程《凿空》所具备的深刻思想内涵,很显然,大约也只有在这样的一个高度上才能够得到合理的阐释。说实在话,远在边远西陲的刘亮程,能够敏感地意识到,并且以《凿空》这样的小说形式,对于现代化的问题做出如此深邃的反思表现,无论如何都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然而,刘亮程的《凿空》对于现代化与生态问题的思考,却并不仅仅只是体现在对于坎土曼与石油管道之间关系的描写上,而且,也还生动鲜活地表现在了对于驴的问题的描述上。实际上,也并不仅仅是对于驴的描写,更准确地说,刘亮程自《一个人的村庄》以来,一个非常突出的写作特点,就是特别地擅长于动物、植物的描写表现。那些生长于边陲西域特定的主要由各种动植物组构而成的自然风景,仿佛只要一到了刘亮程的笔端,就会沾染上别一种特别的灵性,就会显得特别地摇曳多姿,就具有了一种鲜活的艺术生命力。当然了,值得特别称道的,也还有刘亮程的语言功力。曾经以优秀散文作家而名世的刘亮程,其语言的把握运用水平,在当下时代的中国作家中,可以说肯定在一流的行列之中。无论是散文的语言,还是小说的语言,都给读者一种强烈的如同已经在澄澈的清水中过滤洗濯过一般的感觉。如果用一句成语来概括,大概就可以说是清水洗尘。用这样的一种语言来描摹再现新疆地区独有的自然景物,自然能够抵达很高的审美境界,能够以其如同油画般的质感给读者留下极其难忘的深刻印象。对于这一点,雷达先生也有过到位的分析:“有时候会翻开看看,它会使人感到清凉、宁静甚或陷入沉思。也有很多作者刻意地歌吟自然、村庄、花儿、鸟儿,不能说他写得不好,只因为没有入骨的体验和超现实的灵性,没法跟刘亮程比。刘发出的靠近天籁之音。他把村庄里的风、雪、动物、坎土曼,写得很有禅意,它们仿佛都是通灵的,通神性的,但这是天然的禅意,是‘本来’,而非学来,也不是硬做来给人看的。他能在一只狗、一头牛、一头驴的身上,发现奇妙的哲理和感觉。”⑥但是,仅有语言和再现风景的特别能力,对于小说而言,也还是远远不够的。就《凿空》而言,需要我们特别强调的是,刘亮程通过他那特别传神的动植物描写,对于现代化与生态问题,进行了足称深入的思考与表达。其中,最令人过目不忘印象深刻的,就是关于驴的生动展示与描写。
阿赫姆是阿不旦村可以听懂驴话,能够与驴进行深度交流的驴师傅。“阿赫姆不出门,窗户打开听听驴叫,就知道村里发生啥事了。驴闲得很,传闲话,隔着村子传。人说话隔七八米就听不清,喊话一里外声音就飘了。驴能隔着村子聊天,狗能相聚几里地说话,黎明前的鸡叫能传到天边,把远远近近的村庄连成一片。鸡鸣狗吠的事有鸡师傅和狗师傅,阿赫姆不管。阿赫姆只管驴。”作为新疆地区最重要的动物之一,驴和人之间的关系本来是极为和谐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地方的驴,有自己的生活。驴和人过半年,驴和驴过半年。秋天里庄稼收光时,驴就放开了,一直到春播,差不多半年时间,驴和驴在一起过驴日子。成群结队的驴在村里村外跑来跑去,像野驴一样。”必须承认,如此一种传神且富有艺术魅力的关于驴的描写,大约只有在刘亮程笔下,我们才能够看得到。然而,如此一种和谐自然的驴的生活,却偏偏要被当地的决策者们以所谓的现代化的名义而彻底打破。虽然说也有专门以驴为研究对象的京城裴教授的大力呼吁,但却仍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驴被三轮车所取代的悲惨遭际。于是,也就有了那样一次可谓是声势浩大的驴抗议闹事的事件。“仿佛是约定好时间,几万头驴齐声鸣叫。龟兹河滩瞬间被驴鸣的洪水涨满。驴叫是红色的。几万头驴的鸣叫直冲天空。驴鸣的蘑菇云在天空爆炸,整个老城被驴鸣覆盖,新城的所有人肯定都听见驴叫了。驴叫声刺破县委政府的窗户,书记县长肯定都被震惊了。”“它们高昂着头放声鸣叫,驴蹄疯狂地跺地,阿赫姆感觉天和地都被撼动。天空被震碎了,太阳也不在了,驴叫声淹没一切。上万头驴的声音啊,有的往上冲,有的往下落,下落的声音又被上冲的声音顶上去,在这一切声音中,阿不旦的驴鸣最响,飙的最高传得最远,肯定从老城河滩巴扎,传到了百里外的村里。阿赫姆做了几十年的驴师傅,那一刻觉得驴是那么陌生,它们不拿眼睛看他,沉醉在自己狂躁的鸣叫和跺踢中。”只要是认真读过刘亮程《凿空》的人,便无法不承认,以上关于驴群抗议闹事的描写,正是这部小说中最传神的章节之一。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你甚至可以忘记小说中一些人物的名字,但是,小说中的关于驴、关于阿不旦村的种种动物,尤其是关于这次驴抗议闹事的生动描写,你却是无论如何都难以忘怀的。通过如此生动鲜活的关于驴的描写,刘亮程那样一种对于现代化问题的批判性思考,那样一种充满着焦虑意味的生态意识,自然也就得到了堪称淋漓尽致的艺术表现。
最后必须提及的,是刘亮程叙述者设计方面的匠心独运。在对于小说的阅读过程中,读者很可能会一直在误以为自己读到的是一部采用了一般意义上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方式的长篇小说。一直到小说的结尾部分,到了第十一章“凿空”中,我们方才恍然大悟,原来小说的叙述者是张旺才的儿子张金。只不过,此时此刻的张金已经因为出外打工的缘故变成了什么都听不到的聋子。“张金想,我一个聋子,除了老老实实呆在河岸边的家,还能到哪里去呢?在河边张金能听见驴叫。他不知道驴是否真的叫了,还是脑子里以前的驴叫声。村里毛驴已经很少了。张金在隐约的驴叫中努力回想阿不旦村的所有声音,从他出生听到的第一声驴叫开始。”“张金在家里呆了两个月,每天都在回想,在记录这些声音的故事,他从父亲张旺才挖洞写起,写到铁匠铺的‘叮叮’声,写到石油大卡车的轰鸣,写到坎土曼的故事,写到玉素甫、亚生和艾布,写到毛驴的鸣叫和那个十一月的枪声,当他最后写到父亲在地洞里喊他的名字,他知道这个由声音唤醒的故事该结束了。他也该离开了。”原来,小说隐在的叙述者张金,居然是一个听不到现实声音的聋子,而由他所叙述的这个故事,却又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各样声音的故事。聋子可以听到声音么?聋子抗议讲述关于声音的故事么?刘亮程为什么要特别设计出这样一位听不到现实声音的叙述者呢?只要细细地琢磨一下,其中的道理其实是不难明白的。应该说,刘亮程的此种设计是别有用心的。原因在于,大约只有如同张金这样听不到现实声音的人,才能够真正地沉浸在一个回忆的世界中,才能够用他自己的心灵世界去真切地体会并聆听更为内在的声音。事实上,也正是依凭着这样一位特别的小说叙述者,刘亮程才不无真切地捕捉、聆听并表现出了某种存在层面上的形而上的声音。与此同时,恐怕也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能够约略揣摩出小说标题“凿空”的内在含义来。从一种写实的意义上说,这里的“凿空”,首先指涉的,当然是小说中诸如张旺才、玉素甫他们的挖洞故事,是石油人为了攫取油气所采取的挖掘行为,也包括由王加引出的遥远历史中挖掘龟兹佛窟的行为。然而,从一种象征隐喻的层面上说,作家所欲思考表达的,大约就是一种现实与历史乃至于人生的空洞虚无化问题。
【注释】
①何英:《刘亮程:〈虚土〉的七个方向》,《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
②⑥雷达:《实力派作家的新探索》,《小说评论》2010年第5期。
③李永平:《文学的民族语境与世界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2月13日。
④赵毅衡:《因为一本书,“一生从此改变”》,《文汇报》2007年8月11日第7版。
⑤见《伊斯坦布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封底莫言语。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