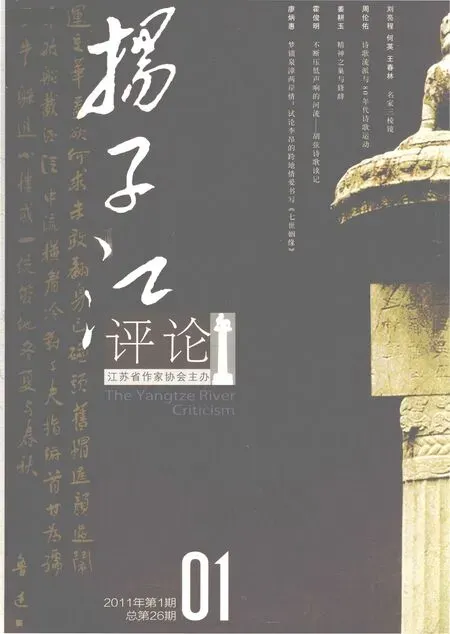精神之巢与修辞
姜耕玉
精神之巢与修辞
姜耕玉
大浪淘沙这句话老而弥新,真诗会因时间流逝而闪光。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随着人们进入全球化视野,观察汉语诗歌有了比较稳定的立足点。初期白话诗的简单幼稚,烙印般的挥之不去,这不单单是指语言形式,也表现在诗意的平面性,主要原因是诗的现代意识的匮乏与精神的贫困。而在五四新诗诞生之际,具有灵魂震撼力的大诗人荷尔德林已经谢世半个世纪。我深深为李金发的《弃妇》而沉醉,正是李氏的诗,洞开了我的灵魂之门,使我精神的树叶飘动了起来,而《弃妇》的语言,未入现代汉语的节奏和流畅,不能勾起人们阅读的兴趣。八十年代以来,具有冲击力的诗人,大多接受了西方现代诗歌与现代哲学思想的启蒙,使诗返归人自身,成为生存体验与灵魂家园之鸟而翩翩起舞。应该说,最近30年是百年新诗的鼎盛期,然而,由于没有进行过新诗的汉语修辞的启蒙或训练,在诗形上仍然尚未去掉初期诗的随意与幼稚。
解放了的新诗观不无偏颇,连海子也说过:“诗歌不是视觉,甚至不是语言。她是精神的安静而神秘的中心,她不在修辞中做窝。”①诗歌精神不在修辞中做窝,那以什么为依托呢?当然,这是海子在自杀前3个月写下的,他因困扰与痛苦,沉迷于荷尔德林的“神圣的黑夜”,以企求灵魂安宁的居所,别让修辞打扰了这种安静而神秘的居所。这是可以理解的。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语言表达的最佳状态,是带有节制的一种状态。莱辛在《拉奥孔》中主张不到顶点,他说:“在一种激情的整个过程里,最不能显出这种好处的莫过于它的顶点。”②节制,至于艺术表现,是留有空间,提供潜能发挥的可能。汉语诗歌的现代精神与修辞,虽有对抗矛盾的一面,却并非二元对立。节制,使矛盾处于一体之中,运作汉语诗性效果最佳的字词组合,营构自身体验与沉迷的精神窝巢,连同生命经验的复杂微妙及其神秘性,获得逼真的显示。事实上,诗人一旦进入诗性状态,只要沉醉于诗性状态,那么每一个汉字,就会带有精神性,带有生命经验的信息,发出纯粹的光芒。要紧的是,要有字词之间汉语智性的构成。汉语词汇或音节组合,是聚敛灵与肉的声音的过程,这种诗意构成,犹如制作成衣,是质料与精神气质的契合,也就是逼真的显示。唯如是,新诗才可能以独具魅力的汉语特色,进入全球化的视野。
虽然新诗形式不尽人意,但在阅读中,还是会被一些涉入灵魂的诗篇所震撼。比如读到昌耀、海子等人的诗时,我甚至对诗形的追求,产生了动摇。当然,精美的诗形,切入汉字音节的韵味,能够给人以阅读的快感。譬如覃志豪的《追求》:“大海中的落日/悲壮得像英雄的感叹/一颗心追过去/向遥远的天边”,诗中经典的隐喻,转化成了现代汉语音节,很好地发挥了汉字的音响,以沉缓——疾速的节奏,将悲壮的气概,抒写得淋漓尽致。不少诗虽也切入现代诗性体验,但几乎在说白话,甚至比白话还罗嗦,有些还存在明显的语法错误,这大概是缺乏汉语诗歌修辞训练而带来的遗憾。
作为诗人,守望自己的天空,写作愈个性化愈好。我欣赏新锐诗人,他们以新思维、新意象给诗坛带来生机。我敬重那些在贫困与寂寞中吟唱的诗人,真诗总是与痛苦、孤独而结缘,与独辟蹊径者同行。诗无国界,诗人不分年龄大小,衡量诗人的身份,要看他是否有创造力。失去创造力的诗人,即意味着才华凋谢,青春已逝。我看重具有冲击力的诗,不仅指诗的意义所独具的震撼力,也指想象力奇特,词语组合(音节)奇妙,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惊喜。洛夫的《午夜削梨》是一首写实的诗,诗笔奇特犀利:“刀子跌落/我弯下身子去找//啊!满地都是/我那黄铜色的皮肤”,谁能在削黄梨皮时想到自己的皮肤呢?即使想得到,也不会这么写,然而洛夫敢,直逼人的感官,写出疼痛感,并表现得如此水到渠成,令人叹服。词语这般纯粹而到位,不可复制,是诗人艺术冒险所致。古代诗歌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语),达到入很严的格律却自然之至的节奏效果。现代诗歌词汇组合的陌生化,也不能不讲究语言的凝练与现代汉语的音节,只是侧重于感觉的语言与修辞效果。孔孚的“佛头/青了”(《春日远眺佛慧山》),“一颗心/燃尽”(《戈壁落日》),两个隐喻性词语,一锤定音,余韵袅袅。诗人竭尽心力,把汉语诗意锤炼到这一境地。诗人的创造力,表现为对汉字的驾轻就熟,每一首诗,都给人以新异感,带给读者一个惊喜。
我们不可一律在诗的意义的层面上要求诗,还要看是否别具一格,独具诗的情趣、意趣、理趣、谐趣等,这集中透视着诗人的灵气。如匡国泰的《一天》,以12个时辰为题,以湘西山村生活为意象创造的资源,既有地道正宗的民俗趣味,又表现了超凡脱俗的境界。“乡土风流排开座次/上席的爷爷是一尊历史的余粮/两侧的父母是如秋后的草垛/儿子们在下席挑剔年成/女儿是一缕未婚的炊烟/在板凳上坐也坐不稳”。首先是诗歌比喻的民俗意趣与乡土神韵吸引读者,然后才有兴趣悟出在这隐喻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关系的表象中,几乎包容着每个人的现存位置。中国汉字的排列艺术,也拥有诗意发现的可能。台湾诗人白荻的《昨夜》,则力借汉字叠合式排列,渲染诗意效果,原属繁体字竖排,效果更佳。新诗形式仍处于探索与健全之中,期待有识之士做出更多的尝试。
21世纪,新诗告别了政治思想运动,回到自身的位置,呈现着无序生长的可能性。因此,不可以“潮”论诗,不可以“潮”写新诗史,只有走出以“潮”论诗的圈子,才能看到新诗生长的全景。诗及文学思潮,总是与一定的哲学潮流紧密联系着。在80年代,朦胧诗或新诗潮是随思想解放运动而兴起的,朦胧诗对新诗坛发生了强大的辐射力,北岛们的诗,至今读来,仍令人亢奋。90年代,告别朦胧诗即意味着告别了诗潮。新诗与中国文学,在中西文化的撞击中进入全球化语境,这是冰河消融、大海与川流之间消长互生的过程。海子、昌耀、杨炼、西川等,即是获得这种诗的自觉的创造个体,因而他们留下了不朽之作。而那执意要把诗推向极端的诗,不可避免地带有先天不足,他们的才华被弄“潮”的亢奋所消耗。
值得关注的,那些远离诗坛,在贫困寂寞中写作的诗人,如老乡、姚振涵等,还有70后、80后的年轻诗人。他们那真诚的作品,给诗坛增添了亮色。老乡的诗独得西部风骨,“长城上有人独坐/借背后半壁斜阳/磕开一瓶白酒一饮了事/空瓶空立/想必仍在扼守诗的残局”(《西照》),真正使汉语字字铿锵,个个立在纸上,展示了空阔苍凉的诗意人生,颇得中国侠客精神之壮美。另一首《黑妻·红灯笼》,以带有善意调侃的通俗口语,低诉糟糠之妻一生的悲苦与善良,却抒写了中国一代妇女的悲情。姚振涵的乡土诗,像庄稼的茬子一样简朴,却于简朴中见纯正。《在平原上吆喝一声很兴奋》,写一个人走在田间小道上,不由得吆喝一声,“那声音很长时间在/玉米棵和高粱棵之间碰来碰去”,在青纱帐割倒的九月,“声音直达远处的村庄”,诗人的这种“幸福”感,诚然带有农民的自足,而给予读者更多的,则是返归乡土、返归生命家园的感觉。丁庆友祖祖辈辈生活在黄河岸边,凭对农民与土地的真情实感,才会有《望一片玉米眼睛里就有泪》,唱出“每一片玉米/泪眼里/一棵是爹/一棵是娘”的传世之句。
70后、80后有一批诗人,走出了新诗写作的怪圈或与大众隔膜的围墙。他们的作品,像是自生自长起来的,虽然还不成熟,但语言朴素清新,使自身生存状态和瞬间情感获得简洁的逼真表现。如朱剑的《磷火》,由坟茔磷火而想到人的骨头里有一盏“高贵的灯”,使这首诗不同凡响。“许多人屈辱地/活了一辈子/死后,才把灯/点亮”,以对人性弱点的批判,使诗具有对灵魂的震撼力的普遍意义。黄春红的《记忆》:“祖父和父亲的村庄/我摘下的野花变成了诗句//野鹅和妇女的河流/我和鸟群低调的飞过//银色的雪,蓝色的雪/天在慢慢变蓝”,这首诗把祖辈的村庄写得很美,“蓝”显然是对自由美好的憧憬,似有现代桃花源之意。女诗人富于想象,取得了独有的汉语修辞效果。从前一首找回人的尊严的企图,到后一首的“蓝”色畅想,标举新一代诗人所具有的现代诗歌精神。
【注释】
①海子:《诗学:一份提纲》,《海子、骆一禾作品选》,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
②[德]莱辛:《拉奥孔》,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页。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