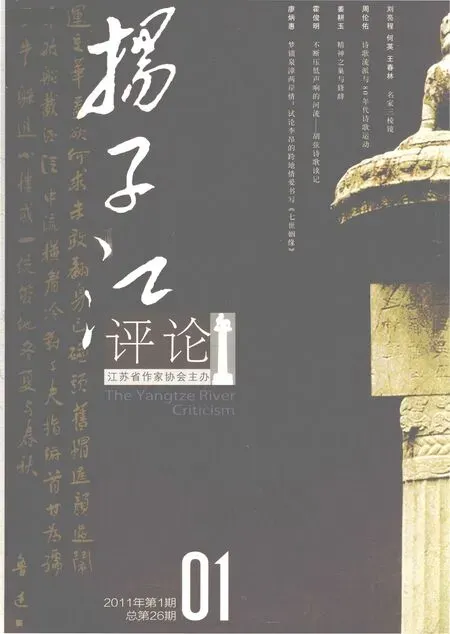“诗歌史”的浮躁
黄梵
“诗歌史”的浮躁
黄梵
1、诗歌选集与诗歌史
撒谎已被广泛用于治当代史,只要在逻辑上说得过去,哪怕它不真实。因为如果照实直说,就会毁坏和谐的人际关系,一些人就觉得这类著述是行恶。如此深入中国人骨髓的和谐观,几乎指导着一切评论与当代史类著作的写作。这类“操纵”自如的结论,传递到新一代那里,就充满需要厘清的荒谬。就是说,我们饱经世故的评论,不是在激励创造,是在给下一代制造麻烦,供应着障眼法。如果我们能如饥似渴地查找真相,不难发现,不论一个诗人的作品是好是坏,作品总是真实的,但谈论作品的评论,若不公允合度,它就成了魔鬼。魔鬼当然都会以善良的面孔出现。我开头说的“治当代史”,是一个含义丰富的词,追得上诗人的想象力,它包括诗人为把自己添进诗歌史,做出的一切诗外努力。无需太多敏感就能发现,与“治当代史”相关的种种努力,正如百花绽放,与过去相比,真是茁壮丰茂。比如,故意找茬骂人,或乐滋滋骂来骂去,给自己颁奖、逐奖或买奖,党同伐异,把写诗变成入史的搏斗,用利益诱使学人做不智之事……历历可见的浮躁,是否由一个源头问题导致?它到底有何法力,竟让这么多人像热锅上的蚂蚁?莫非一个诗人声誉的起落盛衰,与他对“治当代史”的投入密切相关?
我想窦士镛在1906年写《历朝文学史》时,不会意识到他撰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会为后世注入这么多的浮躁。我们应该留意,窦士镛为中国文学写史前,中国历来没有文学史的概念,中国一向只有作品选集和名士传,这是中国文学传统与西方文学传统的不同,从中可以窥见许多珍宝。比如,它基本排除了作品之外诸如运动、流派、思潮等干扰,因为由众口拼凑起来的作品“背景”,往往会产生与甄别作品背道而驰的作用,甚至会使读者一时失去判断力,毕竟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另一个魔鬼——从众心理。这是每个人都害怕投入孤独怀抱的本能反应。可以预计,只需大肆渲染运动、流派、思潮等的历史价值,那个使人头晕目眩的魔鬼,就会从我们心底释放出来,令我们不再追随作品,教我们把作品之外的“伟大”硬塞进作品。好在不管“背景”如何璀璨,中国古人只乐得看作品、比较作品,他们懂得一首诗的伟大,会使一切不实的“背景”渲染,显得拙劣,最终毫无用处。如同不管达达运动多么有魅力,当读到巴尔那首只有声音没有内容的诗,我不会被他的作品“奇迹”打动。西方文学传统把达达派置于这样的境地:他们声名显赫,却没有受后人青睐的作品。“背景”声誉与作品声誉的分离,是西方文学传统乐意包容的乐趣。相反,若是把达达派置于中国文学传统,千年诗歌选集就会拒斥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受此惩罚,不是因为新,是因为与其它入选的作品相比不够好。中国古人的这一招数非常管用,它使类似我们当代的种种“背景”炫示,立刻变得无用。也就是说,一旦以作品为中心,一些诗人最引人注目的东西,那些由歪门邪道导致的璀璨,倒成了深藏难窥之物。比如,古代所谓“四杰”“四家”之类的说法,不是诗人自我认证的产物,是后人通过作品比较作出的判断。入选“四杰”“四家”难于上青天,作品技压群芳不说,人品还要有口碑,因人品顽劣被逐出“四杰”“四家”的比比皆是。例如,陶渊明因品性高洁,后人倒先在名士传中注意到他。事实上,藉着作品选集,中国古人为后人提供的是作品史,而不是良莠杂存的诗人史、运动史、思潮史等等。在古人讲究阅读享受的文学传统中,若是有人想出版一部新诗选集,大概不会选录胡适或郭沫若的作品,理由相当简单:古人不在乎谁是先驱,只在乎作品是否好到有资格入选。
窦士镛的文学史概念,当然来自西方,他以此重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同时,自然使该概念携带的大量“诗外”杂质自西方涌入。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源头,自此全神贯注围绕作品的一切,成了文学评论的常规动机。由于文学史着眼重述文人的历史,这样作品之外的杂沓奇景,就纷纷挤入了文学史。一旦文学史不能忘怀作品之外的东西,一些诗人或批评家便懂得利用它们来谋利。以新诗为例。为理解新诗的来龙去脉,就必须给胡适或郭沫若等先驱以崇高的诗歌史地位;一些当代诗人的争吵之所以变得有趣,是因为一些学者觉得它们能改善苦行僧似的作品史。这是忽略诗歌的最高价值,让诗歌史变成一本传奇读物的做法。究竟是谁需要这样一部诗歌史呢?当然不是读者。我若是千年以后的读者,当然不想费时在一堆垃圾中苦苦寻觅好诗,只希望找到好的选本,能马上领略好诗的美妙。我们对唐诗选本的兴趣高于对全唐诗的兴趣,即是一例。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难看清,诗歌史是属于学人或某些诗人的特殊兴致,它在当代的兴旺,与大学学术有关。出于学术需要,老师和学生对诗歌的长成,比对诗歌本身更有兴趣。以为窥见到它的长成规律,以为藉此可以趁机入史的人,他们强加在奖项、批评、当代诗歌史著述中的躁动,我就不逐一累述。可以说,当代诗歌治史的轻易和低门槛,造成许多诗人也把大量精力投入其中。
我认为,不是西方文学传统太富人性,也不是中国文学传统太难通融,是两者想覆盖的历史时段不同。大致来说,西方传统采用的是百年以内的微观视角,它忠实地用放大镜观察每个历史细节,这样它会在平淡无奇的作品史里,添加丰富多彩的诗人史、思潮史、流派史等内容。中国传统则把注意力放在百年以上,它试图接近恒久的宏观认识,它尽可能舍弃与诗文本无关的东西,这样遭遇诗文本的后人,由于他已“忘却”历史,他的无知中便包含着可贵的“重新发现”。历史环境变了,却能经得住“重新发现”的诗文本,自然就更接近恒久的杰作。陶渊明被后人鲍照、萧统重新发现,李白、杜甫被宋人真正看重,即是一例。可以认为,西方传统一般百年有效,而中国传统企图抵达千年之识。不过在千年尺度上,一本简明西式诗歌史的束缚力,等同于一本中国古代诗歌选集。因为在千年宏观尺度上,文本力量会真正突显出来,相反,隶属运动、流派、思潮等的奇效,会因为后人兴致寥寥,而变得微不足道。当然,中国传统也有西方传统达不到的细致。比如,中国诗歌选集不会忽略只存一首好诗的诗人,而沉溺于诗歌史游戏的西方传统,会把只存诗一首的诗人,视为微不足道,从而在西式诗歌史中不会见到他的面孔……我们目前已到一个关口,应该看到——中国古代诗歌选集有了不起的治史功效,它虽然根置于问题百出的制度,却着眼于宏观远景,能确保它长久有效;西方治史方法之所以在西方有效,在于它能用学术诚信抵消巧谋深算,这是基督教环境决定的良性心态。一旦摒弃信仰环境,只是简单移用西方治史方法,我们便会尝到它带来的躁动苦果。所以,不是我们该从近处还是远处观察诗歌的问题,而是目前的西式治史方法已成了诗坛躁动的源泉。我认为,把中国传统安排进新诗治史的视野,用诗歌选本的方法证明一些躁动的无效,把学者和读者的视线从吵闹不休的诗歌史,转向安静自重的作品史,我们就能创建另一种更智慧的新诗治史传统。一个选本若有不该入选之诗,或编者故意想排斥什么,明眼人或后人都能感受得到。我手头有十种唐人选唐诗的选本,一些选本的可笑便昭然若揭。不同选本会在不懂当时文学政治的后人那里相互竞争,只有善于规避遗憾的选本才会获胜。比如,《河岳英灵集》突出于其它唐选本,宋选本突出于所有唐选本,即是一例。想用诡辩来证明选本的合理是徒劳的,毕竟一言不发的作品会昭示一切,但诡辩在诗歌史著作中只会一时有效。
2、士的精神
当前一些诗人在误述知识分子精神时,我倒更愿意谈论士的精神。就独立、气节、操行而言,两者想避开的东西都差不多。记得有一天,我路遇一个久未谋面的诗人,他刚参加完作家会议,他突然向我感慨:“都说文人骨头硬,我看文人骨头最软。”他的看法其实一点不孤立,与曾在许多乱世拯救过汉文化的士的精神相比,当下诗人骨头发软的例子真是比比皆是。当代一些诗人之所以不堪一击,我认为不是个人言行的问题,是诗界缺了一种精神氛围,这种精神氛围是一面镜子,能照出一个人内心的不堪。是的,曾弥散在古代社会的士的精神,在我们的环境中已经化为乌有。士的精神在古代社会起的作用,大致与西方基督教中的正义、民主,以及文艺复兴萌发的张扬个性、自由等精神相当。它成了古代中国贮存高端文化和良知的庇护所。正是士的精神,令黄公望五十过后归隐山林,不指望靠《富春山居图》名传后世;令陶渊明不去追逐玄言诗或唯美诗的显流,而把诗歌引向更合性灵的抒情。对于他们,艺术创造的体验,是一种基本的修行,与围绕“史”的所有杂念无涉。士的精神使他们避免成为利益的俘虏,使艺术免于受功利之害。元代画家坚持以卖画为耻,即是一例。不能说元代文人画的伟大,与士的精神在元代极其蓬盛无关。纵观历史,士的精神在古代皇家的院体之外,不靠刻意选择,只靠民间口碑,贮藏和创造了古代中国的大部分杰作。民间口碑筛选之严,完全不受官阶或翰林院等级的干扰。比如,宋之问位居唐修文馆的最低一级,但存诗多于第一等级的人……士的精神同时反衬出我们与西方关系的缺陷。我始终认为,西方文化是一个整体,试图只输入西方治史方法,不输入西方治史精神,注定与清末洋务派的做法如出一辙,必败无疑。西方治史精神,说白了就是知识分子精神,是一种对现实存疑的精神,哪怕寡合也要接近真相的精神,可以说是魏晋隐逸、贤士精神的变体。有了它,我们就不会说、写、做自己都不相信的事。谎言无非是靠我们害怕孤单的心理起作用,它在当代必须靠恩赐利益才能维持,由于它无法贿赂后人,自然难在后人那里继续获得成功,早晚会破绽百出。所以,恢复和养育士的精神,在当下应该成为我们心灵的重大课题,它是打破诗坛不诚实的奖项、江湖义气、长官意志、逐利行为、入史渴望等等的精神利器。当然,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庸俗之人变成士,除非他体察到士的精神是他内心之必需。
3、言清行浊
当下还有一种能为谈话注入虎虎生气的虚假,就是我们都能用谈话来营造求真的迷人氛围,可是一旦自己行动,就没有了谈话中的那些美德。就是说,只要谈起人的修为,都喋喋不休,不知疲倦,仿佛自己占据着美德的制高点。无论评价这个或那个诗人,嘴上都挂着修为的最高标准。不必奇怪,此人一旦行动,他所做的一切,可能正好是他谴责的一切。我曾经想用一个词概括这个现象,久觅不得,一天突然从旧书里遇到这个词——言清行浊。行了,它足以说出我想说的东西。当我把这个词告诉友人何同彬,他也诧异这个词的洞察力。看来,潜伏在我们内心的这个恶魔,古已有之。为什么人在谈论时内心特有律条,一旦行动则毫无自律呢?我认为,根源在于我们身边的“两层皮文化”。中国当代文化由两层皮构成,一层真皮一层假皮。吊诡的是,我们在公开场合抖搂的都是假皮,假皮供应的观点一般都十分悦耳,都是冠冕堂皇的真理、美德等等。由于这些观念在当下社会,缺乏对应的生活经验,比如,谁若在当下生活中坚持这些美德,他注定会四处碰壁,成为精神孤儿。这样一来,多数公开抖搂假皮的人,为生存所迫,便会悄悄用另一张近乎本能的真皮,去图谋利益,不管它在道德上多么粗野和刺耳。没有了传统“言必行”的束缚,没有了冒死进谏的士的精神,那张供应着人类全部欲望的真皮,便成了裹住我们心灵的汪洋大海。是的,当社会现实造成观念和经验的分离,同时向所有人供应着截然相反的两张皮时,“诗人何为”的问题,就只成了少数诗人的苦恼。在我看来,置身于这样一个魔性环境,与其对一个诗人的行为敲敲打打,不如有人带头有所不为。一个对某些事有所不为的人,说明他心中有与众不同的诫律。比如,正是陶渊明的多次辞官,昭示着他卓尔不凡的品性。所以,昭示人品性的不是有所为,而是某些特定时刻的有所不为。
4、圈子批评家
西方学者有过一个总结,认为批评兴旺之时,恰恰是作品衰落之际。他们提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作为希腊戏剧衰落的证据。如果不怀疑这种说法,那么当代诗界批评的乱象,倒反证出当代诗歌创作的蓬盛。不是说没有好的有开明作风的批评家,当然有,但他们为数甚少,难以影响整个诗界,这样,我们感到喧嚣的批评之声,多数来自“圈子批评家”。“圈子批评家”并非我们时代的独创,前辈中已有成仿吾等先驱,他们向我们供应着一种意识,即除了他们自己所在的圈子,其它圈子的东西都无足轻重。在圈子批评家看来,对当代诗歌的评价非常容易,它不过是一个权力问题。多年苦心经营得到的权力,马上可以在改变他人的观念上收到效果,使圈子内的诗歌成为命运的宠儿。我曾说过“观念可以改变感觉”,但,是不是观念一变,真的就处处皆诗呢?当然不是,凭借智慧,观念可以让我们放弃本能的感觉排斥,接纳一开始不喜欢的趣味,使我们有机会去接触诗歌的全貌。观念打破的是感觉的排斥。不过感觉并非不会“思考”,感觉对形象、修辞、结构、层次、声音等的敏感,使它会排斥同一趣味里的愚蠢和空洞之作。就是说,感觉依旧会在同一趣味里,捍卫品次高低的分类。彻底依赖观念来拯救劣作,缺乏长久的人性根据,理所当然会最终失败。所以,圈子批评家与中国当代只知道诠释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没有两样,他们提供一系列所谓的依据,本质上是干扰了对诗歌真相的认识,他们以为哑寂的真相抵不过高亢的批评之声。但是且慢,近年因教书,我重读过成仿吾的评论,记得没多久,我就体察到他要拔高同人的心境,接着我看清了他下笔时的隐秘动机,说真的,我对他勇而不智的文章一下失去兴趣。只消几十年,他的破绽就历历在目,对那些落笔于纸上的当代批评家,真是一个不小的前车之鉴。后人一样会运用全部本领,来审视我们的文章,一旦瞥见不洁的动机,一样会毅然弃我们而去。我认为批评的活力不在于文章多寡,无论新添多少文章,都不如诚实更能令批评有效和兴盛。难以估量,机智的撒谎已给诗坛造成多大的混乱和伤害。我只期待能出现更多诚实的批评家,靠他们打破诗界人为的精神割据。毕竟,笨拙的诚实与机智的撒谎相比,更能赢得明眼人和后人的尊敬。
5、“废纸篓诗歌”
本来发表是这样一种文学安排,它既要向水平高的读者证实编辑没有看走眼,也要向水平比作者低的读者,提供具有吸引力的摹本。由于这类摹本在回应当下意识方面,比过去的杰作更有新鲜感,它们就成了部分读者眼中文学仲裁的结果——它们的水准最接近过去的杰作。读者藉此可以跟踪进入当代诗人的诗艺世界,诗人最新的探索之作能成为读者欣赏和学习的对象。比如,诗歌仲裁在杂志社进行时,会产生大量的“废纸篓诗歌”。编辑因感到自己处于诗歌史的末端,便会尽力谋杀与杰作水准相去甚远的作品,把它们驱入废纸篓。废纸篓就像诗歌孵化器,作品不去除稚气,读者永远别想见到它们。我因有过在《扬子江》诗刊做二审的经验,知道“废纸篓诗歌”的数量真是大得惊人。知道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一旦提升自然来稿的用稿率,杂志质量必会下降。我认为“废纸篓诗歌”的恶运,是过去诗坛智慧的一部分。不过近年,情况大变,随着太多的诗歌版面和杂志问世,过去寸步难行的“废纸篓诗歌”,突然间赢得发表的机会,藉着冒出来的众多版面,“废纸篓诗歌”改变了发表诗歌的性质。当任何水准的写诗者都能发表,说明诗界已经走到了诗歌的反面。导致普通读者值得学习的对象,已经深藏难觅。太多的庸常之作,已把所有诗歌版面覆盖起来,以致需要学诗的读者,已辨不清哪些是高明的诗作。有时,这真是嘲讽,一些诗还没写上路子的人,就侃侃而谈写诗的经验。若在过去,我们只好去杂志社的废纸篓里捡这些人的作品。于是我悟出,发表在当代正在对诗歌施加负面作用,它在普及诗歌的同时,实际在给批评和鉴赏添乱,给批评施加说奉承话的巨大压力。常常,有的批评家真那么说了,在容忍肤浅和幼稚方面,有的批评家真是有雅量。这些在诗歌版面安定下来的浅薄之作,许多就成为羡慕发表的读者,充作学诗的样本。于是,就出现一个怪象,新加入写诗的人群,很多在学那些速朽的浅薄之作,只因为它们上手快,可以堂而皇之在诗歌版面发表,沽名钩誉。发表竟成了挡住读者视野的高墙,成了把民族的后续智力引向速朽之作的功臣,实在有违杂志或诗歌版面创办者们的初衷。他们有心给现代汉诗一个美好的前景,但忘了一个基本法则:好诗的数量不是无限的。说得确切点,每年全国的诗歌版面足够发表二十万首诗,为要填满版面,只好发表大量的平庸之作。这就产生了由数量决定质量的怪象。对于已经写出好诗的诗人,人们只对他能否继续写出感兴趣,继续写出是他作为诗人的唯一证明,哪怕他已力不从心,只是用像诗的东西填满纸页。一旦不再写诗,人们干脆就忘了他,干脆不提他曾有过的美妙之作。继续写的另一层含义是,人们懒得对诗作本身多加注意,只注意一个诗人在各种版面的出镜率。一个诗人维持着声名,不是他每首写得好,而是他写得多,不停地写可以使他克服被遗忘的危险。可以相信,一些诗歌版面对诗人的追逐,也导致一些诗人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灵感。我认为,在人们对单首诗的关切度越来越低时,在发表已演变成诗人“还活着”的证据时,维持诗坛秩序与道德的批评家们,应当通过批评来使单首好诗的价值获得应有的承认,以此检讨我们对数量的迷恋,同时看到我们当下思维与大跃进思维的隐秘关联。最近我发现,沈苇主编的《西部》已经在矫正这种数量意识,他用“一首诗主义”来抵御灵感受到的数量威胁。所以,在把新诗变成我们新文明的过渡期,我们应该充分估量诗歌普及与诗歌探索的不同需要,诗歌的传播不应以牺牲水准为代价。我们既要懂得传播属诗之必需,也要警惕它会把诗歌的视野弄得很狭窄,因为在缺乏士的环境中,传播倾向于瓦解诗歌与诗艺的关联。明清士人早已寻出一条防范市场力摧毁文化的法则,那就是把品味作为基本的指导原则。假如现状真可以改变,我倒希望出现大量关注品味的普通鉴赏杂志,和为数不多的高水准探索杂志。我们应当放慢“见到杰作”的速度,对杰作的承认越严格,就越能把新诗推向大家期待的方向。
6、政治思维的痕迹
政治在当代汉诗中的位置,虽然已经被审美取代二十多年,但政治思维的痕迹仍以各种方式,显露在批评家和诗人的作为中。这里我只想阐述两种思维痕迹,一种是大跃进思维,一种是“文革”思维。一些人希望快速产出或甄别出当代大诗人,认为靠评奖、投票评选就能选出大诗人,靠基本的路线设计就能造就大诗人,靠多写就能成为大诗人,恕我直言,这是政治思维习惯导致的作为,它的下意识源自大跃进思维。大跃进是用激情、神话、意志淘汰理智、真相、客观的范例。隐在这种思维后面的人,一般会这样构想当代诗坛——当代有产生大量大诗人的无限可能,只要打破某种成规陋习,当代就能成为史上罕见的伟大时代。这是前个时代遗留给我们的颂扬恶习,是政治思维污染诗坛的结果。既然庞大的诗人群中隐着不少大诗人,为了及早发现他们,一些人就忙于通过投票、文章来进行遴选、推荐。无知的公众当然也期待能有大量的文化卫星上天。我说这类行为带有政治的性质,是因为任何奖项、评选、推荐都只涉及我们时代的审美,企图只以一个时代的审美,来支配“大诗人”的称谓,无异于夸耀本时代的审美胜过未来的所有时代,这不过是“抑古扬今”政治思维的翻版。其实,给谁戴“大诗人”的帽子,不是单属于一个时代的“小事”,“大诗人”至少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时代的验证,我们应该懂得,最擅长把握此称谓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时代,中国古代史学向来强调“隔代写史”,旨在消除一些歇斯底里的主观气息,能令事实、真相脱羁而出。六朝体认的诸多“大诗人”在后朝消失,即是一例。别林斯基做批评之前的俄国,也弥散着“大师”林立的亢奋,他做批评的结果是,前朝在他眼里只剩下普希金、果戈里……由于“大诗人”是一个复杂而丰沛的历史概念,我们不必用自己时代的软肋去触碰它。值得我们留意的不是给谁什么称谓,而是当现代汉诗正在发展时,尽量不去做不可原谅之事,即眼看着少数好诗被大量垃圾淹没。弥尔顿当年呼吁建立观点的公开市场,他认为真理最终会在自由竞争的观点市场获胜。同样,我们应当建立诗歌选本的公开“市场”,让各种选本在后人那里自由竞争,把我们力不从心的找“大诗人”的事,丢给后人去烦心。尽量按照个人真实的审美感受去编辑诗歌选本,才是值得我们时代颂扬的诗歌善事。后人将会根据这些诗歌“文献”,甄别出真正的大诗人。当代诗坛另外还深深浸染着“文革”的“斗争”思维。它表现为党同伐异、相互攻讦、辱骂、置对方于死地等等“文革”积习。斗争思维的本质,是对现代性明显的不适应。斗争是逼迫对方认同“唯一真理”的手段,隐藏在它背后的是一元思想,即认为只有一种思想能揭示真理,除此,真理再也无法在别的思想中显形。一元思想来自专制的农耕社会,它企图创造稳定社会的威力,是一种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远离现代社会的思想。而把对峙变为多元并存,恰恰是现代性的本质和兴趣所在。即认为最好的东西不在“唯一”那里,“最好”恰恰隐身在各种可能性里,它导致出现自由竞争的观点“市场”。现代性其实指出了如何消除“文革”积习的方法,即对当代任何一方的“定论”可以置之不理,只去关注诗坛最鲜活的部分——诗歌文本。诗人或批评家的美德,在于不要抛开自己的审美真实来谈诗,哪怕它只是错觉或错误。在一个由诗歌选本构成的公开“市场”里,担负起矫正“错误”职责的,不只有别的诗人或批评家,还有作为明眼人的读者和后人。
7、口碑的原生态
口碑一般潜伏在人群里,它不企图统驭或消灭不同的评价,而是所有不同评价竞争的结果。它对文本虔诚至极,一般劣诗很难获得它的青睐,它一时也难以影响当代诗歌史。它就像古代的隐士有着可敬的品质,带着客观冷静的眼光,在当代诗歌史外的人群里过着隐匿的游荡生活。当某诗歌奖选中的作品名不副实,当三流诗人获得一流地位,当刊物刊出的作品质量低劣,当写文章的人受控于撒谎的意志等等,它就会在人群中传播一种轻视。实际上,它着迷的是作品与作品的比较。口碑是作品在阅读流转中形成的品级金字塔,只不过它是即时的,会因为有更好的作品添加进来,而随时重排品级的次序。它的性质非常类似于每周的歌曲排行榜,当然它不会敏感到能觉察这周和上周的差别。它敏感的时间尺度并不确定,也许是两首好诗出现的间隔,也许是两个好诗人出现的间隔,也许是两个好选本出现的间隔……它基本体现了坚守真相的精神,是阅读感受最真实的流露,自然规避着地位、官阶、奖项、评选、文章等造成的盲目热情,它是一个时代企图靠自身力量恢复真相的努力,企图接近更久远的后世评价。当然,与后世评价相比,它也有自己不利的一面——时代的整体审美倾向会影响它,它摆脱不掉的时代趣味,有时会使它偏离后世评价。比如,王维在唐人选本中,之所以比李白、杜甫明显占优势,我认为与唐人推崇出世精神有关,与王维相比,李白、杜甫当然显得过于入世。所以,口碑还要经受从一个时代移到另一个时代的考验,直到不同的时代达成一致为止,那时它才能触及更恒久的评价。由于口碑不会站在当代阵营的任何一方,它赖以生存的土壤是阅读感受,所以,我把它视为最适合当代汉诗生长的绿洲,或说批评的原生态。当然,不诚实的奖项、党同伐异、利益批评等都在向它进攻,企图把这块绿洲或批评的原生态变成可以操纵的沙漠。我想说,这些人当然注意到了大众的无知或盲目,知道大众需要有人为其心灵指路,但他们也高估了自己能蒙骗口碑的能力,忘了口碑是当代明眼人的一种意志——追随和实现评价真相的意志。它就像是从远山传来的晚祷钟声,声音虽然轻微但始终充满染感力,一些真正珍惜当代汉诗发展的人,才会驻足认真聆听……
2010.11-12初于南京六合里
┝诗人、小说家,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