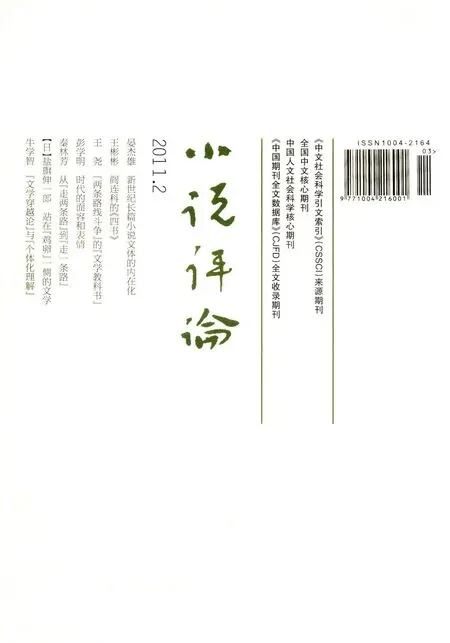论新时期长篇小说的乡土叙事
张晓平
论新时期长篇小说的乡土叙事
张晓平
为了盘点新时期30年(1979—2009)长篇小说创作成就,2010年伊始,《钟山》杂志社便邀约全国12位评论家投票,列出他们认为最好(文学标准)的10部作品,并简述理由。根据得票情况,当选的前11部(因其中后四部得票相同,列出11部)作品为:《白鹿原》《长恨歌》《尘埃落定》《心灵史》《许三观卖血记》《圣天门口》《废都》《秦腔》《生死疲劳》《活动变人形》《花腔》。①从投票入选的大部分作品来看,也是以“乡土叙事”为主。为此,我想就长篇小说中的乡土叙事,谈谈新时期以来的当代作家,对于中华民族在现代以来的精神与生存的书写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并借此重新认识和评估新时期长篇小说的文学成就和创作规律。
一、乡土世界的诗意书写
中国无疑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即使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步伐加快的今天,中国依然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国文学积累了丰富的中国式的小说叙事经验。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等充满活力的历史性巨变。中国社会的这种空前发展,对于当代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仅为当代文学包括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开阔的、具有多种可能性的外在环境,同时也内在地、深刻地影响了当代文学包括长篇小说创作的新格局形成。
新时期的乡土小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悄然发生着变化,出现过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贾平凹的《浮躁》、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等优秀作品,它们书写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内心的躁动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恢复了文学的人性书写和内心探秘。而到1980年代中期,随着“文化热”的出现和“寻根文学”兴起,中华传统文化、民间乡土文化和作家的主体性被凸显出来,乡土文学创作有了很大的改观。莫言、张炜和张承志、韩少功等人在锐意创新和个性化追求中都根据自己的生存经验和艺术思考分别构筑了像高密乡、葡萄园和西海固、“马桥”等各具特色的文学世界。在思想内涵上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间生命力的书写
作家关注民间是新时期人文精神的一种体现,更重要的是作家的视野由传统的政治、历史的视角转向了民间视角,甚至作家站在民间的立场发掘民间丰厚的文化资源和生存智慧。
莫言的《红高粱》可谓一曲民间生命欢歌。作者塑造了一个生龙活虎的形象——“我爷爷”余占鳌。他杀人越货、强占民女,他抗日卫家,一切充满了血性。如果从身份的角度说,他是个复杂的人物:农民、土匪、流氓、抗日英雄复合于一身,很难界说清楚。但如果从生命形态角度说,他一个强悍的生命个体,是生命的自由、奔放而富有激情的挥洒书写。在余占鳌身上,杀那个与他妈偷情的和尚、杀单扁郎父子、杀花脖子、杀余大牙和杀日本人,都是出于生命的直感,出于性情。一切自然而然,既没有犯罪感,也没有自豪感。作品张扬着人的“原始野性”的雄强、狂放和生命力的健旺。可以说,莫言的“红高粱”系列激情四射地书写了民间的生命活力:那血红的“酒神精神”和碧绿蓬勃的高粱一样的生命力构成了野性、粗犷与美丽、善良相交融的丰富复杂的艺术审美世界,彰显了民间文化自由自在的艺术风格。他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则超越了政治、转向文化母题的书写,颂扬了“大地”般深厚的母爱。评论家张清华认为:“它以一位民间母亲为见证主体,书写了二十世纪中国风雨沧桑、波澜壮阔和血泪夹杂的历史,再现了传统民间社会及其伦理在各种现代外部力量的侵犯之下的瓦解崩溃。它浓郁的悲剧笔调和坚定的民间意识,是对进步论历史观和意识形态樊笼的强力冲击与突破。”②
陈忠实《白鹿原》对白嘉轩的生命力的书写,不仅表现了民间生命力的强悍、坚韧,而且表现出传统文化在现代政治动荡中逐步消弭。正如丁帆所言:“这是二十世纪中国乡土小说最具经验性的描写,它不仅仅旨在揭示‘一个民族的历史’(其实是家族史摹写),更重要的是作品所散溢出来的对于人的生命力的弘扬,以及对文化长河中人性渺茫的悲剧性表达,是二十世纪长篇小说抵达的新境界。”③
(二)乡土世界的哲学性思考
传统的乡土小说基本上停留在乡村风俗、乡民生活和生存状态的直接书写中,写实地反映乡村的现实人生。当然,乡土文学离不开这些基本的书写,但新时期的乡土小说由一时一地的乡土人生书写提升到了普遍人生和民族命运的哲学性思考。农民的苦难不仅是个人性的苦难,而且是人类的苦难;农民的奋斗不仅是个人性的抗争,而且是人生命运的抗争。
评论家洪治纲在评价《白鹿原》时说:“这是一部具有“民族秘史”意味的小说。作者从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以及这种精神所培育的文化人格入手,致力于探究民族的历史命运和文化命运。从复杂的党派政治斗争到民生经济的冲突,从剧烈的民族矛盾到宗法背景下的家族纷争,从乡村文化伦理的纠葛到人性欲望的争斗。作品既描述了风云变幻的历史,又通过出走与回归、繁衍与毁灭、腐朽与再生、必然与偶然、机遇与宿命等等结构的设置,将思考提升到某种哲学的高度。”④
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书写许三观通过卖血,建立了家庭;通过卖血,许三观击败了苦难;通过卖血,许三观看到了自身的价值,颠覆了屈辱,获得了自尊。当他不能卖血时,他便感到自己没有什么用场可派,是个“废人”了。因此,“卖血”成了许三观的生存方式,也便具有了象征意义和哲学内涵。“卖血”不过是表象,“卖命”才是根本。许三观通过“卖血”——“卖命”实现对苦难和命运的抗争。生命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输出血液的消耗过程,只不过在许三观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更加集中、更加惊心动魄罢了。同时作品传达了创作主体对苦难人生的深厚的体恤之情,也展示了中国民间特有的生存智慧与生命韧性。评论家何言宏认为,这部作品是“关于我们民族生存的一则寓言,更是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现实。”⑤
(三)现代文化精神的张扬
新时期是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期。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复苏了知识分子的文化意识。他们开始反思过去的政治文化、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文化,寻求中国文化的历史根基和新的文化重建。在思潮跌宕的20世纪80年代,艺术家们开始了自觉地清理固有的文化遗产,沟通民族发展的历史感、现代感和未来感,积极地张扬和发展民族的自我意识,张扬现代文化精神,不因袭和依傍任何一种现成的哲学体系,而宁愿从哲学的最基本的命题,如自然和人生、理性与情感等等,来探求植根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土壤深层的人生哲学和艺术哲学。
阿来《尘埃落定》以文化想象的方式洋洋洒洒地书写了西藏“麦其土司的兴衰过程,展示了神秘而又深厚的藏族文化形态,包括宗教信仰、文化伦理、人与自然的特殊关系。同时,它又通过土司之间的明争暗斗,土司家族内部的生存形态,以及土司与民众、土司与汉族党派之间的矛盾,隐喻了人类迈向文明的艰辛与曲折、痛楚与希望。从罂粟到梅毒到战争,这些特殊的文化符号,不仅改变了麦其土司的命运,改变了藏族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命运。”(洪治纲语)⑥作品形象地展现了人对权力、金钱、情欲等的欲望和因此导致的病患,揭示了土司家族部落统治史的悠远和宿命。我们可以从作品的很多地方感受到鲜明、独特而且也很强烈的藏域文化风情,理解到西藏民族的生活方式。但最为重要的是作者在非常明确的现代文化精神的立场上,书写了藏地生活与藏地文化的命运,进而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思考。
现代文化精神的确立主要表现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冲突过程。五四以来的现代性启蒙既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现代文化精英立场,也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待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拒斥态度。但从人文精神角度,现代知识分子又怀有同情的态度,如鲁迅之于阿Q、茅盾之于老通宝等。而新时期的乡土作家对待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态度不是简单的拒斥,而是更为复杂的理性透视,如陈忠实之于白嘉轩、莫言之于余占鳌、韩少功之于丙崽等。不可轻视的是,新时期的许多乡土作家因为对现代都市文化理解不足而走向了对都市文明的过度排斥和批判,沉迷于乡土民间文化之中。正如评论家朱小如指出的,“中国的现当代作家基本上还是习惯于把‘精神家园’建造在‘乡土’而非‘城市’。”⑦这必然影响到作家对现代文化精神的张扬,寻根文学的匆匆收场就是其突出的表现,而这与作家的个人性生活经验密切相关。新时期无论是资深的老作家还是新生代作家,基本上都生活在城市,农村生活经验缺乏,他们书写乡土大多数是想象性地表现,并没有真正贴近民间大地。因此,真正书写新时期中国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苦辣酸甜和情感世界的长篇力作还是很少的。
二、叙事结构突破与创新
中国传统的长篇叙事,在结构形式上变化不多,最为突出的是历史和传记流传下来的编年体式和章回体式,以及完整的有头有尾的线性故事情节结构。编年体式的叙事与历史记录的客观性要求有关,时间交代清楚,情节有条不紊地发展。章回体式的叙事虽有人物和故事情节为线索,但时间顺序依然呈自然状态。总之,传统小说故事情节的逻辑结构则要求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方可构成其独立的完整性。然而新时期的长篇小说开始了叙事结构的突破和创新。
(一)家族史的叙事结构
家族史小说其实是世界文学中的基本类型,即使在现在,西方国家也有很多家族小说的。它确实是历史讲述的重要切口,但在中国,由于民族传统的世界观与伦理观,对于家族的理解与表现在意义与特点上显然又会与西方不同。中国有着悠久传统的“家国”观念,家族就是一个国家的缩影,国家的兴亡与家族的兴衰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无论写家族生活,还是写时代变迁,家族史都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阿来的《尘埃落定》和张炜的《古船》、《家族》等小说,突出的一点就是都有一个家族史的内在叙事结构,但这种叙事结构与曹雪芹的《红楼梦》、巴金的《家》、柳青的《创业史》相比又有一些新的变化。
《白鹿原》书写了白嘉轩和鹿子霖两大家庭几十年的恩恩怨怨,揭示出从大革命到日寇入侵、三年内战期间西北人民的苦难以及家国情仇。虽然家运起伏是和时代风云紧密的纠缠在一起,但左右方向的始终一直是人性善恶的伦理道德力量。其中的家族关系,以及白家和长工鹿三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们以前用“阶级斗争”分析方法获得的对“乡土世界”的简单认识。可贵的是《白鹿原》在家族叙事中巧妙地穿插了一些民间传说、古典戏剧和神话传说等,将现实与神话传说、寓言以及鬼魂故事融合在一起。这样不仅丰富了结构,而且增加了作品的神秘色彩和传奇风格,民族革命史变成了“家族秘史”。
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书写雪、杭两家之间连绵不断的紧张“阶级”对峙,所有的家仇与国恨、人性的善与恶,也是和“革命”的社会时代风云变幻复杂矛盾地纠葛在一起,演化成激烈的、尖锐的、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作品是通过对乡土中国和家族史的写作所展开的对中国革命的思考,换句话说,作品是从人性和伦理的角度来反思革命的暴力的。文本结构视角的转变源自作家对文学表达的新的感悟与发现。张炜的《家族》叙事时空交错,穿插着作者的议论和旁白,打破了叙事的连贯性而呈现出叙事的跳跃性,从而使长篇小说的结构趋于多元化、复杂化。
新时期家族结构的小说既有对传统长篇小说结构艺术的继承,又融入了作家新的思考和审美追求。家族结构变得丰富多彩,叙事视点也有了新的转换,可以说,新时期长篇家族小说有了新的突破和创新。
(二)互文性叙事结构
“ 互文 ”(intertext)、“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原本是语义学、修辞学的术语,古语对它的解释是:“参互成文,含而见文。”具体地说,它是这样一种形式:上下两句或一句话中的两个部分,看似各说一件事,实则是互相呼应,互相阐发,互相补充,说的是一件事。20世纪它成为一种新的文本理论。其继承了结构主义的优点,并吸取了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破坏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强调于文本本身的断裂性和不确定性。由于其理论符合现代文本理论的发展方向,故受到了普遍重视,也成为艺术家创作的一种叙事方法。
《圣天门口》在书写雪、杭两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时还穿插了“黑暗传”和“光明史”,它们互相对照、映衬、补充,这种互文策略对拓展作品的时空有着重要的作用,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审美内涵。
《檀香刑》则采取“散点透视”的方式,让每个主要人物都提供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叙述视角,而正是这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叙述视角之间的互相支撑,才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立体叙述。如孙眉娘的视角,是构筑亲爹、公爹和干爹之间矛盾纠葛的枢纽,集中体现了自然的家族血亲伦理冲突。而亲爹、公爹和干爹分别又提供了民间社情伦理和国家政治伦理的视角。应该说这样一个相对完整的立体叙述,已经不等同于我们过去那种“统一”的全知全能叙述,而更像是一个多面体的透视镜,每一个面透视出来的都有其相对独立的价值而非绝对价值。
《马桥词典》则以“词典”的结构,书写了乡土中国的历史悲欢、风俗民情、逸闻趣事及世相百态,以及那种处理生老病死和驱邪消灾的文化方式,以及“万物有灵”的古老哲思和敬“天地鬼神”的民间信仰等。作者运用词语的阐释、串联、互文等独特的叙事手段立体地呈现丰富而复杂的民间世界。一方面它所突破了叙事语言的成规,另一方面是彻底打破了情节结构的成规,“开拓出了小说文体新的类型与可能”(何言宏语)。
三、叙事语言的个性化追求
叙事语言是使故事内容得以呈现的口头或书面陈述。叙述语言中对叙事有重要影响的是叙述时间、叙述视角和叙述标记等。传统的叙事作品中叙述主体主要是采用旁观者的口吻,即第三人称叙述,按照时间的客观链条讲述故事,表达自己的叙事意图。中国传统的长篇小说叙事多采用第三人称的宏观叙述策略,讲述历史传奇、英雄传奇或家族生活。在近现代的历史动荡中而逐渐形成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公共化语言”叙事,如革命史叙事、阶级叙事等。评论家朱小如认为,“何谓‘公共化语言’?在我理解中也就是那类以‘我们’、以‘群众’、以‘集体’、以‘大家’、以‘社会’、以‘国家’、以‘主义’、以‘阶级’为‘中心指向’的言辞。”⑧何言宏则进一步解释:“我所理解的‘公共语言’,实际上所指涉的,就是‘公共经验’,是大于、甚至吞没或压迫着‘个体经验’或‘地方经验’的公共性的东西。现代以来,你所说的上述公共性的东西,而且大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公共性的东西,一直在我们的文学、政治和思想文化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非常有力地排斥着后者。”⑨新时期随着作家文学主体性的觉醒和文体的自觉,他们便开始了对“公共化语言”的逃离,采取了“个体语言策略”。
个体语言的追求是所有文体自觉的艺术家的追求,也是艺术家风格形成的标志。鲁迅的冷峻、巴金的热情、沈从文的柔和以及老舍的朴实都给读者留下了鲜明深刻的印象,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独到的人生(社会)感悟和情感表达。在集体话语、政治话语、阶级话语盛行的当代,作家们深感“公共话语”的挤压,个人性话语缺少发展的空间。也只有到改革开放时代,作家们才获得了表达的自由,才有可能自觉规避“公共话语”,寻求属于自己的语言方式表达个人性的对社会认识和人生体验。
例如,李锐的《无风之树》用了13个叙述者“我”,敞开了吕梁山矮人坪的时代政治和乡村伦理。这些叙述者以各自不同的身份参与了乡村事件的过程,一方面他叙述自己遭遇的事件,展现自己内心所思所想和心理状态,另一方面又被其他叙述者叙述。李锐正是运用口语叙事和独白的方式直击中国最沉默的底层社会的生存状态,显示了作品的力度和深度。李锐在作品后记中写道:“我希望自己的叙述不再是被动的描述和再现,我希望我自己的小说能从对现实的具体再现中超脱出来,而成为一种丰富的表达和呈现。当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视角出发讲述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千差万别的世界。”⑩
韩少功说:“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所谓‘共同的语言’,永远是人类一个遥远的目标。如果我们不希望交流成为一种互相抵消、互相磨灭,我们就必须对交流保持警觉和抗拒,在妥协中守护自己某种顽强的表达——这正是一种良性交流的前提。这就意味着,人们在说话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每个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特有的词典。”⑪他正是在湘西楚文化的民间资源的寻找中实现了自己文体的自觉和话语的个性化追求。
新时期乡土作家贾平凹、陈忠实、何申、张炜、莫言、韩少功、阎连科等都在自己的艺术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语言个性和创作风格。
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作家对民间资源的自觉寻找。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山东高密乡、韩少功的湘西、李杭育的葛川江、阿来的藏地等。正是这些地域文化资源(语言、风俗、信仰、生存环境)孕育了作家,也成就了作家。所以,方言写作成为新时期乡土创作的普遍现象,也成为作家个体经验的深刻表达的“个人性标记”。何言宏在推选《马桥词典》时说:“韩少功《马桥词典》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在于它以‘词典’的方式结构和组织文本,开拓出了小说文体新的类型与可能,更在于它通过对马桥方言的释义与考古,来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出方言的文化潜能,从而颠覆和改写了被普通话所严重覆盖与遮蔽的民间世界,这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实际上具有根本性的意义。”⑫
但是,知识分子对于民间资源的寻找,不应该是对民间话语的彻底皈依,而是应从民间大地汲取营养、孕育诗情之后重新出发,在社会现实的历史进程中重新整合民间话语在内的各种的话语资源,找到属于自己的话语资源和思想资源,重新建立知识分子现代性的话语体系。
另外,新时期乡土作家还汲取了现代、后现代艺术技巧和思想资源,通过对公共化语言的戏仿和反讽,实现对“公共话语”的突围。
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就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叙事文本。作家叙述了文革在中国农村程岗镇展开的场景,表现了文革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以及个人的政治野心、性意识与革命暴力之间的关系。作品采用了大量文革话语(公共语言)的表现形式,诸如流行一时的革命领袖语录体和诗词体,革命样板戏的唱词和对白,以及标语口号式的政治短语,革命歌曲等语言形态,一方面复原了文革语境,另一方面在主人公的“疯狂”表演中凸现小说的反讽功能,从而深化了作家对文革现实的批判意向,达到了深层反思文革审美效果。
纵观中国乡土文学叙事,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艺术质量上,新时期长篇乡土小说无疑是一个高峰。它们艺术地书写了中国农村变化的历程和中国农民在历史的变迁中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轨迹,更从哲学的高度深入思考和揭示人的命运和面对苦难或幸福的内心隐秘,而且在艺术上实现了突破和创新,在作品中深刻地烙下了鲜明的“个人印记”和地域特征。
张晓平 广东省韶关学院文学院
注释:
①②③④⑥⑫《长篇小说三十年(1979——2009):十二个人的排行榜》《钟山》2010第2期。
⑦朱小如、何言宏:《〈废都〉与〈长恨歌〉——关于中国当代十部长篇小说经典的对话之一》,《芳草》2010年第3期。
⑤朱小如、何言宏:《〈我的帝王生涯〉与〈许三观卖血记〉——关于中国当代十部长篇小说经典的对话之三》,《芳草》2010年第5期。
⑧⑨朱小如、何言宏:《〈马桥词典〉——关于中国当代十部长篇小说经典的对话之二》,《芳草》2010年第4期。
⑩李锐:《重新叙述的故事(代后记)》,《无风之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05-206页。
⑪韩少功:《马桥词典·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377页。
- 小说评论的其它文章
- 揭示灵魂隐秘与生命迷津
——评胡学文《从下午开始的黄昏》 - ">"文学穿越论"与“个体化理解”————吴炫文学批评理论
- 祛积极赞同之魅
——重评《艳阳天》 - 玫瑰底色是真诚,洗尽铅华识不俗
——读叶兆言新作《玫瑰的岁月》 - 站在“鸡卵”一侧的文学
——今读《白鹿原》 - 延异的创伤与断裂的诗学
——重读废名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