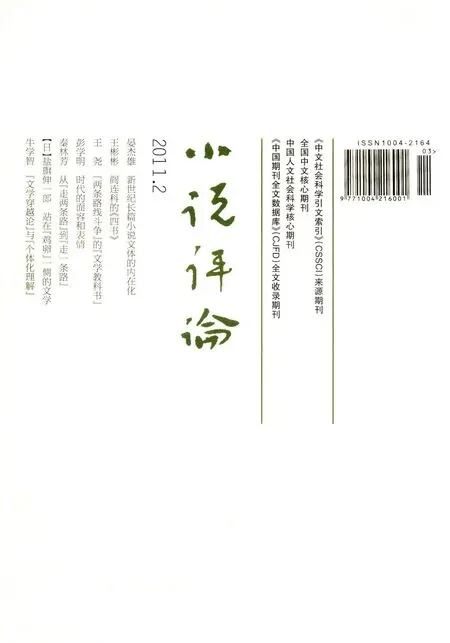《音乐小屋》:灵魂震颤的多重乐章
王 瑶
《音乐小屋》:灵魂震颤的多重乐章
王 瑶
刘醒龙的小说始终以乡土为根,深入社会现实,追问人性本源。无论是《凤凰琴》《天行者》,还是《分享艰难》《痛失》《政治课》,其中的主人公,总是顽强地与沉重而吊诡的现实世界相抗争,他们有的动摇了、妥协了甚至堕落了,但是更多的人却始终不肯出卖自己高贵的灵魂,始终不曾放弃自己的人生信念。这一点,在他的中篇新作《音乐小屋》里再一次获得了突出的表现。
《音乐小屋》描写了一位擅长吹口琴的打工乡民万方。小说通过“一只口琴在历史与当下的处境”①,展示了城市人对乡村人的歧视,反映了城市文明对人的严重异化,也奏响了灵魂震颤的多重乐章。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现实境遇中,人分三六九等,乐器也有高低贵贱。唯有万方吹奏的美妙音乐,吸引着纯洁的孩童,也慰藉着那些在繁华外表下早已满目疮痍的心灵。作者试图通过万方的口琴,向人们发出诚挚的呼喊:不管现实如何,人们都应永不放弃对生命的诗意追求。
一、梦想与现实:底层生命的尴尬生存
在小说的开端,刘醒龙便为我们精心勾勒了一幅北风肆虐下的城市图景:暴烈的北风,刮开了城市繁华的面纱,露出颓唐的肌理。几株营养不良的菊花,散落在冬青植物的缝隙里,唤不起任何路人的注意。这也似乎预示着,在城市中如菊花般品质高洁的人少之又少,人格与气节在这里不会受到重视。而万方的城市生活,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万方是一个有音乐天赋、擅长吹口琴,并有着高中文凭的乡村人。以乡村人群体的文化水平来看,他属于知识分子。在一般人群体中,他也称得上是一位艺术家。但在城市里,他依旧遭到众多人的歧视。他作为一名清洁工,和工友陈凯一起住在楼梯下的小屋里。小屋虽然有九平方米,而能直起腰的地方只有两平方米,两人还必须睡在一张床上。最让他们感到困扰的是住在他们楼上的胖女人——小男孩“丹麦王子”的母亲。胖女人每天回家时都要在楼梯上狠狠地跺几脚。她作为一个摆地摊的商贩,自身的社会地位也不高,但她仍有资本瞧不起他们,因为她是“城市人”。小女孩伊丽莎白的母亲也一样。单从把孩子叫“伊丽莎白”、“丹麦王子”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两位母亲对身份地位的崇拜程度。
在工作中,万方和陈凯也常常遭“城市人”鄙视。刮风天扫地时,过路的男人们认为大风把垃圾自动归为一堆,便宜了扫大街的万方,就纷纷往地上吐痰;陈凯不小心将地下的一点湿东西弄到了过路人的脸上,就被毒打一顿;诊治陈凯的值班医生对清洁工被打的事实毫无反应,还用很重的手法治疗;在去晚报社告状的路上,车上的人对万方的询问也是爱理不理,让万方错过了晚报社站;到了晚报社后,记者也只是敷衍万方说她会争取让事件曝光,而第二天的报纸上根本没有出现这一消息;甚至环卫站的会计也明目张胆地瞧不起万方他们……
小说通过万方这个人物为圆心,以万方的生活经历为半径,辐射了乡村人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刻反思了乡村人在进步中依旧被歧视的原因。这些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身份歧视。万方自身带有的乡土气质,时刻暴露着他的乡村人身份。即使他为了见心仪的女孩芦苇而换上了西装,也未能遮掩自己的乡土气质。因此他敲开芦苇的门时,芦苇还以为他是自己不认识的普通农民工,竟一把将他关在门外。这种乡土气质,不仅使他在关键时刻碰壁,还让他不断地在人际交往中遭受冷遇。相比之下,万方的同乡——做了总经理助理的万有,不管走到哪里都受到恭恭敬敬的待遇。
第二,职业歧视。由于清洁工处于社会地位的底层,极大多数城市人根本不屑于搭理他们,甚至有部分人会欺凌他们。万方遭到旁人的嘲笑不能还口,陈凯遭受路人的毒打不敢还手,这些都反映出身为社会底层人物的悲哀。相比起那些歧视、欺凌他们的人,待他们友好的人似乎能给他们一些温暖,如何大妈、马站长等人。但历经了多个事件后,万方才发现这些人的关怀也只是一种伪善。他们跟万方搞好关系,更多是为了让万方配合他们,利用万方来完成眼前的工作。这些人本质上跟歧视万方的城市人并无区别。这些人的伪善,比起赤裸裸的歧视而言更具有杀伤人的威力。
第三,技能歧视。刘醒龙曾在创作谈中提到“口琴这东西,一直以来是有属性的。”②在知青他们人手一把口琴的年代,口琴代表着先进文化,也代表着城市文明。而当下,时代在进步,口琴却落伍了。现代都市人普遍认为,拥有口琴并不算得什么,只有拥有了钢琴,才是身份、地位、财富、知识的象征。因此,纵使万方的口琴吹得再好,也只能吸引极为少数的城市人,更多的城市人表现出的态度是不屑。
万方为了寻梦而来到城市,但他所拥有的一切都被所谓的“城市人”鄙视了:首先是身份,进而是职业,最后是自己最得意的技能。这些都让万方感到梦想在逐渐分崩离析。
《音乐小屋》似乎想要呼吁社会,逐步地提高乡村人群体素质,进而改变乡村人尴尬的生存现状。但无论怎样,当下这种身份歧视,不仅拉大了乡村人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更阻碍了部分乡村人追求上进的步伐。它注定了城市并不是乡村人的归宿,也使乡村人的梦想与现实之间难以沟通。
二、受虐与自虐:人性的撕裂和堕落
在《音乐小屋》中,“歧视”不仅来自城市人,同样也来自乡村人之间的不信任。像陈凯就瞧不起万方。他认为万方像个初出茅庐的孩子,对城市没有清醒的认识。他希望拔除万方对城市的所有希望之苗,迅速“成熟”。他三番四次地嘲笑万方的热血与无知。表面上,他的嘲笑是一种鄙视,也是一种劝解。而事实上,他认同的是“乡村人抗争无效”这一经验。他放弃了反抗,默认了城市人的欺压。他敢于对万方大声嚷嚷,却不敢动打他的城市人一根汗毛。他长时间地压抑自己,把满腔愤怒全部化为粗鲁的咒骂和写在报纸上的涂鸦。他习惯了被动承受,总是不断忍耐。但也正是由于他的被动,差点儿让他错失转变身份的良机。而正是他瞧不起的万方,一次次地为他争取机会,为他发出呐喊的声音,才让他最后得偿所愿。
比万方早一年进城的万有,刚开始也歧视万方。他对于万方而言既是竞争对手,又是重要的朋友。万方两次有困难,都是靠万有帮助才得以解决的。因此,刚开始的时候,万有往往以高高在上的城里人姿态对待万方,并对万方炫耀自己的“成功”。但万有却是靠着跟五十多岁的女老板鬼混,坐到了总经理助理的位置上。并且,这个事实还被万方撞破了。万有对万方的歧视,就此转变为万方对万有的鄙夷。万方靠良心吃饭,脚踏实地赚钱,而万有靠出卖自己的肉体换得金钱、权力、地位。他看似融入了城市生活,拥有了光鲜的外表,其实仍然只是城里人的欲望工具,没有自由,也没有尊严。
陈凯明白到,乡村人如果无法努力摆脱身份的束缚,就永远不能奢望得到城市的接纳与认同。在绝望的现实境遇之下,陈凯开始自甘堕落,由“受虐”走向了“自虐”。为了融入城市,过着“像城市人的生活”,陈凯发生了彻底的裂变。他设计了“救人计划”,企图成为“英雄”。他偷走井盖,让路过的人掉进去,自己再及时救援。但是计划只成功了一半。后来,他救的胖女人却迟迟没有回应,他自己却因喝了脏水得了病。记者采访时,胖女人对自己的辩护是:那井盖肯定也是进城的农民偷的,她虽被进城的农民救了,但那本是他们应该做的。这一辩护颇有“解铃还须系铃人”之意味——虽然她并不知道“解铃人”是否是“系铃人”,但这一说法,恰好讽刺性地击中了陈凯的所作所为。
所幸的是,陈凯最终还是因祸得福,戏剧性地成为“荣誉市民”,将户口转入城市,还当了治安联防队副队长。此后,他还做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带万方到桑拿洗浴中心,还叫了小姐。陈凯认为,只有这样,自己才真正地被城市接受了。这种乖张的行为,表明陈凯虽然无可救药地自甘堕落,却没有丝毫的醒悟,反而将自我堕落当作城市对自己的宠幸,并对此感到心满意足。
从万有和陈凯的命运中,我们可以看到,挣扎在城市里的乡村人,除了受虐,就是自虐。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因而常常不由自主地撕裂人性,走向堕落。他们在改变自我、努力追求进步的同时,自己也被城市严重异化。他们出卖了自己的心灵,逐渐成为追求物欲的行尸走肉。
三、口琴与钢琴:让诗意在都市中生长
马站长对个人被群体同化现象司空见惯。因此马站长曾预言,万方工作三个月后将爱上香烟,因为万方的工友都吸烟。但是万方却一直没有碰烟。他始终用口琴抚慰着自己的心灵。小说藉此细节,表现万方始终坚定不移地守护着自己的人生信念。口琴和音乐是万方与现实抗争的有力武器。
《音乐小屋》把小屋、口琴、音乐三者融合在一起。它们看似并不相配,却代表了一种诗意的生活。三者中,口琴无疑是联结小屋和音乐的重要纽带。作者精心设置了“口琴”这一意象,并通过乡村人与城市人的视角,将口琴与钢琴进行相互对比。
乡村人自然也明白钢琴代表着富足、高贵。但在乡村人的视角中,无论是钢琴还是口琴,都是知识的象征,它们都和城市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在城市人的视角下,钢琴“摆在家里既气派又能显示出人的身份,既能陶冶灵魂又能成为明星挣大钱”;口琴则“学得再好也不能当明星,反而将人弄丑弄俗气了……”。口琴只是一个落伍的东西。因而在极大多数城市人的眼中,无论是口琴、小屋,还是口琴吹出的音乐,都一文不值。乡村人、城市人的视角对比,将城市中的拜金主义思想刻画得淋漓尽致。
然而实际上,无论是钢琴还是口琴,它们都与文化、艺术、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使是一只口琴,它也“能让一间小屋的破烂与简陋,焕发出生命本质的光艳和生存意义的色泽……”。生命本质和生存意义不分阶层。生命的本质是人类所共有的。我们更不能说草根、平民阶层就没有生存意义。因此小屋、口琴、音乐、钢琴之间不应分出高低贵贱,它们之间应当是平等的。
小说为了说明两种乐器之间的平等性,特意设置了一个细节,让万方这一草根人物在读书时学过键盘乐器。并据此安排了万方弹钢琴这一叙事片段,让万方在胖女人家里进行了一曲成功的演奏。由此说明,无论是钢琴还是口琴,都只是一件乐器,一种表达的手段。钢琴也好,口琴也好,它们都能发出震撼人心的音乐。美妙的旋律其实隐藏在人的心灵与才华之中。
但在万方走向钢琴以前,刘醒龙就通过“零视角叙述”③,预言了即将发生在万方身上的倒霉事件:“……万方听说芦苇都关心起他的去向,心里激动起来,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竟懵懂地要小男孩带自己去看看他家的钢琴。小男孩很高兴,扯住他的手就往楼梯上走。”一句“不知如何是好”,表现出万方在兴奋、迷乱、忘乎所以的状态下做出了弹钢琴的选择;一个“竟”、一个“懵懂”表达了叙述者隐隐的不安,也揭示了即将上演的尴尬场景。
虽然万方弹奏的音乐非常美妙,且在演奏完毕后很文明地做了个鞠躬礼,他仍被匆匆赶到家的胖女人以极其狼狈的姿态赶了出去。这一叙事刻画,比之前的所有叙述都更能深刻地表达出歧视的根源所在——阻碍了万方的不是“口琴”,而是他的“身份”。即使万方能够做出演奏者的姿态,并使钢琴发出美妙的声音,也不会跟钢琴有太多的缘分。钢琴这一物件并不属于他,而属于胖女人一家。对于他而言,口琴、音乐、小屋才是完完全全属于他的。无论何时,他都可以自由地在小屋中,用口琴吹奏属于他的音乐,通过音乐让城市变得可爱,让小屋变得空阔。
任何人都可以鄙视这种音乐,但谁也无法剥夺它,因为那是只属于草根的诗意生活,那是谁也夺不走的草根的浪漫。为了表现草根诗意生活的顽强属性,刘醒龙在叙事上有意地设计了一系列悲剧事件。这些事件,无不是为了从肉体、从精神上一步步将万方推挤到人生最低谷。按时间顺序排练这些事件:第一是胖女人和其他人的歧视;第二是何大妈、马站长等人的伪善、欺骗;第三是陈凯的裂变、堕落;接着是万有与老女人鬼混事件的曝光;第五是万方与芦苇脱去衣服被何大妈撞见;最后是万有道出芦苇本为妓女之事。这些事件的破坏力逐级递增,事件的发展层层深入。它们不仅彻底摧毁了万方心中的期待,也无情地剥夺了万方对城市的最后一丝梦想,就像刘醒龙自己所说的那样:“……会吹口琴的清洁工万方,在瞬间的城市之爱后,陷入到从未有体察过的骨感之痛,这些反而近似巨大股灾后的最终探底与筑底。”④
但是,无论在何种打击下,万方从来都没有放弃口琴与音乐。他虽然常常沉默,但他并不软弱。他的音乐抚慰着自己的内心,也净化着他者的灵魂。他吹口琴时想象着家乡的美景,因此口琴中飘逸出的是心灵的乐章。优美的旋律凭借着簧片的震动,沟通着心与心。正是因为万方心灵纯洁,他吹奏的旋律才具有治愈他人灵魂创伤的疗效。而只有那些心存一方净土的人,才能被心灵的乐章带回到自我的本真状态,重新发现自己那颗曾经单纯美好的心。这些人的心灵未被完全异化,他们能意识到自己的灵肉分离。因此,芦苇听了万方的音乐后,才会爱上这种音乐,并发出来自灵魂的忏悔与痛哭。
对于芦苇而言,表面的穿金戴银,生活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与内心感到的龌龊、不堪有着强烈的对比。对于万有、陈凯等人而言同样如此。这种强烈的对比,促使一个人质疑自己曾经定立的生存目标,并认真思考自己存在的真正意义。万方将心灵的旋律献给那些愿意为他的音乐感动的人,用诗意的乐章去震撼他人的灵魂。
小说结尾,万方与万有进行着口琴与小提琴的二重奏,陈凯在一旁敲打桌子伴奏,此时的三人颇有与城市达成和解之意味。万方从小屋、口琴、音乐中所获得的满足,至此完全成为了他全部幸福感的来源。
王瑶 暨南大学中文系
注释:
①②④刘醒龙:《一只口琴的当代史》,《中篇小说选刊》2010年第4期。
③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第2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 小说评论的其它文章
- 揭示灵魂隐秘与生命迷津
——评胡学文《从下午开始的黄昏》 - ">"文学穿越论"与“个体化理解”————吴炫文学批评理论
- 祛积极赞同之魅
——重评《艳阳天》 - 玫瑰底色是真诚,洗尽铅华识不俗
——读叶兆言新作《玫瑰的岁月》 - 站在“鸡卵”一侧的文学
——今读《白鹿原》 - 延异的创伤与断裂的诗学
——重读废名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