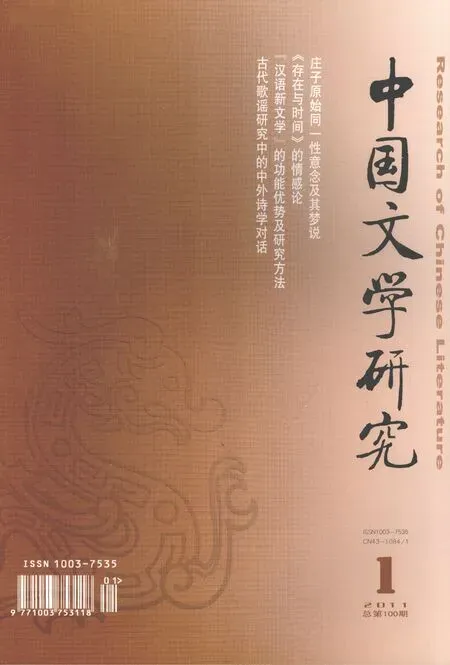论鲁迅小说中的贱民话语
朱崇科
(中山大学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鲁迅先生曾经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提及,“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实际上,他在小说(本文所用鲁迅小说版本出自金隐铭校勘《鲁迅小说全编》插图本,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如下引用,只标页码)实践中的确也向“不幸的人们”倾注了相当复杂的感情,即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粗略梳理相关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论者更多的是从小说主人公的身份归属加以处理:比如小知识分子、农民(游民)、妇女等等。这样的操作固然有利于增益我们对上述归纳的了解和认知,但对于“不幸的人们”的判定却似乎仍有“盲人摸象”之嫌,而实际上,“不幸的人们”指涉各异,毕竟,现实人生中,“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语)。
话语分析和贱民(subaltern)理论的巧妙结合其实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痛恨理论或者对以西方文论诠释中国问题的做法过敏者似乎找到了杀戮和挞伐的标的,而在我看来,“贱民话语”之于鲁迅小说却是相当有意味而且颇具针对性的问题意识,如果我们对它重新加以界定的话。
“贱民”这个概念,或许更容易为人所知的是印度社会中的“不可接触的人”阶层。〔1〕而相关研究也是相当著名,那就是由印度拓展而日益国际化的“贱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比如其代表学者之一的古哈(Ranajit Guha)在《贱民研究》第一卷的序言中说,该学派致力于促进南亚研究中贱民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贱民”这个词来自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指的是“在阶级,种姓,性别,种族,语言,文化中处于从属地位”〔2〕的边缘从属群体。
无疑,在贱民研究学派中,对这个概念的界定也是众说纷纭的,但无论如何,它们往往都有着强烈的批判性指向,比如其中的对精英主义、殖民主义的反思等,如人所论,“贱民研究学派作为印度本土一个有力的后殖民批评学派引发了学界对西方殖民主义在东方确立知识的再思考,揭露知识与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3〕。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界定并不完全适合鲁迅,尤其是如果我们严格界定殖民主义等概念涵盖的话。
耐人寻味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其实也有对“贱民”的划分和规定。根据研究,至少在唐代,中国就有贱民,而且亦有相关的法律规定。贱民,又称“贱口”,是指与“良人”相对的被法律排斥于社会权力、分配之外的连自身最基本的权利也无法保障的社会群体。〔4〕但毋庸讳言,由于贱民更多属于“化”外之民,它们的划分更多是政治的,有学者在研究唐代法律中贱民的权利后指出,“贱民的权利实际上是不完整和扭曲的,各种繁苛的义务才是权利表面下的真实形态,显示出了我国古代刑罚浓厚的等级性特征……唐律将对贱民的压迫写入法典……从侧面对贱民的权益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5〕但结合鲁迅个案,这样的界定似乎也不太吻合。毕竟,“不幸的人们”中的阶层其实还是挺复杂的,既有革命者,也有普通民众;既有读书人,也有寡妇等。
需要指出的是,贱民(subaltern)有时也被翻译成“底层”或“属下”,而上述词语一旦结合了中国语境,就往往变成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语境内部的一种群体生存状态描述。相关的还有连带的“底层写作”问题,“相对来说,从观念上做些区分与界定要略显简单些。底层写作当然是描写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上极为贫困的各式人物在这个时代所遭受的种种艰难与不幸,以及在这过程中所显示的底层人物的心理、道德、精神等特征。”〔6〕但同时,这当然也很难对底层进行整齐划一的界定,毕竟,它身上的纠缠太多,“从当前来看,给底层一个精确的定义似乎比较困难。因为除了包含群体的日益复杂,底层还面临意识形态化和工具化的问题,这给底层蒙上了政绩化和商业化色彩。”〔7〕
如果把此议题复杂化,贱民和大家所熟知的“民间”术语似乎也不乏交叉之处,尤其是在藏污纳垢层面上。但同样也不能一概而论,毕竟,“贱民”中其实缺乏民间那么繁富的内涵以及积极的冲击力。在本文中,“贱民”的划分更多地源于权力的话语指向终端,而要超越相应的人为切割,比如《孔乙己》中,作为准士人的孔乙己本来其实可以高高在上的,但作为一个时空错位中的认同失败者,他其实更是“贱民”的代表。据此可以总结,“贱民话语”则是依据笔者一贯的话语定位,要考察与分析鲁迅小说中贱民书写中的权力流动轨迹。
一、传统形象: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
整体而言,贱民给读者最常见或曰传统的形象就是他们的不幸——被侮辱与被损害,而且,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他们长期遭受统治阶层及其意识形态的欺压与诈骗,他们往往也成为意识形态及权力统治机器中的牺牲品,乃至帮凶。如人所论,“底层最大的心理障碍就是自卑自贱,这实际是长期以来统治者实施压迫性教育的结果,它把奴性变成了底层意识的一部分,并灌输有财富就有权力的观念,使压迫合法化;由此造成底层对财富与权力的畸形渴望,一旦有了‘翻身’的机会又会制造另一种压迫性的统治”。〔8〕
(一)被异化:顺受与麻木。
毋庸讳言,贱民的社会位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相对悲惨的生活与精神状况。而长期或者习惯于这种被压抑的状态,他们实际上往往都是被异化的产物和牺牲品。
1、闰土:双重麻木。在鲁迅小说中,相当明显而且经典的文本就是《故乡》,而中老年闰土则是不折不扣的贱民。尽管鲁迅在闰土出场前曾以豆腐西施杨二嫂的世俗化演变作为铺垫和缓冲,但中老年闰土和少年闰土的巨大差异还是令人震撼不已。首先是物质层面的,他的身体日益粗糙和被摧残,“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第53页)其次,也是更严重的,则是他的心灵创伤,“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经过一番心灵的挣扎,他终于选择认可自己的现实卑微身份而恭恭敬敬地叫了声昔日的玩伴“老爷!”而面临可以诉说的生计的困苦时,他似乎已经被压迫到无话可说,“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
同样在选择可以拿走的物品时,“他拣好了几件东西:两条长桌,四个椅子,一副香炉和烛台,一杆抬秤。他又要所有的草灰”。(第55页)很显然,除了实用的物品以外,“香炉和烛台”恰恰也是引人注目的精神追求的实用品,这恰恰可反映出闰土的麻木与宿命感。虽然作者在结尾指出小说中“我”的理想和闰土的精神追求并无本质的高下之分,但闰土在被现实打压之下的精神苦闷是极其深重的。
2、被忽略的他者群像。在鲁迅的小说中其实还有不少被忽略的贱民。比如《孤独者》中,魏连殳的祖母有一个女工,始终照顾她老人家,并为之送终。但她的处境其实相当悲惨,准备将儿子过继给魏的堂兄其实除了通过过继小孩将魏连殳纳入传统伦理体系外,“他们父子的一生的事业是在逐出那一个借住着的老女工”。(第208页)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阿Q正传》里面的小尼姑。小说中,作为游民的阿Q虽然备受关注,但实际上还算不上真正的贱民,毕竟他还可以去调戏以及羞辱更加羸弱的小尼姑,“阿Q走近伊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头皮,呆笑着,说:‘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在小尼姑躲避后,他还紧追不舍,“扭住伊的面颊”。(第67页)极尽羞辱调戏之能事。而小尼姑除了带着哭声地诅咒他“断子绝孙”外则无计可施。
当然,其实在这样的贱民群象中,也不乏有着美好寄托的人。《在酒楼上》中长富的长女顺姑乖巧能干,同时也积极追求美感,比如对剪绒花的执着。但最终却因为长庚的流言——她男人比不上偷鸡贼长庚而生病终究送命。更典型的或许是《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小说中大多数人关心宝儿丧葬礼仪的表面性和周全性,而往往忽略并压抑了她内心深处对宝儿的情感寄托〔9〕,“下半天,棺木才合上盖:因为单四嫂子哭一回,看一回,总不肯死心塌地的盖上;幸亏王九妈等得不耐烦,气愤愤的跑上前,一把拖开他,才七手八脚的盖上了。”(第29页)更进一步,如果从当时现实的角度思考,单四嫂子对宝儿的依恋其实更是别有原因。作为寡妇,单四嫂子甚至受帮闲蓝皮阿五的性骚扰,但如果她的儿子不死,靠这个男丁的成长和闯荡,她还有可能正常乃至不错的明天,而宝儿一死,其实也就宣判了她的穷途末路,她很可能在社会上很难拥有起码的身份、尊严。
(二)从他奴到自奴再到奴他。
令人遗憾的是,贱民们往往由于压制的强大和持久以及意识形态宣传的欺骗性而变得愚昧和脆弱,所以在精神状态上也就出现了一些深层变化,从他奴(别人来压抑自己)变成自奴(自行强迫性压制),甚至变为奴他(奴隶摇身一变成更残暴的奴隶主),鲁迅小说对此颇为关注。
其中相对经典的则是《理水》中的下民代表。从他被选举为代表开始,就充斥着荒谬的利己主义、偶然性与懦弱,“然而谁也不肯去,说是一向没有见过官。于是大多数就推定了头有疙瘩的那一个,以为他曾有见过官的经验。已经平复下去的疙瘩,这时忽然针刺似的痛起来了,他就哭着一口咬定:做代表,毋宁死!大家把他围起来,连日连夜的责以大义……他渴睡得要命,心想与其逼死在木排上,还不如冒险去做公益的牺牲,便下了绝大的决心,到第四天,答应了”。(第294-295页)而他和大员们的见面则似乎更是一场表演的闹剧——在被问询灾情的影响时,他回答,“‘吃得来的。我们是什么都弄惯了的,吃得来的。只有些小畜生还要嚷,人心在坏下去哩,妈的,我们就揍他’。大人们笑起来了,有一个对别一个说道:‘这家伙倒老实。’这家伙一听到称赞,非常高兴,胆子也大了,滔滔的讲述”。不难看出,他在战战兢兢中很容易呈现出贱民常见的奴性,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他会揣摩并逢迎上司的心理作答,甚至不惜扭曲灾民严重受难的事实,而令人感到可悲的是,他的言行举止中也呈现出他对同类人中异见和其他想法的排斥以及奴役。
如果说《理水》中更多的是以个体呈现出贱民们的劣根性,而《头发的故事》则呈现出对集体贱民思想的批判:他们对于新生的现代性不理解,也很健忘,而对传统意识形态的秉持却不遗余力。从剪辫、留辫的政治史嬗变中其实更可以看出贱民们的头脑恰恰是不同粗暴意识形态的跑马场。N先生留学时因为剪辫遭到厌恶和警告,回国工作不得不装假辫却被人研究要拟为“杀头”;废了假辫子,却又被人一路笑骂“假洋鬼子”(第37页)。而相当可悲的是,无辫的他终究以手杖代替辫子,“打了几回,他们渐渐的不骂了”。手杖居然成为压制贱民们奴性的手段,其中的悖谬实在令人慨叹。〔10〕但在这种记叙与控诉中,我们恰恰可以感受到贱民们头脑中的桎梏,不仅长于自奴,也时不时准备奴他。
二、贱民的反弹:再现与消解
如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言,权力、知识其实和社会制度密切相关,权力往往经由一个网状组织加以配置和行使,而制度其实更多的是分布式的权力网络的运行载体和规则。〔11〕贱民们在被形塑和压制过程中,其实也有反弹,通过考察他们反弹的轨迹及其后果,我们恰恰可以反思鲁迅对贱民话语的深刻揭示。
(一)再现压抑机制。
若从福柯的视角考察鲁迅,不难发现,鲁迅原来是个洞察权力流向的高手,而凭借他对贱民身上凝结的权力的细描,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相关压抑机制的精彩再现。
1、排除与聚焦:《肥皂》中的学程书写。《肥皂》中权力的流向是相当复杂的,它的核心事件当然是女丐和肥皂。恰恰是因为旁观女乞丐时听到光棍闲汉们以肥皂“咯支咯支”的方式意淫女丐,四铭被调动了淫欲而前去买肥皂;在广润祥,他在买肥皂给太太用时,因为百般挑剔而受到女学生的嘲笑,因为不懂她们用英文辱骂的意义,才将矛头和怒火指向了学程。易言之,《肥皂》中间,在四铭与女丐、四铭与女学生、四铭与太太女儿们之间都是有权力流动的,但由于诸多原因,四铭在此过程中都是失败的,至少有被挫败或淫欲难以发挥的经历,比如女丐的难以靠近、不可触摸,女学生现代性话语的高高在上难以逾越,太太的洞穿内心、戳穿虚伪等等。〔12〕
学程在小说中逐步被确立了贱民的形象。表面上看,作为长子,他似乎该有自己一定的主体性,而实际上,他更是四铭淫欲难以宣泄之下的出气筒。他被选去现代学堂念书表面上看是接近现代性的产物,而实际上这恰恰也是四铭父亲权威的结果,而同时他又被父亲勒令“国粹”地练八卦掌。甚至在饭桌上,他因为吃了四铭中意的一个菜心而受到父亲的质疑和责骂。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更多是权力流向终端的承受者,但借此鲁迅恰恰考察出权力在四散奔流后的聚焦,更反映出四铭的虚伪卑劣、色厉内荏。
2、层层递进:《祝福》中祥林嫂的悲剧。在祥林嫂作为贱民形象的确立过程中,鲁迅采用了层层递进的叙事策略。祥林嫂从一个追求幸福、热爱劳动的下层妇女慢慢变成乞丐,最后在祝福的节日里孤单惨死,她的死亡可谓是“集体谋杀”〔13〕。族权、神权、夫权及其执行者固然罪不容赦,如鲁四老爷、卫老婆子、婆婆等等,都是祥林嫂受难的推手。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同属被统治阶层的柳妈,恰恰是以封建迷信流言将祥林嫂逼上了一条不归路:以一年的工钱捐门槛给人踏赎身,但终究还是被剥夺了祭祀中帮忙的权益。而当祥林嫂将精神寄托的解答指向知识人“我”后,又未得到满意答复延续点滴希望,只好在冰天雪地别人的欢天喜地中如草芥般死去。鲁迅正是以剥洋葱的方式将祥林嫂贱民化的过程和权力运行机制加以精彩展示的。
(二)反弹的悖谬。
鲁迅小说意义的精深表现之一就是对深层国民劣根性的入木三分的洞察与刻画,其中无疑也包括了对贱民劣根性的巨大悲悯与批判。这种深刻有时也可通过极左的幼稚病分子、理想主义者的可笑加以衬托:无论是1928-1930年代急不可耐地宣布阿Q时代的结束,还是大陆十七年文学(1949-1966)对工农兵题材的刻板化和神圣化处理都可反衬出鲁迅的高度预见性与深刻性。甚至和鲁迅写作路径差异很大的张爱玲也对鲁迅的深刻性传统惺惺相惜,“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14〕耐人寻味的是,贱民们的某种反弹恰恰呈现出复杂的悖谬性。
1、消极反弹与杀伤力:《采薇》中的阿金姐。《采薇》中的伯夷、叔齐作为主角,其经历是丰富多彩的,比如因为对前朝的效忠激怒了伐纣者,但终因姜子牙的“欲擒故纵”得以逃脱(在我看来,阴险的姜子牙早已断定迂腐的伯夷叔齐短期内必死,他犯不着动手做坏人反倒可以落下仁义之师的美名);即使遇到言行不一、极其伪善的山大王小穷奇,伯夷叔齐仍然得以狼狈解脱。然而他们的终结者却恰恰来自于贱民,“有一天,他们俩正在吃烤薇菜,不容易找,所以这午餐已在下午了。忽然走来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女人,先前是没有见过的,看她模样,好像是阔人家里的婢女”。(第318页)
这个婢女就是贰臣小丙君府上的丫头阿金。从更准确的意义上说,阿金不过是其主人的传声筒,因为小丙君曾经激烈批评伯夷叔齐不会作诗(因为穷,“有所为”,“有议论”),而且,话锋一转,“尤其可议的是他们的品格,通体都是矛盾。于是他大义凛然的斩钉截铁的说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难道他们在吃的薇,不是我们圣上的吗!’”(第318页)正是阿金的鹦鹉学舌一举击中了已经苟延残喘的二老们的精神要害。不仅如此,在二老死后,阿金还继续散播流言,言及二老贪心不足,想吃上天派给他们喝奶的鹿的肉,因此最后被上天抛弃致死。这个来自贱民的流言的杀伤力是相当巨大的,它以卑劣的世俗性彻底消解并玷污了伯夷叔齐所坚守的高风亮节或不识时务,所以,人们仿佛看见,“听到这故事的人们,临末都深深的叹一口气,不知怎的,连自己的肩膀也觉得轻松不少了。即使有时还会想起伯夷叔齐来,但恍恍忽忽,好像看见他们蹲在石壁下,正在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拚命的吃鹿肉”。(第320-321页)这样,这帮苟活的贱民也就轻易卸掉了自己的负罪感和精神节操责任(如果他们有的话)。
2、逸出的狂欢:《起死》中的汉子。《起死》中的汉子,其前身原本是骷髅。在庄子看来,他应当是很容易被操控的东西,从此意义上说,他也是贱民之一。在小说中,鬼魂曾经批判庄子的糊涂,但庄子反过来批判鬼魂的不通,“要知道活就是死,死就是活呀,奴才也就是主人公。我是达性命之源的,可不受你们小鬼的运动”。(第362页)甚至司命也劝他少管闲事,因为“死生有命”,但庄子执意不听,于是汉子得以跳出来。然而,荒谬的是,从骷髅到汉子,并非生死的简单转换,有关时空的历史记忆、血肉丰满的具体现实以及人生体验也被印刻在其脑海中,此时的汉子作为贱民开始反弹,庄子的齐物论和生死哲学在具体的人生体验与欲望要求面前显得软弱无力,甚至于最后近乎老拳相向。无奈之下,庄子只好请现实中的巡士帮忙,而第一个巡士由于和汉子的历史记忆难以对话,只好狂吹警笛继续寻求帮助。表面上看,鲁迅在借此嘲讽庄子,而实际上,在贱民的反弹中亦可以看出逸出的狂欢〔15〕色彩,这种狂欢既是现实与历史的对应,又是哲学精神与物质人生的张力,同时又是造物者与对象之间的对立关系描述。
三、性别视角与贱民的话语权
斯皮瓦克(G.C.Spivak)曾经有一篇非常著名的论文《贱民能够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其中涉及到贱民的话语权问题。斯皮瓦克认为,由于长期以来性别意识形态的建构,使得男性居于主导地位。可以理解,在殖民生产的争论中,如果属下阶层没有历史,不能言说,妇女属下阶层就身处更幽暗的边缘。〔16〕这个发问和反思无疑都是耐人寻味的。
也有论者指出,中国现代文学中,“这些底层叙述主要的话语方式可以归纳为四种:国民性批判的启蒙话语,阶级性凸显的革命话语,人性与诗性交织的审美话语,通俗文学中延续的传统话语”。〔17〕这当然是非常笼统的总结。但以此观照鲁迅的同类书写,令人眼前一亮的是,鲁迅的小说书写中的贱民话语别具风格、引人注目。耐人寻味的是,鲁迅小说中,鲁迅如何从性别视角处理这个问题?如果他让贱民们发言,效果又如何?
(一)男贱民:说的悲剧。
某种意义上说,作为贱民,即使他们是男性,其言说也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悲剧性,这主要可包含两个层面:1、说了等于没说。《肥皂》中的学程对待他父亲四铭,无论如何认真,都难免被训斥的结果。同样,《故乡》中的中老年闰土,他的言说毋宁更是一种简单至极的对苦难的粗略描述,其背后依然是无尽的压迫和凄苦。2、言说是对贱民身份的强化。《理水》中的乡下人代表再见到大员们后的言说其实更是奴性十足的表演,无论是出于恐惧的含糊其辞,还是刻意逢迎的巧言令色其实都未能突破其角色。当然,《起死》中的汉子虽然有过度反弹引起的狂欢色彩,但就其身份而言,他的言说仍然是中规中矩的,其杀伤力只有面对庄子的虚妄才会具有针锋相对的反讽效果。
或许最具悲剧意味的则是《孔乙己》中的孔乙己。作为一个自我认同错位的可怜人,他高不成低不就的现状注定了其悖谬性和悲剧性,更可悲的是,自恃甚高的孔乙己其实是最低的贱民,因为他不过是咸亨酒店里面的谈资和笑料,但离开他,别人也照样这么活。孔乙己的台词不多,但寥寥数语已足够显现其悲剧性。
孔乙己无疑是八股考试制度的牺牲品,他没能借此实现乌鸦变凤凰的飞跃,但变化过程中的镌刻却残存下来。他的满口之乎者也表面上看不合时宜,但实际上却又是他自我认同的标志与遮羞布。如“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第12页)此处的文言表达和咬文嚼字其实是他为自己劣根性遮羞的工具。而他教小伙计茴字的四种写法在善良之余更呈现出其迂腐性,实则为小伙计看不起。甚至是在分茴香豆给小孩子们吃后,唯恐他们继续要,便先用白话文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之后又用自己的擅长语言/惯性语言,“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第13页)。孔乙己对《论语》中经典话语的生活化生搬硬套其实更反映出其精神话语与生活话语的“古典化”与僵化,易言之,他的言说更表明他的无法自如言说。他被打断腿后而又要酒的白话文言说开始回归现实语境,如“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第14页)等,但这却意味着他所认同的精神身份的彻底挫败,实际上,他从身体上和精神上已经不得不走向失败,乃至灭亡了。
(二)女贱民:说的孤寂和艰难。
与男贱民比较,绝大多数女贱民会显得更加沉默与悲惨,相当大一部分女贱民其实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她们被剥夺了话语权,而更加令人悲叹的是,在同阶级或同类人的生存状态中,她们甚至又是被男权压抑的底层与弱势群体。而在现实语境中,有论者指出提高她们地位的对策,女贱民发言的效果需要代言人的帮助,但也要警醒新的陷阱,“属下妇女依然还要通过其他表述主体的代言才能被听到,在这种情况下代言者的立场至关重要。代言者要不仅仅是‘代表’属下阶层,还要‘表现’属下阶层。另一种情况是在属下妇女能说话时,她们的言语行为可能并不为主流的政治再现系统所承认,或者说属下妇女所说的话可能被殖民主义话语和男性中心主义话语重新编码”。〔18〕
鲁迅小说中,女贱民大多数是相对沉默的弱势群体,《药》中夏瑜的母亲受人冷眼,原因是她作为革命者的儿子被官府杀头,他们母子之间虽然在情感和物质上“血浓于水”,但精神上却只有隔膜,可悲的是,夏母无法用启蒙思想以及相应的荣耀感来支撑自己,只能以朴素的迷信加以辩护。《风波》中的小女孩六斤作为女贱民,她只能成为父母转移难堪和发泄淫威的被动接受者和牺牲品,〔19〕是毫无话语权的。类似的还有《端午节》中的方太太,她其实也是无能的方玄绰虚张声势欺骗下的牺牲品。鲁迅小说中的女贱民当然也有发声后效果显著的个案。比如之前所论述的《采薇》中的阿金,但她不过是鹦鹉学舌的产物,毫无个性与灵魂,她的话语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负面能量的传声筒,而非自我的话语。〔20〕
但鲁迅也注意到给予女贱民发声的必要性,其中的代表人物则是祥林嫂。有论者指出,“职业、身份、婚姻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等级化、世袭化是中国和印度古代贱民制最为显著的特征”。〔21〕从整体上说,祥林嫂虽然未必完全符合上面的总结,但作为体制内追求卑微幸福感的小人物,她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婚姻方面。当她备受摧残时,她亦曾经反抗过,比如被逼二嫁时她以死相对,但其反抗也有悲剧性——她的反抗其实更多的是对封建伦理制度的认同与致敬。当然,她也困惑于自己的二嫁身份与两个死鬼老公的纠缠,愿意捐门槛救赎,但一切无效后,她从精神上陷入了极端的困惑。
恰恰在此时,鲁迅先生让她发声了,她面对回乡的知识分子“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1、“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2、“那么,也就有地狱了?”3、“那么,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的?”(第135页)当时的“我”为逃避责任,只好以“说不清”匆匆做结。水晶曾经批评过鲁迅让祥林嫂发声的写法,人死了之后有没有灵魂?“这句话,固然达致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效果,却不很‘写实’。我怀疑一个愚孥如祥林嫂的乡下女人,会吐出这样文艺腔十足的名词来!”〔22〕
但在我看来,这是对鲁迅小说精心设置的误读。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思考这个问题。第一,就祥林嫂层面——因为这其实是祥林嫂穷途末路之下的必然质询,她在成为一个“眼珠间或一轮”的“活物”后唯一可以寄托或具有自救可能的就是精神方面的满足,一方面,她从同阶层人中间已经找不到温暖和支持;另一方面,其实祥林嫂还是有较强的挣扎习惯存在的,无路可走时,她不得不转向精神关怀了。
另一个层面是鲁迅层面,这是他的自我心境在现实遭际后转向的标志,从“呐喊”到“彷徨”的精神再现,也是对呐喊者自身的质疑,如人所论,“鲁迅必得质疑和询问呐喊者本身,呈现于《祝福》开篇的那场历史性‘对话’无异预示着呐喊者自我质疑的开端”。〔23〕如果结果是积极的,她还可以苟延残喘;若是否定的,她就会很快灭亡。然而,“我”以“说不清”逃离其实也是加速了其死亡。从此角度看,祥林嫂的发声更多地与话语权关系不大,而是她生存与否的最后推动力实验,然而她发声的无果其实更注定和反证了其悲剧性,这种巨大的落差也让我们慨叹鲁迅反讽的深度和力度。
考察鲁迅小说中的贱民话语,其实不是单纯以术语重新拼凑、重复劳作,而是要将“不幸的人们”的不同生存状态、权力话语运行轨迹、反弹的悖谬性和发声的差异性及其后果进行新的梳理与剖析,这对于我们理解和体悟鲁迅小说创作的匠心与意义的深度是有帮助的。
〔1〕迪利普·希罗作,林锡星译.印度的不可接触者——贱民〔J〕,民族译丛,1982(2).
〔2〕Ranajit Guha,Subaltern StudiesⅠ:Writings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M〕.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Ⅶ.
〔3〕陈义华.贱民研究学派与后殖民批评〔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4〕陈宁英.唐代律令中的贱民略论〔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3).
〔5〕徐燕斌.试论唐代法律中的贱民》〔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9(2).
〔6〕范家进.底层叙事:文学界的一场话语自救运动〔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6).
〔7〕〔8〕刘旭.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7-8;205.
〔9〕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4.
〔10〕范颖.论鲁迅小说中的手杖意象及其隐喻〔J〕.名作欣赏,2009(8).
〔11〕〔日〕樱井哲夫著,姜忠莲译.福柯——知识与权力〔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2〕朱崇科.“肥皂”隐喻的潜行与破解——鲁迅《肥皂》精读〔J〕.名作欣赏,2008(6).
〔13〕朱崇科.论鲁迅小说中吃的话语形构〔J〕.鲁迅研究月刊,2007(7).
〔14〕〔22〕水晶.蝉——夜访张爱玲〔M〕.水晶.替张爱玲补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21;38-39.
〔15〕朱崇科.张力的狂欢——论鲁迅及其来者之故事新编小说中的主体介入〔M〕.上海三联书店,2006:中编.
〔16〕G.C.Spivak.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M〕.Cambridge:Harvard UP,1999:274.
〔17〕彭松.深沉的变奏——中国现代文学中底层叙述的话语方式〔J〕.北方论丛,2007(3).
〔18〕都岚岚.论属下妇女的再现〔J〕.外国文学,2006(6).
〔19〕朱崇科.论鲁迅小说中的儿童话语及其认知转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1).
〔20〕竹内实.阿金考〔M〕.竹内实著,程麻译.中国现代文学评说.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21〕朱伟奇.中印古代贱民制之比较〔J〕.郑州大学学报,2008(5).
〔23〕吴康.书写沉默——鲁迅存在的意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27-128.
——《祝福》的文本细读与推理